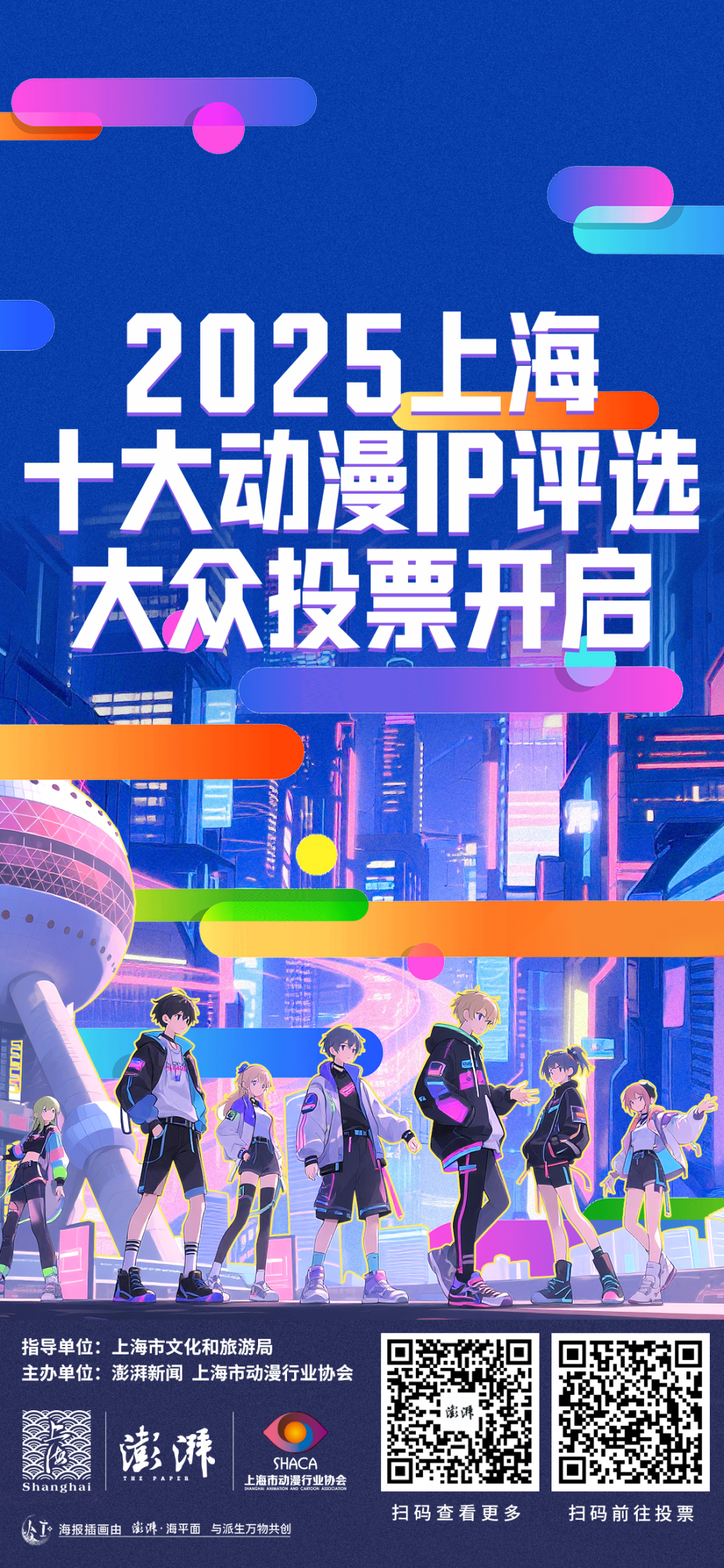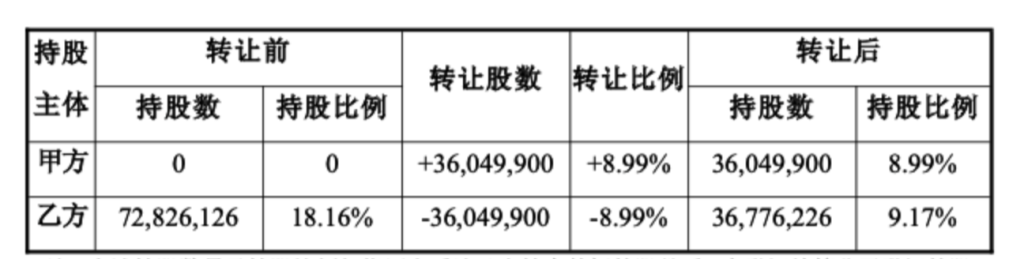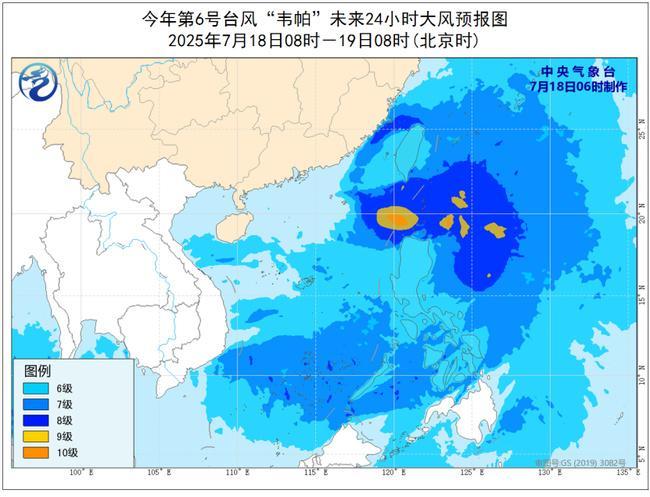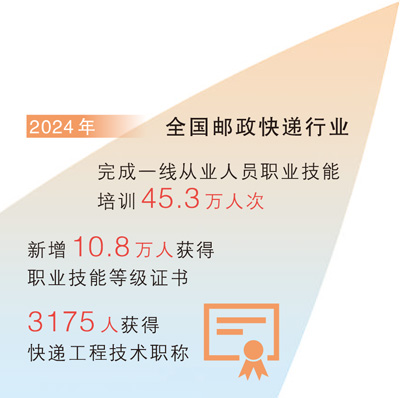《穿越百年中东》:充满回忆的岁月
董曦阳告诉我《穿越百年中东》的再版已进入流程,叮嘱我写一个新的后记。接到任务后我陷入了重重的回忆之中。
严格来说,《穿越百年中东》是第一本给我带来一定知名度的书,在它之前,我出版了小说《告别香巴拉》、历史游记类作品“亚洲三部曲”,但作为新人都显得不温不火,关注度不大。对于立志以写作度过一生的我来说,纯粹依靠版税还无法养活自己。
但接下来出版的《穿越百年中东》却给了我一个惊喜,上市后,很快获得了我的伯乐之一俞敏洪的关注,他的无私推荐带来了第一批认真阅读我的书的读者,也让人们意识到,有一个新人至少是在真诚地写作,没有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更没有纸上谈兵,而是以实地考察加深度阅读的方式在写作。
事实上,我的每一本书都争取做到认真考察、大量阅读。我的写作主要分成两个条线,一个是写现代中国在全球的定位,去走访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考察它们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以及与中国的联系,思考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借鉴什么、利用什么,又要注意避免什么。在写作这个条线的每一本书时,我都要求亲自走访,走访也一定不能像普通旅行者那样走马观花,而是要和当地人有深入接触,然后才能动笔。
另一个条线是写作中国历史,表面上看这些主题只需要阅读历史文献就可以了,但我也尽量做到不管写什么题材,都要实地考察。比如写《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这样的通史性作品,就要考察全国的战略要地和关隘,这花了我大半年时间,几乎每天都要去往不同的地方,有时一天要走好几处,这还只是集中考察的时间,不算那些零星的积累;而写《汴京之围》这样的事件性作品,我也必须去发生地开封看过,更要对作为历史胜负手或者关键节点的北京、山西、燕山、太行山、大运河等都有深度的考察和清晰的认知。
写作尚未出版的小说《花剌子模千年之恋》(或者《似曾相识于花剌子模》,由于尚未出版,我还无法在艰难的抉择中确定最终的书名)时,我也要求自己首先将小说中的发生地中亚、伊朗、高加索等地都拜访过,才动笔写作,虽然是虚构作品,但考察的难度和广度已超过了纪实作品。
可以说,我的写作风格(走访加深度阅读)在创作小说《告别香巴拉》时(为此我专门穿越了西藏的部分无人区)就已确定,但真正受到激励,并坚持下来,却是在《穿越百年中东》。它第一次让我确信自己可以写出受人关注的作品,并且有人认同我这样的写作态度。它至今依然是我最喜欢、写得最真诚的作品之一。
充满回忆的岁月
《穿越百年中东》让我充满了回忆,除了书本身的影响力,还有我最留恋的时光。那是属于学习和漫游的时代,也是属于爱情和生活的时代。
在我去往中东时,我心里打算的是写一本类似“亚洲三部曲”的书,也就是为每一个地区写通史。比如我的书籍《印度,漂浮的次大陆》,就对从岩画时期到现代的印度历史进行了梳理,这样写是因为我看到,国内当时最缺乏的书,是那种对一个地区进行深度解读的,我希望好奇的读者能够利用我写的这一本书,了解整个地区的历史脉络和发展逻辑。
我考察中东,也希望写一部类似的通史性作品。但到了现场之后,却意识到现代中东才更加吸引我,于是集中去了解现代中东问题的由来,并整理出几个关注点,最终形成了本书。
只有到了中东,才意识到那些原本只出现在新闻里的情节,在当地却是人们的日常。当书中的马麦德带着我在夜晚去往真主党的控制区,当另一个马麦德不动声色地消失于北方的黎叙边境,当叙利亚的难民们想方设法逃往土耳其、黎巴嫩、埃及以及任何能够收留他们的地方,当现代贫民窟和历史建筑聚在一起,形成了绵延数千年的图景,才知道中东地区是多么复杂。
当时的我也许正处于人生漫游和学习时代的高峰,能够不知疲倦地去寻找任何问题的答案,甚至忽略了身边的风险。直到后来在阿富汗和西非遇险,我才慢慢地学到怎样保护自己,避免成为复杂冲突的牺牲品。
当我于2014年年底从中东和非洲回来,本书的写作已经开始:这本书一部分是在埃及和非洲之角创作的,剩下的一部分在广州朋友文学锋的家中完成。由于我有同时创作两本书的习惯,《穿越百年中东》是和《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一同写完的。
两本书稿一本交给了中信出版社,另一本交给了鹭江出版社下属的时代飞鹭出版公司。交稿后,我就开启了全国的漫游,为下一本书《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做准备。出版社要求我修改时,我就在路上停下来休息两天,在无名的小旅馆里完成修改工作。
这两本内容完全不同的书稿,命运也殊途同归,交给中信出版社的《穿越百年中东》,经过了大半年就出版了,而交给鹭江出版社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却拖延良久,花了两年多才出版。但事后来看,这个时间差对我非常有利,《穿越百年中东》给我带来了最初的声誉,发酵了一段时间后,《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正好上市。如果两本书同时上市,反而如同左右手互博,出现失焦。
在《穿越百年中东》上市时,我恰好刚定居大理,和一位女孩确立了关系,并搬入她开的小饭店的顶层居住,至今,我们依然在一起。
我记得十本样书就是发往饭店的,书籍的设计和制作都非常精美,但很快就不知道都送给了谁,反正家中一本都没有了。梦舞君也很喜欢这部书,认为这是我写的最有希望的一部,前面几部她认为太小众了。为了收藏,她又偷偷地买了三五本,想自己留下,但被我发现后又拿出去送人了,因为总有人在找我要书,而我又总是手头没有(舍不得买)。她发现没有了,只好又买个三五本回来,我一面责备她不要乱花钱,买自家的书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一面又把她买的书送人。如此三四次。
从此以后,我签合同时都会要求出版方比正常合同多送十本书给我,以免自己一本都剩不下。
那时我还在她的饭店里兼职洗碗工和点菜员,为了吸引客人,本来不善言辞的我学会了向客人们展示我的作品,换取他们多等一会儿。客人们有时也会惊叹:一个作家竟然只能靠点菜为生!在大理,确实是什么事儿都会发生啊!
如今,我和梦舞君回忆最多的依然是这段时光。那时的我们谈论着理想和未来,又陷在生活之中,充满了乐趣,也不乏焦虑。现在我们的生活依然充满了乐趣,但我们已经过了那个就算是有忧虑、却依然乐观的人生阶段,我们安然和宽容地对待周围的人和事,却对历史进程总是向上的看法抱有深深的怀疑。
摒弃站边思维,意识到世界的复杂性
《穿越百年中东》给我的另一个惊喜是,虽然写作已接近十年,但它的生命力似乎超越了大部分的游记作品,至今看不出太多过时的地方。
当我去往中东时,叙利亚正处于鏖战中,令人谈之色变的伊斯兰国(ISIS)组织刚刚兴起(我恰好成了见证人),阿富汗战争处于一摊烂泥中,塔利班还在等待机会。
在本书出版后,历史继续演进,埃及的塞西总统已经变成了另一个穆巴拉克,他的统治持续到现在,而且还将持续下去。叙利亚的局势在政府军控制区逐渐趋于稳定,但依然有一些区域是游离于政府军之外的。巴以冲突又进入了另一次恶性循环,以死亡数万人为代价。伊朗经过了一次众心所向的开放,但这一次被美国强行又推回隔离的轨道上。沙特在一个政治强人的带领下,决定走改革开放的道路。而美军撤出了阿富汗,导致塔利班的再次上台。
在这十年里,我也去过了更多的地方,但在不同的地方依然会遭遇到本书中许多熟悉的角色。比如,在西非撒哈拉的深处,我就遇到了《穿越百年中东》中提到的那个新势力:ISIS。只是这时候的ISIS已经不再新了,它经过了一段摧枯拉朽的崛起期,后来被从叙利亚和伊拉克赶走,于是分散到了更加广阔的地方,一部分去了阿富汗,另一部分则选择了西非的撒哈拉深处藏身。这两个地方,我都游历过,并深刻地体会到ISIS的到来带来的巨大不稳定。
可是,不管后续如何发展,《穿越百年中东》却抓住了最根本的东西,这些本质性的要点决定了后来历史的走向,从这个意义上,《穿越百年中东》在十年后再版,依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以书中花费大量的篇幅谈到的巴以问题为例,由于最新一轮的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冲突,巴以问题再次上升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中国人有站边的倾向,总是试图假定一方是完全正义、而另一方是完全错误的。但事实上,世界上大部分的事物并非如此泾渭分明。
我曾经提出两个问题给支持巴以两方的人们。
对于那些支持巴勒斯坦和哈马斯的人,我试图让他们思考:在中东,许多国家和势力可以承受一次次的失败,但只有以色列是无法承担哪怕一次彻底失败的。因为一旦他们战败,犹太人在敌对的环境下就无法生存下去。就像是两千年前罗马对犹太国家,或者萨拉丁时期对基督教十字军国家的清理那样,他们将失去在中东的立足点。正是因为无法承担失败的代价,即便是整个世界都在质疑它,以色列也必须用一切手段将巴勒斯坦的抵抗力量清除,避免未来的危险……
对于那些支持以色列的人,我请他们想象,如果他本人就是一个生于加沙的孩子,他的一生会怎样?他孩童时期的理想也许和我们中国孩子一样,是成为科学家、医生、企业家,他希望用自己的努力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但他的理想在18岁之前就破灭了,因为他享受不到合理的教育,也没有正常的生活,由于没有必要的教育,注定了他不可能成为理想中的样子。而他承受的一切,来自以色列为了防范哈马斯而采取的过于严苛的措施。留给孩子的道路,也许只有成为下一代反抗者……
对于巴以双方来说,他们都是困局中的一个角色,完全没有别的选择。不管是弱势的巴勒斯坦人,还是显得强势的以色列,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充当着害人者和受害者的双重角色。所谓悲剧,并非是人们做出了错误选择,而是即便再重新选择千百次,还是只有这一条不归路可以走。
我的任务不是给这样的困局找一条出路,而是详细地追溯困局的形成。
在我的另一本书《失落的世界》中,我提到,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顺利发展,是因为这个国家在世界秩序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我用了生态位一词),并在这个生态位上,谋求与世界的联合、开放。不管是改革开放的中国,还是日本、韩国等从落后走向现代的国家,都是在遵循现有秩序的情况下找到了自己的生态位。
但是,并非所有的国家都能够找到生态位,在世界近两百个国家中,拥有舒服的生态位的国家不会超过50个。那些丧失了生态位的国家往往会陷入困局之中,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间悲剧的深层原因。
更可惜的是,有的国家本来已经找到了生态位,却由于各种原因自己放弃了,导致陷入历史的困局中。这些国家的教训更值得我们警惕,因为一旦迈出那一步,将再也没有回头路。
除了《穿越百年中东》之外,后来我又写了《穿越非洲两百年》,以及未出版的《穿越劫后中亚》,还有总结性的《失落的世界》,都谈到了在世界各国的交往中存在的各种陷阱和教训。

本文为《穿越百年中东》“再版后记”(郭建龙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 火与风,2025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