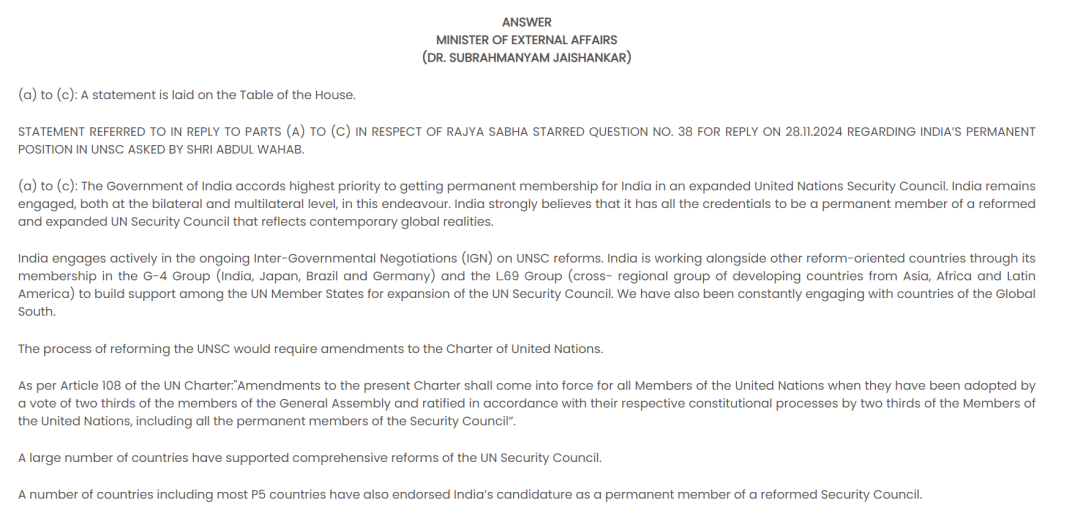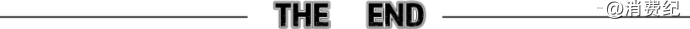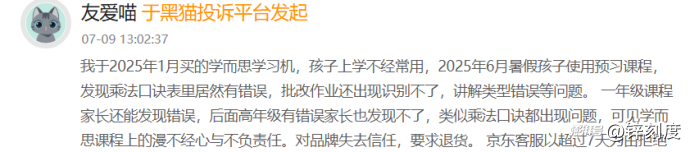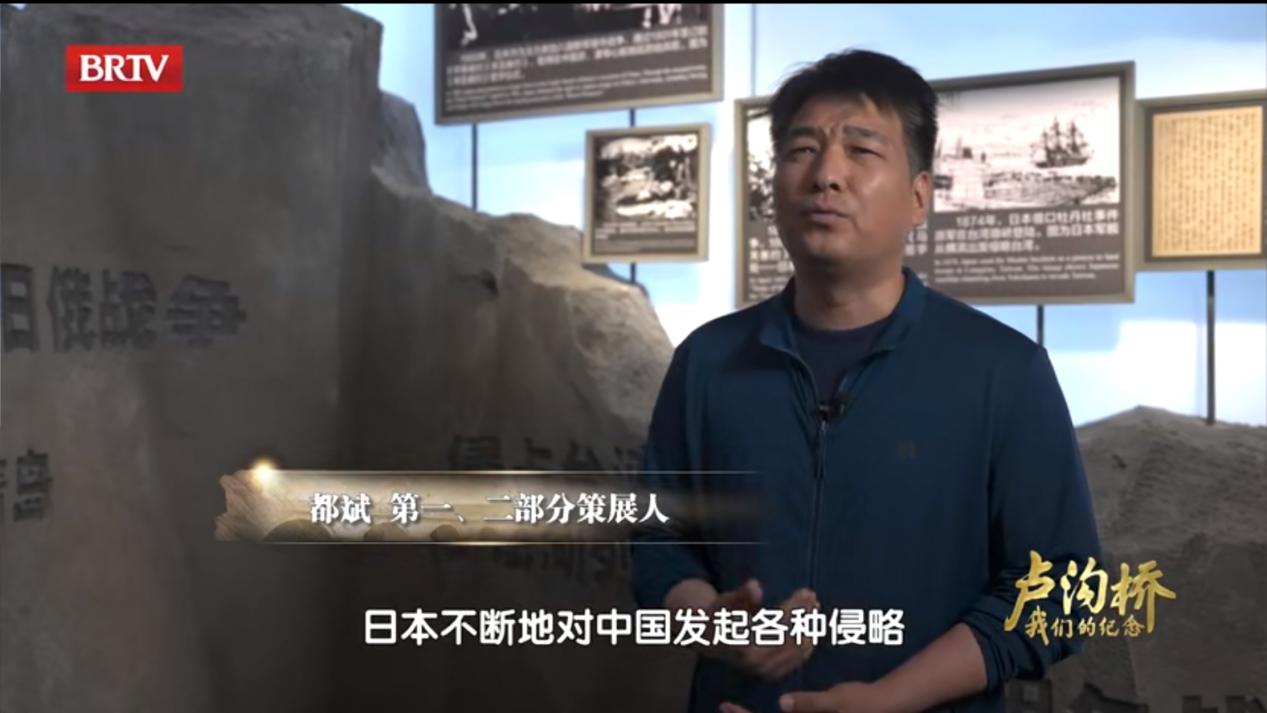《聊斋志异》被拍过很多次了,这次的《兰若寺》有哪些新意?
《聊斋:兰若寺》的改编立场值得关注。该片出品方近年来以“新神话”、“新传说”和“新文化”三个系列布局动画长片,融合了赛博朋克、工业废土等后现代美学风格吸引青年观众,而《长安三万里》则面向全年龄段观众打造了中国风“合家欢”动画电影。
中国志怪小说源远流长,其中流传度最广、艺术成就最高的,莫过于“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王冠上的明珠”《聊斋志异》。一生壮志未酬、科举屡屡落第的蒲松龄,用如椽大笔构造了一个鬼狐精怪人神共处的奇谲世界,故事出人意料、场景神奇绚丽,满纸云烟看似虚无缥缈荒诞不经,实则深情款款不离人间烟火,刺贪刺虐写尽百姓疾苦,至情至性喟叹世道人心。
《聊斋志异》全书24卷近五百个故事,名篇云集,上世纪以来改编为影视作品的亦不在少数。就改编策略而言,单篇居多,有杂糅若干篇章情节人物的,也有依托原文重新演绎的,基本着眼小说故事改编。电视剧《聊斋先生》算是另辟蹊径,叙述内容交织了蒲松龄的人生经历、文学观点和小说情节,而最近的动画电影《聊斋:兰若寺》则更有新意,它的改编对象,是《聊斋志异》小说集本身。

蒲松龄《聊斋志异》
影片叙述主线源于书生蒲松龄投奔友人途中,突遇兵患,道阻难行,只好借宿破败的兰若寺,不想落入枯井,遇到爱讲故事的蛤蟆精灵蟾上人和乌龟精玄龟子。二精怪欲一决高下,拉书生做裁判,精彩故事由此展开。这里的“讲述”,既致敬了蒲松龄书斋“聊斋”中的“聊”字(小说故事多来源闲聊,短篇集主要收录区别庙堂文章经世之学的市井故事),也符合《聊斋志异》小说全知全能的说书人视角;书生既然充当裁判,听完故事便需点评,寥寥数语概括精要,借古讽今点明主旨。这又暗合了蒲松龄喜欢在多篇小说结尾加上 “异史氏曰”,借此大发感慨的评论方式;《聊斋志异》是短篇故事集,电影同样借助二精怪以及书生本人的讲述,借用单元剧形式连缀多个故事。除了完整篇目的《崂山道士》《莲花公主》《聂小倩》《画皮》《鲁公女》外,还涉及《青凤》《种梨》中的代表性情节,再加上书生坠入奇幻世界偶遇精怪的神奇遭遇,亦可算作志怪故事,整部《聊斋:兰若寺》大故事套小故事,如同万花筒般绚丽多姿。
此外,《聊斋:兰若寺》的改编立场也值得关注。作为出品方,“追光动画”近年来以“新神话”、“新传说”和“新文化”三个系列布局动画长片,视效美轮美奂精益求精,目标观众略有不同。同样是弘扬传统文化,“新神话”、“新传说”的《新神榜》和《白蛇》系列更偏成人向,结合诸多青年亚文化元素,用融合赛博朋克、工业废土等后现代美学风格的传统故事现代演绎,吸引青年观众。而以《长安三万里》开篇的“新文化”系列,则更面向全年龄段观众,试图打造别具一格的中国风“合家欢”动画电影,文化定位上,更接近传统经典的全民推广。因此,同属于“新文化”系列的《聊斋:兰若寺》,改编基调就有两种面向,一方面,相对贴合原著,用生动活泼的动画语言赋形传统经典内在神韵,让低幼观众感受中华文明的鲜活魅力;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表达形式或内容主旨方面的创新,链接当下文化场域,吸引更多成人观众。

蒲松龄与二精怪
二精怪的故事比拼,共分两回合。第一回合“自选主题”的《崂山道士》和《莲花公主》,带有明显的儿童向。《崂山道士》讲述青年王承一心求仙慕道,追随道长上崂山修行,无法吃苦屡生退意,临行习得穿墙术,回家却法术失灵,落人笑柄。这一故事的改编亮点在于表现形式。渲染量巨大的毛毡画风,从表达陌生化的角度,增添了故事的新鲜感,毛毡的柔软质感、穿墙动作的拉丝效果,和景观的拼贴结构,又增加了故事的童趣。此外,多组快速剪辑蒙太奇完成的场景转换,保证了影片叙述节奏和叙述线索的简洁明晰,仙人聚会一段灵活的场面调度,亦精彩纷呈地再现了原著剪纸为月、掷箸化嫦娥的瑰丽想象。

《崂山道士》篇
总体上,这个故事如同整部影片视觉盛宴的开胃菜,排盘用心精致,可惜口味略为寡淡。事实上,《崂山道士》看似简单的故事背后,另有深意,完全可以兼顾成人观众。故事表面讽刺青年贪心虚荣不能吃苦,劝诫世人保存赤子之心,文末的“异史氏曰”却宕开笔墨,从愚人受小人谄媚以为横行霸道通行天下,终要南墙碰壁的小故事,表明蒲松龄对王生遭遇的看法,即很多人都活在自己的思维桎梏里,不了解自我又脱离现实,终日沉迷某种观念或追求。而区分幻想与现实、避免沉溺空想的主题,时至今日,依然具有实际意义,可惜影片没有进一步发掘,仅仅停留在讽刺贪心的层面。
如果说,《崂山道士》通过王承穿梭仙凡两界,打开了通往奇幻世界的大门,《莲花公主》则渐入佳境。原著小说中,青年窦旭两次借梦入“桂府”,国王重其才遂下嫁公主莲花,二人恩爱有加,不料妖敌入侵,窦旭遽然惊醒,发现枕畔蜜蜂嗡鸣似在求救,随后另搭蜂巢救出被大蛇攻击的群蜂,此后再无异梦。影片最大的改编即改主角为儿童,以窦旭诗作“心中有一剑,侠义走四方”贯穿全篇,才子佳人的陈旧套路被注入少年意气和昂然生气。窦旭与莲花一派纯真,先为师友,后又并肩作战保卫家园。此外,改国王为爱子民有担当的女王,硕大花朵流淌着金色蜜流、屋舍六边形门窗、花朝节全城欢庆处处花灯等细节,也都从人物到环境立体地建构出流光溢彩的奇幻世界。影片结尾,窦旭对着蜂群的会心一笑,模糊了梦境与现实的边界,而此种今夕何夕的喟然之叹,无疑加深了故事深度。

《莲花公主》篇窦旭与公主莲花
第二个回合比拼“命题作文”,题目是“情”。《聊斋志异》大IP之一的《聂小倩》率先登场。且不论改编电视剧,仅就电影而言,值得关注的就有1960年李翰祥版、1975年姚凤磐版和1986年程小东版三部佳作,近年还有2011年叶伟信版、2022年马玉成版再登银幕,动画方面也有1997年徐克编剧的《小倩》,以及2024年刚上映过的改编长片。诸多珠玉在前,故事早已毫无悬念,想要做出新意着实不易。
现在这个版本的改编亮点,主要有两方面。其一,保留原著全文故事架构,添加宁采臣、聂小倩回乡安居,凭借剑仙燕赤霞留下的法器皮囊,彻底打败寻仇夜叉的情节。以往多个版本的改编,多聚焦宁采臣、聂小倩的人鬼相恋、勇而抗争,往往结束于人妖大战救出小倩的高光时刻。这次全文改编固然稀释了一部分戏剧张力,却更符合“新文化”系列弘扬传统文化,唤起读者对经典文本阅读兴趣的创作初衷;其二,改变故事时代背景,让一段人鬼传奇发生在时局动荡的民国,以乱世反衬真情,更显世间百态。穿中山装和旗袍的男女主角固然令人新奇,跳出单个故事,这一设定还有加深《聊斋:兰若寺》全片内在主题的重要作用。

《聂小倩》篇故事背景改变为民国时期
生活在三百多年前的蒲松龄,对蛤蟆精讲述里出现的蒸汽火车、手电筒大感好奇,故事上演于民国,从全片叙述结构看,乃是为了增加了时空流转的未来向度。原本《聊斋志异》中的故事背景,大多以蒲松龄生活的清康熙年间以及明末清初为主,《聊斋:兰若寺》则为几个故事增添了明确的时代。《崂山道士》发生在晋,《莲花公主》来到唐朝,《聂小倩》跳到民国,《画皮》则发生在明。一旦设定具体时代,人物服饰、妆容、气质,以及生活环境,甚至具象的自然景物和抽象的时代风貌都要做出相应设计。好在影片出色的视觉呈现完成了这一挑战,充分展现出中华文明不同时期的文化精髓。同时,结合兰若寺的自身变迁点明全片主题,即一寺一树一井历尽沧桑看遍悲欢,纵白云苍狗超然物外,仍感怀人间真情难得。
这一回合,乌龟精出场打擂台的《画皮》,影视改编热度同样不低。其中影响较大的改编电影,就有1966年鲍方版、2008年陈嘉上版,2012年乌尔善版,和1993年胡金铨版。与前述《聂小倩》的改编思路一致,影片对《画皮》的演绎,同样从时代视效和故事完整两方面着手。美术风格参考明代文人画,构图缜密、含蓄典雅,相较其他故事世俗生活气息更加浓郁。原著中王大郎被女鬼剖心后,妻子陈氏求助高人,忍辱食唾救回丈夫的情节也得以全面呈现。改编亮点在于加入陈氏的叙述视角。

《画皮》篇从夫妻二人婚后多年日趋平淡的生活讲起
影片先从夫妻二人婚后多年日趋平淡的生活讲起,床榻前一整洁一邋遢的鞋履、蚀锈的铜镜、饮食口味的差异,尽显一段婚姻的寡然疲沓。王大郎收留女鬼后心猿意马,陈氏亦有所察觉,女鬼只求“一瓦遮头三餐温饱”的愿望破灭后上门寻仇,陈氏气恼又恐惧,而当女鬼被道士降服灰飞烟灭之际再次说出此心愿时,陈氏感同身受心有戚戚。至此,《聊斋:兰若寺》大胆提出了《画皮》的另一种读法。女鬼正是陈氏的心念所幻。面对丈夫的淡漠薄情,恪守礼法端庄娟秀的陈氏希望自己能如妖冶女子般,给丈夫“换换口味”,但这终非她内心所愿,委曲求全不过是作为丈夫的附属品,希冀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女鬼消逝后,陈氏无法回答疯癫高人“救活了他,你可还愿意跟他生活在一起”的锥心之问,忍辱吞下的泥丸,未尝不是生活的种种不堪,哪怕王大郎转醒后信誓旦旦,这龌龊生活也不过是一句发自内心的“恶心”。影片多次出现铜镜意象,有趣的是,陈氏多次从镜中审视自己,而王大郎自始至终都只是被动投影,及至结尾处铜镜跌落,镜光打亮陈氏,女性觉醒跃然镜中。

《画皮》篇陈氏从镜中审视自己
二精怪难分胜负,蒲松龄只好自己下场,延着“情”的主题,讲了一个至情至性生死相依的故事。整部电影中,《鲁公女》篇幅最长,最接近追光“新传说”系列的青年定位,因此表达最为流畅。相较原著,改编主要增加了张于旦与鲁瑛的情感历程。原著男方一见钟情、女方感怀报恩的情感模式显然无法打动当下观众,于是,影片为二人情感升温设计关卡,在完成救九条命换取投胎机会的过程中,相依相伴彼此认可,感情基础牢固,才有其后二世情缘发生。原著鲁公女投胎卢家后不认识重返青春的张于旦,忧愤而亡,张于旦土地祠招魂后,二人喜结连理。影片增加了张于旦闯冥府历尽艰辛带回鲁瑛的情节,由此突显二人对承诺的坚守和对情感的珍视,亦对整部影片前序故事的情感讲述做出收拢升华。

《鲁公女》
故事讲完,蒲松龄回到人间,补全兰若寺残缺的对联,“一方净水由有相处知虚妄,几则乱谭自无稽间见真情”,由此点出影片颂扬真情之外的另一主题,世事苍茫星河流转,明月、古镜、孟婆汤、忘川水构成的种种镜像互为映衬,现实、梦境、幻想、臆想,如何自处,究竟境由心生。
一部《聊斋:兰若寺》,用拼盘故事打造东方奇幻,试图从不同层面吸引不同观众,至于观众能从中看到什么,也就因人而异了。不可否认,影片在视效设计、传统文化表达方面的用心,但故事风格、受众定位的分裂,也导致了影片难以复制《长安三万里》的市场认可。或许,前两个故事、后三个故事分别做成不同系列,更能精准抵达目标观众。“追光动画”成立以来常被诟病画面精美剧情拉胯,但好在每一部作品都可以看到用心和成长,“追光宇宙”的建立依然值得期待。

电影结尾,蒲松龄回到人间,补全兰若寺残缺的对联
(本文作者刘春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相关文章
“AI查AI”怪圈如何破?媒体:不必纠结表面“AI纯净度”
2025下半场,如何在新周期中破浪前行
浙江日报:黄仁勋的“唐装秀”折射了什么?
明查|印度第七次申请入常失败,遭五常集体否决?误导
7月以来多地高温日数已达5至8天
毕业就医美,入职前他们都忙着“改头换面”
AI学习机在“下沉”
德国总理访英,将签署首份《英德双边友好与合作条约》
动漫短剧,行至爆发前夜
日均外卖2.5亿单,MAD都赢麻了
纪录片《卢沟桥》:一件文物展示一段历史
美国阿拉斯加州以南海域发生7.3级地震
比利时著名音乐节场地发生火灾,现场浓烟滚滚
美国阿拉斯加半岛附近发生7.7级左右地震
乌总统泽连斯基:已提名什梅加尔担任新国防部长
乌军总司令称完成与北约新任盟军最高司令首次通话
特朗普:暂时没打算解雇美联储主席
以军总参谋长:若不能达成加沙停火协议,将扩大战斗规模
- 国台办:赖清德当局“打左脸送右脸”,“跪美卖台”行径令人不齿
- 湖南省委书记人民日报撰文: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 重庆网红景点“莲花茶摊”被市民投诉,官方:采纳意见,整改!
- 九部门:将符合条件的家政从业人员纳入公租房等保障范围
- 杜甫、韦应物背后的世家大族,在这个展览上一览传奇
- 河南社旗县委书记张荣印转任南阳市人大常委会农工委主任
- 德黑兰将实行夜间限水措施
- 美国参议院继续就政府“停摆”谈判
- 比利时列日机场因发现无人机一度中断运营
- 美国纽约地区三大机场均因人手短缺出现航班延误
- 台湾各界秋祭白色恐怖死难者,呼吁携手推进统一大业
- 新闻调查丨广西百色排涝情况如何?记者探访受灾村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