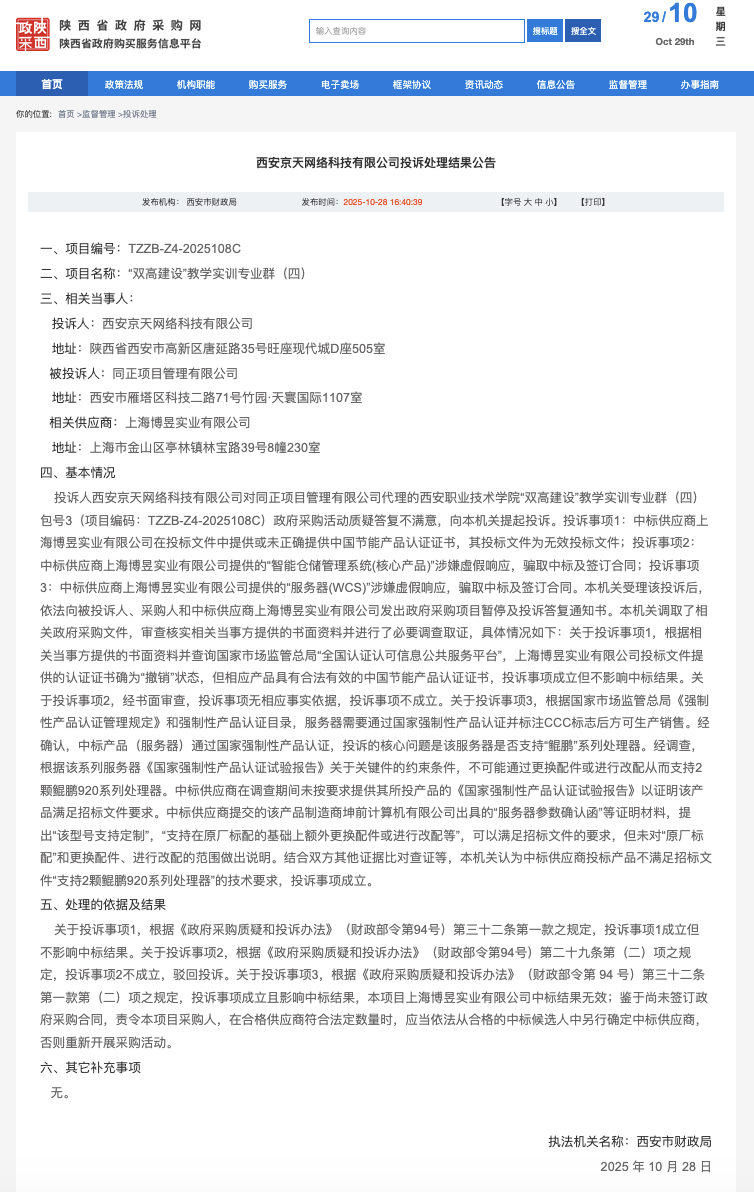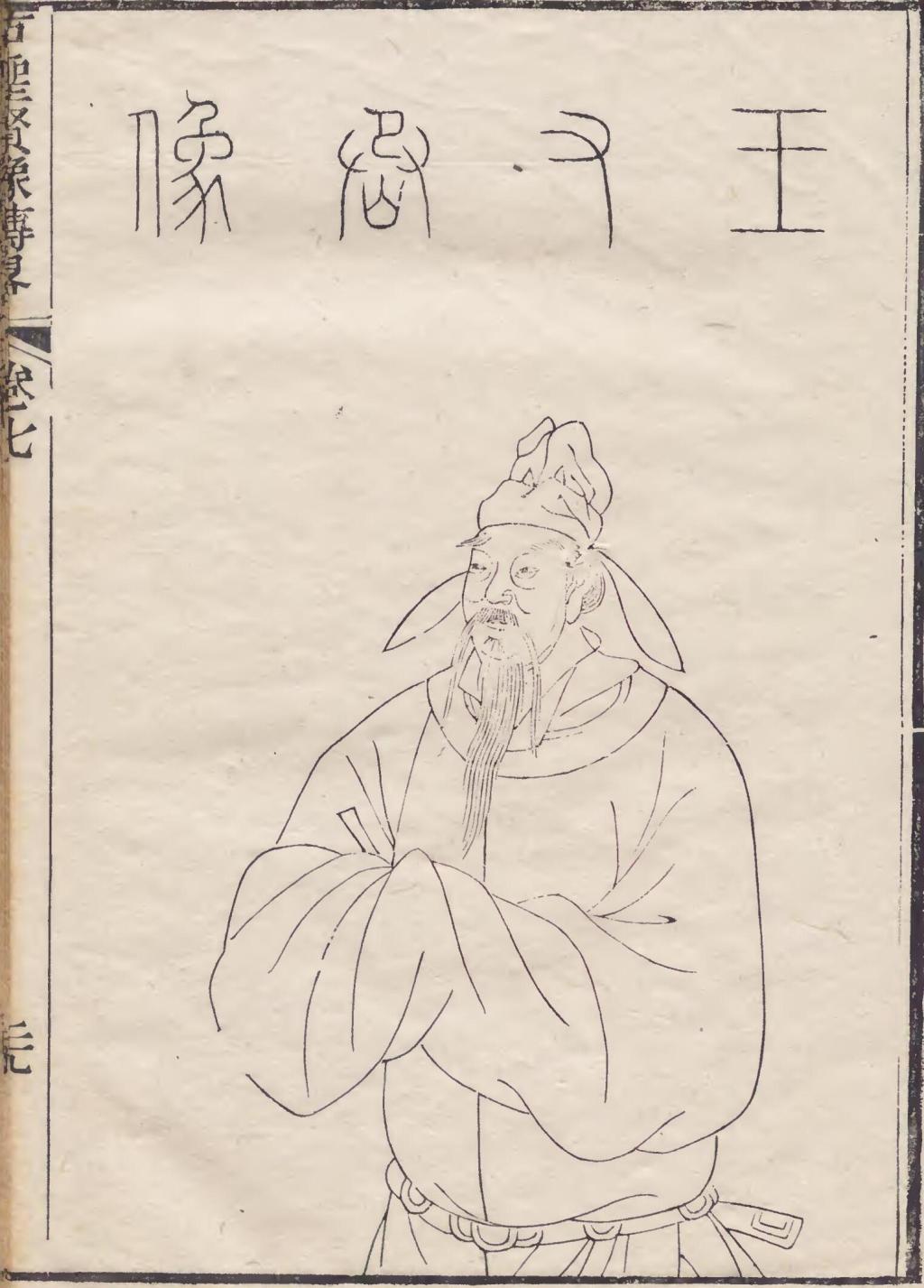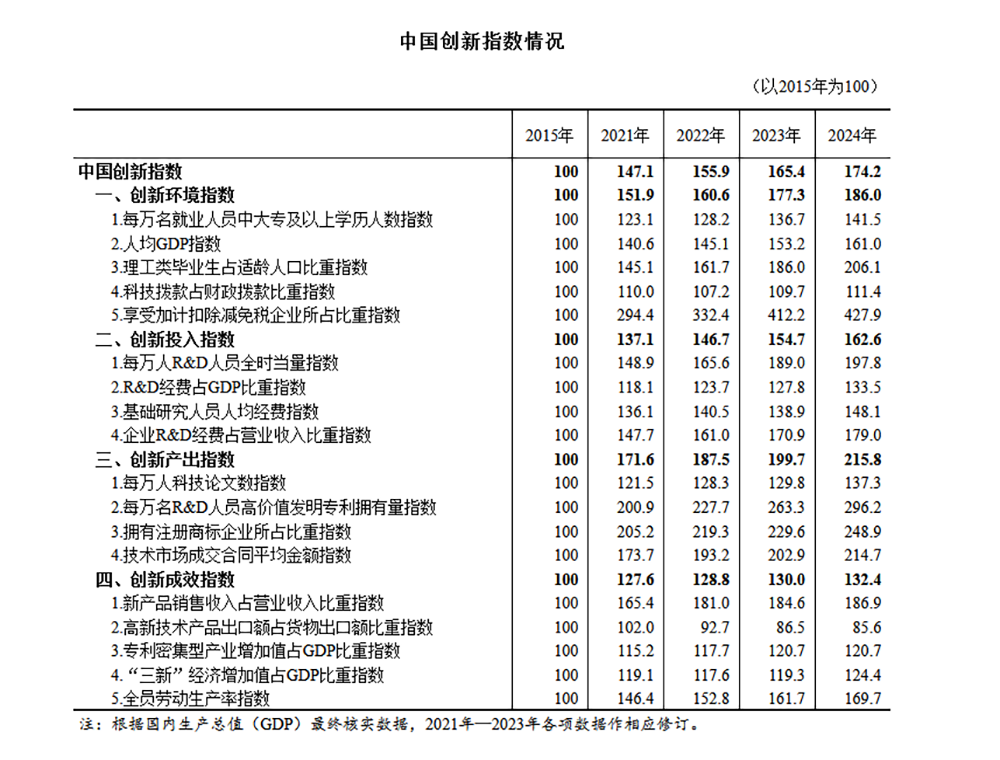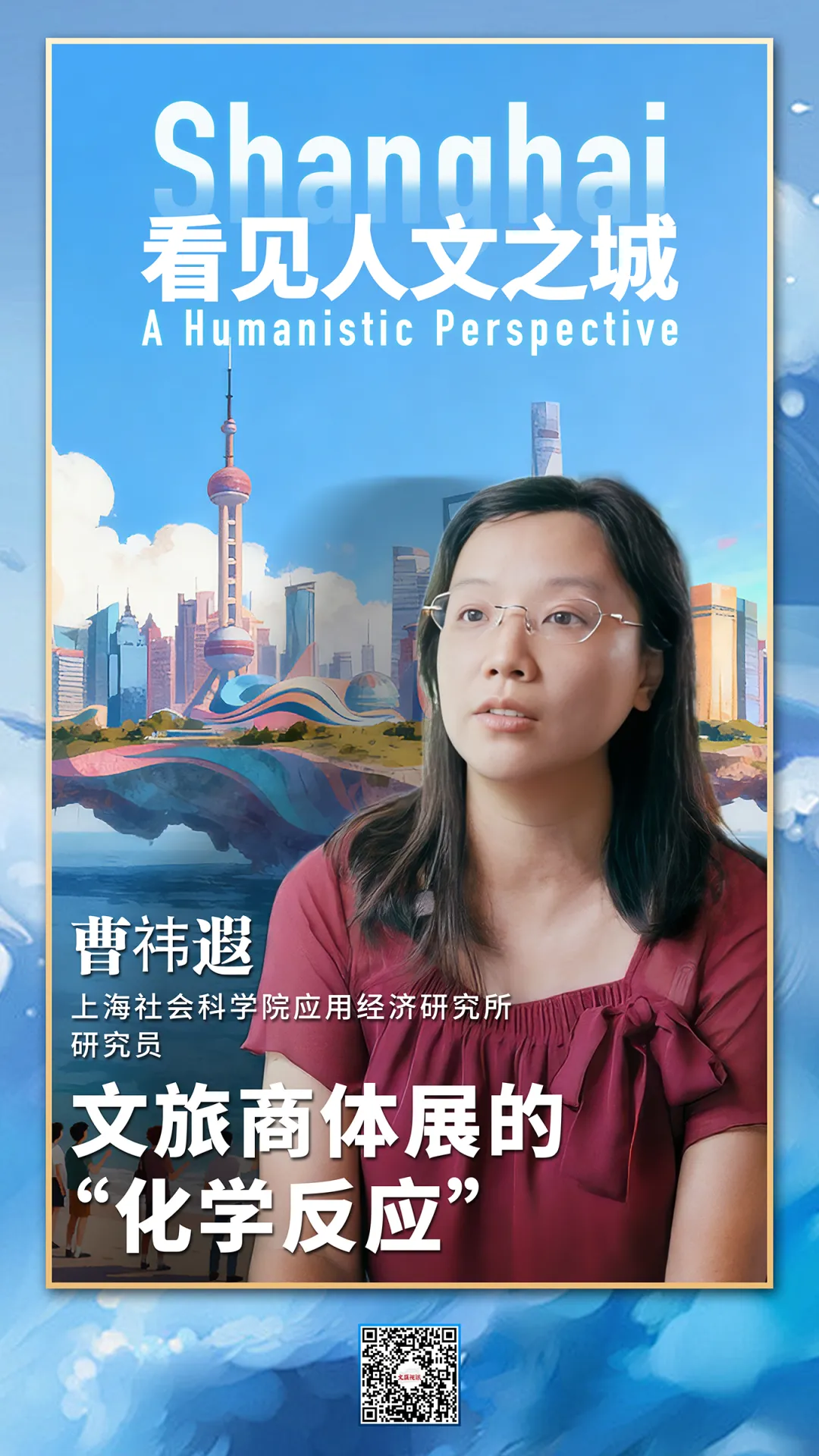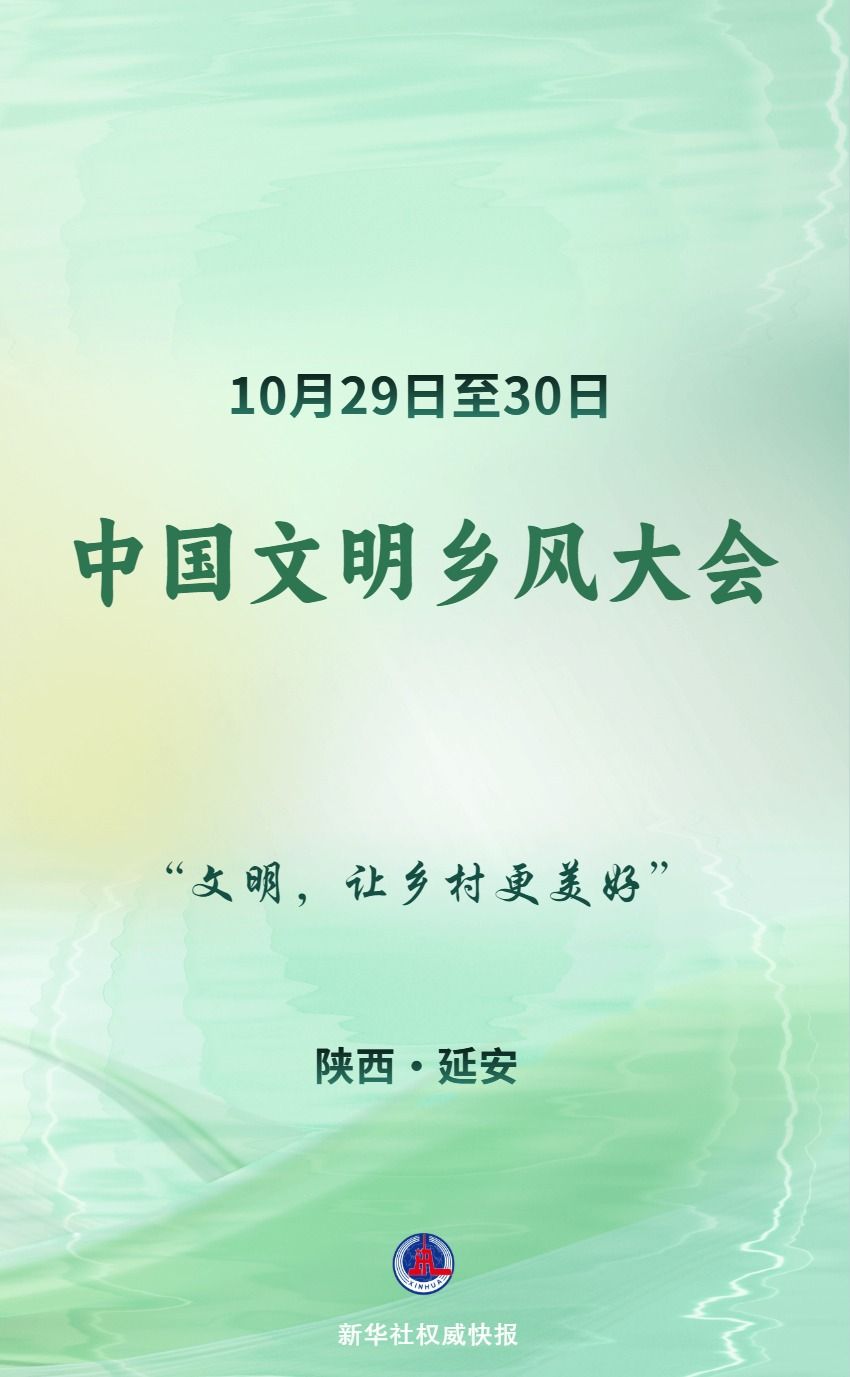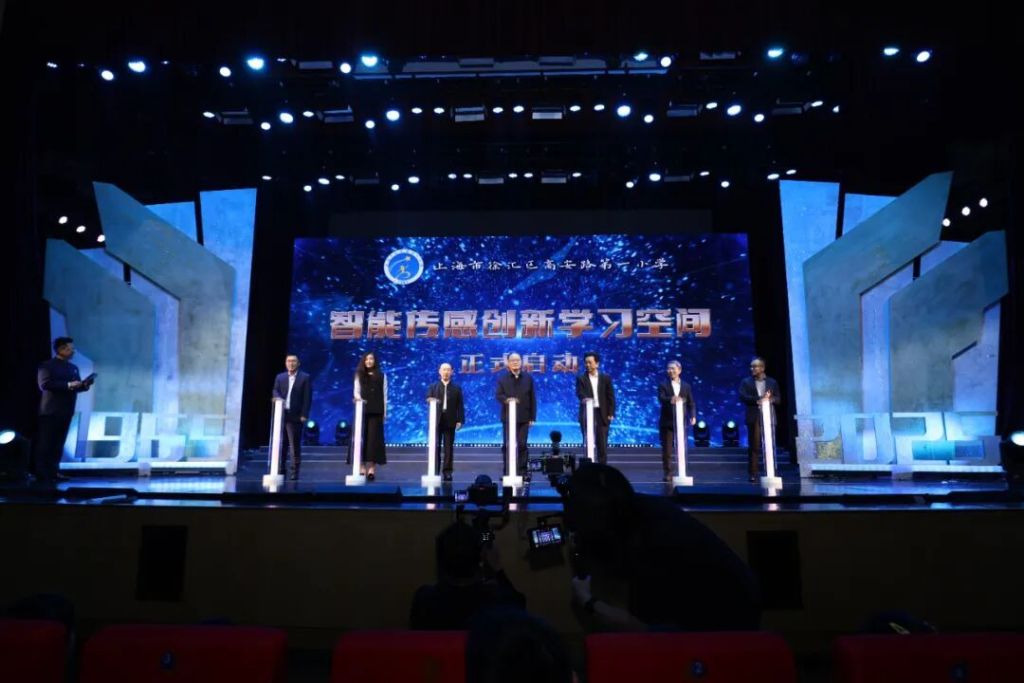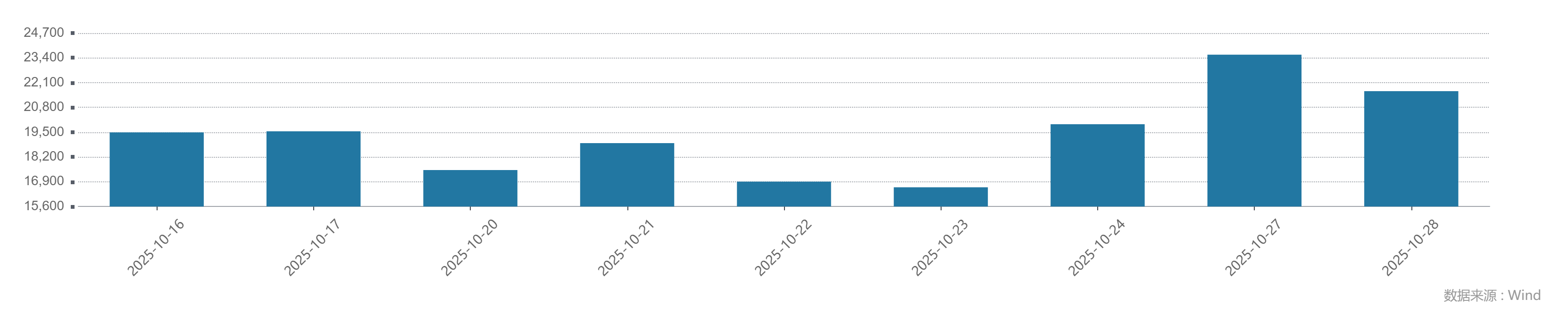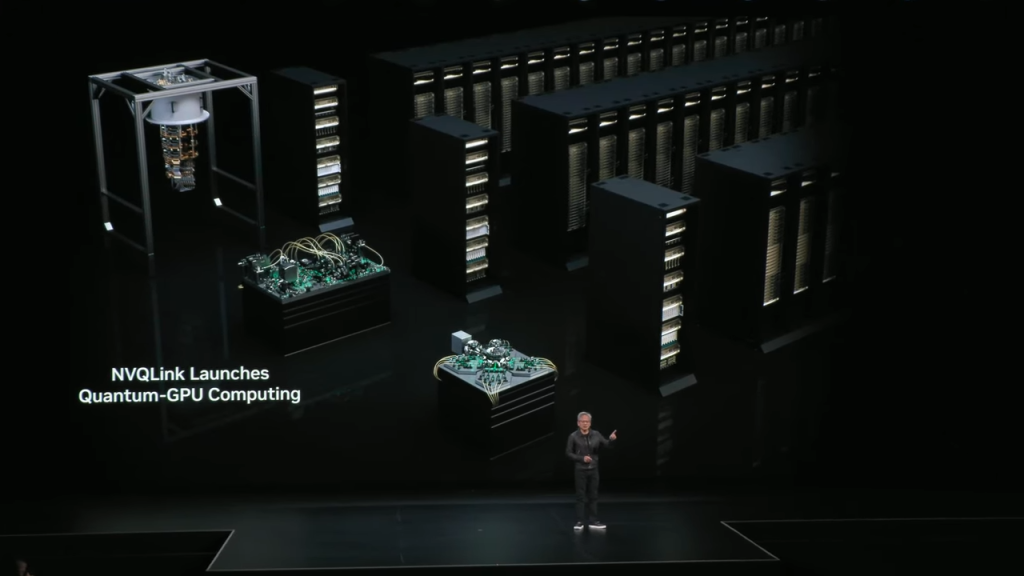波特伦·谢弗德︱“剑桥之花”琼·罗宾逊的理论之路(二)
2023年10月初,我(姜宏)和谢弗德完成了在北京和武汉的访学交流,准备按计划取道香港返回德国。我知道老教授一向对异域文化颇感兴趣——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这似乎让他对各类文明有着强烈的敏感和好奇。于是,我带着谢弗德去了香港有名的黄大仙祠,准备让他领略一下民俗文化。黄大仙祠的一个项目就是抽签“算运势”,求签者将所求之事写在一小张红纸上,然后从签筒里摇出一签。到现在还清楚记得,谢弗德为了避免我看懂,在红纸上写下的是拉丁文。片刻之后他就摇出了“孔子击磬”一签,签文解为“告诫人们,要惜取少年时,应该做的就及时去做,否则老之将至,就有心无力了”。我将此意翻译给谢弗德,看着他陷入沉思,但我依然不知道他所求何事。第二天中午,他终于告诉了我他写下的是什么:他是否应该写一本回忆录。我不能确定这次香港“算卦”之行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他的决心,但他的的确确开始撰写回忆录——以下缅怀罗宾逊夫人的内容就是此回忆录的重要部分。经作者授权分四篇刊发,本文为第二篇——“生平”。

青年谢弗德,法兰克福大学
琼·罗宾逊于1903年10月31日出生,在五个孩子中排行第三,家中共有四女一子,她的父亲是弗雷德里克·莫里斯爵士(Sir Frederick Maurice),母亲是海伦·玛格丽特·马什(Helen Margaret Marsh)。这是一个具有鲜明家族传统的家庭,琼的曾祖父是一位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祖父及父亲都是军人,外祖父是著名外科医生、剑桥大学唐宁学院院长弗雷德里克·马什(Frederick Marsh),她的舅舅爱德华·马什爵士(Sir Edward Marsh)是知名艺术鉴赏家、文学评论家,也曾担任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私人秘书。哈考特(Geoffrey Harcourt)曾评价道:“琼·罗宾逊的父亲是一位极富原则性的人,尽管他的信念有时显得近乎古怪,他仍将这些品质深深传递给了女儿。”琼的父亲莫里斯爵士被公认为是一位出色且忠诚的军事指挥官,对下属一视同仁。1918年,德意志帝国在与俄国签署和平协议后,似乎又有可能腾出手来在西线取得突破,在此背景下,他公开批评英国国防部关于兵员数量的统计数据,在英国下议院引起了一场激烈辩论,最终他被迫辞职——当代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一事件显然对当时年仅14岁的琼·罗宾逊产生了深远影响。她后来曾回忆,那一年,她的“梦想破灭”了。
中学毕业后,琼·罗宾逊进入剑桥大学的吉尔顿学院(Gerton College)就读,该学院成立于1869年,是英国第一所女子学院。她于1922年顺利毕业,1926年与基督圣体学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的院士爱德华·罗宾逊(E.A.G. Robinson, 1897-1993)结为连理,随后随丈夫前往印度。在印度,爱德华获得了一份高薪职位,为一位土邦大君的儿子担任家庭教师,琼也略显羞涩地参与到殖民地精英阶层的社交与活动中。塔希尔(Pervez Tahir)对这段鲜为人知的经历进行了细致描写:琼不得不面对印度社会发展滞后所带来的冲击,这种冲击部分源于她所受的马歇尔主义经济学训练。这对年轻夫妇共同关注经济议题,后转而研究印度问题及人口问题。返回英国后,爱德华于1929年被聘为讲师,1931年成为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Sidney Sussex College)的研究员,琼于1934年开始担任助理讲师。
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于1927年抵达剑桥,琼·罗宾逊曾聆听过他的讲座。在那之前,她的经济学训练几乎完全源自剑桥的马歇尔学派。正是借由斯拉法的影响,她首次接触到了欧洲大陆的经济思想潮流。可以说,琼·罗宾逊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她与斯拉法及其他经济学家之间持续不断的学术交流与个人互动。除斯拉法之外,对她产生重要影响的还包括杰拉尔德·肖夫(Gerald Shove, 1887-1947)、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以及丹尼斯·罗伯逊(Dennis Robertson, 1887-1947)。在她求学和早期研究时期,阿瑟·塞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 1877-1959)依然是学院的核心人物,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理论逐渐成为理论主导。在众多交往中,她与理查德·卡恩(Richard Kahn)关系最为密切。当她将“不完全竞争理论”确立为主要研究方向、准备撰写代表作时,卡恩凭借其出色的分析能力,为她和当时的其他学者提供了关键支持。尽管如此,琼·罗宾逊依然毫不犹豫地宣称:“皮耶罗是我最珍贵的宝石。”
如今我们所理解的“剑桥经济学”发展史,通常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阿瑟·庇古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三位学者紧密相关。在他们之后,剑桥传统由斯拉法学派与后凯恩斯主义者继承和扩展。然而,这一理论脉络实际上可以追溯到斯拉法与琼·罗宾逊的早期贡献。当时,琼·罗宾逊在回应斯拉法对马歇尔学派的批判时,逐渐转向不完全竞争理论,并进一步发展出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础的模型。正是这种理论转向,帮助开辟了从凯恩斯短周期理论通向增长理论的路径。在凯恩斯的影响下,学界开始更为深刻地吸收和分析资本主义在短期发展中的不稳定性,而在此背景下,任何关于长期稳定发展的理论建构都显得颇为脆弱。一旦对凯恩斯理论的起源与阐释有了充分理解,斯拉法便致力于重建古典理论及其对长期发展路径的解释——至少在他最重要的学生加雷尼亚尼(Pierangelo Garegnani)的诠释中情况是如此。与此相比,路易吉·帕西内蒂(Luigi Pasinetti, 1930-2023)则将因果关系的解释置于次要位置,他更倾向于设定一种规范性路径:经济应当沿着恩格尔曲线(Engel Curves)以相同速度实现增长或经历结构性转型,从而实现充分就业与稳定发展。
我想把重点将放在对琼的学术成果及其相关解读上。然而,琼本人的经历也具有历史价值。面对当时大学内部对女性权利的偏见与制度性障碍,一个自然的问题是:琼·罗宾逊是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取得职业成就的?一本名为《好斗的琼·罗宾逊:一位剑桥经济学家的成长》(Aslanbeigui & Oakes, 2009: The Provocative Joan Robinson: The Making of a Cambridge Economist)的传记几乎执着地反复聚焦于这个视角单一的问题。两位作者似乎对这样一个事实感到不安:他们在传记及制度史叙述中,不得不偶尔进入经济学本身的内容,以解释学院内部的竞争,并指出为何某些竞争最终得以和平解决,而另一些却导致了冲突升级。这部著作的优点在于严格依赖资料,尤其是档案中大量书信,避免诉诸模糊记忆或八卦传闻。书中展现了琼·罗宾逊如何在斯拉法引发的不完全竞争讨论中整合关键观点,并发展出更大的理论框架,由此确立了主要模型的表述。然而,观点先后顺序却引起了激烈争论。即使在那个阶段,琼·罗宾逊仍将经济学看作一个“工具箱”,而边际收益曲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工具。她后来又热情地追随凯恩斯从《货币论》到《通论》的思想轨迹。凯恩斯最初对是否将她纳入核心圈子犹豫不决,因为她与卡恩的关系让他担忧,这一关系也一度威胁到爱德华·罗宾逊的地位。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在由斯拉法、米德、卡恩、爱德华与琼组成的“马戏团”中,她成为凯恩斯的重要合作者。凭借简明清晰地剖析理论核心的能力,以及在“马戏团”中的训练,琼·罗宾逊在《通论》发表后迅速成为凯恩斯革命的重要代言人,撰写了首部关于就业理论与政策的教科书,即《就业理论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Employment),以及相关学术论文集。她随后获聘为大学讲师。尽管卡恩回忆称,评审过程略显尴尬,因为委员会未能正视她在国际上的学术成就以及她作为助理讲师所赢得的声誉,但她最终还是获得了与自身声誉相称的正式职位。早在1932年,她就曾在给远在非洲的丈夫的信中写道:“这些年来,我一直承受着身为聪慧女性的压抑感与性别角色间的内在冲突,但现在我(几乎写完)写出了一本该死的好书。”
几个月后,胜利的喜悦转化为深重的沮丧。在这五年间,她生育了两个孩子,撰写了三部著作;而在这段高产的时期结束之际,她却陷入了一场严重的精神危机,不得不在精神病院接受六个月的治疗。关于她为何会走到这一步,传记作家们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解释。她与理查德·卡恩关系密切——卡恩曾为她提供数学上的指导,两人通信频繁,尤其在卡恩远赴美国期间更为热络。在剑桥的学院内部,违反行为规范是极具风险的。琼也知道,不久之前还有一位研究员因一桩在今天看来纯属私人的行为被解职。尽管琼与爱德华在外人眼中保持着体面的婚姻形象,并始终保持低调,但琼和卡恩仍试图把握一切机会相见——可以说是幽会——尽管他们的信件中也频繁探讨经济学问题。在这样的多重张力下,家庭、情感与学术工作的压力令她几近崩溃,而国际局势亦令她痛苦不已。她被要求公开支持《慕尼黑协定》,这对于一位坚持和平主义、充满正义感的女性来说无异于精神打击,也因此与身边亲近之人发生了激烈争执。最终,她精神崩溃,整整一周无法入眠。她被送入一家精神病诊所,接受了弗洛伊德开创的那种现代心理治疗。爱德华与卡恩也分别做出了有限的自我反思,并与她的治疗医师沟通。在此之后,他们三人各自重新回归了学术生活的轨道,表面上仍维系婚姻关系的外壳,但彼此之间却获得了更大的行动自由。
琼·罗宾逊逐渐赢得了国际声誉。之前她主要依赖丈夫的收入生活,因此在能够通过自身工作获得额外收入,尤其是在被任命为讲师之后,她感到由衷的满足。然而,更为关键的一步出现在1932年——她意识到自己完成了一部具有真正理论意义的著作。这本书围绕不完全竞争理论展开,可以说是对庇古学派所代表的马歇尔主义知识体系的一种综合。正如保守派学者沃特曼(A.M.C. Waterman)所描述的那样,她是一位令人难以忘怀的教师。
在此,我将略去一些传记性的细节,包括她在战时如何幸存的经历。她始终热衷于旅行,乐于在博物馆中欣赏意大利绘画,在英国乡野间漫步。1961年,她对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行了重要访问,并与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就经济思想史进行了深入交流。她在理论和政治立场上日益激进:在理论方面,她对均衡概念的批判日趋尖锐,甚至质疑自己早期在新古典理论框架下对不完全竞争问题的研究价值。她逐渐倾向认为,均衡只应限于增长理论与古典传统的长期分析场景中使用,前提是国家的持续存在被视为稳定、可预期的。她将此称为“黄金时代”——这个带有神话意味的术语正是为了强调持续增长状态的脆弱性。在经济政策方面,她继续坚守凯恩斯主义立场,例如她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大加批评。她在政治层面则大幅左转,深受毛泽东“文化大革命”道德严苛性的吸引,并因此引起巨大争议。然而,琼未能活得足够长久,未能亲眼目睹这些理念如何被现实所颠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本意在于打破等级制度,尤其是在学校、大学及工厂内部的等级结构。“文革”结束后的中国改革基于如下设想:一方面在工业和农业中暂时维持计划体制,另一方面逐步缩减配给供应,扩大市场导向型生产的空间,而市场需求又反过来受到新型收入结构的驱动。正如今日所见,这一体制缔造了持续数十年的经济奇迹——使数以亿计的人口实现小康及富裕……也许我们会好奇:倘若琼·罗宾逊在世,她会如何评价这一结局——一个通过大规模生产令千万人小富即安、又使千万人暴富的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