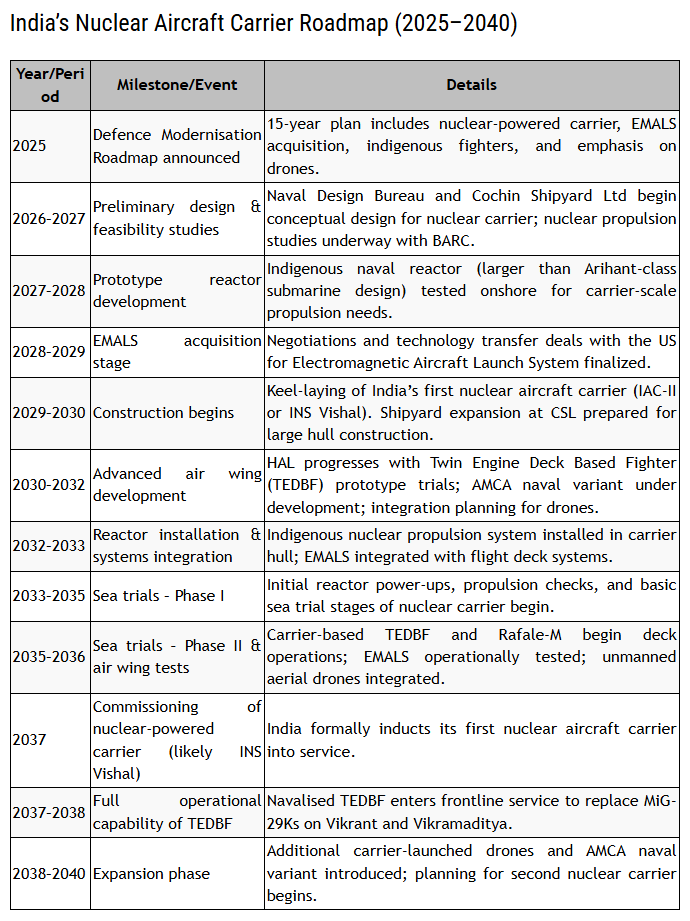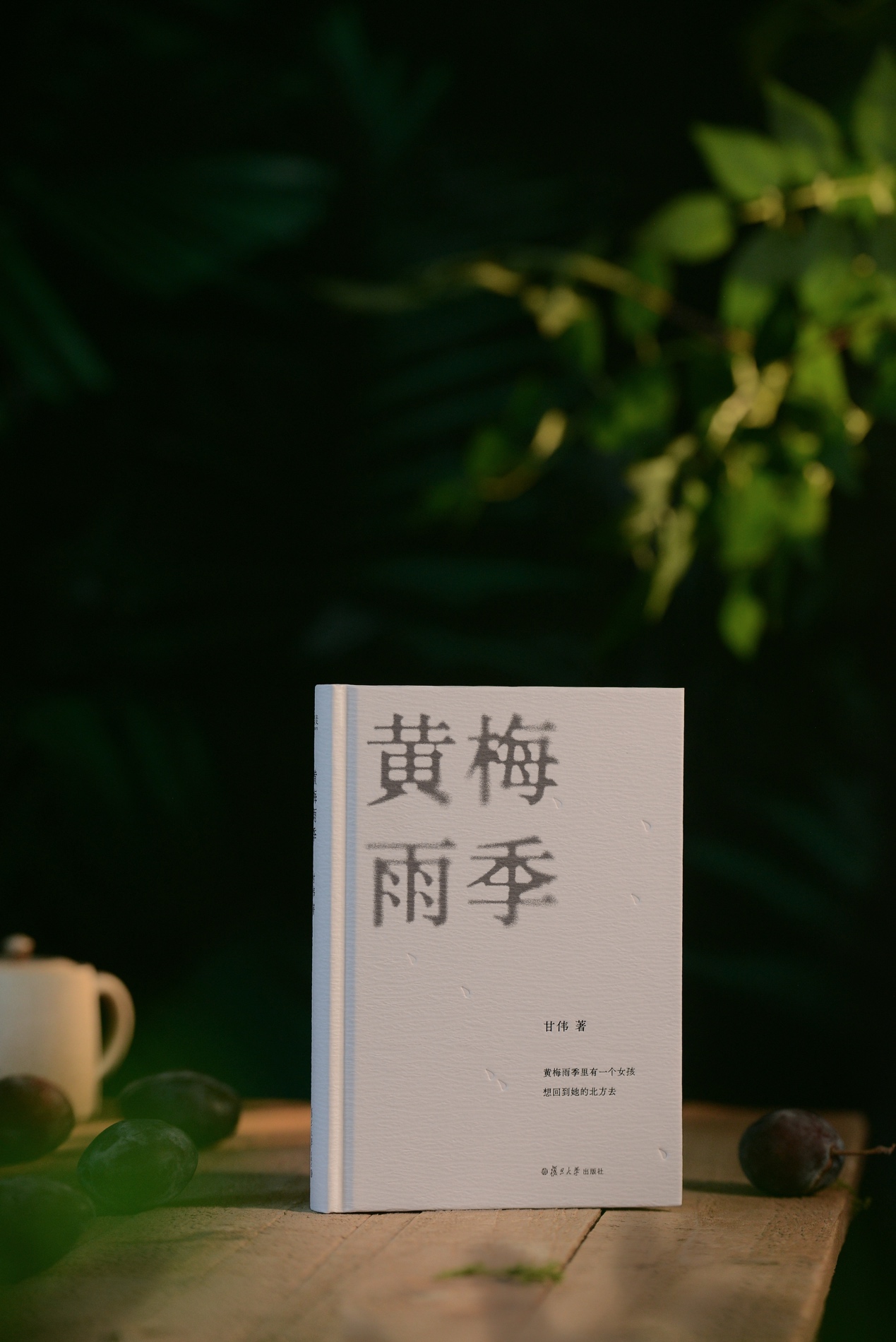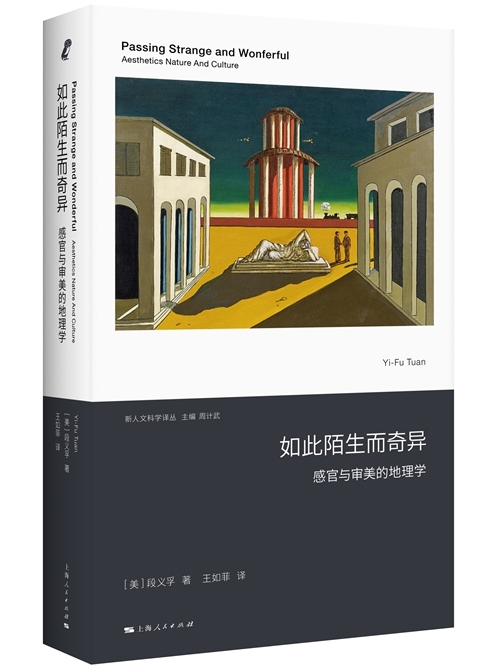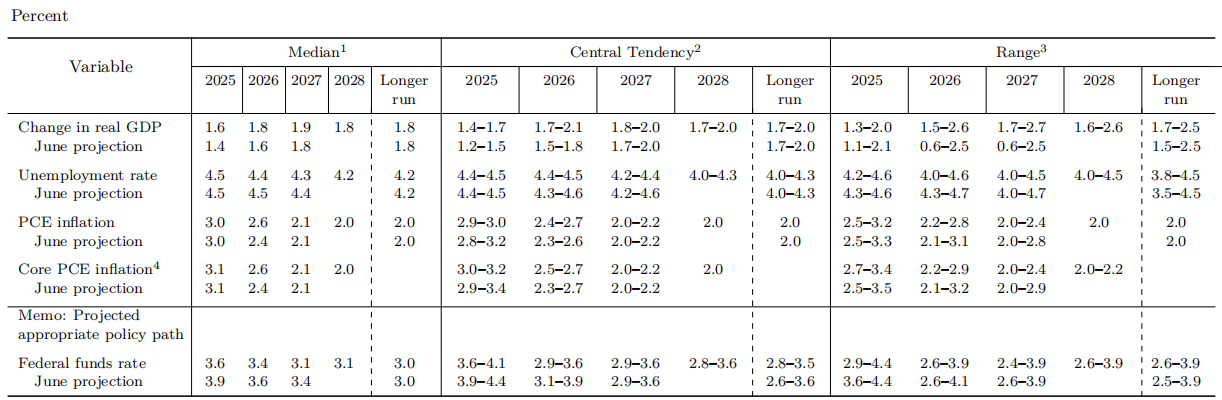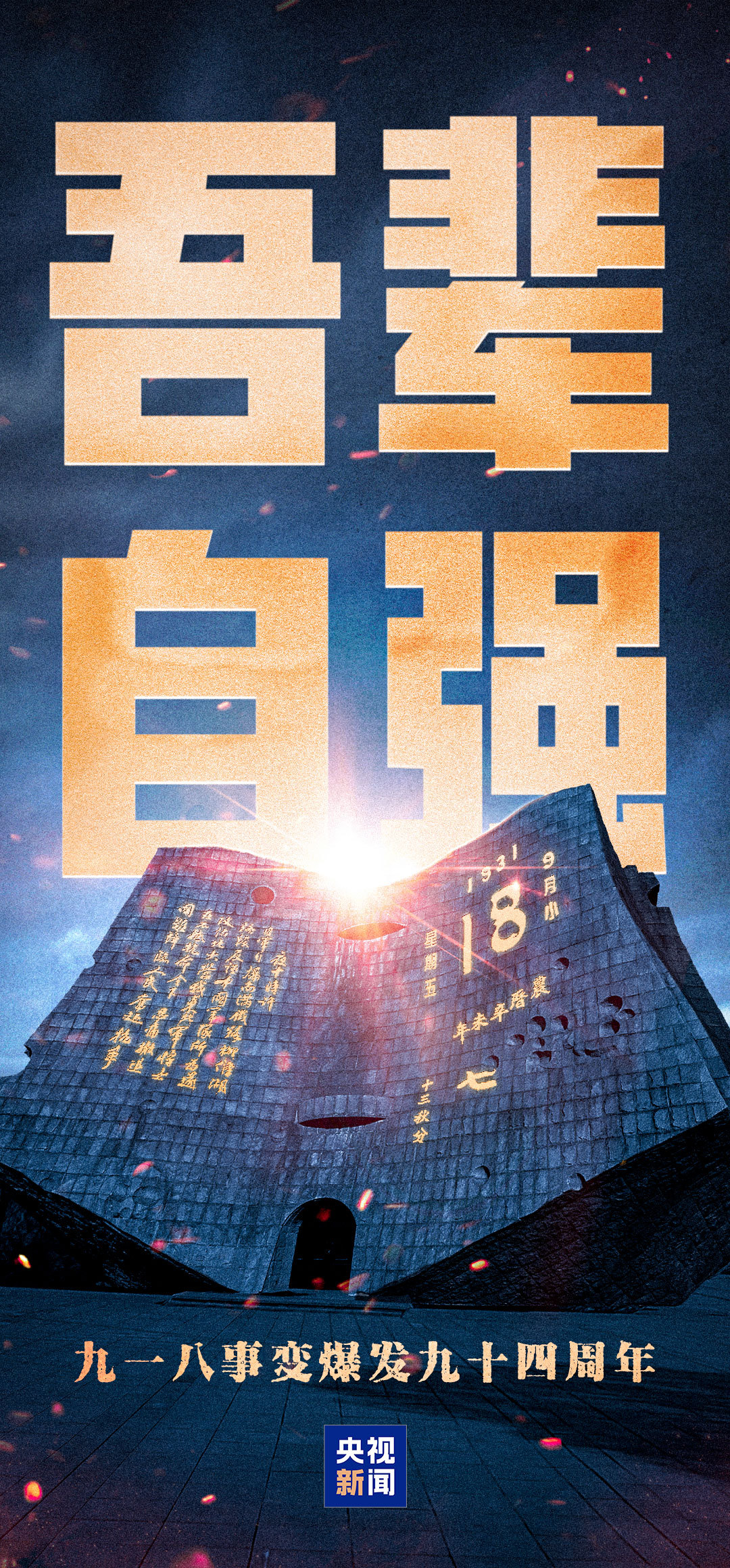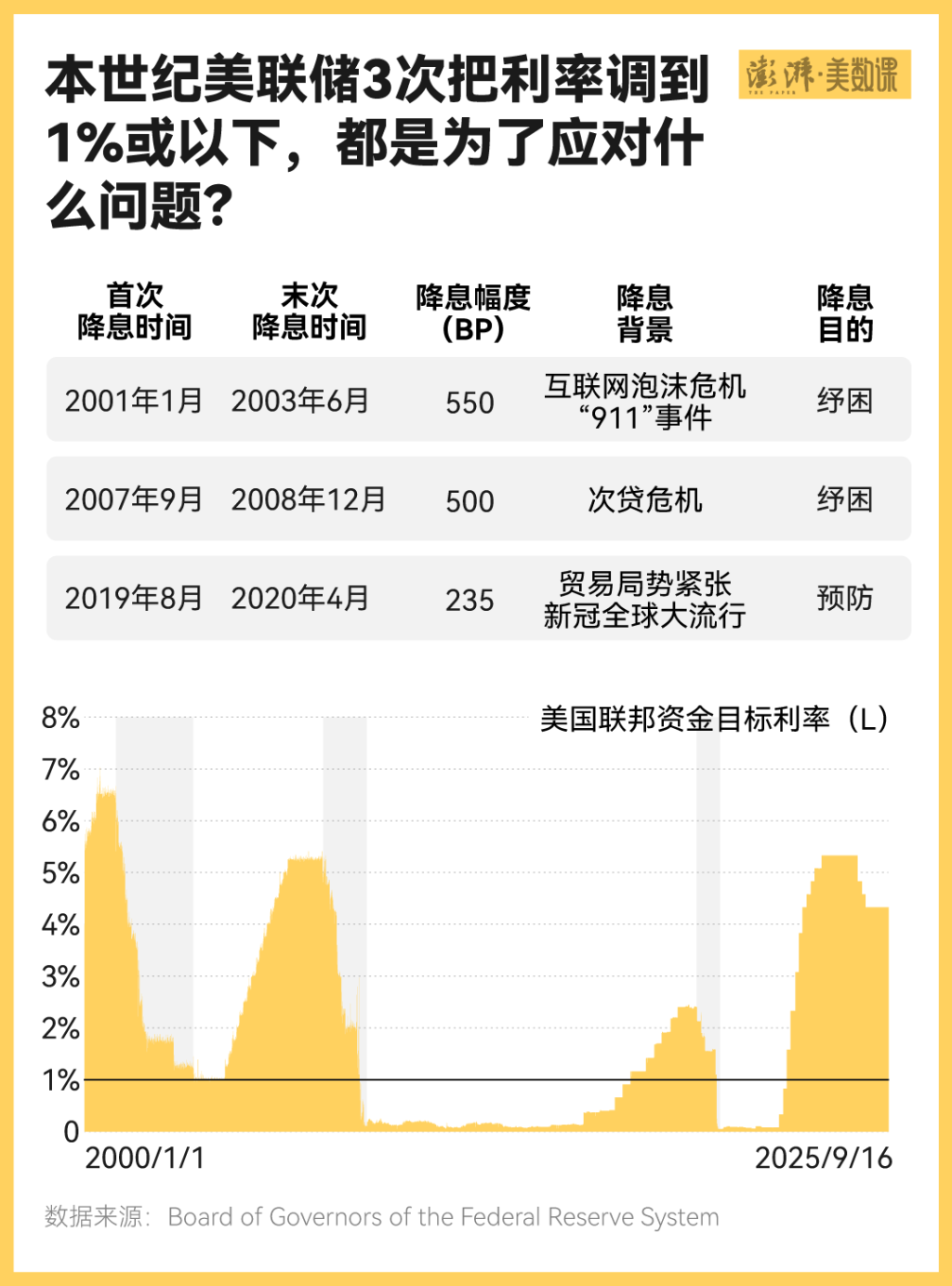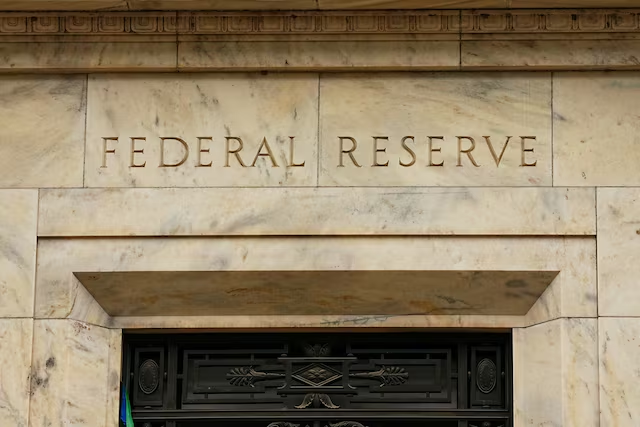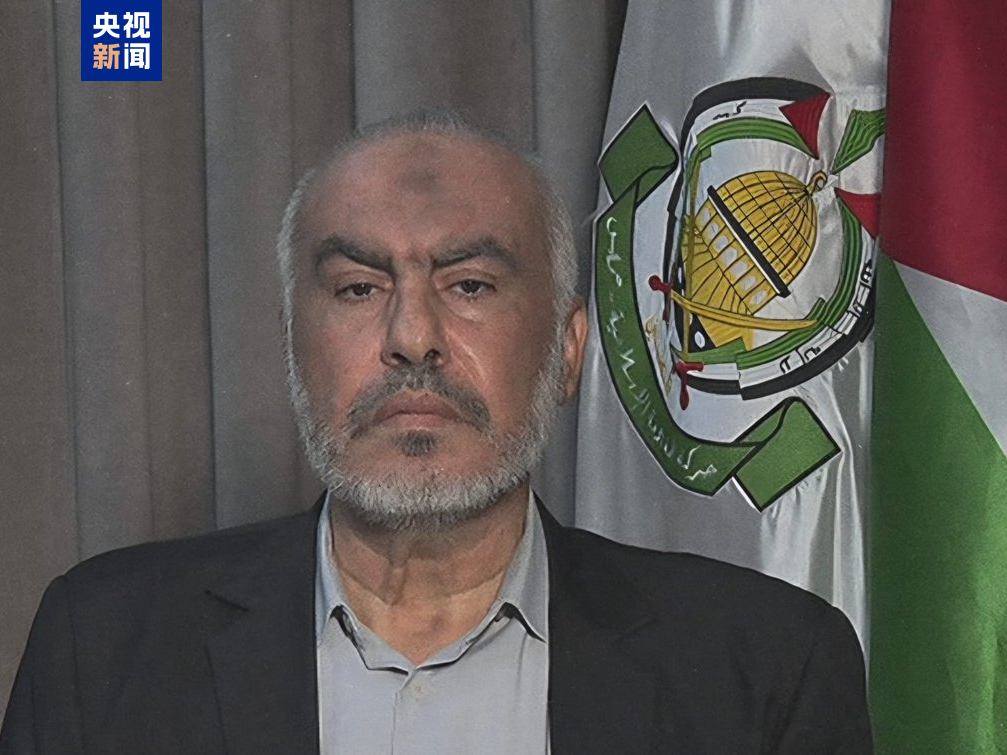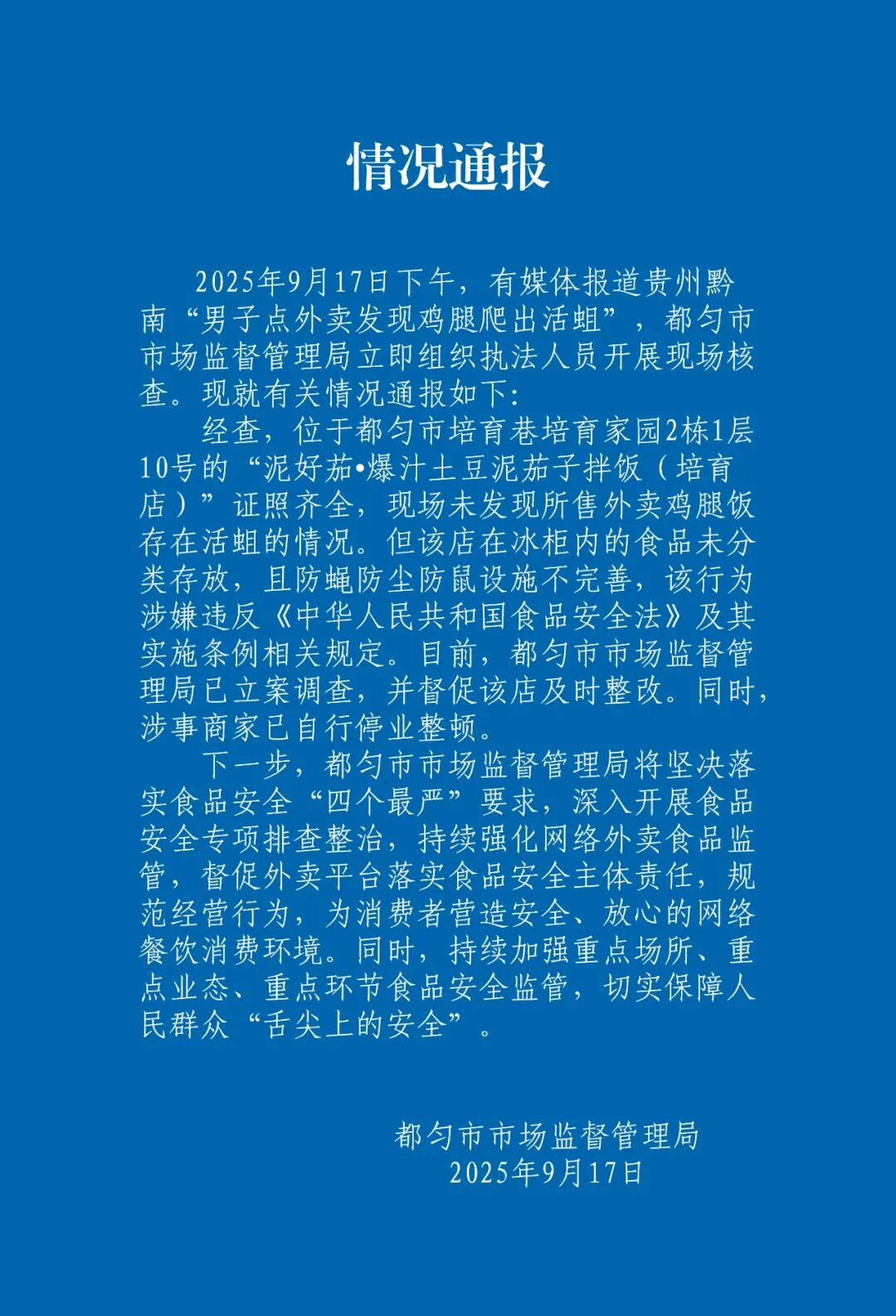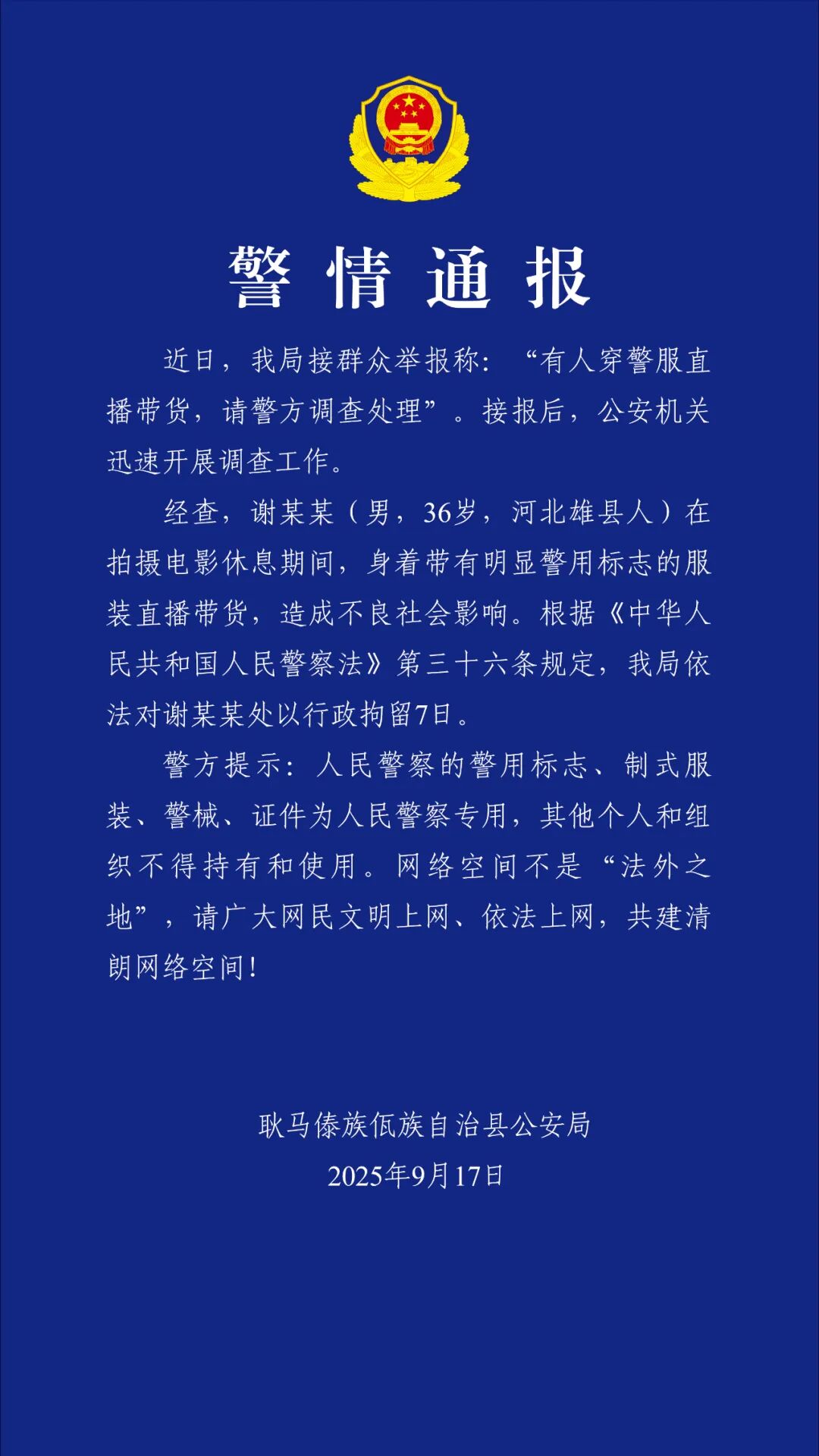首届“历史与哲学上海论坛”在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举行
2025年9月12日至13日,由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首届“历史与哲学上海论坛——历史与哲学的对话”在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同新楼成功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鱼宏亮、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王献华教授发起,邀请了来自哲学、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等不同领域的十余位学者参会,共同探讨历史与哲学研究的新路径与前沿议题。
开幕式于9月13日上午在上海财经大学同新楼举行,由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郭美华教授主持,鱼宏亮教授致辞,为论坛拉开序幕。鱼宏亮教授介绍了本次论坛的缘起与目标,他说首届“历史与哲学论坛”借上海财经大学成立新人文学院之机隆重举行,是上海财经大学新人文学院成立之后第一次重大学术活动。论坛强调跨学科的交流与对话,希望通过此次会议能够在打破研究壁垒的同时,为近年来人文学科领域的重要议题提供新的讨论空间。

会议现场
本次论坛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与哲学研究所、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与哲学系、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与国学院、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北京大学历史系、上海交通大学哲学院及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等十几位学者分别就政治哲学及其与历史的关系、历史学的方法及历史与价值、哲学与哲学史及一般历史的关联、古今中外文明的哲学反思与历史重建等领域,进行了深刻的阐发与热烈的讨论。有意思的是,论坛四场讨论及其发言次序,是由AI安排的。由于时间关系,上午两场有五位学者发言,下午两场有七位学者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周濂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周濂教授以“政治哲学需要历史”为题,强调哲学只有进入历史,才能完成自身使命。政治哲学若要回应当下的理论与现实挑战,必须进入历史语境。周教授梳理了对历史主义的经典批评,尤其是施特劳斯对“历史主义”可能导致地方主义、保守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担忧。然而,他认为这三种风险并非历史主义本身的逻辑必然后果,而是一种对于滥用历史研究的方法论的警示,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并实践“历史性的哲学反思”。周濂教授指出,“政治哲学需要历史”是一项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任务:一方面研究者要诚实地面对地方性、偶然性和历史性,解释我们身处其中的生活与知识活动;另一方面也要保持对地方主义、保守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批判警惕,以问题为导向,采取融合而审慎的态度,在理解社会现实的同时追求更公正的生活方式。在他看来,这种既保持反思又充满希望的批判实践,构成了后形而上学时代政治哲学的应有姿态,为哲学与历史的深度对话开辟了新的可能。

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陈志武教授
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陈志武教授以“春秋战国中的强者生存:铁器技术何以让秦国胜出、统一中国?”为题,从经济史与量化历史的角度解析了“春秋战国中的强者生存”,借助现代计量方法与考古数据,为中国思想史、制度史等领域提供了新的视角。他强调,量化方法并非意在取代传统的历史研究,而是与之互补,尤其在数字人文与思想史结合方面的潜力巨大。通过大规模整理自汉代以来近三十万种中文出版物的题材与结构演变,可以洞察不同时代群体的关注重点。陈志武教授总结到,铁器技术在公元前一千年间于欧亚大陆广泛传播,与亚述、波斯、希腊、罗马和秦等早期大帝国的兴起存在深刻关联。对春秋战国的量化研究,不仅有助于解释秦国统一的历史逻辑,也为理解中国思想与社会演变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他呼吁人文学科应积极吸收量化和统计方法,拓宽对历史与思想发展的认知视野。

上海交通大学哲学院余治平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哲学院余治平教授以“质文法统与亲亲、尊尊……牟宗三《历史哲学》诠释之得失”为题,展开其关于本次“历史—哲学对话”的方法论思考。他指出,若要为论坛确立可持续的学术方向,首先必须把经学与哲学的关系、经学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历史与哲学的关系的内在逻辑厘清。余教授强调经学并非站在哲学的对立面,而是对哲学的一种根基性补充。他主张以哲学作为诠释工具进入经学:既不复归为纯粹的“古典主义”或“汉学情境”,也不放弃现代哲学的分析资源;其中的关键在于把哲学当作方法与视域。余教授认为,真正高水平的跨学科对话,终将汇入对文明秩序与人的共同处境的追问;研究者不仅要在学术上自洽,更要在历史责任与公共理性上能够经得住检验。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鱼宏亮教授
鱼宏亮教授以“历史事实中的价值与价值中的历史”为题,指出史学不仅是事实的考证,更承载了特定价值取向;研究者需意识到材料的留存与解释常常会受到价值结构的引导。他肯定陈志武教授所提出的考古与量化方法对于揭示历史机制的重要性,同时提醒量化模型预设所可能带来的局限性。鱼教授提出,史学的核心在于说明“价值如何进入历史并塑造叙述”,从而形成“历史中的价值、价值中的历史”二者相融互通的研究路径。他呼吁在快速变化的技术与制度环境中,人文学科应重建公共性的价值叙事,使历史研究在事实阐释与规范判断之间保持张力。通过与哲学对话,史学不仅要积累知识,更要在思想层面回应当下社会的价值危机,为重塑集体的“真实”提供论证与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刘丰教授
刘丰教授以“思想史与哲学史视域下的宋学研究”为题,对于历史与哲学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刘丰教授指出,对于中国哲学研究多以“哲学史”方式展开,而史学则强调事实考据与价值中立,两者对同一材料往往形成不同叙述。以宋明理学为例,理学家强调“道统”与文化主体性,而历史学家更关注其制度背景与观念源流,二者对朱熹、二程及王安石的定位明显有别。这表明,价值立场与史实脉络之间存在着天然张力。他强调,哲学研究并非无根的抽象,同样需要严谨的文本与史料支撑;而史学也无法完全剔除价值判断。如何在“价值承诺”与“历史真实”之间建立桥梁,是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的核心课题。而本次论坛的意义正在于提供一个对话平台,使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在保持方法与边界自觉的同时,探索价值与历史相互生成的可能性。
下午场的报告则着重于在文明史与思想史的交汇处,对中国经典传统、哲学史写作与史学范畴进行系统性的反思与重构。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李若晖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李若晖教授以“道家如何出于史官——《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小序研究”为题,剖析该文本的逻辑结构及其背后的史学—哲学意涵。他强调,在《艺文志》所示的语境中,道家继承了史官对“天道”的关怀,却质疑史学将历史归结为可预测、可操控的成败利害之预设,转而强调人之有限与命运的无常。由此,道家通过“无为”将对历史的关注转化为对人及其内在联系的省察:君主应以“有而不用”的方式保持与万民的潜在关联,而非将其现实化为压迫性的统治,从而使历史秩序在免于混乱的同时,保持其开放性与方向性。李若晖教授总结到,对于《艺文志》“道家出于史官”之说的考察,不仅关乎史官传统与道家思想的渊源,更关乎如何在历史事实与价值、政治秩序与存在意义之间建立起细致而富有批判性的解释框架。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郭美华教授
郭美华教授以“秩序、圣人和隐逸”为题,指出秩序是天地人以及万物之整体的固有自在之物,而不是由圣人外在建构的主观性规范。即使在社会关系领域,两方及两方以上的社会关系有着由此关系而有的规范,此规范形成的秩序优先于关系中任何一方;关系中的任何一方既不能凌驾于关系及其规范之上,也不能凌驾于其他关系者之上。在秩序与圣人的关系问题上,儒家倾向于圣人优先于秩序(儒家所谓圣人是类本质与秩序的完满化与绝对化化身),而道家倾向于秩序优先于圣人(道家所谓圣人则是领悟自身有限性并依循自然秩序自为限制的相对存在者)。郭教授强调,必须警惕孟子式儒家“圣人立法”的自我膨胀冲动。就政治-社会的治理而言,其终极目的应指向自由个体的自由生存。隐逸并非岩居穴处,而是说政治-伦理的纲常名教罗网下,自由个体生存于非名言之域(非名教所能羁罗之域)。作为人类生存的整体之域,政治之域、伦理之域、教育之域与隐逸之域必须保持相对独立的分界,以为个体自由生存的普遍可能性提供担保。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李永晶教授
李永晶教授以“道家自然主义:《老子》中的哲学、历史与心灵”为题,回应了当代科学主义的价值困境。他指出,科学一旦被绝对化为唯一的认识框架,就会容易导致工具理性膨胀、价值相对主义与意义“内卷”。为此,应以“道”为宇宙秩序的起点,同时在认识论上承认理性的有限性,从而为不可知与不可说保留空间。他主张要从“智力”转向“智慧”,恢复心灵的开放性;李永晶教授强调对“圣”的理解应该是“圣需仰视方可望见”以及“圣对人之善在于超越私域而不强制”。圣人之得道而有之心,就是天地宇宙之心,不再是为肉体所束缚的有形个体之心。最后,李永晶教授承认这一话题不可避免会具有可争辩性,意在为经典再阐释与当代价值重建提供可供检验的讨论框架。

北师香港浸会大学董铁柱教授
北师香港浸会大学董铁柱教授以“中国哲学史的‘僵硬’及其‘复苏’的可能性”为题,指出传统中国哲学史写作在宏观结构与微观人物两方面均呈现“僵化”问题:宏观上,百年来的叙述模式仍多承袭胡适以来的范式,未能充分突破“朝代—人物—思想”的线性架构;微观上,研究过度集中于“显赫人物”,而缺乏对小人物、边缘文本及多样思想资源的系统发掘。董铁柱教授认为,中国哲学的生命力并不在于僵化的谱系,而在于“故事—思想”的互动结构。他倡议在文献研究中注重“人和事”的具体情境,避免以固定理论框架束缚材料解释,同时鼓励引入文学叙事、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多重视角,拓展哲学史写作的边界。他特别强调出土文献与区域资料的重要性,但提醒学界不应把这些“热点”局限于细碎考证,而应思考其对整体格局的重构价值。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成一农教授
成一农教授以“谁的中国历史?”为题,分享了对于“中国历史”概念及其书写方式的再思考。他指出,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叙述多承袭民国时期的框架,而“历史”本身亦是近代学术语境的产物,古人并无今日意义上的“中国历史”整体观念。“王朝”“天下”“帝国”“边疆”等范畴,多在近代被重新定义并纳入民族国家与世界秩序的话语结构。当代史学若不反思这些预设,便易陷入某些“假问题”。成一农教授呼吁学界回到历史语境,探究古人如何理解与书写他们的“天下”与秩序,避免受“国家—民族”框架限制。他指出,唯有尊重材料与情境,同时保持价值判断的自觉与开放性,跳出近代话语束缚,重建与传统对话的视野,才能赋予“中国历史”更具生命力和批判性的叙述方式。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赟教授
陈赟教授以“文明观的省思与重构:以中国思想为视阈”为题,聚焦于“文明”概念的谱系学重建及其范畴边界。陈赟教授强调,从“文明”概念的历史语义出发,可追溯至18世纪中叶。在这一时期,“文明”概念兼具价值论的单数文明(进步、等级、目的论)与描述性的复数文明(类型学、比较叙述)两重向度。以此为据,文明化既意味着秩序、礼貌与理性约束的生成,同时亦伴随着活力钝化、英雄主义退场及“文明化暴力”,揭示出文明概念本身的张力与边界。进而他提出以中国古典“文字论”重释文明:将天文与人文并举,以“质—文—字”的显-隐双重过程建构文明。据此,“人与万物共生”不再是前文明,而可被理解为文明的高阶形态。最后,陈赟教授强调,重新审视文明并非否定其历史效力,而是为不同的文明意识找到恰当的边界。只有在价值判断与经验描述之间建立可以调适的高阶框架,文明概念方能避免中心主义,为理解多元历史与未来共生提供开放的哲学视野。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王献华教授
王献华教授以“史学实践的文明史反思”为题,系统阐述其近年来对“文明史”与史学实践关系的思考。他指出,现行人文学科的许多范畴与系统性框架,仍深受“蒸汽机时代”的机械论与功能主义影响,导致知识被割裂为彼此孤立的领域,而文明史写作亟须跳出对于这一路径的依赖。以此,王献华教授以“共域”(Ontopia)概念为切入点,强调文明应被理解为人类社会在真实“生活世界”中的生成与演化,而不仅是某种单一的进步叙事。在此视野下,史学不仅是书写活动,更是对于“过往”进行制度化记录与赋义的综合实践。最后,王献华教授强调,史学研究应在保持价值自觉、尊重材料与历史语境的基础上,同时跳出既有范式、重建与文明传统的深度对话,才能够为人类文明史开辟更具开放性、更具批判精神的书写空间。
十几位学者发言结束后,会议进入“人文社会科学十大热点选题推选”环节。国际学界近年来持续反思人文学科处境,近年来不同的研究范式为此次“十大热点”评选提供了更宽广的语境,而这次推选也能为未来跨学科研究议程汇聚意见。敏锐的人文学者,总是能跨出自己的专业界限而洞察到时代的整体问题与根本问题。此次候选议题有三大方向:一是人工智能与哲学、价值重估和政治伦理;二是历史理论与叙事方式;三是思想史与哲学史的范式自觉。热点评选的目标并非立即形成终极的探讨命题,而是为跨学科研究搭建持续交流的平台,激励学界在技术变革、文明视野、史学与价值等议题上形成更具共识性和创造力的对话空间。

会议现场
会议总结由鱼宏亮教授主持,王献华教授致辞,总结环节中,王献华教授指出,本次论坛不仅展示了历史与哲学在研究方法与问题意识上的互补性,也为青年学者提供了开放对话的平台。他指出,跨学科对话的价值在于促成真实的交流和批判性反馈,但也必须正视语境差异:若学科背景相距过远,往往难以立即听懂彼此的问题意识,因此需要时间与共同的“高度”来建立有效沟通的基础。他特别提到会议设置“学术十大热点”环节的初衷,是希望形成一种“仪式化的严肃”,鼓励大家明确、精准地表述问题,并在集体修订与讨论中形成具有共享意义的议题池。这既是一次探索,也为后续研究奠定平台。最后,王教授强调,本次会议标志着一项新的学术实践的开端,他期待未来能够邀请更多同道参与,同时在选题上不断打磨,使跨学科交流真正生成共识与创新成果。

参会人员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