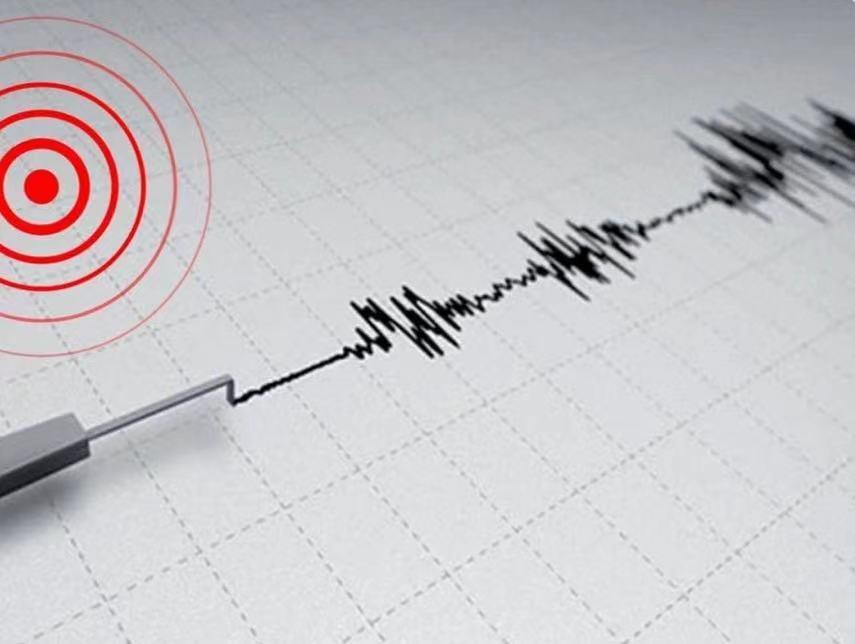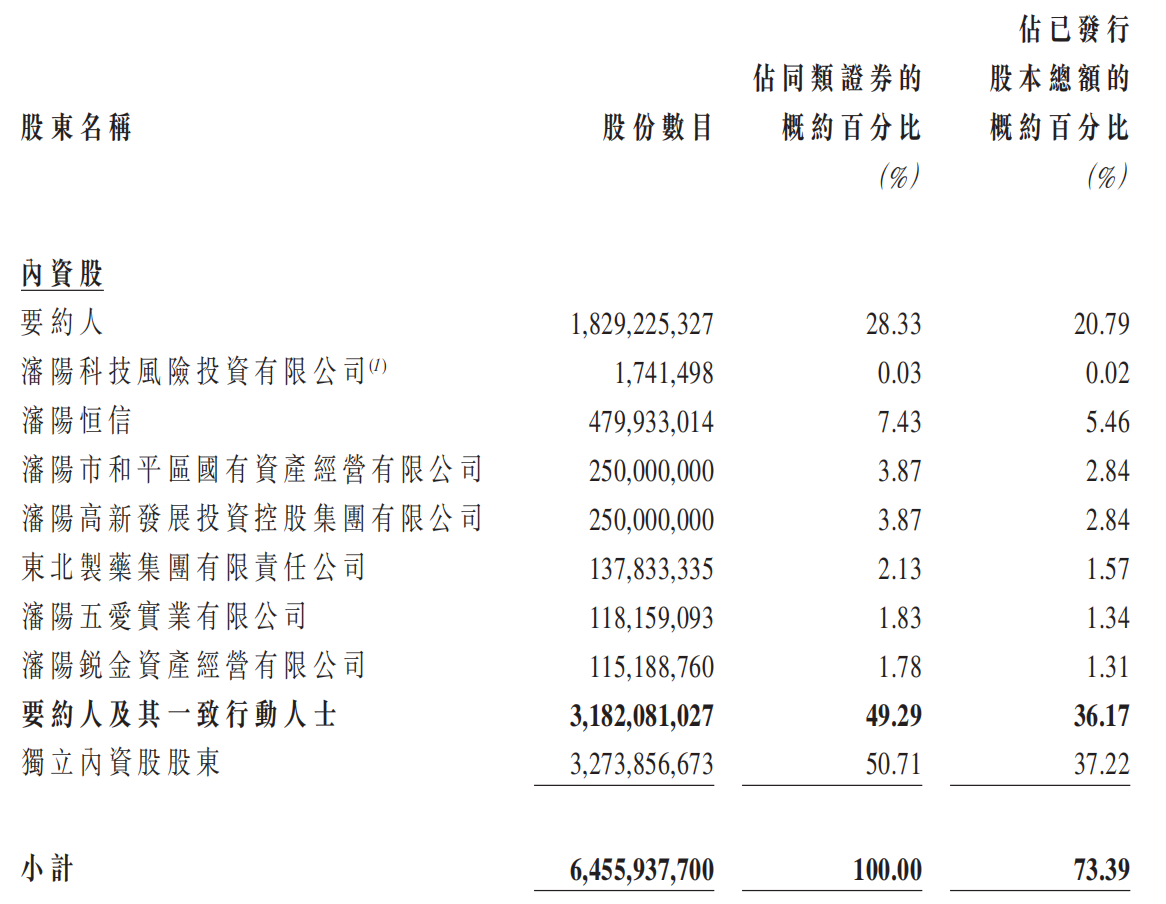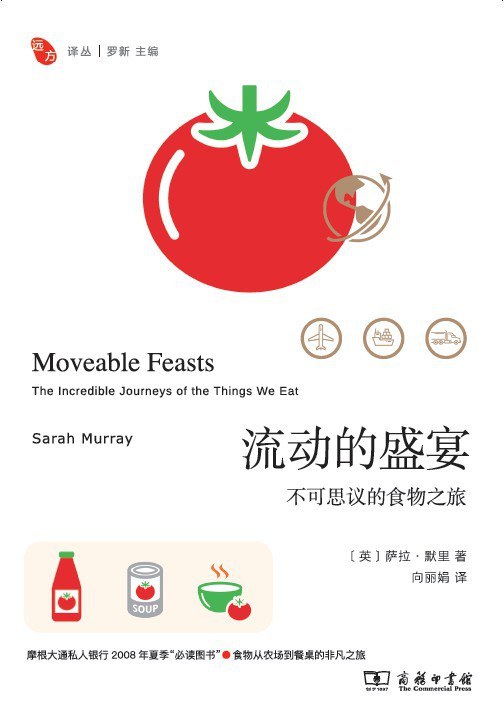学者麦克法兰、赵鼎新对谈:欣赏文明多样性,差异不是威胁
“我们就像一只被困在玻璃瓶中的苍蝇。”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这个著名比喻,被英国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艾伦·麦克法兰用作其新书《宇宙观与现代世界》序言的纲领性意象。
10月19日晚,年过八旬、访华多达20次的英国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艾伦·麦克法兰,与浙江大学教授赵鼎新一起,与读者在北京万圣书园优盛阅读空间,共同进行了一场名为“重拾现代生活的精神地图”的漫谈。

活动现场
何为宇宙观?我们为何对其视而不见?
座谈伊始,《宇宙观与现代世界》的译者秦雨晨抛出了核心问题:什么是宇宙观(Cosmology)?它如何塑造文明?
在麦克法兰教授看来,所谓宇宙观,是一整套关于信仰、观念和假设的思想体系,它处于最高层次,如同水之于鱼,空气之于鸟,是人们日用而不自知的底层思维框架。
他引用明代洪应明的《菜根谭》的名句生动地说明这种隐形性:“鱼得水逝,而相忘乎水;鸟乘风飞,而不知有风。”我们所处的宇宙观,正是这样一个环境。它高于托马斯·库恩提出的范式(paradigm)和福柯所说的知识型(episteme),是所有学科理论的基础框架。“范式”和“知识型”处理相对具体一些、不那么宏大的学术领域问题,而最底层则是各种具体的理论。
麦克法兰指出,他这本新书的工作,正是试图将这种“不可见的”宇宙观变得“可见”,解释我们当今所具有的世界观是如何历史性地形成的。

《宇宙观与现代世界》,(英) 艾伦·麦克法兰 著,秦雨晨译,中信出版社,2025年3月。
中西宇宙观的根本差异:二元对立与阴阳调和
中西方宇宙观的本质对比,是《宇宙观与现代世界》中最引人深思的部分之一。
麦克法兰指出,西方思维模式根植于希腊逻辑,其核心是二元对立。例如,善与恶、黑与白、男与女、天堂与地狱、真与假。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构建了整个西方价值体系的基础。在艺术领域,自文艺复兴以来,绘画与诗歌就被视为分离甚至对立的领域,被称为“哑巴的绘画”与“盲目的诗歌”。而中国文明则展现出截然不同的特质——强调阴阳调和与万物互联。
在赵鼎新看来,这并非意味着中国没有发展出复杂的技术与思想,而是中国文明很早就走向了不同于以归纳、分类为基本逻辑的西方科学的路径。这种思维方式根植于早期周代思想,更注重对复杂社会现象的整体性理解。麦克法兰进一步指出,这种整体性、关联性的思维,展现出其前瞻性。

活动现场
西方如何看待中国的变迁
宇宙观并非一成不变,其演变与权力结构密切相关。麦克法兰提出了一个精辟的论点:思想体系的变化与权力关系紧密相连。在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们曾将中国视为理性治理的典范,充满仰慕之情。
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西欧(尤其是英国)在技术与军事上取得绝对优势后,这面赞赏的镜子骤然翻转。到了19世纪,在西方视角下,中国似乎迅速从“典范”跌落为“停滞”、“落后”乃至“野蛮”的文明。
麦克法兰坦诚地说道,这种“帝国的傲慢”曾是他所受教育中“隐性甚至显性”的一部分。当文明之间的权力关系对等时,时间观念不会有突出的改变。然而当一方明显掌握了权力,这一方就会认为自己更优越。
对于中国曾被西方认为“落后”的原因,赵鼎新则谈及在西方传教士一开始接触中国时,曾经有耶稣会士与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修会的分歧,即为了更好地传达上帝的福音,是否需要了解中国人的所思所想、中国人的知识体系。最后认为无须过多适应中国文化的多明我会等取得胜利,这也间接地导致中国的形象在此后开始被认为不如西方先进。
不过,西方对中国看法的转变(从“典范”到“落后”),根本动力在于欧洲自身通过工业革命和扩张取得了军事与经济上的绝对优势。这种优势需要一套话语来证明其合理性,从而将中国构建为“停滞”的他者。传教士的争论只是这个宏大叙事转变中的一个侧面,而非决定性原因。
世界大战与技术革命下的存在危机
宇宙观的崩塌往往是剧烈而痛苦的。麦克法兰回顾了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方信仰体系的摧毁性打击。19世纪末,西方坚信历史是线性进步的,文明如同阶梯,西方自居顶端,鼓励其他文明“攀登”。然而,1914年,这些自诩“理性”“优越”的国家陷入了一场持续四年的血腥屠杀,约千万人丧生。
“我们真的那么理性吗?我们的信念被彻底粉碎了。”麦克法兰说道。
那些自诩最先进的国家,却用最野蛮的方式互相屠杀,信仰体系随之崩塌,社会科学也从进化论转向了关注当下社会机制的功能主义。麦克法兰将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类比为一场堪比“一战”巨变的技术革命: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社会、政治和经济。
赵鼎新强调“一战”不仅是西方文明的转折点,也深刻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认知。梁启超、梁漱溟等人意识到西方文明并非唯一答案,开始重新审视西方文明的局限性,并转而从中国自身文化传统中寻找现代性的出路。这种反思打破了对中国现代化路径的单一想象,也催生了多种思想流派的争鸣,其中包括学衡派的文化保守主义和对新文化运动激进的反思,促使中国人在全球变局中寻找一条根本性的、自主的现代化路径。
对话中最能引发共鸣的,是关于现代人精神困境的探讨。他提到自己在中国的B站、小红书等平台收到大量年轻人的留言,他们倾诉对就业、人生意义、幸福真谛的困惑与焦虑。
“这不仅仅是中国的现象,”他强调,“西方年轻人,尤其是美国年轻人,正经历一场更深刻的存在主义危机。他们不仅担心工作,更开始怀疑制度本身,怀疑资本主义是否真的能带来幸福,怀疑宗教的意义。”
在麦克法兰看来,中世纪实际上思想多元,19世纪印刷术促进知识扩散,而当今社交媒体和AI算法加剧认知割裂,形成信息茧房和对立群体。两位学者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对社会共识的挑战,以及AI如何通过个性化推荐强化用户已有信念,造成群体间世界观彻底分化,并警示这种自我验证循环可能带来的社会极化风险,呼吁保持开放思维以应对认知污染。

艾伦·麦克法兰
“未来是交响乐,不是独奏曲”
面对差异和冲突,未来的出路在哪里?麦克法兰说,有人认为不同文明最终会融合成一体,但这就像希望一棵橡树长成山毛榉一样,是不可能的。他给出了两个充满东方智慧的比喻。
其一是树的共存:每条街道上都生长着不同的树,它们各自挺拔,共同构成美丽的风景。其二是交响乐:乐团里有钢琴、小提琴、鼓,它们各不相同,各司其职,但在一起能奏出宏伟和谐的乐章。
他认为,未来的图景并非一种文明同化另一种,而是像油与水一样,虽然难以融合,但可以共存于一个容器中,形成一种“和而不同”的交响乐状态。
“我们必须学会像欣赏交响乐一样,欣赏文明的多样性。”他总结道,“差异不是威胁,而是创造力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