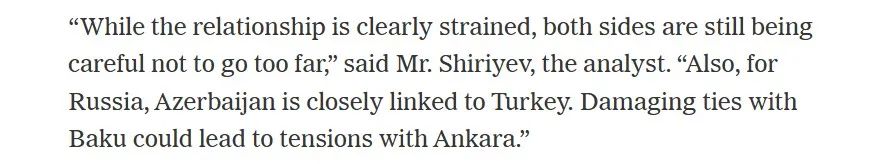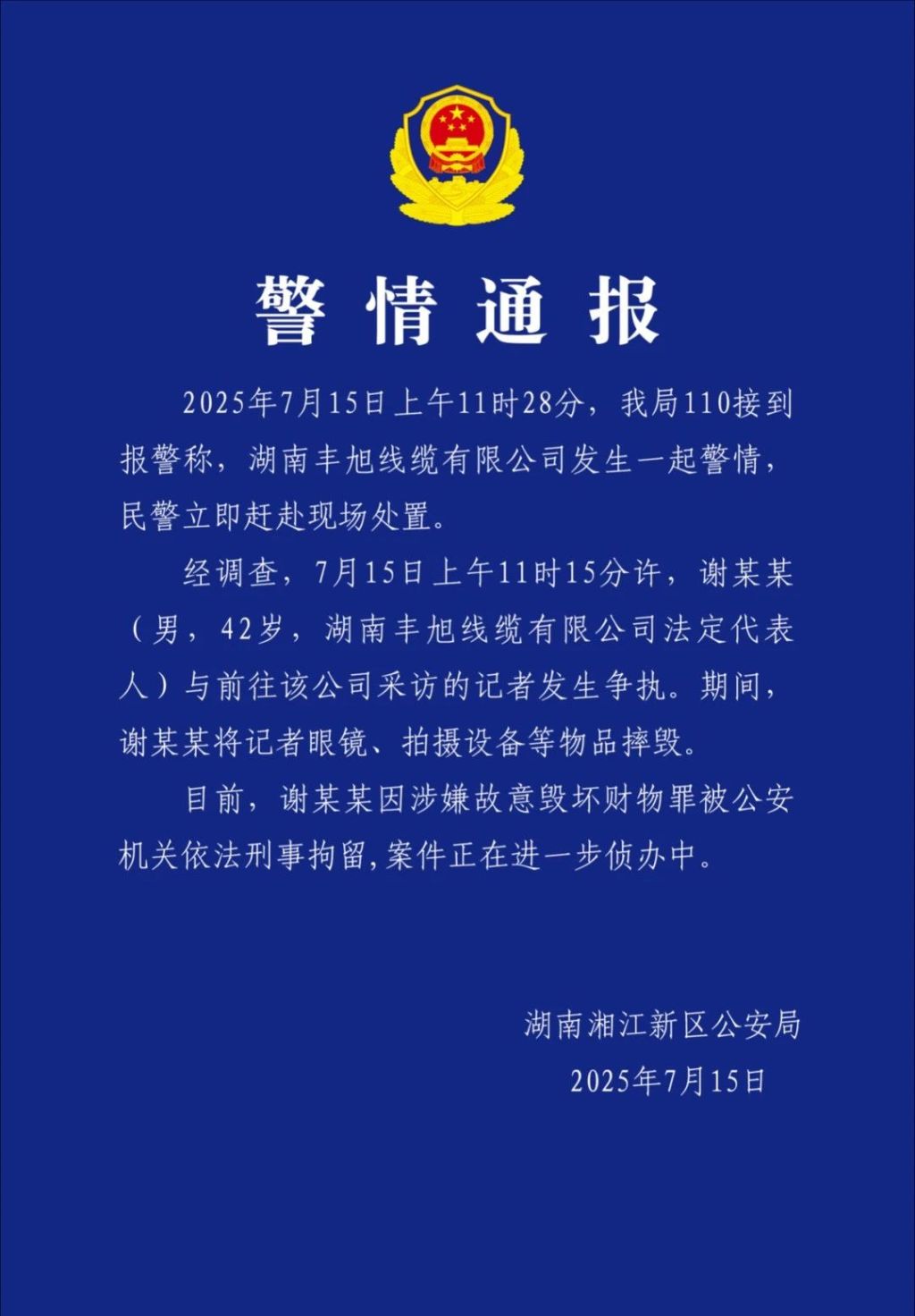记录中国丨从老辈弄潮到“10后”试水,半世纪渡江节里的武汉江水文化
【编者按】
从2016年出发到今年,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共同创立的专业报道品牌实践项目——“记录中国”已走过十年。经过十年的培育,“记录中国”已成为主流媒体赋能名校社会实践的知名IP。
2025年“记录中国”的主题是:“城市不打烊:高质量发展活力密码。”记者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师生将实地探访上海、重庆、安徽合肥、湖北武汉、湖南长沙、四川成都、广东广州等地,走进这些在昼夜交替中始终散发勃勃生机的城市,破解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密码。
今天刊发的是来自“记录中国”湘鄂线的报道《从老辈弄潮到“10后”试水,半世纪渡江节里的武汉江水文化》,讲述的是在武汉这片热土上,老一辈的坚韧与新生代的活力如何在7·16渡江节中交织。方队横渡的每一寸水程,既是训练中智慧与协作的凝聚,更是所有“游泳爱好者”对长江最热忱的告白。

一号方队队员训练。李一钒 摄
武汉,别名江城,长江与汉江在此相汇,滋养出武汉人独特的亲水文化。人与水的羁绊早已融入城市血脉,在烟火日常中静静流淌。
每年7月16日武汉渡江节,是这座江城一年一度的水上盛事。今年是第50届渡江节,分为个人抢渡长江挑战赛和群众方队横渡长江活动。其中,个人抢渡长江挑战赛的约70名参赛选手将从武昌汉阳门1号明口码头下水,在汉阳南岸嘴起水,游程约1800米。
渡江节的一大经典项目——群众方队横渡长江活动,包含来自广东、山西、河南新乡、江苏盐城、湖北孝感以及武汉本地的2000余名泳者,组成27支方队,以队列的形式从武昌汉阳门1号明口码头下水至汉口江滩三阳广场起水,游程约6000米。这一横渡长江的节日,历经半世纪风雨洗礼,早已超越体育赛事范畴,成为武汉人精神的集体记忆。
近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记录中国”团队(以下简称“记录中国”团队)来到武汉,了解渡江节不同方队的队伍训练情况,试图走进这场盛会背后的故事:方队队员们与长江结下了怎样的情缘?江水在武汉人心中,究竟占据着怎样特殊的位置?
“记录中国”团队了解到,本届渡江节方队队员中不仅有年过半百的前辈们,更有不少“10后”的新生力量,不同年龄、身份、背景的参与者怀揣各自的故事与追求跃入江水,以泳姿丈量长江,在这条城市母亲河的怀抱里,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人生渡口”。
对他们而言,渡江不仅是一场运动,更是一种精神。

吴建钧队长指挥货船避让。李一钒 摄
保持方队队形的核心是速度
7月6日,在训练现场,“记录中国”团队注意到,一号方队的队员们穿着泳衣、佩戴泳镜,脸上涂抹着五彩的防晒泥,手里提着被称为“跟屁虫”的亮黄色游泳浮标。
队员们在负责训练与后勤的王匀处签到后,按照方队队列位置集合,一排排、手牵手地从汉阳门的台阶处走下水,下到腰腹深的位置开始游。待游出岸边约50米后集体右转,在岸边起水,再整队下水。在2个小时的训练时间内,如此循环往复大约数十次,不断练习着如何整齐有效地完成下水动作。
据一号方队的耿教练介绍,第50届渡江节与往届相比,有两大变化:一是纪律更严明,要求每支方队至少完成8次训练,每次训练队员需通过官方小程序拍照打卡、签到签退,缺勤两次即取消资格;二是选拔更严格,从3372名报名者中,通过400米静水蛙泳(10分钟内完成)测试,选拔出2400人组成27支方队,每队规模由以往的上百人精简至80余人,对体能要求更高。
两小时岸边训练结束后,一号方队队员自发从汉阳门横渡至汉口江滩,全程约4.24公里,耗时约55分钟。在这约一小时的游程里,一号方队总队长吴建钧操控着一号方队专有的保障船,为队员们指引前进方向。
“压着游!”“向排长对齐!”当队形不稳,吴建钧通过扩音器及时提醒。当方队行至江心,他便将保障船驶至队伍侧翼二三百米处,挥舞起印有“汉口江滩”的红旗,引导大型货船避让。若队员稍显倦怠,他还会绕圈激起浪花,模拟风急浪高的场景,提升队员的适应性。
方队游至武汉港码头水域,一名队员体力不支,双臂抱住岸边货船边的轮胎。吴建钧迅速驾着保障船贴近,伸手将他拉上船休息。“昨晚熬了夜,今天状态差了些。”队员声音带着歉意。吴队长却严厉地说:“一号方队从没有‘被拉上船’的先例。”
王匀介绍道,一号方队队员年龄跨度从27岁到66岁,其中20多人是首次参加渡江节,更有十余人是初次挑战长江。
因此,在方队训练内容安排上,首先要做的是让新队员们克服心理上对长江湍流的恐惧,适应长江、熟悉长江。前几次训练会安排在汉口江滩与武汉港中间宛若“天然大泳池”的半包围水域内,下水之后逆江而上顶着水游。在与江水的不停对抗过程中,队员们能逐渐熟悉长江水流、水情的变化。而后逐渐过渡到自由渡江。
渡江过程中想要保持队形,王匀认为最关键在于“速度”。在江水里,每一排不同位置的队员所感受到的水流状态都是不一样的,需要队员们快速适应并做出调整,控制好自己游泳的节奏。所以,只有当方队整体速度慢下来,才能保证每个队员都能跟上并对齐。
除了水上的保障船,诸如武昌方队等群众方队在陆上还配备有专业的医护人员,提供急救和避暑药品、AED除颤仪等设备,能够处理外伤、抽筋、中暑等突发情况,形成水路双重保障。

一号方队队员以“抬头蛙泳”泳姿渡江。李一钒 摄
以长江水酿就情怀的武汉人
“汉阳门外水初平,忽见长龙破浪行。八十银鳞翻细甲,一声铜嗓裂啖晶。”53岁的公务员陈刚,是汉口江滩冬泳队的“诗人”,每次渡江必赋诗一首。
长江边长大的陈刚,从小看着家中长辈们日日泡在江里,“不能横渡长江,就枉为武汉人”的观念深植于心中。转眼间,今年已是他参加渡江节的第十个年头。当被问及为什么坚持参加了这么多年,陈刚说,“就两个字,信仰。”
42岁的李泳澄是土生土长的武汉姑娘。在江滩的淤泥里捏泥巴,和街坊邻里坐在洗澡盆、旧轮胎里随波漂流,或是泡在湖水里扯着嗓子聊天,长江边的水痕早已刻进了她的童年。今年是她第二次报名渡江,“恰巧碰上50周年,也算是一种心愿。”
在一号方队,李泳澄和另外六位姑娘充当起排头兵。她们不仅要控制好自身节奏,还要时刻关注队伍的整体协调。值得一提的是,在组委会选拔时男女生的标准是相同的。在渡江节,性别差异似乎被弱化了,“游泳爱好者”是众人共同的标签。
江水里的故事,不只属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武汉人。
来自云南红河州蒙自市的唐贸名今年32岁,在外企工作,2012年来武汉上大学,断断续续在武汉扎根有近十年。
谈起参加渡江节的契机,唐贸名告诉“记录中国”团队,自己两年前开始学习游泳,逐渐萌生了挑战户外自然水域的想法。“起初很担心户外游泳有一定危险性,但听说渡江节当天救援队员的数量可能比参赛者还多,我觉得它的安全保障是非常到位的,就想借此机会突破一下自我。”
唐贸名说,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早已习惯了往返长江两岸,在武汉三镇间穿梭往来,可当第一次真正从水面仰望长江大桥时,那份视觉冲击仍让他心头一震。
他提到,相比于泳池清澈见底、脚能踩实池底的水完全不同,长江的水深不见底,流速也快,游到江中央时,他偶尔会涌起一种独自面对浩渺水域的孤独感。但好在“这是一次特别像‘军训’的集体活动”,队友们互相鼓劲、彼此照应。

青春渡方队队员合影。郑淑芬 摄
“10后”接棒,续写渡江新故事
对于更年轻一代的武汉人来说,对游泳技能的习得往往始于正规泳池,所接受的安全教育让他们对长江的初印象多是“风大浪急漩涡险”,甚至会问队里有经验的前辈“长江里会不会有蛇?”。
2010年出生的高俊杰今年刚中考完,在父母的鼓励与支持下,第一次报名参加渡江节。作为九州通方队最小的队员,他时常受到队里长辈们的关爱和照顾。此次渡江节训练中,他感触最深的就是方队团结合作的精神。
为方便喊口号和保持队伍整齐,武汉渡江节的群众方队统一采用“抬头蛙泳”的泳姿,在整个渡江过程中一直抬着头。对于高俊杰这样的渡江新人来说,“抬头蛙泳”不同于以往在泳池中熟悉的自由泳、蛙泳等,需要自己在几次训练中不断自学、摸索。
在训练中,方队里的前辈会教他如何“踩水”,即如何通过同手同脚蛙泳做到在水中不低头、保持平衡,掌握在水流中保持队形的呼吸技巧等,在训练结束后会同他一起回看视频录像帮他分析动作、增进技巧。
事实上,像高俊杰这样的年轻人并非少数。为鼓励年轻人参与传统活动,自2019年起武汉7·16渡江节成立了专门的青春渡方队。
青春渡方队的领队王溯阳介绍,青春渡方队选手最小的14岁,最大的35岁,平均年龄为26.7岁。今年青春渡方队报名人数约800人,最终选拔出80人,报录比达到约10:1。相比普通方队队员400米蛙泳10分钟的要求,青春渡方队要求更高,需达到8分钟以内的成绩才有机会入选。
青春渡方队的口号,相比其他方队更多了几分蓬勃的朝气与独特的锋芒。为了让口号节奏更贴合划水时的呼吸韵律,王溯阳特意换掉了沿用六年的“长江后浪推前浪,青春渡江我最棒!”。今年,这群年轻人将带着新的十六字口号跃入江流:“青春方队,利落干脆。泳者无畏,渡江之最!”

武汉市民在大堤口岸边戏水。邱思宇 摄
武汉的江滩边可见戏水的男女老少。带着两个孩子的家长说,带孩子来长江里泡泡,可以除痱子。跑滴滴的快车司机说,武汉人相信长江的江水能够疗愈身上的小伤口。在渡江节之余,武昌方队的队员们还会因为爱好聚集到一起,用多样形式自发横渡长江,如“V渡”、“N渡”、“W渡”等。
在一号方队训练时,不少人在正午的烈日下,仍在汉阳江滩驻足围观。55岁的许女士作为武汉本地人,虽已看过比这规模更大的训练和往年渡江节的现场,但仍然表示“看不厌。一看到这个运动,就觉得很喜欢。”
江水仿佛已经成为武汉人血脉的一部分,漫延至新的一代,续写下这座城市与这条河的约定。
李泳澄回忆自己牵着四岁多女儿的手走进体育馆的长训班,“就好像当时我父亲牵着我”。她告诉“记录中国”团队,“无论是在泳池还是江湖,游泳教人坚定、平静、豁达、‘泳’往直前面对江湖与人海。”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海报设计 祝碧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