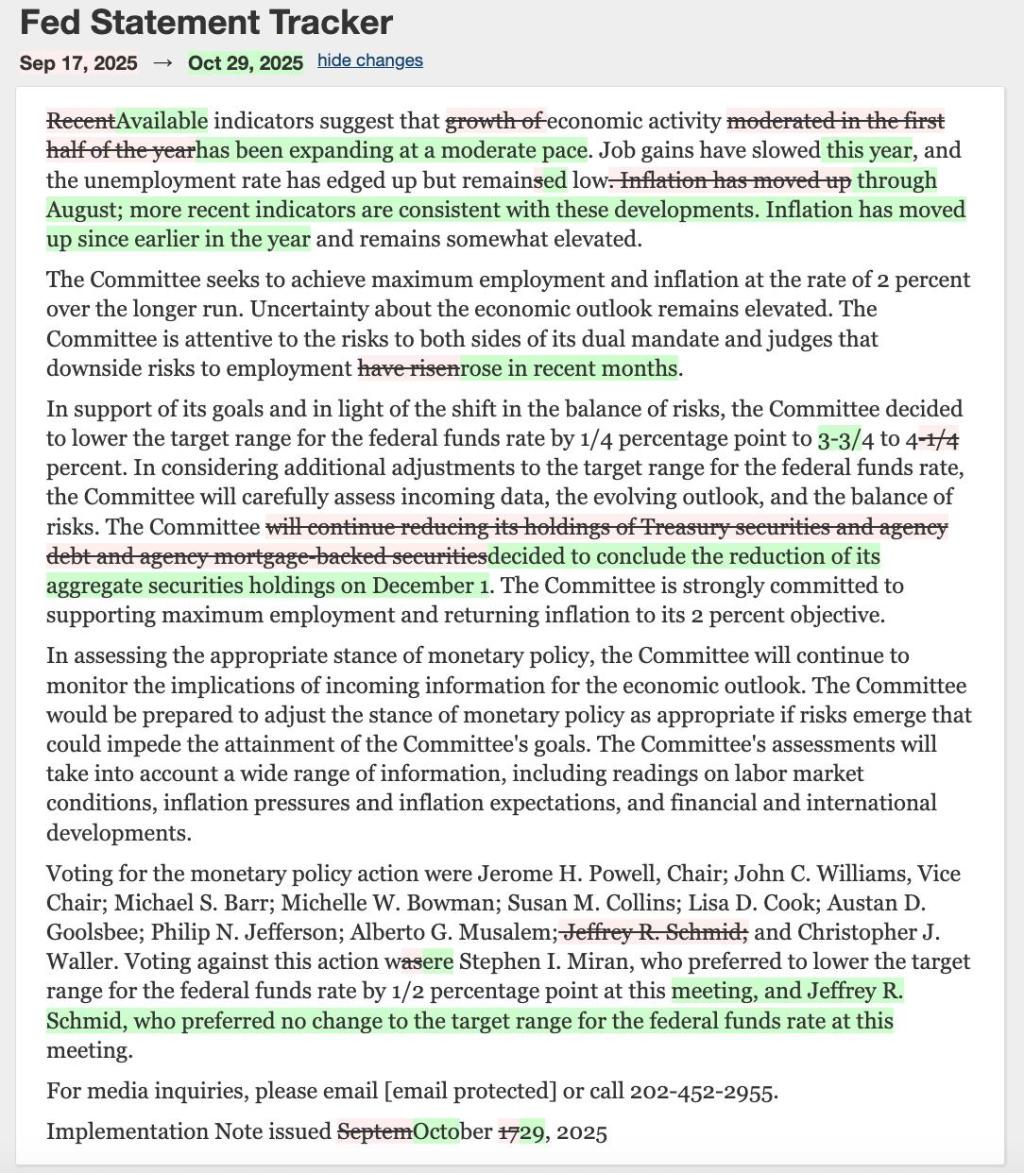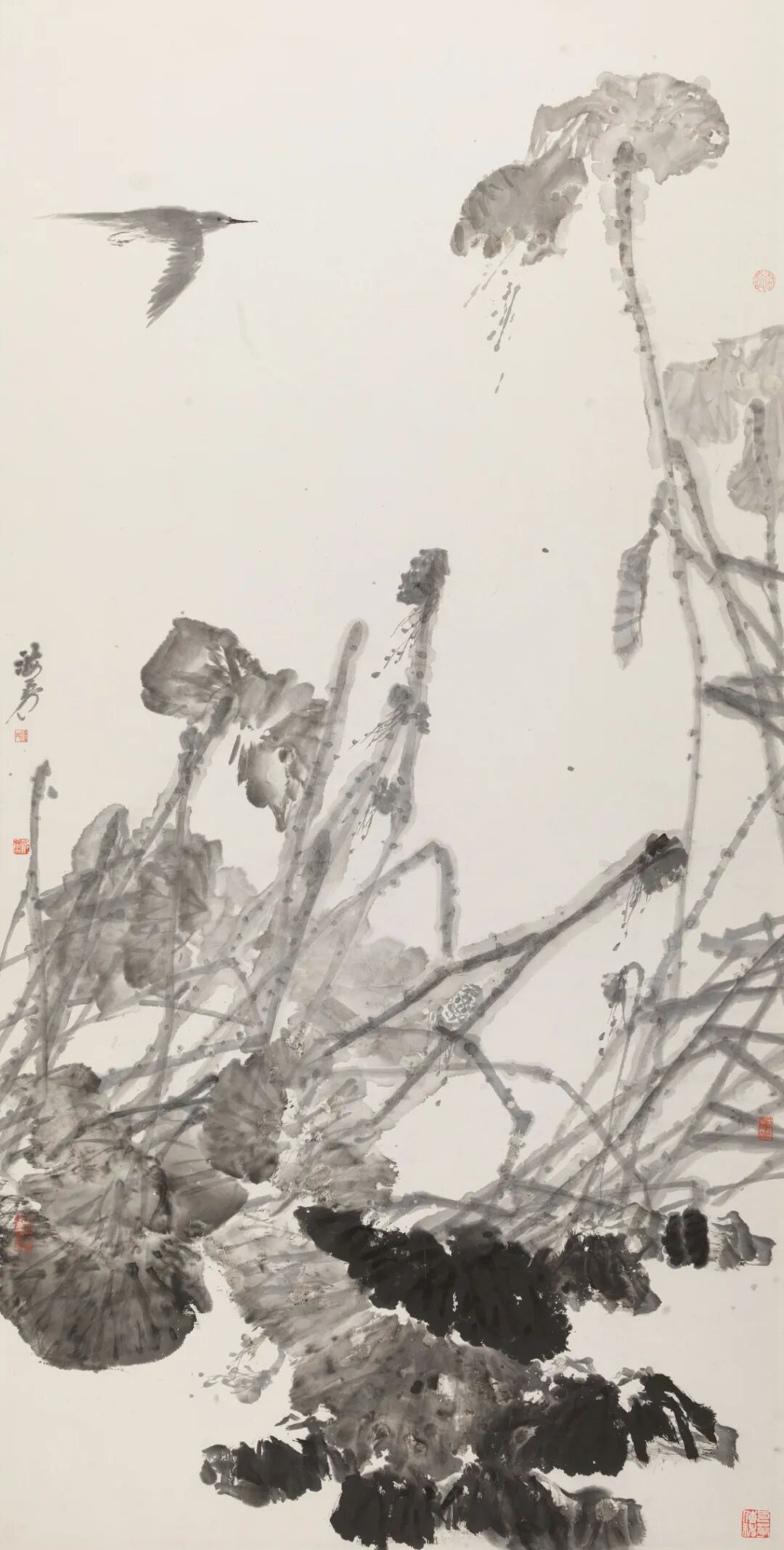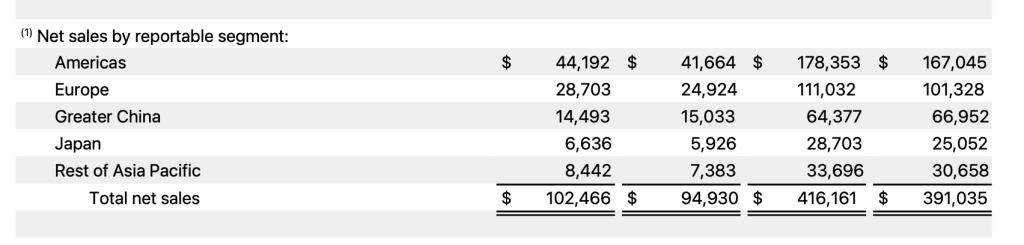老刊物有新变化,《中国作家》创刊40周年
1985年,《中国作家》创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冯骥才的中篇小说《感谢生活》,鲁光的报告文学《中国男子汉》;第二期则发表了王安忆的中篇小说《小鲍庄》和莫言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等等,这些当时领一时风气之先的作品,如今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
10月29日,“《中国作家》创刊四十周年”座谈会举办,作家、原文化部部长王蒙与《中国作家》杂志社历任主编、副主编等分享了自己与这份刊物的故事。

座谈会现场
回顾《中国作家》杂志的四十年——1985 年冯牧主编提出 “百花齐放、质量第一、立字当头、贵在创新”,创刊号便以冯骥才《感谢生活》、鲁光《中国男子汉》引领风气;1991年《中国作家》以“雅俗共赏、曲高和众,贴近时代、关注现实”为新的办刊方针,次年推出巴金、冰心、夏衍、张光年、陈荒煤、王蒙、冯牧等作家的文章,呼应思想解放和社会改革的现实热潮。
如今,《中国作家》刊物已从最初的一本月刊,扩展为当下《中国作家·文学版》《中国作家·纪实版》《中国作家·影视版》三刊并进的刊物群。
《中国作家》主编李云雷介绍,2006年《中国作家·纪实版》的推出是“中国文学期刊史上的一次创新突破”,纪实版聚焦中国变革历程中的重大事件,旨在发表兼具新闻深度与文学温度的作品,“《马家军调查》、《落泪是金》等作品,就以单期全文发表的形式引发关注。”
“2010年7月,《中国作家》再次自我突破,创办影视版,《中国作家·影视版》已成为国内唯一全本刊发电影文学剧本、电视文学剧本、戏剧剧本的专业刊物。相继推出了《建国大业》《辛亥革命》《理想照耀中国》《红船》《悬崖之上》《我的父亲焦裕禄》《县委大院》等一系列剧本。”李云雷谈道。
今年以来,《中国作家》杂志也有了新调整,开设了新大众文艺、当代文艺前沿、新媒介与新大众文艺等新栏目,举办了素人写作与新大众文艺、纯文学观与大文学观、全媒体时代文学与读者的关系等系列座谈会,发起“中国的一日”征文活动。
这些栏目的开设持续激发大众文艺创作的热情,推动普通读者成为时代叙事的参与者,李云雷分享道:“我们开设了诗歌信箱、小说信箱、散文信箱等栏目,从基层作家和自然来稿中发掘优秀作品,我们也开设了大众阅读专栏,注重倾听读者声音,加强与读者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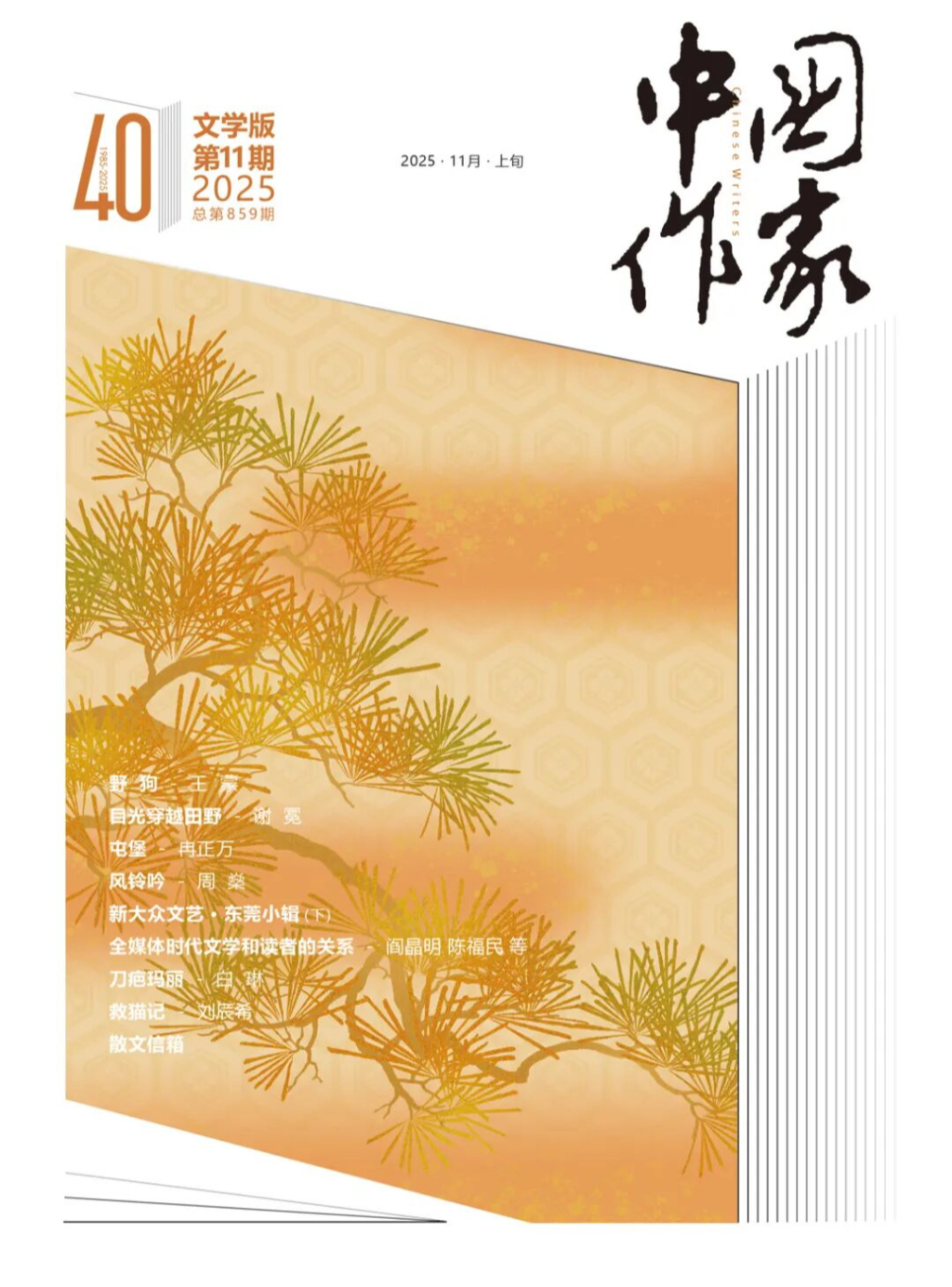
《中国作家》2025年第11期
座谈会中,最生动有趣的部分是作家们分享与这份杂志的故事。
王蒙分享道:“回顾《中国作家》的40年,我个人也想借此机会见到一些多年未见的老朋友,看到他们我想起很多旧事,看到各位身体都很健康,我希望我们能够珍惜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成绩、事业,也能够珍惜,特别像我这样的余生、余年、余热,做一些对文学的发展有益的事情,同时我也还愿意借这个机会来表达我对老一代的领导、作家、作协,像周扬、光年、冯牧等等的怀念和感恩。”

王蒙
《中国作家》原编审徐刚回忆了杂志初创时期的艰辛:“当时杂志部在一个简易棚,冬天上楼梯的时候,如果结冰、下雪,你很有可能会滑倒。”然而正是在这里,诞生了很多优秀作品。徐刚列举了自己编辑的、在当时曾产生很大影响的作品如《中国的“小皇帝”》、《土地与土皇帝》、《中国西部大监狱》等等,编辑这些报告文学,也引领他走上创作之路。
即便年届八十,徐刚依然在杂志纪实版编辑的鼓励下持续创作。他分享了与艾克拜尔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采风和创作的经历,“坐了沙漠车,进入沙漠腹地,我们看到在沙漠公路旁,隔200公尺就有一间小房子,小房子里有一对夫妻,守着一个开关和电视,每隔一个小时勤查线路,滴水灌溉。没有滴水灌溉那些小树、植物不能生活,它使我想起人类面临各种艰苦,人类正在以各种自己的方式来改变这个世界,来创造我们新的生活。”
《中国作家》原主编何建明在贺信中说,在《中国作家》的工作经历奠定了他一生文学事业的发展方向,“这些经历和往事,都在我过往的岁月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由此也对这本杂志充满深情”。何建明认为,40岁的《中国作家》还属于“青春期”的文学阵地,相信一定会越办越好。
作家徐晨亮是《中国作家》的作者,在2020年到2022年之间为《中国作家》杂志的科幻小说专号、《中国作家》之声栏目、青年作家小集撰写过评论与综述。在分享中,他谈道:“《中国作家》杂志的创刊主编冯牧先生在编辑部内有一个特殊的称号,叫做老船长。我由此想到在当代文学史上独具风骚、各领风骚的那些著名的刊物,都像一艘艘大船,几乎都有一位或者几位为其航程确立坐标的老船长,如巴金、靳以之于《收获》,秦兆阳之于《当代》,冯牧之于《中国作家》。40年来《中国作家》从文学巨轮到文学舰队的航程,也正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涌动的热潮与一波波激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