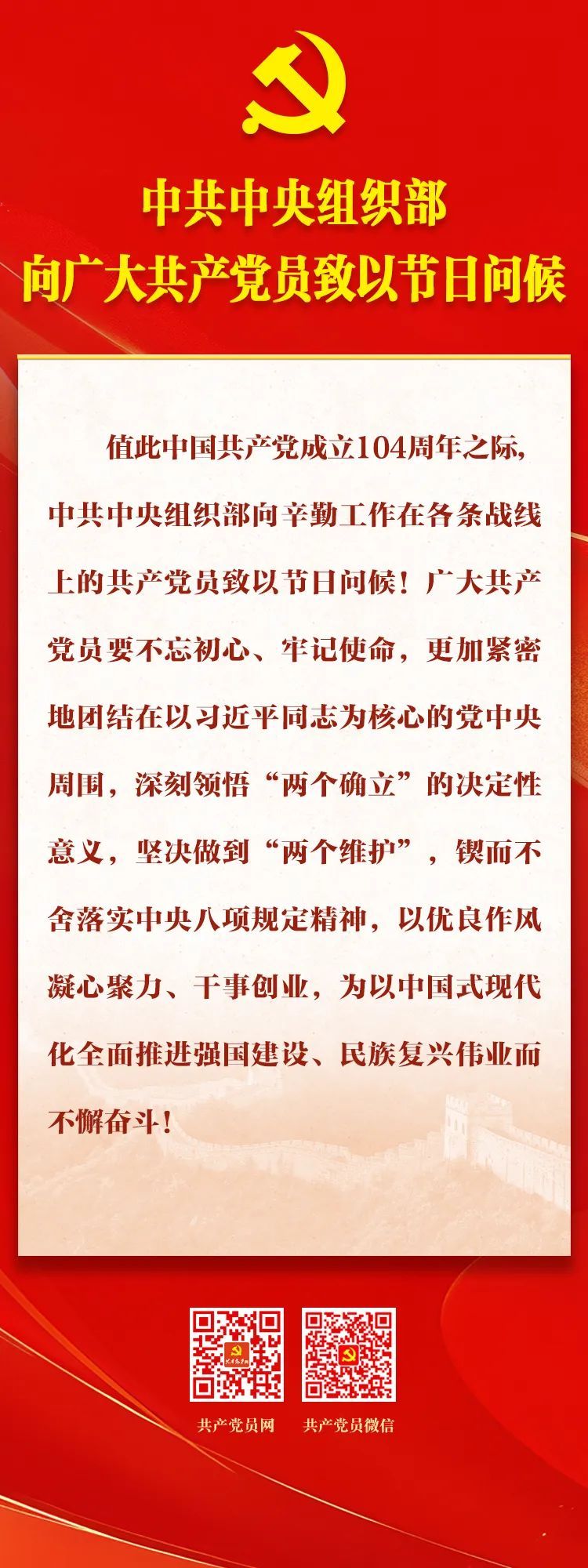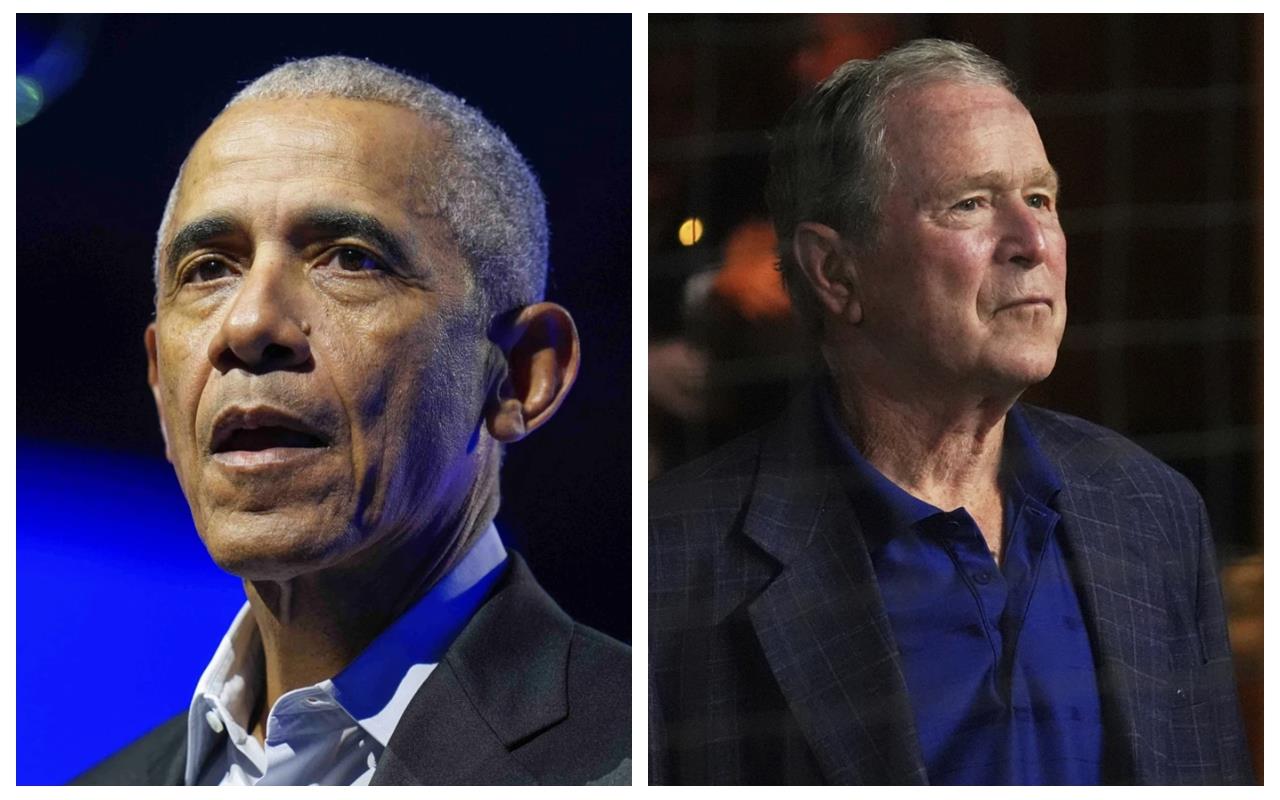郎朗王健史依弘张军金承志金郁矿,听听他们和东艺的故事
2004年12月31日拉开演出大幕,2005年7月1日正式对外运营——20年前,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在浦东丁香路绽放,逐渐成为世界交响名团的大本营、上海演出文化的金名片。
20年来,这里迎来送往过无数名家大师、新人新秀,而每一个艺术家都在这里留下过他们的动人故事,绽放了属于他们的艺术青春。
“这里来过太多大咖,我必须弹好”
“东艺不只是老友,更像我的家人。”郎朗说。
2004年12月31日,22岁的郎朗以一曲《黄河》,为东艺亮声,“我们像两个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准备一起闯荡世界。”二十年间,郎朗与多支交响劲旅牵手,有些演出很刺激,甚至差点“玩命”。
2012年,郎朗与捷杰耶夫的牵手,堪称惊心动魄。捷杰耶夫钦点郎朗,担任“普三”的钢琴独奏。演出前,郎朗以为有充足排练时间,结果只试了开头5分钟,捷杰耶夫大手一挥,决定直接演。
“5分钟?!我的心疯狂打鼓,差点跳出来。”郎朗弹得热血沸腾,捷杰耶夫指挥得风驰电掣,乐团的声音像西伯利亚的暴风雪席卷全场。弹完后,他长舒一口气,“太刺激了,比坐过山车还过瘾。”郎朗当晚睡了一个好觉,“和姐夫合作,要有一颗大心脏。”
2020年12月9日,东艺见证郎朗艺术生涯的重要转折,在上海首秀巴赫《哥德堡变奏曲》。
这部巨作像个迷宫,越弹越深,根本看不到尽头。成年后,他无数次想公开演奏,却总在最后一刻退缩。38岁时,郎朗终于突破自我,上海乐迷见证了一个全新的郎朗诞生。
“坐在舞台中央,我就像在葡萄园里收获艺术的果实。”郎朗点赞东艺音乐厅的葡萄园式设计,声音像月光一样均匀洒在每个角落,连最轻的触键都能传到最后一排,整个音乐厅变成了巨大的共鸣箱,所有人的心跳都在跟着音乐走。
“我在这里尝试过最疯狂的合作,也在这里找到最安静的自己。”每次来东艺,郎朗都会把状态拉满,因为这里来过太多大咖,还有最有品位、最为挑剔的观众,必须弹好!

郎朗和捷杰耶夫
“我很幸运,见证并成为其中一员”
2004年的跨年夜,和郎朗一起为东艺揭开面纱的,还有36岁的王健。那一晚,他奏响老柴《洛可可主题变奏曲》,用动人琴声,送上祝福。
王健从此成了东艺常客。2010年,他与伦敦交响乐团共演肖斯塔科维奇《第一大提琴协奏曲》, 他记得自己很满意,“拉得出彩的音乐会,我一定会记住。”
2012年,他又与悉尼交响乐团合作德沃夏克的“思乡之作”《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返场时,他特别加演陈其钢为八把大提琴改编的《我和你》,琴声仿佛化作莎拉·布莱曼的歌声。
“为家乡的观众演出,我更紧张,因为肩上的责任更重。”王健说。
2023年4月28日,阔别三年的王健,选择东艺作为归国首场独奏会的舞台。音乐会开票两小时即告罄,加座也被抢购一空,堪称那一年最著名的“文化事件”。
多次返场后,他转身面向舞台后方的观众,加演肖邦《g小调大提琴奏鸣曲》第三乐章。这一举动刷屏朋友圈,被乐迷称为“最动人的背影”。
“大提琴可以坐钢琴旁或钢琴前,试音后,我发现钢琴前声音更佳。”问题随之而来,钢琴琴盖打开后,王健的身影被彻底挡住,“花钱来听,连人影都看不到,很对不起他们。”于是,他转身加演,弥补遗憾。放眼他遍布全球的演出足迹,这也是只属于东艺观众的“福利”。
“作为幕后的巨大推手,东艺推动了古典音乐在中国的扎根与繁荣。”在他看来,东艺的20年,也是上海古典音乐行业突飞猛进的缩影,映射着上海从文化追赶到文化自信的历程,“我很幸运,能赶上这段历史,见证并成为其中一员。”

王健独奏音乐会
“每一次演出,都像一场考试”
“东艺很难征服,每一次在东艺演出,都像参加一场考试。”指挥金承志说。
2005年,东艺正式运营时,金承志还在读高二。这些年,他频繁带领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做客东艺,既有辞旧迎新的跨年音乐会,也有《白马村游记》《罗刹国纪》等大作品。2021年年底的那场跨年音乐会,甚至位列东艺“最难忘演出TOP20”榜首。
“东艺很直白,你的好、你的瑕疵都会完全展现出来。如果不好好排练,不把技术练到位,你会暴露得很彻底。”
金承志还发现,东艺的观众既热情又专业,能够区分“特别好”和“还可以”,如果是前者,他们会不吝啬掌声,甚至会激动地站起来,“东艺的观众像一面镜子。你做了多少,他们就回馈多少,既铁面无私,又充满温情。”
有一次唱到《想要的一定实现》,他问观众的愿望是什么,一个小孩脱口而出“希望奥特曼存在”,一位大人说“希望全世界一起跳舞”,全体观众开始欢呼,台上台下一起唱歌跳舞,工作人员也加入进来。这个瞬间,让他难忘至今。
还有一次唱合唱剧《罗刹国纪》,他们在台上立了一块和管风琴一样高的大屏幕,“不是每个场地都愿意让你改变环境,但东艺允许改变,这种支持和包容非常难得。”
对金承志和彩虹合唱团来说,东艺既是考场,又是摇篮,他们所有新作的首演几乎都在这里发生,“它像一个温柔但严肃的朋友,会给你压力,但会一直认真听你说话。最好的朋友是不急于表达自己的。东艺就是这样一个人,不喧哗、不张扬,你知道它一直在那里,等着你说话,等着你拿出作品。”

金承志和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
“只要你们敢来,我们就敢演”
“我一开始是台下的乐迷,后来成了台上的指挥。”对“00后”指挥金郁矿来说,东艺也是他的梦想起步的地方。
14岁,金郁矿开始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学指挥。刚到上海,这位少年就迫不及待去东艺看演出了,每年至少要去四五次。
印象最深的是2017年,西蒙·拉特率领柏林爱乐乐团来访,那也是他担任艺术总监的告别之旅。为了买到80元的学生票,金郁矿连夜排队。“特别幸运,我拿到的正好是面对指挥的学生票。”金郁矿直面西蒙·拉特,得以亲见大师如何带动乐团,让激情和音乐融为一体。
还有一次,他排队去听捷杰耶夫的访谈,“姐夫”给了年轻指挥很多干货满满的建议。那场访谈在东艺333座的演奏厅录制,没想到若干年后,他也踏上了那个圆形舞台演出。
2022年12月24日,圣诞夜,金郁矿带领新古典室内乐团,新鲜亮相。他已经忘了曲目,但仍然记得观众们热烈的欢呼,大家一致认为,那是他们年度最棒的一场演出。演出结束后,他兴奋地对观众喊话,“只要你们敢来,我们就敢演!”
这是东艺“未来大师”系列的其中一场音乐会,走过18年,“未来大师”始终在为新星和新秀提供舞台。
这也是金郁矿毛遂自荐得来的演出机会。当时,他正在为新古典室内乐团寻找演出舞台,在东艺官网,他找到了曾任节目总监的刘爱华电话,直接打了过去,“接到电话时,她很讶异。”那次演出,金郁矿切身感受到东艺对年轻人的扶持和体贴。
未来有机会,他希望,能带着一支真正的交响乐团,去隔壁1953座的音乐厅演出,“希望梦想成真!”

金郁矿和新古典室内乐团
“有一个品牌来推广戏曲,很难得”
“第一次走进东艺是20年前。我们当时在想,这么偏远的地方,有人来看戏吗?没有想到幕一拉开,观众很多。”梅派青衣史依弘回忆。
后来,史依弘的京剧身段频现东艺,“东艺声场出色,建筑很有特点,剧场管理严格,对演员来说,这是很舒服的一个地方。”
2012年,史依弘向昆曲跨界,与“昆曲王子”张军搭档,连演三场《2012牡丹亭》。在过去,昆曲是京剧演员必修的课程。对史依弘来说,昆曲《牡丹亭》是自己必须攀越的山峰。她还记得,现场来了很多不看昆曲的观众,年轻人扎堆。
这些年,东艺一直在主动地、积极地推动戏曲演出。“东方名家名剧月”更是对戏曲推广举足轻重,让众多“小白”对戏曲有了初体验,积累了一大批戏曲迷。
史依弘参加了近10届“东方名家名剧月”,把拿手的、看家的大戏都搬来了。
2025年,“东方名家名剧月”迎来第15届,开幕两场演出是史依弘“双戏双派”的巅峰对决—— 梅派经典《霸王别姬》和程派大戏《锁麟囊》。
这两部京剧也是史依弘久演不衰的作品。其中,《霸王别姬》是她宗梅派之后最常演的剧目,《锁麟囊》则是她2011年开始“跨界”尝试的程派名作,她将“梅韵程腔”融为一体,至今仍然广受欢迎。
“东方名家名剧月”让传统的戏曲焕发出时代的新生。不仅仅是京剧、昆曲,史依弘还在这里看到了越剧、沪剧、锡剧、滑稽戏等剧种和地方戏,百花齐放,“有这样一个品牌来推广戏曲,很难得!”她也希望,自己在专业领域继续进步,每一次都让观众看到更有生命力的戏曲和人物出现。

史依弘《牡丹亭》
“一个戏要想成长,需要反复演出”
“我第一次和东艺邂逅,是因为我向往了很久的柏林爱乐,为这里开台做表演。”2005年,和世界最顶级乐团的同频共振,为张军后来和西方古典音乐对话,埋下了一颗种子。
2008年,正逢中国戏曲市场最艰难时期,“东方名家名剧月”横空出世。上海昆剧团带着《牡丹亭》和《十五贯》亮相,34岁的张军惊喜地发现,戏票都卖得一张不剩,备受鼓舞。他还观察到,2/3的观众是18岁至35岁的年轻人,“这给我们的昆曲推广很大启发,昆曲也要现代化,必须聚焦年轻观众。”
2019年,独角戏《我,哈姆雷特》登陆“东方名家名剧月”,以传统昆曲的四功五法演绎《哈姆雷特》故事内核,用汤显祖的语汇为莎士比亚名著编写东方版本。张军一人分饰多个角色,涵盖生、旦、末、丑4个行当,说起普通话、韵白、苏白、英语4种念白。
当代昆曲《春江花月夜》,一票难求。张军曾经多次带着这部爆款,亮相“东方名家名剧月”,“很温暖,很受鼓舞,一个戏要想成长,需要反复地演出、不断地演出。”2025年,他又带着“十周年特别版”冲回熟悉的舞台,庆祝这个品牌走到第15届。
在这方舞台,张军大胆探索着昆曲的各种可能。他希望,昆曲可以走进当下的生活中,真正地活着。
“传统艺术的艺术家也要对未来充满好奇心。”张军说,走过六百年的昆曲赶上一个全新的时代,AI等新科技又扑面而来,“传统艺术面临着新的挑战,但我更觉得它获得了一个新的机遇。我们始终要走在时代的前沿,去观察,去实践,让更多年轻人和昆曲一起共同成长。”

张军《春江花月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