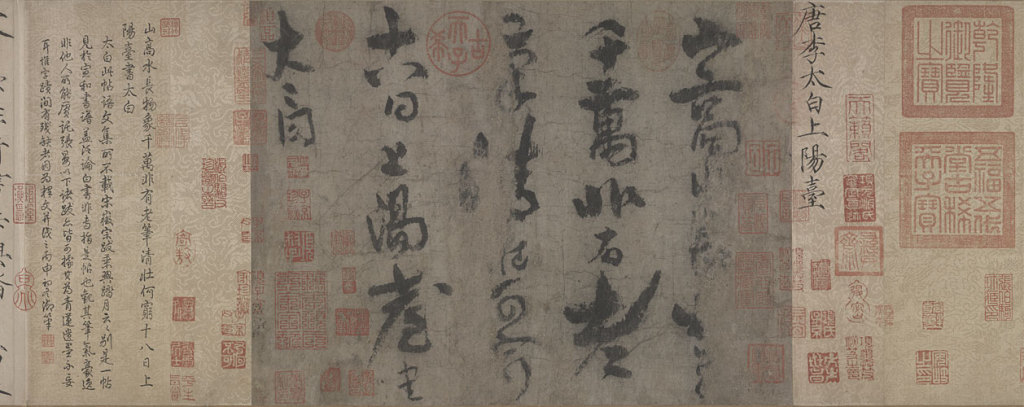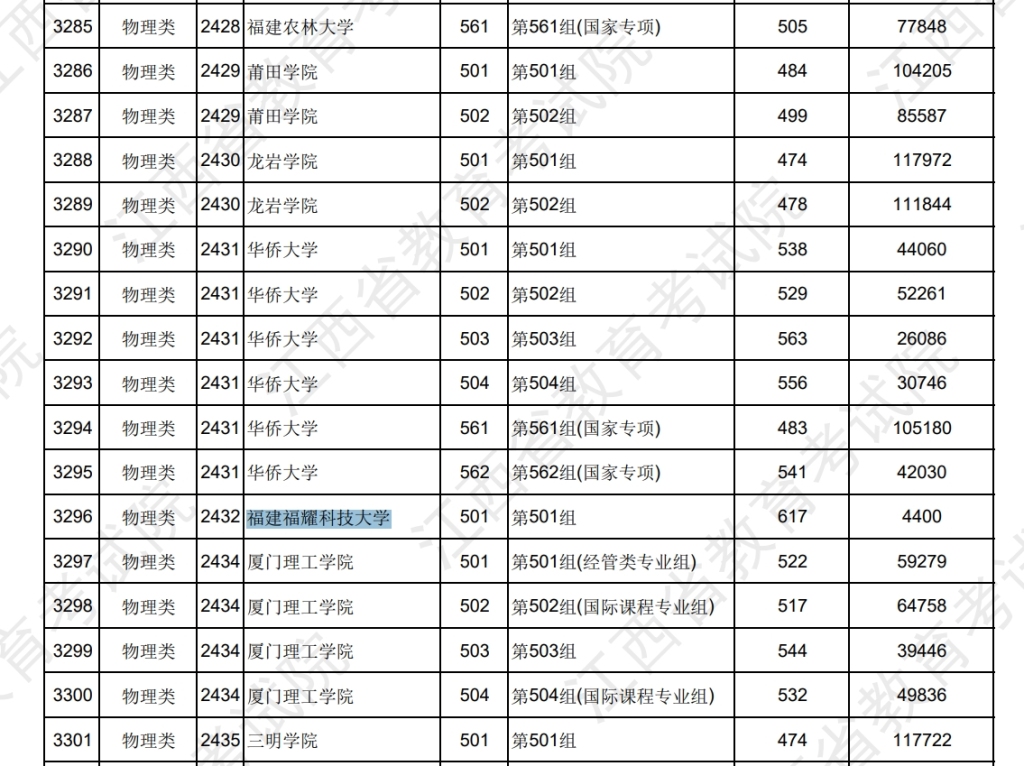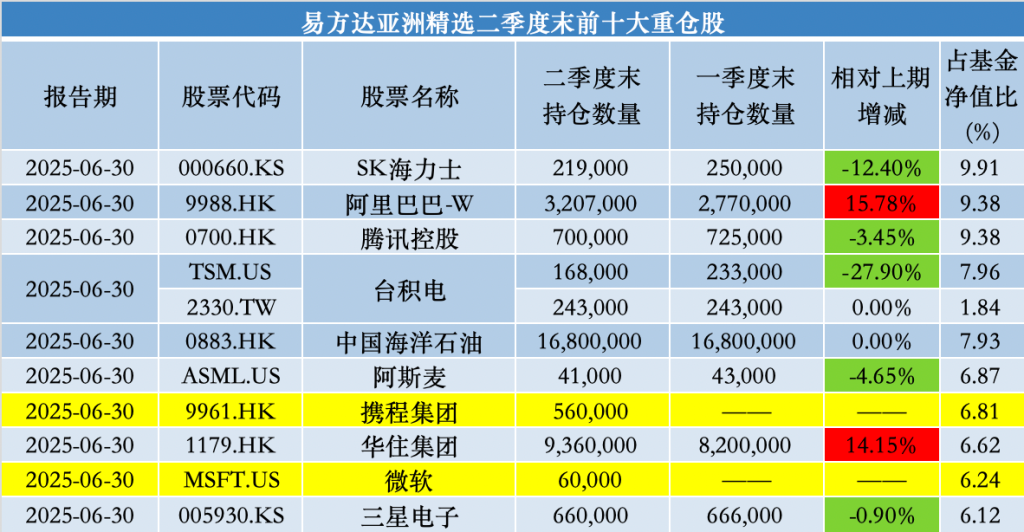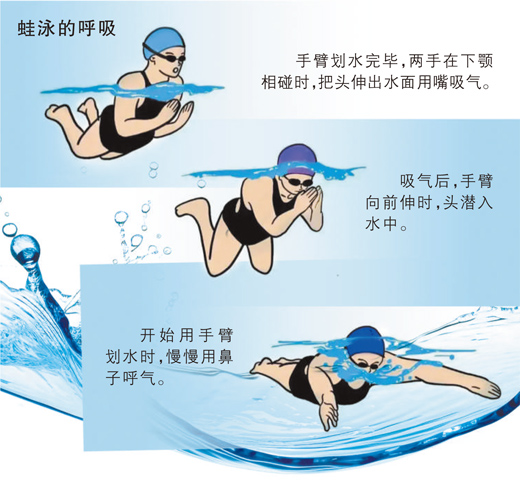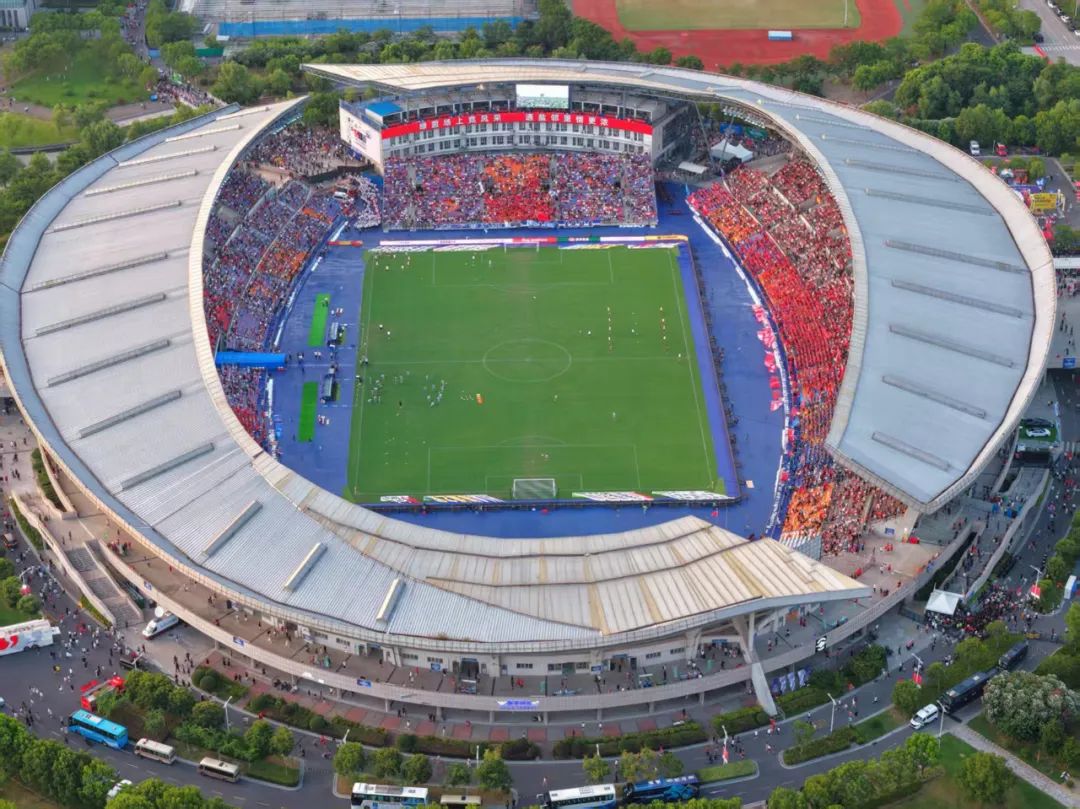在对正义做判断和为实践定向时,确定那个理想是什么至关重要
【编者按】
在《多元社会中的正义》一书中,当代政治哲学家杰拉德·高斯对追求完美正义的理想理论提出质疑,并通过构建开创性的道德思考框架,发展出一套更加契合现代社会特质的正义理论。高斯提出:只有在价值观念多元共存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才能真正把握理想正义社会的样貌,他系统阐释了“多元开放社会”这一核心概念,并为其道德结构进行了有力论证,高斯强调,正是通过不同理想的碰撞与对话,个体才能更清晰地认识自身所秉持的正义观念。本文摘自该书第一章,经译林出版社授权发布。
正如我所强调的,我们还会在接下来的章节中看到,这种多维度的、通过理想来定向的政治哲学进路很复杂。我们需要知道各种社会状态的正义,还要知道这些社会状态与理想的接近度(它们是不同的、关联性不强的正义维度)。一种避开这些复杂情况的方式是阿马蒂亚·森的方式:解除比较性判断对理想的依赖,从而使理想变得没有必要。这样,我们就只需要知道各个社会状态的相对正义。相反的简化策略是仅仅描述理想的正义状态或条件,而不去讨论不太理想的情况下的正义。这里并不存在什么不一致;可能所有不太理想的状态都是不可通约的,或者相同的(除了赢家之外每个人都同样是输家),因此无法根据在严格意义上比其他状态更好或更差进行排序。说这种理论毫无用处未免太过分了,但一种不能描述除顶部理想以外的任何社会状态的政治哲学,在帮助整理我们面对的正义选项时用处不大。这就好像,我们对理想的正方形有了一个明确观念,但却不能说出三个图形,即一个正方形、一个长方形和一个圆形,哪一个最接近它。
或许有人认为,只有展现完美正义社会的那种政治哲学才是有价值的。这一论点似乎会被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所具有的历史意义所支持。然而回想一下,他在美国说了一连串关于正义与和谐的梦想,将其作为希望和信念的来源,帮助听众克服疏离感和痛苦,这是由于这些听众当下对正义的实际要求遭到了蔑视和憎恨。这个演讲并非以纯粹的梦想开头,而是宣称美国的建立者发行过“一张期票,而每一个美国人都要将它代代相传。这张期票是一个承诺,即所有人对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会得到保证”。所以,金向游行者宣告:“我们来兑现这张支票了,它会给我们宝贵的自由和正义的保障。”一个完全满足全部正义要求的世界,甚至一个彻底实现美国建立者承诺的世界,或许是一个达不到的理想。我并不是说一种有用的理想理论必须设定可以达到的理想。但金还是坚持主张理想为当前的政治要求定向。虽然金要求兑现的支票远低于它所承诺的价值,但关键点在于理想能在我们这个显然非理想的世界中为政治要求定向。金的“梦想”不是我们从中醒来的一场梦,即一场关于完美社会的梦,与在非理想的社会世界中追求正义无关。我说的“做梦”是另一种与此不同的理想正义观,它不仅提出一个达不到的理想,而且愿意承认这种理想可能且经常与改进非理想状况下的正义完全无关。
脱离了对那些我们身处其中的,以及我们或许向其移动的社会世界的正义判断,理想正义的纯粹梦想可能会刺激人们或给人希望,虽然这些梦想也可能导致失望、绝望和愤慨。如果没有任何方式能将梦想与我们社会世界中出现的问题和疑问联系起来,那么从完美正义世界的梦中醒来并面对我们社会的现实就极有可能会使对正义的思考迷失方向。我们或许认为这是超现实主义的正义,它企图在我们的世界中描绘一个我们无法真正理解的梦想世界。一个人对正义有多少“了解”,与一个人在实际和相近的社会世界中生活而产生的正义问题之间是割裂的。大卫·米勒(David Miller)说得很对:从这种观点来看,“在政治哲学所捍卫的理想与人类生活的实际状况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除了对此表示哀痛之外,政治哲学别无可为”。大卫·艾斯特兰德持有这样一种“无望的”正义观:
考虑一种理论,它要求个人和制度恪守能力所及的标准,但却没有理由相信他们将会到达那个标准……假如这些标准是不可能达到的,那么这种理论就是道德上的乌托邦,但是根据假设,这些标准并非不可能达到。很多可能的事情永远都不会发生。那些被构想出来的理论仅仅制造出了事情应该怎样或可能怎样的幻象,即便承认它们不会发生……至此,我认为这种理论不存在可见的缺陷。就我们所说过的一切而言,使人们和制度恪守的标准可能是合理且真实的。人们本可以但偏偏不去遵守它们,这是人类的缺陷,而不是理论的缺陷。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词,我们可以称这种理论为无望的现实主义。
我已经说过,这样的理论毫无用处。艾斯特兰德也承认这一点:“不切实际的理论有什么价值不是我要讨论的重点……我的重点在于,一种无望的规范性理论或许正是正确的理论。不可否认,不是所有真理都具有很大价值。电话簿就包含很多相对不重要的真理。然而,我们正在谈论有关正义的真理,而且我倾向于认为它的重要性更大,但也许这只是因为我们原本就认为它是有实践价值的。”让我们像正义“要求”的那样行动很可能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如果考虑到自己的不完美,询问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的时候,这种正义“或许没有一点实践价值”。艾斯特兰德似乎很欣赏这种可能性。他列举出大量“阿尔夫应当做X”的情况,即使对于阿尔夫而言做X是极其不明智的,因为他有可能失败,并且比起追求一个更“现实的”备选项,他在尝试做X的过程中容易导致更糟糕的后果。但是,艾斯特兰德的论点甚至更为激进:它强调,在给出一些理由去寻找(不是现在就是将来)实现X的方式这一层面上,知道应当做X对于实践无关紧要。因此,应当做X的知识可能“没有一点实践价值”。
像其他人一样,艾斯特兰德借用了利普西(Lipsey)和兰开斯特(Lancaster)的“次优理论”。根据这个理论,u是帕累托有效状态,并不意味着与u差不多的事态就差不多是帕累托有效的。因此乍一看,想要接近理想的目标似乎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我们不可能达到理想,那么接近它对于实现正义可能毫无用处。因此,知道理想正义更像是知道深奥的数学定理,而不是知道了行动指南。
大体上说,艾斯特兰德的观点是概念性的:一种正义理论可能是正确的理论,即使它没有实践价值。很多人否认这一点,这当然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然而,裁决这个争论并不是我所关心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把它置于一旁。我最关心的是分析一类理想理论,根据这类理论,在对正义做出相对判断和为实践定向时,确定那个理想是什么至关重要。但是,即使不参与这个争论,我也在想,在它的悠久历史中,政治思想家经常被乌托邦的理想所吸引,因为他们相信这些理想确实有助于为我们不够理想的判断定向,并且确实为如何思考社会和政治变革提供了建议,就算这一变革从目前,甚至不远的将来看来都是不可行的。这不是一个概念性的真理,而是一个关于政治哲学中乌托邦传统的真理。正如我强调过的,把乌托邦思想等同于无望的、不可实现的理想,是对乌托邦思想的一种误解:由此根本得不出,抵制“无望的乌托邦”的人就是“乌托邦恐惧症患者”。我们很难不对纯理论哲学中的一种趋势感到担忧,这种趋势以严重背弃上述传统的方式探索“真正的正义”和“乌托邦”,坚决捍卫这种理论可能毫无用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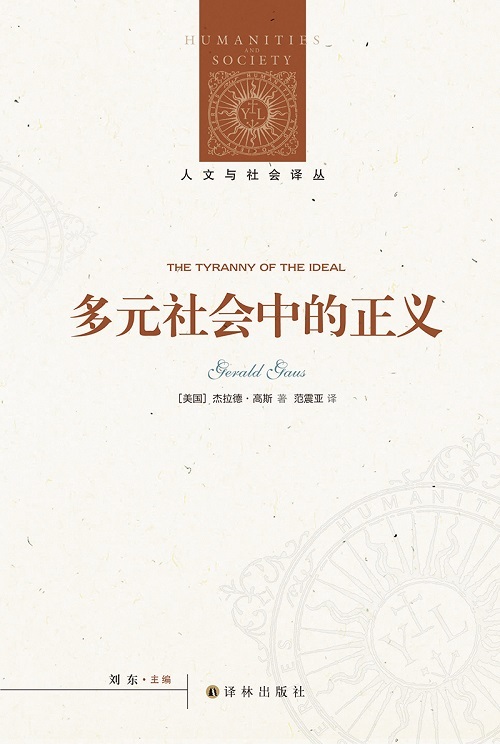
《多元社会中的正义》,[美国]杰拉德·高斯著,范震亚译,译林出版社202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