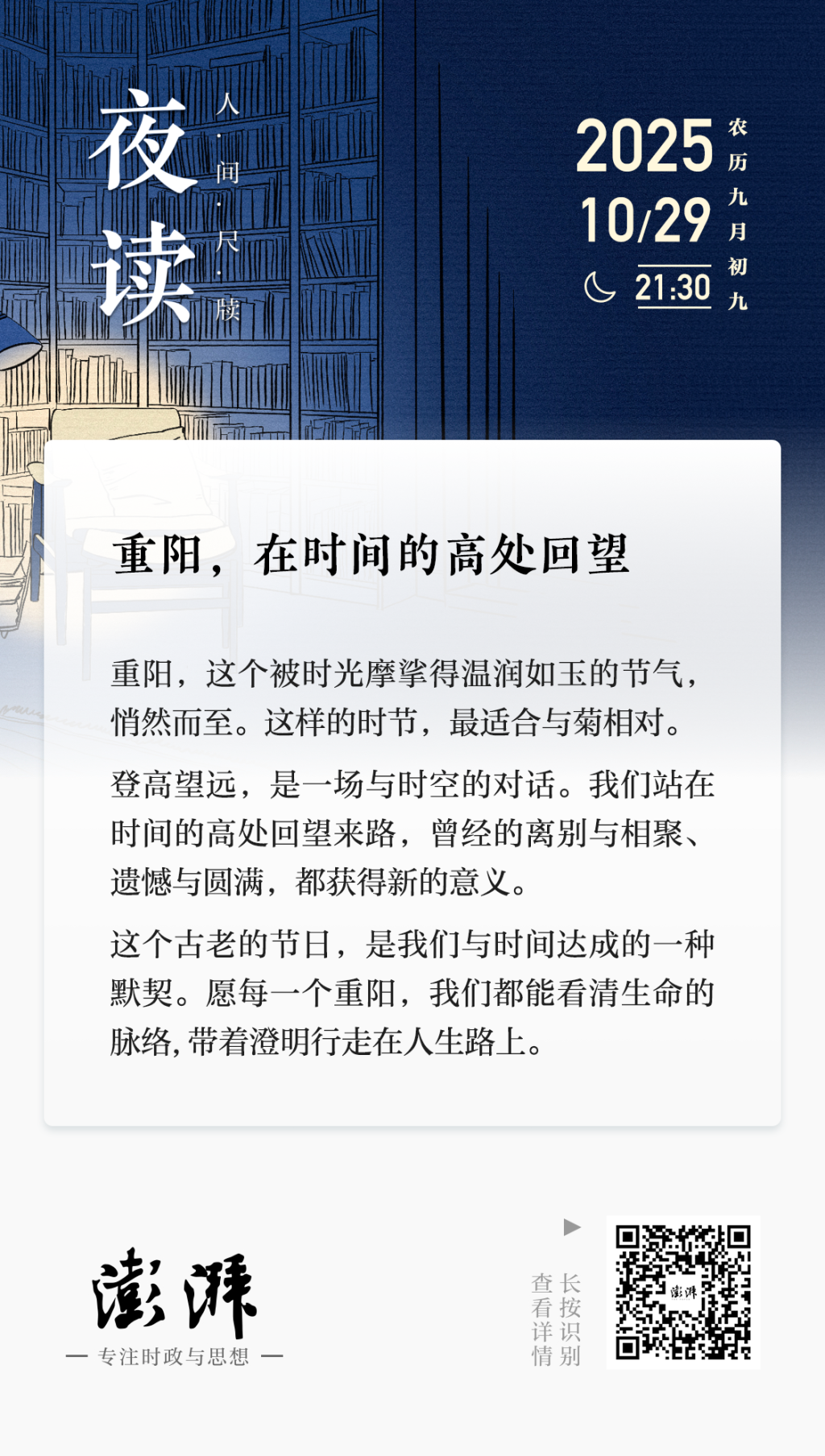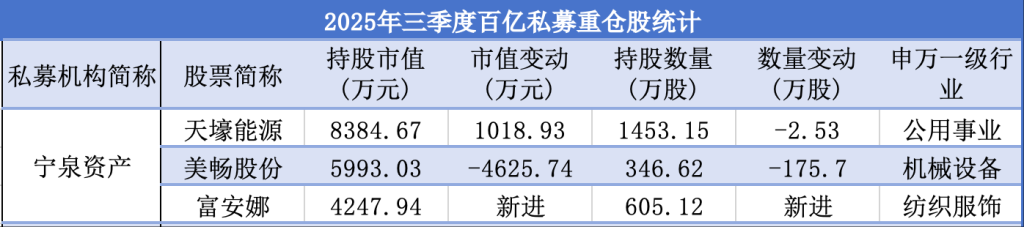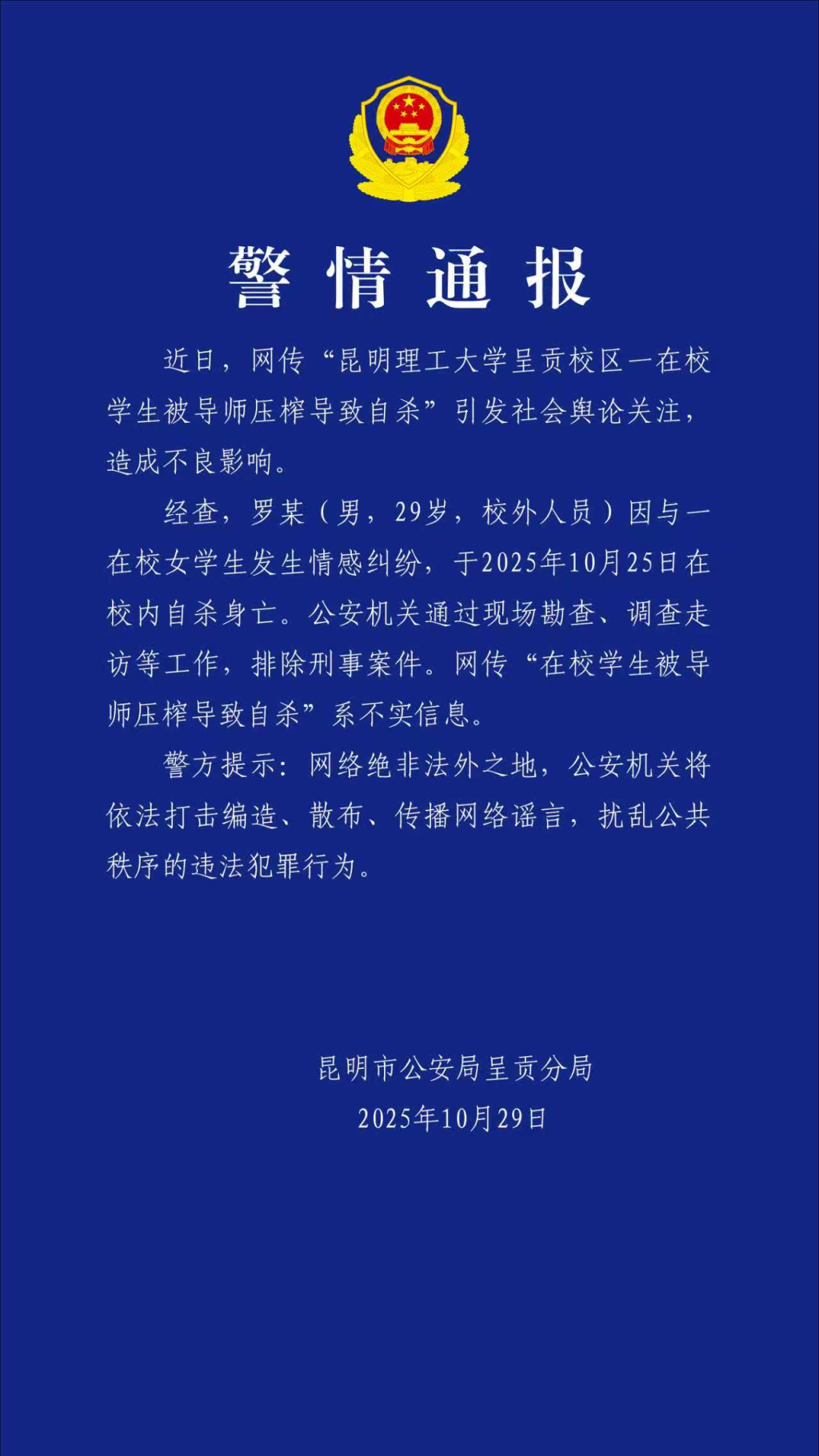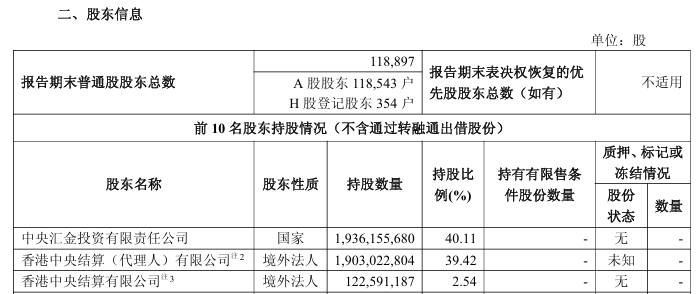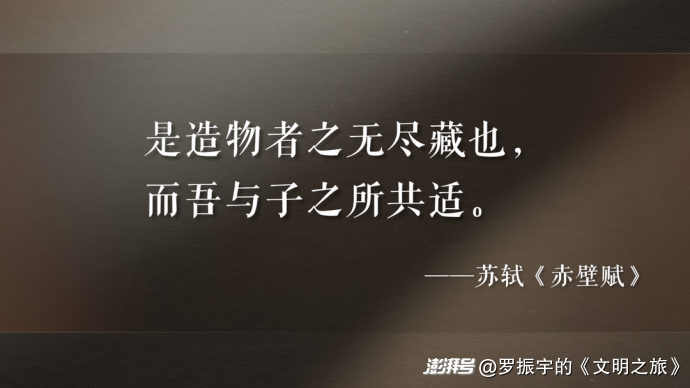夜读|重阳,在时间的高处回望
深秋的日光斜斜地穿过梧桐叶隙,在青石板上洒下斑驳的金黄。重阳,这个被时光摩挲得温润如玉的节气,总在不经意间悄然而至。天空是经过夏日喧嚣沉淀后的碧蓝,澄澈如一块巨大的琉璃,偶尔有雁阵掠过,翅膀划破云影,留下悠长的鸣叫在天地间回荡。
这样的时节,最适合与菊相对。
晨露未晞时,园中的菊已悄然绽放。不是春日百花的喧闹,而是独属于秋的沉静——金黄色的花瓣层层舒展,在微凉的空气中凝成一片寂静的光晕。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大抵便是在这样的晨光中获得的。
细看那菊,瓣如丝绦,蕊含清露,在疏疏落落的秋风中保持着自己的姿态。它的香气不似桂花浓烈,而是幽幽的、淡淡的,如远山传来的古琴声,需要静心才能品味。
赏菊的人,心也该是静的。在这茫茫俗世里,我们习惯了追逐与奔忙,唯有面对这一簇秋菊时,才忽然明白何为“人淡如菊,心素如简”。菊花不争春色,不慕夏荫,只在万物开始凋零时独自开放,这何尝不是一种生命的智慧?它的美,不在形态,而在风骨;不在颜色,而在气节。白居易曾叹:“耐寒唯有东篱菊,金粟初开晓更清。”这份历经风霜而愈发清朗的品格,或许正是重阳给予我们的第一重启示。
午后,适合温一壶菊花酒。
酒是陈年的糯米酒,浸着新摘的杭白菊,在青瓷酒壶中微微荡漾。斟一杯,琥珀色的液体泛起细小的涟漪,菊花的清芬与酒的醇厚交织。此时的秋风已带着几分萧瑟,凉意从门窗的缝隙间渗入,但一杯温酒下肚,暖意便从心底缓缓升起。
古人重阳饮酒,不只是为了驱寒,更是为了在微醺中抵达某种精神的自由。李白“携壶酌流霞,搴菊泛寒荣”的豪情,杜甫“竹叶于人既无分,菊花从此不须开”的感慨,都是借着酒意,将人生的悲欢离合化作诗行。我们今日虽不再如古人那般对酒当歌,但在酒香氤氲中,依然能感受到时间深处的回响——那些关于聚散、关于得失、关于生命本质的思考,都在这杯酒中沉淀、发酵,最终成为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
酒至半酣,最适合登高远眺。
山不算高,石阶上铺满金黄的落叶,踩上去发出细碎的声响。越往上走,视野越发开阔。待到山顶,整座城市尽收眼底——远处的楼宇在薄雾中若隐若现,近处的江水如一条银带蜿蜒东去。凉风拂面,带来远方稻田的气息。
王维在《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写道:“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登高望远,本就是一场与时空的对话。我们站在时间的高处,回望来路,那些曾经的离别与相聚、遗憾与圆满,都在这极目远眺中获得新的意义。城市的喧嚣在脚下沉寂,内心的纷扰在风中消散,只剩下天地间的辽阔与清明。此刻方才明白,登高不是为了逃离,而是为了更清楚地看见;不是为了忘记,而是为了更深刻地铭记。
夕阳西下,天边燃起绚烂的晚霞。下山的路上,遇见几位老人相携而行,银发在夕阳中闪着温暖的光。他们走得很慢,却很稳,偶尔相视而笑,眼角的皱纹里藏着岁月的故事。忽然想起“重阳”之名——《易经》中以“九”为阳数,农历九月初九,两九相重,故曰“重阳”。九是最大的阳数,代表着极致与长久,而重阳节又被称作“老人节”,这其中是否暗含着古人对时间、对生命的深刻理解?
时光如水,奔流不息。我们都在时间的河流中漂泊,青春会老去,容颜会更改,但有些东西却能在岁月的冲刷中愈发珍贵——比如对美好的感知,对生命的敬畏,对情感的珍重。重阳就像一个时间的坐标,每年此时提醒我们:在追逐前路时,别忘了回望来处;在适应变化时,别忘了守护不变。
暮色四合,家家户户亮起温暖的灯火。空气中飘来蒸重阳糕的香甜气息,那是糯米与枣泥、栗子交融的味道,软糯中带着韧劲,恰如生活本身——有甜蜜,有质朴,更有需要细细咀嚼才能品出的深意。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这个古老的节日,从来不只是日历上的一个标记,而是我们与时间达成的一种默契。它在年复一年的轮回中,教会我们如何在变化中寻找永恒,在流逝中把握当下,在孤独中体会圆满。当夜色完全笼罩大地,抬头可见星辰闪烁,如同时间深处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愿每一个重阳,我们都能在时间的高处相遇,看清生命的脉络,带着这份澄明,继续行走在各自的人生路上。时光易逝,真情不老;山水万里,心光长明。这,或许就是重阳给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