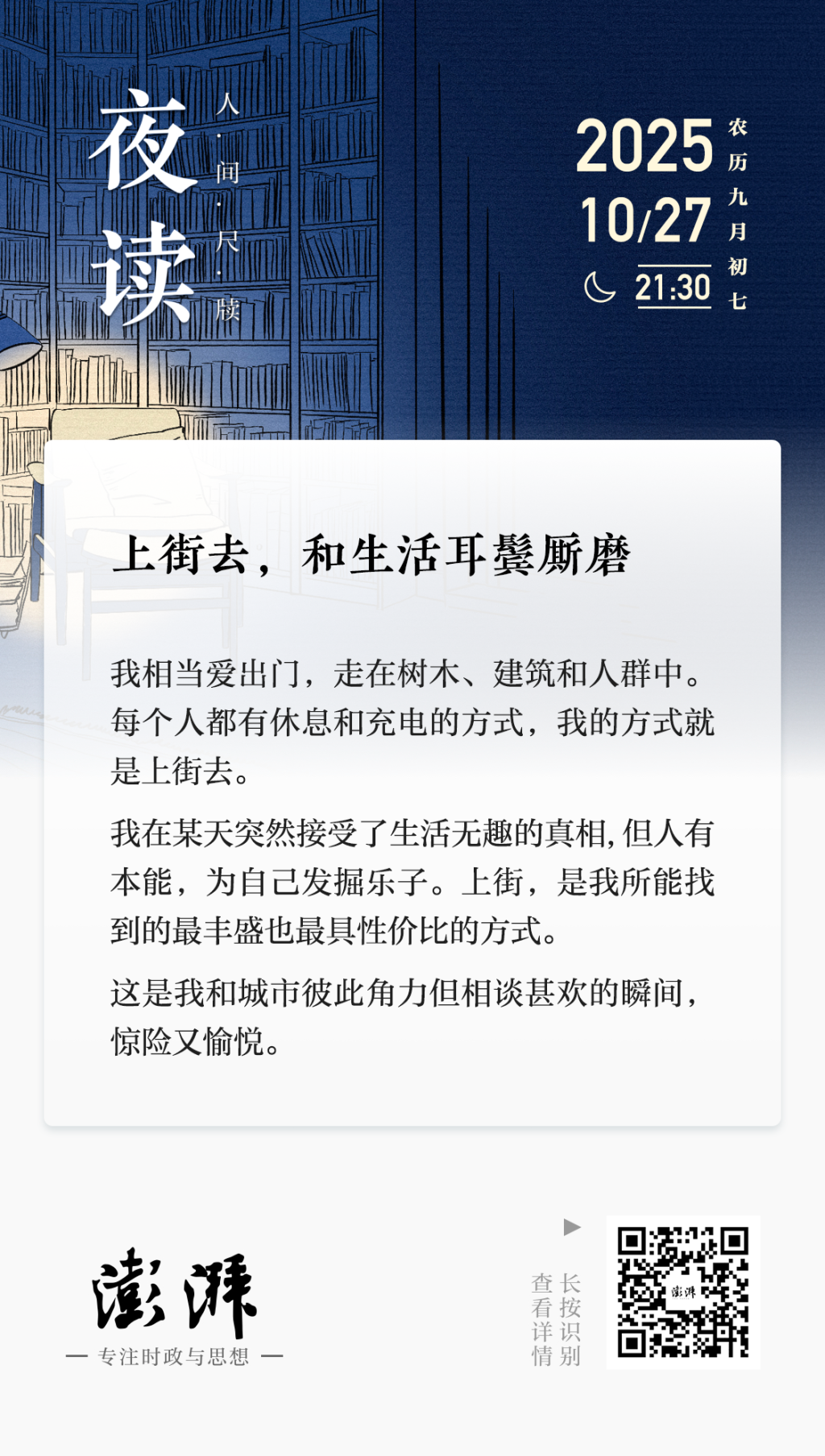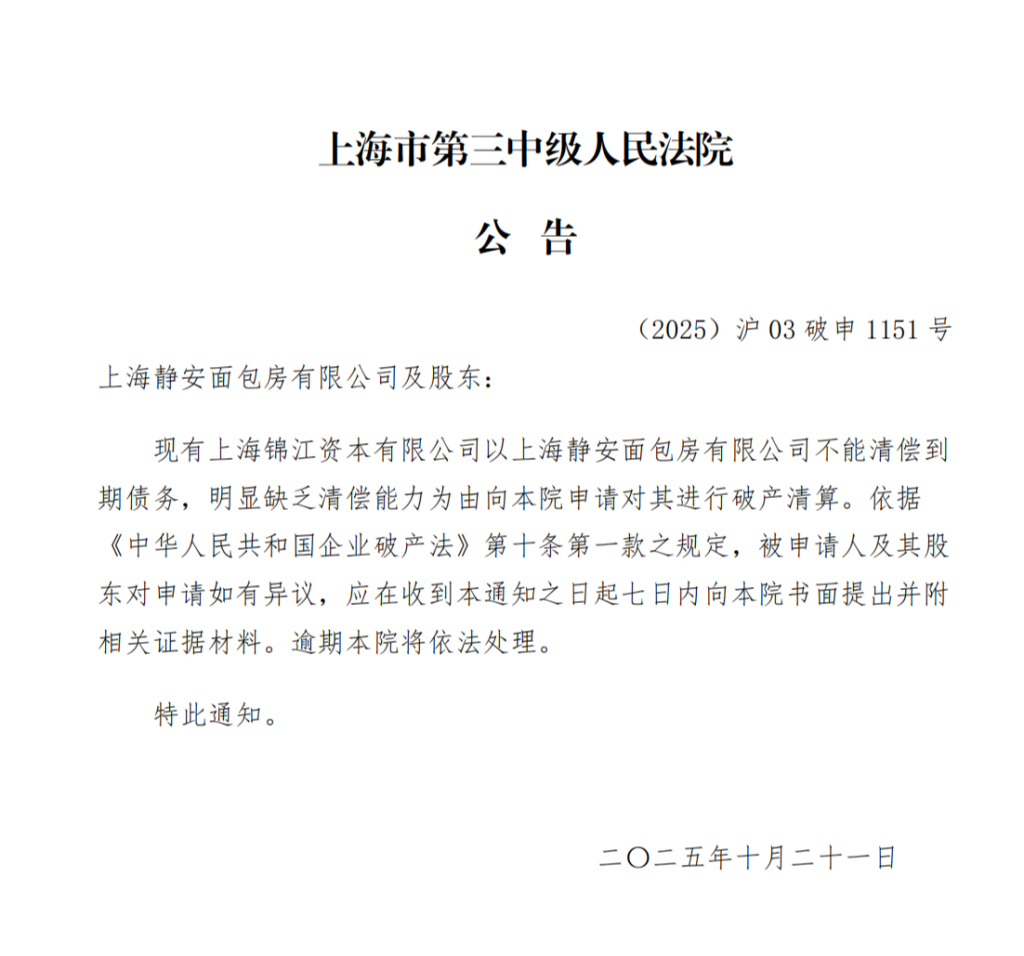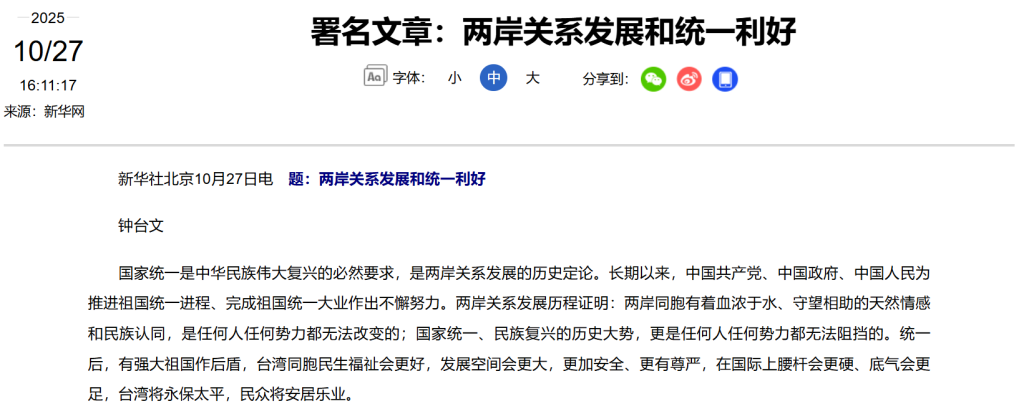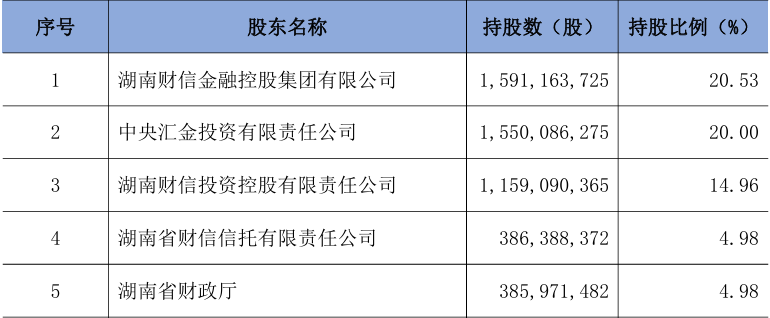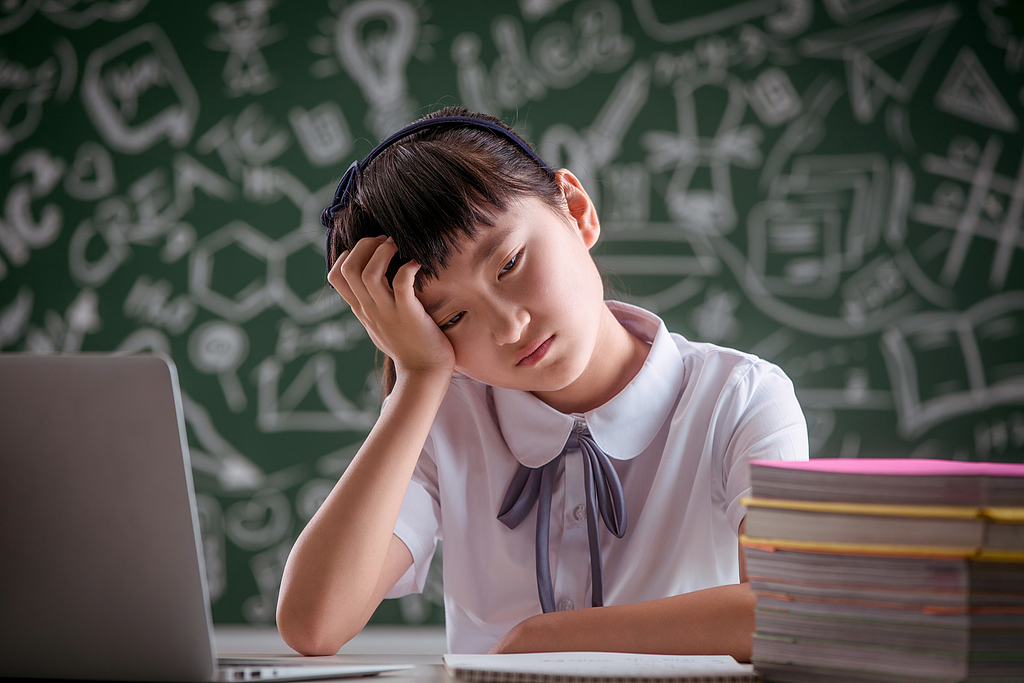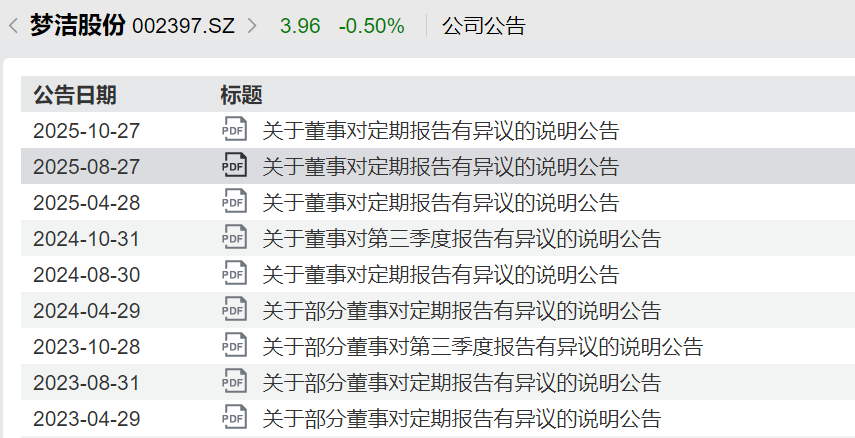夜读|上街去,和生活耳鬓厮磨
在很多朋友眼中,我是个又i(近年流行的MBTI人格中的一种,比较偏内向)又不太热情的人,不爱参加社交活动,懒得交流八卦,日常也看不出有多享受生活,甚至合理猜测我应该很宅。
虽然我确实对摇人扎堆或者长途旅行之类的不太感冒,但我其实相当爱出门。即便没有任何目的,也要出门,上街,走在树木、建筑和人群中。每个人都有自己休息和充电的方式,我的方式就是上街去。
在某个地方居住数年,日常半径之间早已长出血肉,一并构成了生活的真实知觉。有可能是某条街道一夜之间黄得耀眼的银杏叶,小店门口大功率音响循环播放的古早金曲,或是咬开刚做好的奶油泡芙夹心沁出的凉意。上街体验这些,就是和生活耳鬓厮磨。
但在我看来,这些经历又实在没什么值得分享的,可供加工创作的空间也不大。私人体验的幽微之处在于,一方面非常考验讲述者的能力,另一方面也需要接受者能感同身受甚至富有想象力。从这个层面来说,八卦才是最好的生活物料,宜室宜家。
有阵子我整天窝在咖啡馆里看书,不限定是哪家,隐藏菜单是其他顾客的八卦。有次我特意统计了一下,书才看了二十页,已然经邻桌诸位绘声绘色的高声讲述,间接掌握了沪上某家企业至少15人的深度八卦。
不过我很难从八卦中体验到乐趣。八卦的母题翻来覆去都是那几个,主角永远是老板、同事、对象,而且永远是一家之言。听多了,不免令人产生怀疑:人类的快乐难道就和关在笼子里的仓鼠那样,只是重复去踩那个滚轮吗?
还有段时间,我爱在通勤途中用手机备忘录手搓简笔画,记录一些现实的瞬间,或是由此激出的脑洞。画了百来个,难以为继。生活实在是太琐碎庸常了,想要强行制造出乐子或者灵感,也是为难人了。
总之,我是在某天突然意识并且完全接受了生活原本无趣的真相。但人总会有生物本能,要为自己发掘新的乐子。上街,恐怕是我所能找到的最丰盛也最具性价比的方式。
刚到上海时,我的足迹漫无目的,走到哪里全凭莫名其妙的脑洞——像遇到20个背双肩包的人后就换条路走啦,或是在路口一律只左转啦。乐趣就藏在这些即兴之中。我会遇到些特别的小店,美得令人鼻头一酸的巷弄,或者莫名就聊起来的自来熟的人。当然也有现炒现卖的八卦。
后来,我就像圈地自萌的宠物狗一样,只在既定路线上溜达。除了少数街道会在短时间里改变面目,大部分都很稳定,但人总是新的,或者看它们的人总有新的心情和眼神。就像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写的那样,“如果走近她,她就变了。在路过而不进城的人眼里,城市是一种模样;在困守于城里而不出来的人眼里,她又是另一种模样;人们初次抵达的时候,城市是一种模样,而永远离别的时候,她又是另一种模样。每个城市都该有自己的名字。”
绝大多数时候,我都不会掏出手机,而试图用手机代替眼睛来记录。为抓住不可捉摸的时刻,我总要凝住心神。这是我和城市彼此角力但相谈甚欢的瞬间,惊险又愉悦。
本质上,这也是一种仓鼠踩滚轮。只是因为它总撺掇我走出去,去现场,似乎又次次都变成了新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