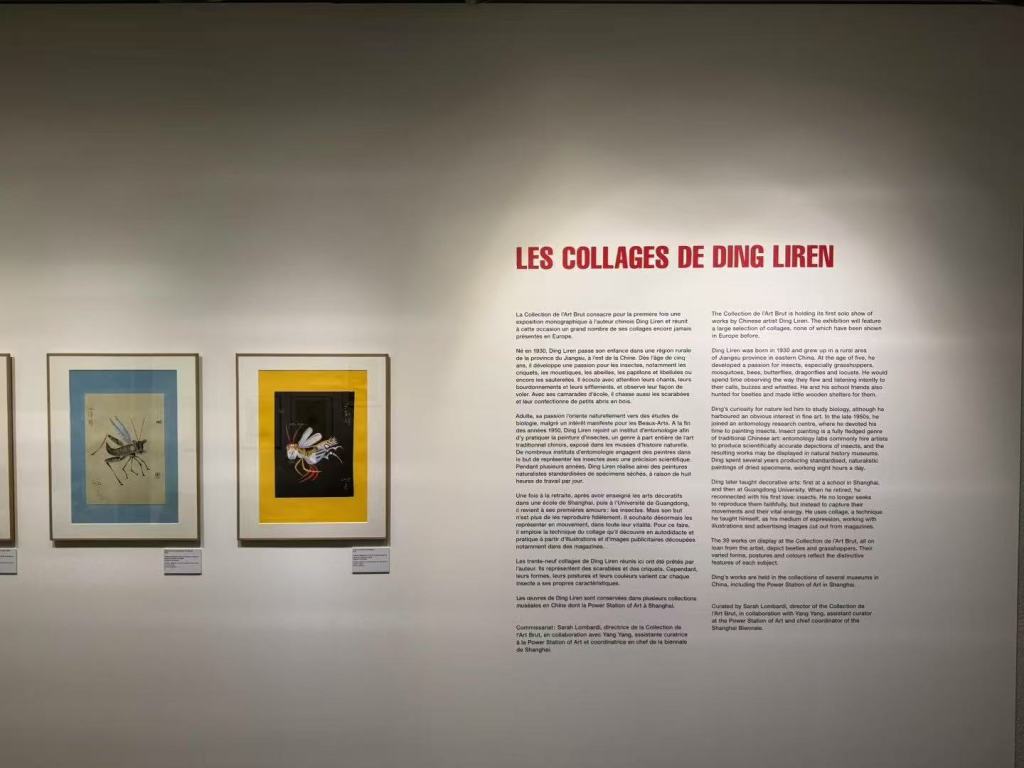从荒诞到反抗:加缪的追问与执着
从2024年《周处除三害》《九龙城寨之围城》的热映,到2025年《攻壳机动队》的重映,以暴制暴的类型片,一直在商业电影市场中占据重要角色。这些电影在现代社会备受关注的根源,是刺激了人类的暴力欲望,还是折射了一种荒诞的现实?
以学者加缪的哲学观点来看,“反抗者最初的冲动是拒绝被物化”。
这句话出自他的代表作《我反抗,故我们存在》(L'homme révolté)。要想理解这句话,或许需要先了解加缪的成长与思想历程,以及这本书对暴力的思考逻辑。

阿尔贝·加缪
加缪,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贫民区。自幼丧父,被严厉的祖母抚养成人,在17岁时患上肺结核症......死亡的阴云,笼罩着他的成长之路。二十多岁时,他便觉察:由于贫穷,我才不会相信,阳光下和历史中一切都是美好的;而阳光又让我明白,历史并不等于一切。
从地方新闻到法庭纪事,从专题报道到重磅社论,他笔耕不辍。他为贫民、囚徒、难民等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而呐喊,勇敢揭露法国殖民者对当地的残酷奴役。学者赛恩斯的《记者加缪》,曾提到加缪积极为奥当案蒙冤的小人物展开调查、仗义执言,“主张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普遍权利”。这些义举,让他被踢出了由法国殖民当局钳制的阿尔及利亚新闻界,也预示了他后半生追求理想、毫不妥协的“愚者”立场。

《西西弗神话》书封
1940年,加缪开始撰写《西西弗神话》。在他看来“事关如何在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里保持清醒”。在他青年时期的启蒙老师让·格勒尼耶看来,创作《西西弗神话》是加缪“希望统帅他的生命与思想,与他热爱的一同度日。但他认为除非极端情况,这几乎不可能实现。尼采便是这样疯的”。
加缪通过彼此呼应的“荒诞三部曲”创作序列,不断迈向自己的目标。

《局外人》书封

《卡利古拉》书封
被动式荒诞的《局外人》,结局为默尔索拒绝神父救赎,展现出反抗规训的萌芽;主动式荒诞的《卡利古拉》,结局为卡里古拉拒绝躲避刺客,展现出倒反天罡的虚无与戏谑;1942年7月出版的《西西弗神话》,则以哲学逻辑究极式求解“荒诞”——自此,渴望意义的人类、世界的无理性(“人类呼唤与世界沉默的对立”)终于完整展现在世人面前。
在翻译过《西西弗神话》的袁筱一教授看来:加缪的可贵之处,或许正在于他将非理性的激情与理性的推理连接起来。如果说荒诞的命运是任谁都回避不了的,也并不因为清醒的认识就可以避开......
自此,对荒诞任何一面的否定,或何种方式的否定(如自杀),都被加缪瓦解了。
正如加缪说的“否定荒诞赖以生存的对立的两项中的一项,就是逃避它。废除意识的反抗,也是在回避问题。永恒的反抗这一主题由此也转变成了个人的经验。活着,就是经历荒诞。而经历荒诞,首先就是直视它”。

《我反抗,故我们存在》书封
1951年10月18日,《我反抗,故我们存在》(L'homme révolté)甫一出版,便引起巨大反响和争议。法国《现代》杂志的编辑弗朗西斯·让松,甚至撰文直言这本书“首先是一部失败的巨作。正因为如此,神话也就诞生了。我们在此恳请加缪顶住诱惑,重新找回个人的风格——对我们来说,他的作品由此才显得不可替代”。
难道这本巨作,真是加缪思想的倒退或迷惘之作吗?
在我看来,关键争议在于加缪对“革命”究竟持有什么态度。
一封回应其作品《正义者》的公开信,注解了加缪的相关思考。《加缪传》的作者赫伯特·R.洛特曼也强调了这封信的重要性——让· 达尼埃尔提出的问题可表述为:(革命者)为了越狱,是否可以把拖家带眷的狱警杀死?加缪(的公开信)认为,问题应该以不同的方式提出:是否应该把狱警的孩子也杀了,以便解救所有的在押犯?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极限,狱警的孩子只是其中的一个,但不是唯一的极限......
由此可见,加缪始终拒绝将革命异化为无限暴力的仆从,强调人在一切苦难中仍需守护人性的底线。加缪的《我反抗,故我们存在》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在他看来“反抗者的逻辑是要追求正义,绝不在生存状况里再增加不正义”。他始终警惕的是对于“革命”的滥用会导致屠龙者成为恶龙,而不是否定“革命”本身对于反抗的正向价值。
这本书的出现,是对“荒诞三部曲”的接续。加缪首先从文学与历史去追问“反抗”的发展脉络,将意涵丰富的“反抗”分为“形而上的反抗”和“历史上的反抗”。
对“形而上的反抗”,加缪围绕“人对世界本质性荒诞的拒绝”展开,指出这种反抗如走向极端,则可能异化为“虚无主义”或“绝对否定”,导致反抗的自我毁灭;对“历史上的反抗”,加缪围绕反抗的本质特征与历史演进的变异,揭露那些异化的引领者如何利用“历史必然性”要求个体绝对服从,实施对人性的奴役。
回顾历史长河,会让我想到柏克的《法国革命论》,柏克和加缪均认可“反抗”是对压迫的合理回应,其分歧点如何界定反抗中的理性。
加缪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为反对反抗、矮化反抗,而是在思考如何为反抗确立方向感与边界原则,如何不让人在有意义的反抗中迷失自己作为人类的主体性。作为加缪思想的见证者,格勒尼耶在《阿贝尔·加缪:反抗永恒》也作了佐证。在他看来,加缪“试图借这本书驳斥荒唐的历史崇拜、权力意志崇拜”。

结合开篇提到的暴力电影来看,《周处除三害》、《九龙城寨之围城》、《攻壳机动队》面对的荒诞情境各有不同:《周处除三害》的男主角陈桂林,主动拒绝被黑帮身份规训,以自毁式暴力终结荒诞循环,揭示了个体反抗的道德困境;《九龙城寨之围城》的桩脚们,被动拒绝外来暴力组织的统治,以暴制暴来争取生存空间,而暴力秩序的本质或许并没有改变,在客观上走向虚无陷阱;《攻壳机动队》的女主角素子,通过“接纳异化”完成初步反抗,预言人工智能时代进行反抗的新可能,接近加缪“在荒诞中坚守”的生存哲学。
在加缪看来:反抗证明了它就是生命运作本身,若否定反抗就是放弃生命,反抗每一声纯粹的呐喊,都使一个人挺立,因而它含有爱与建设性,若非如此它便什么也不是。
当然,暴力电影的局限性是艺术局限性的折射。就像加缪在书中说的:它想成为真正的写实主义,必然要描述个没完没了......写实主义冗长无趣地一一列举,我们从这一点看出它的目标不是寻求一致性,而是达到真实世界的全体性。
作为20世纪的哲学经典,加缪的《我反抗,故我们存在》为怯懦与漠视、反抗与彷徨的人们,提供了与时俱进的理论武器与道德信条。但哲学不是烹饪手册或电器说明书,任何言语的留白或语义丰富,都可能产生无尽的争议。甚至可以说加缪的后半生,也活在这种令他痛苦的误读中。但任何人都无法抹除加缪在思想领域的深入思考与直言不讳。
正如加缪在书中所写的:不知晓一切的人无法磨灭一切,反抗者不将历史视为绝对,而是以他本性中所拥有的想法来拒绝它、质疑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