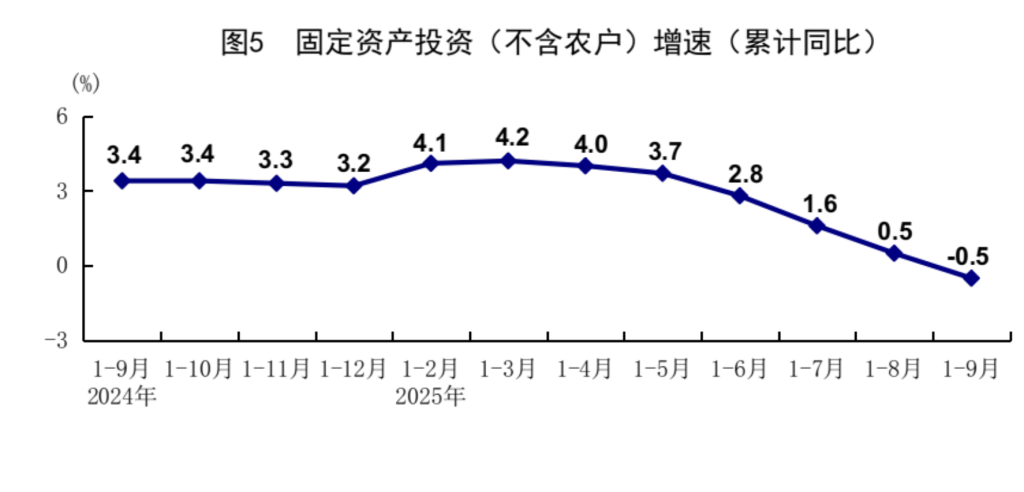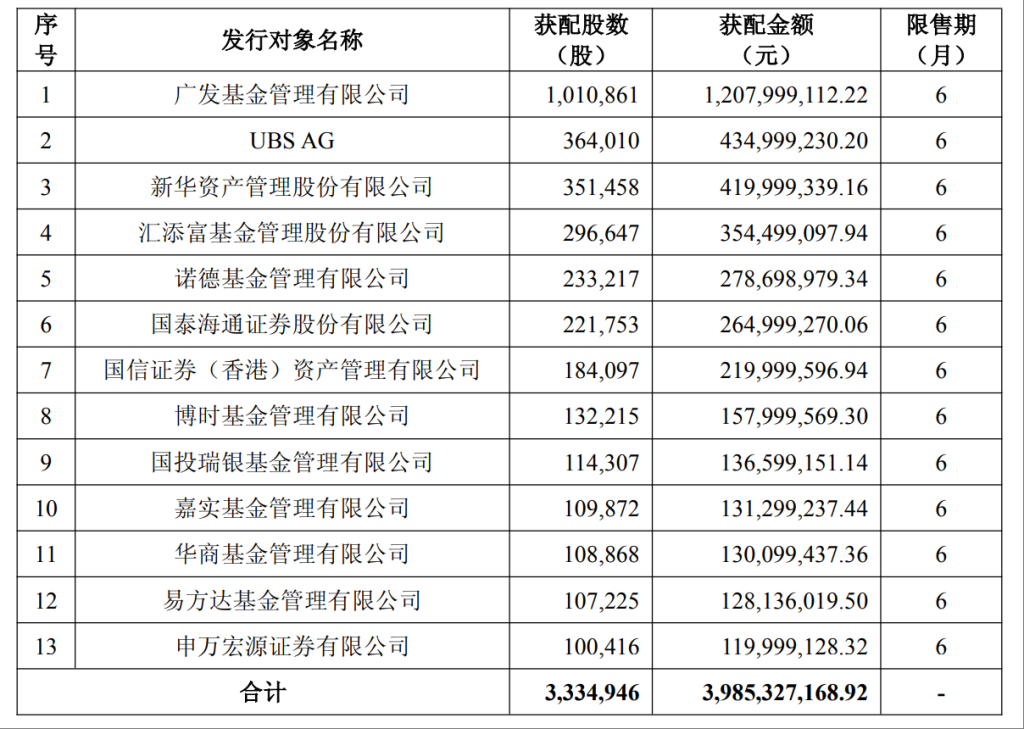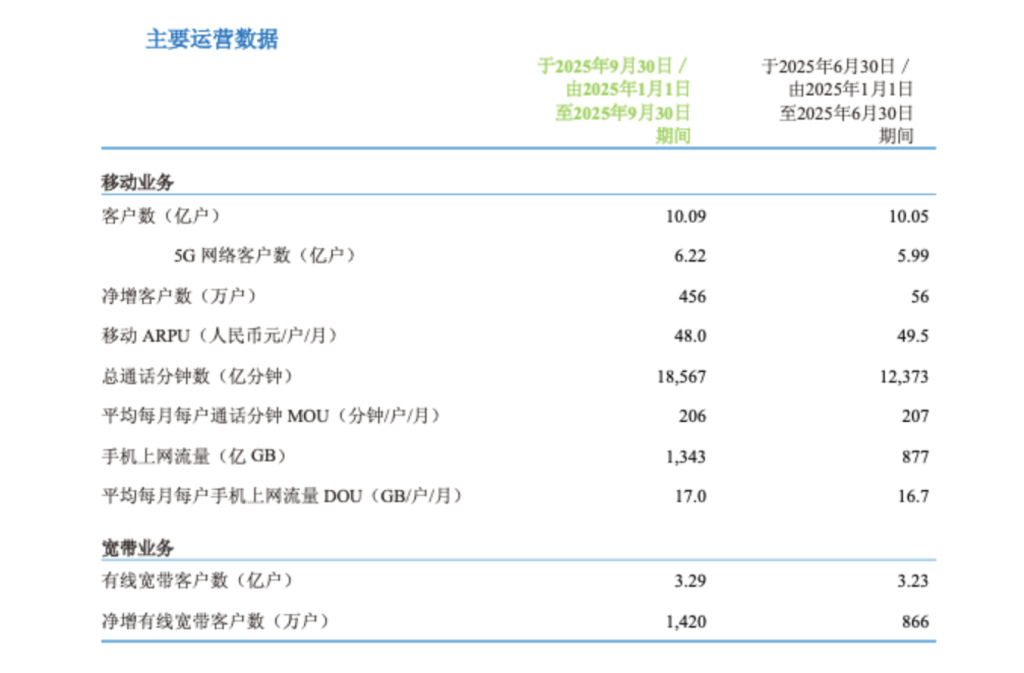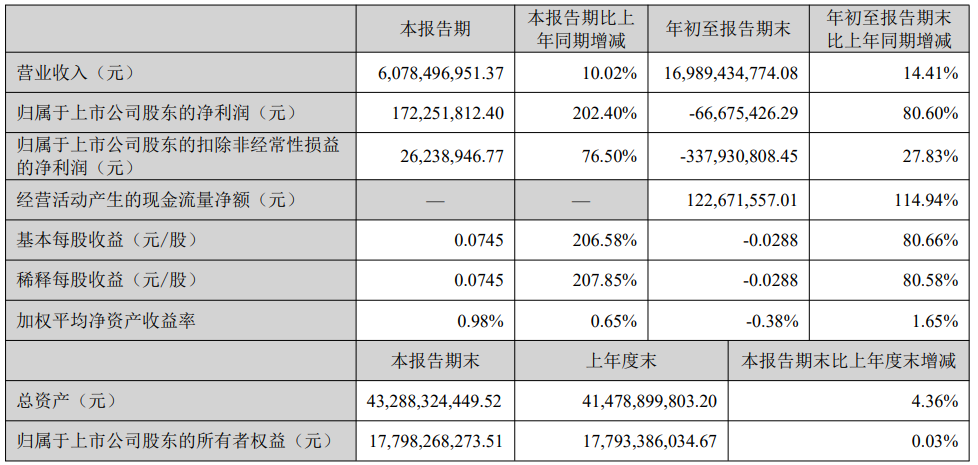纪念|熊昌锟: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敬悼朱荫贵师
9月23日,敬爱的导师朱荫贵教授与世长辞。噩耗传来,我陷入了深切的哀痛,久久不能平复心情。明知生命无常,人生终有离别,但真正面对那一瞬间,依旧痛彻心扉。除了无尽的怀念,脑海里不断浮现与老师相处的点点滴滴。
自2012年有幸拜入朱师门下,我跟随老师学习迄今已历时13载。与许多同门相比,时间并不算长。然而,正是这13年时间,深刻影响了我一生的学术方向与人生道路。老师不仅是我学术道路上的引路人,更是我人生中可以倾诉的朋友。对我来说,老师的辞世,让我失去了一座随时可以求教,永远值得信赖的精神灯塔。
老师去世当天,我在朋友圈写道:“老师一生襟怀坦荡、与人为善;严谨治学、精益求精;奖掖后学、不遗余力。道德文章,皆为楷模。忝列门墙,不胜荣耀。”这是我的肺腑之言,以此送别我最敬重的老师。

作者与朱荫贵教授合影
一
朱师出身名门,自北大毕业后进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开启学术生涯,他的研究始终关心、紧扣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重大问题,并将近代中国经济置于社会转型和中外比较的框架中加以考察,使学术界对近代中国经济的认识更为全面、深刻。老师的学术起步于近代航运史,早年他跟随聂宝璋先生整理、编纂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并以此为基础开展深入研究。航运业作为近代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领域,不但与近代中外贸易、资本积累与制度建设密不可分,更关系到洋务运动以来中国近代化的自主探索。通过对轮船招商局的深入研究,老师不仅系统揭示了航运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和经营模式,还进一步考察了航运业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
在航运业研究的基础上,朱师又将研究视野扩展到企业史、金融证券、资本市场及银行业史等领域,形成了一条逻辑清晰且颇具个人特色的学术脉络。他从我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招商局的研究入手,考察招商局是如何筹集资金,如何实现资金运行,并以此为基础,把研究范围扩大到整个股份制企业。朱师对证券金融史的兴趣,也来源于招商局。他很早就在思考,作为中国最早公开发行、买卖股票的企业的招商局是如何在证券市场实现融资的。由于早期的企业融资离不开银行的助力,他后续还进一步将研究触角伸向近代中国银行业史。在他看来,银行业史可谓连接证券金融和资本市场的桥梁。可以说,老师的研究最初是以招商局为核心的点状结构,最后通过资金运行、资本操作等形成网状结构。这些研究最终汇聚成系统和立体的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格局,其中既有对具体企业和行业的个案剖析,又有对经济制度与宏观体系的综合归纳。扎实、严谨的研究成果,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
老师常教导我们经济史研究要史料与理论并重,尤其是强调史料收集与整理的重要性。他在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和上海等地,收集了大量的档案和一手资料。他在课堂上和办公室里,结合这批材料,耐心指导我们如何阅读与分析史料。然而,他认为资料只是开展学术研究的一方面,理论的运用也很重要。他认为经济史不仅要解释经济现象或经济事件,更要揭示产生这一现象或事件的深层原因。这种史料与理论并重的研究方法,使他的研究具有兼具广度与深度。他的这种学术风格,既成为他个人的研究特色,也深刻影响了包括他的学生在内的众多学人。
在学术研究上追求精益求精,是他毕生的追求。在临近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笔耕不辍。除了《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史》已提交出版社尚待出版外,老师还在撰写一本航运史的书稿。朱师曾跟我说过,当年他和聂宝璋先生编辑航运业史料时,已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后来又在日本、中国台湾地区收集了很多航运业的资料,因此重写一本航运史专著是老师的心愿。另外关于近代中国的资本市场,老师也还有系统的想法,可惜天不假年,最终未能完成,留下遗憾。
二
老师的一生,不仅是学术探索的一生,更是奖掖后学、成就弟子的一生。他深知学术事业的延续需要一代代学人的传承和接力,因此在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始终把培养学生、传承学术放在首位,在学生的成长与发展上倾注了大量心血。无论是在学术训练、职业发展,还是人生道路的关键节点,他都给予学生毫无保留的指导与支持。
老师平等对待每一位学生,选择学生从不以学历和学校为评判标准。他认为学术成就主要依靠个人努力,而非出身背景。我亲身感受到老师的这种慈爱与宽厚。2012年,我自广西师范大学硕士毕业后,报考了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由于我在硕士时期主攻近代城乡经济,因此也希望博士阶段继续投身近代经济史研究。在确定方向后,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备考,也认真拜读了老师的著作和系列论文。学习之后受到极大启发,也坚定了我要努力去复旦深造的决心。记得面试时,有位老师问了一个深奥的理论问题,我当时一下未能回答上来。朱师一方面打趣称该问题对硕士生而言有些超纲,但另一方面也鼓励我整理思路,勇敢表达自己的理解。他的解围一下缓解了我紧张的情绪,此后回答较为流畅,也顺利通过了面试。后来在师生见面会上,朱师径自走过来跟我打招呼:“你是来自广西来的熊昌锟吧,我是你的导师朱荫贵。”我急忙回答道:“老师,我是熊昌锟,不过我是湖南人,之前在广西读书。”老师听闻后连忙道歉说,事先没看到我的具体信息,还以为我是广西人,并对我入学就读表示欢迎。老师平实的话语和鼓励,成为我日后坚持不懈,努力前行的动力。
作为导师,朱师对学生的学术训练十分严格,他要求学生必须通过大量阅读来夯实基础。博士刚入学时,他专门开了一个较长的书单,让我认真学习相关经典著作,其中囊括了吴承明、汪敬虞、李文治、张国辉、彭泽益、全汉昇、王业键、滨下武志、久保亨、科大卫、李伯重、彭慕兰、卞历南等多位先生的论著。此后,我每两周与朱老师交流学习心得。应该说,近一年的阅读极大开阔了我的视野,也让我逐步认识到经济史优秀著作的标准,从而进一步引导我思考应该如何进行近代经济史的研究。
在博士论文选题上,老师既能给学生提供好的研究建议,又充分尊重学生自身的意愿。关于我的博论选题,他最初推荐了两个方向:一是利用上海档案馆藏的盛宣怀档案,围绕轮船招商局开展研究;二是利用清水江文书进行社会经济史研究。当时老师正和复旦历史系以及贵州大学的老师们合作开展清水江文书的相关研究。因此,无论是轮船招商局还是清水江文书,都是朱师十分熟悉的领域,也方便他对学生进行深入指导。结合老师的建议,我认真查找和阅读了相关的学术史成果,起初我更偏向以轮船招商局为选题,但又考虑到黎志刚教授的博士论文也是写轮船招商局,且听闻黎老师一直在修改完善他的博论,他看过的材料和研究深度均令我难望项背,短时间内似难有较大突破,因此最终放弃了这一选题。至于清水江文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和贵州大学的多位老师也做过很多深入的研究,我在研读清水江文书的过程中,一时也未能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加之我浅薄地认为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史研究属于冷门,于是又放弃了这一选题。在跟老师汇报我的想法后,老师认为无论是轮船招商局还是清水江文书,都还有广阔的探索空间。但我仍坚持自己的想法,老师不以为忤,并未责怪,反而鼓励我自主探索,让我先去翻阅一手史料,看看能不能从史料中发现问题。他同时还提醒,选定题目后不要盲目动笔,一定要跟他协商并深思熟虑后方可进行下一步工作。根据老师的指点,我先后阅读了《中国旧海关史料》《申报》《北华捷报》以及盛宣怀档案等大部头资料。经过几个月的阅读、思考,我发现自己对近代中国的银元问题很感兴趣,于是去跟老师汇报。老师认为货币史问题值得探索,但也提醒我研究货币史难度很大,涉及很多理论问题,需具备良好的理论素养,才能解释币制演进和社会经济之间的内在逻辑。有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当时没太把老师的提醒当回事,仍然选择做这个选题。老师表示支持,并推荐了黑田明伸、城山智子和林满红等多位前辈的著作让我学习。在老师的引导下,我冒昧地发邮件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林满红老师求教,把我略显粗糙的想法告知于她,林老师在电邮中表示很高兴有人愿意做这个题目,她说此前想让她的学生做近代中国的墨西哥银元问题,但一直无人承接。她建议我主要研究墨西哥银元,但我考虑到近代文献中很难细致区分,于是仍以近代中国市场上的外国银元作为研究对象。
由于此前缺乏货币史研究的基础,我在研究写作中走了不少弯路。直到博士三年级,才陆续写出一两篇小论文。其中一篇《试论张之洞与晚清自铸银元》,经过老师逐字逐句修改,并经他推荐后,发表在《复旦学报》上。作为一个籍籍无名的博士生,能够在重要的学术刊物亮相,更体现了导师对学生的关爱与信任。另一篇投稿至一个经济学刊物,经过近半年的评审,编辑部通知拟采用,但因为我是博士生,需缴纳版面费。考虑到数额较大,我准备放弃。老师得知此事后,毫不犹豫地表示这笔费用他来出,无需我费心筹措。他提醒我将来找工作时,可以考虑去经济学院,在经济学刊物上的发表将助于未来求职。当时我尚未想到求职的事情,老师却已替我考虑周全。这种“为之计深远”的厚意,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由于时间紧、基础薄弱,博论完成较为粗糙,答辩时遭致几位老师的善意批评。老师看出我情绪不佳,鼓励我选题很好,虽暂时有不足,但相信我将来能够改好。这也坚定了我继续从事货币史研究的信心。惭愧的是,虽然老师多次敦促我出版博论,但由于我的疏懒,至今尚未完成博论的修改完善,也失去了请老师作序的机会,这是我深觉愧对老师的地方。
三
老师不仅关心学生的学术成长,也为我们的职业发展倾注心血。记得我在完成博论的过程中,也在四处求职。老师主动帮我打听,并向几个高校和科研机构加以推荐。他希望我寻找一个较高的平台,认为好平台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最终在老师的推荐下,我有幸进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跟随魏明孔老师从事博士后研究,两年后顺利留所工作。他不仅为我提供机会,更在临行前叮嘱我在新的工作环境中谦虚好学、尊重同事、踏实工作。老师殷切的希望,成为我初入职场时重要的指引。进入经济所后,所里的前辈和同事对我诸般照顾,使我在职场起步阶段的适应和发展较为顺利。而在正式进入学术界后,通过朱师也得以认识很多资深学者,他们对我也颇多提携、关照。我想这都与老师的与人为善,与他的“好人缘”密切相关。学界前辈和同仁把与老师的深厚情谊转移到了我的身上,让我感到特别温暖。
工作后我仍然没少叨扰老师,包括申请课题和一些自认为还不错的文章,都曾请老师提意见后,才敢申报或投稿。老师无不应允,并极为认真,提出很好的修改建议。如我202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当时我在暑假期间将初稿发给老师后,觉得老师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会给我修改意见,于是和家人一起去内蒙古旅游了。当时正在锡林郭勒的旅途中接到老师的电话,老师跟我说了近半小时,告知我哪些地方需要修改完善。想到自己在外面旅游却要老师帮忙看论文,感动之余也深觉不安,于是在当地买了一些土特产寄给老师,他坚决不肯接受。因我有老师家里地址,直接寄了过去,事后老师一再表示感谢。老师帮了我很多,一点小心意他却如此多礼,让我感到非常惭愧。最近几年,考虑到老师身体欠佳,我已很少请老师看论文。但所里组织编写学人文集时,从每篇文章的选定,以及作者小传的编写工作均由老师完成,我仅做了一些格式修订以及联系责编的工作。今日想来,名义上由我来编,实际大部分工作由老师自己完成,这让我十分汗颜。
此外,老师淡泊学术名利,总是不遗余力提携和帮助学生。老师近些年想组织编写一套《中国近代工商行业史丛书》,本来他完成的《近代中国银行业发展史》完全可以独立出版,鉴于老师的学术地位,几家知名出版社也明确表示老师的专著不需要出版费用,由出版社全额资助。但老师舐犊情深,坚持要求与学生们(也有几位非朱老师指导的学生)撰写的书稿共同出版。由于册数较多(共15册),出版费用将近百万,虽经多番努力,仍未筹措成功。在几次申请国家出版基金无果后,此事趋于停滞。老师为此颇为焦虑,后来我们辗转联系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他们同意以较低的价格出版这批丛书,于是老师以自己名义申报了用友公益基金会的重点课题,同时由西南民族大学卢征良师兄申报了该基金会的一般课题。得益于用友基金会的资助,两个课题的经费全部用于丛书的出版费用。也就是说,老师未从他申报的课题中获取分毫。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不仅让学生深受感动,也在学界传为佳话。
更难得的是,他还亲自参与组织行业史学术会议,搭建学术平台,邀请众多青年学者交流研究成果。在这些学术活动中,他从不以资深学者自居,而是耐心倾听、悉心指导,与青年学者平等对话。2024年10月,在皇甫秋实师姐的操持下,在复旦举办了第四届行业史会议并进行丛书的签约仪式。当时老师病情有所反复,我们劝他不必亲自到会,但他仍坚持全程参加并跟出版社商讨细节问题,最终完成签约。并于今年7月16日提交了《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史》的书稿(事后回想,老师为了抓紧完成这本书稿,可能加重了他的病情)。老师只管为我们搭桥铺路,可惜未能见到这批丛书的出版。
四
在学生心中,老师不仅是一位学术严谨的导师,更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宽厚智者。他关心学生的生活,常常在学术之外给予温暖。无论是人生大事,还是日常琐碎,他都不吝关怀。他经常提醒我们要平衡好工作与生活,照顾好家庭。他对师母和孩子的爱护,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新冠疫情之前,我每次到上海,总会去拜访老师,跟他畅聊学术和生活。他既关心我的工作,也很关心我的个人生活。2019年底,当得知我要结婚的消息,老师、师母还想亲自到武汉参加婚礼。后因疫情渐起,我劝老师、师母不要冒险,老师坚持要给我们送上祝福的红包,并表示是他和师母的心意,一定要我收下。那份温暖与关怀,让我和爱人感动不已。
2020年8月,疫情稍缓,我和我的爱人前往老师家中拜访。老师非常高兴,亲自下厨包饺子,期间不小心还割伤了手指。他却笑言“无妨”,坚持要亲手做饭招待学生。饭桌上,老师、师母与我们促膝长谈,话题不仅是学术与工作,更多的是关于生活与家庭。当时那温馨的场面还一直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中。后来得知我爱人怀孕的消息,老师每次见到我时,总还要叮嘱我照顾好我爱人和腹中的孩子。这些琐碎的日常关怀,让我觉得这份师生情谊是那么真实和细腻。
老师的宽厚并不意味着迁就,他一生坚守自己的处事原则,尤其是在与学生的交往中,始终保持清正。2023年底,我和所里的几位同事去日本访问,回程路过东京,约好跟老师见面。当时师母刚做了手术,跟老师见面后,我将老师的文集拿给他,并悄悄放了一个红包夹在文集中间,等老师回到住处后才发信息告诉他。老师当时就立即将红包用微信转给我,说不能收学生的红包,这是他的原则。等到老师、师母在2024年底回国的时候,师母还专程给我爱人带回了精致的礼物。
此外,在我的印象中,老师沉稳内敛,与人为善,从未有过激烈的言辞或情绪化的举动,更未对他人有过负面评价。他几十年如一日,保持平和的心境。这样的人生态度,也值得我用心学习。
五
作为学生的我们对老师也是发自肺腑的感恩。2017年老师退休时,复旦历史学系组织了一场荣休讲座。我们外地的学生瞒着老师、师母,悄悄奔赴上海,一起出现在老师的讲座现场,这让老师、师母十分惊喜。当师母看到我时,惊讶地说:“昌锟,你上周不是刚从上海回北京吗,怎么又来了?”我则笑称:“师母,我是爱热闹的,这样的场合我怎能缺席呢!”看得出来,老师、师母一方面担心影响我们工作,另一方面也很高兴能在这样的场合相聚。
2019年底,在同济大学朱佩禧师姐的辛苦操持下,我们悄悄筹备了一场活动,为老师庆祝70岁生日。后来听师母说,当时老师已检查出身体异常,起初并不打算过生日,但看到弟子们从各地赶来,怕扫大家的兴,还是高兴地同我们一起庆祝。尤其看到师兄、师姐的孩子们,老师尤为开心。那一晚老师讲了很多故事,全然忘记了身体不适。本来我们今年也在筹划给老师过75岁生日,可惜老师没能等到这一天,让人不由得无限哀伤。
老师、师母于2024年底回国后,我一直想去上海探望,但因各种事务缠身,直到今年5月下旬才得以成行。老师见到我也很高兴,并和我、于广师弟一起聚餐。返京路上,我发微信希望老师、师母保重身体,老师表达了对我专程探望的谢意,并嘱咐我照顾好家人!6月底,趁在上海开会的间隙,我又和袁为鹏师兄、卢征良师兄及宁波大学的雷家琼老师一起去看望老师、师母。当时老师状态还很不错,跟我们有说有笑。到了7月下旬,老师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此后未敢多打扰老师治疗和休息。
到了8月底前往上海参加中国经济史学会年会,我和朱佩禧师姐、刘涛姐夫、杨琰师姐、于广师弟一同去医院探望老师,发现老师身体状态差了很多,说话也很吃力。为了让老师多休息,我们仅在老师病房呆了十几分钟。走出病房后,几位同门纷纷感慨老师正遭受巨大病痛,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刻,老师仍保持一贯的镇定从容,他很少流露痛苦的神情,总是以儒雅的姿态面对病痛,连照顾他的护工阿姨也被他深深折服。他的言语越来越少,却仍不忘询问学生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也一直挂念着未竟的书稿与行业史丛书出版事宜。这种执着精神,让人动容,也让人心痛。
9月初,老师病情突然恶化。9月7日上午,佩禧师姐在群里通知,说老师昨晚刚经历抢救,医生说可能只剩一两天时日。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纷纷从各地赶到上海,希望见到老师最后一面。也不知是上天垂怜还是得益于老师顽强的生命力,在渡过艰难的两天后,老师生命体征逐渐平稳,此后更是能吃一些流食,精神也明显好转。大家都非常高兴,每天在群里询问老师的状态变化,而细心的同门还在老师的病房里贴上了照顾老师的注意事项。外地的同门得知老师转危为安后,陆续回到工作岗位,在沪的同门则自觉轮班照顾老师。我当时在师门群称“老师是最好的导师,精心照顾老师的各位同门也是最好的学生”。师母后来也说,这争取出来的两周(指9月7日老师一度病危),弟子们轮番陪伴以及老师生前好友的集中探望,给了老师莫大安慰,老师应无遗憾了。诚如斯言,在老师最后的半个月里,他的至交好友、同事以及众多学生纷纷前来探视,尤其是他的好友田岛俊雄教授专程从日本赶到上海,连续四日到医院陪伴老师,可谓中日学术交往的一段佳话。
六
在我的印象中,老师一直是一位谦谦君子。无论在学术交往中,还是日常生活中,他总是那么谦逊、温和,以理服人,以德育人。这种风范使他赢得了学界同仁、身边朋友和众多学生的广泛敬重。
老师的追悼会上,场面庄重而又充满哀思。老师生前故旧、同事及学生无不泪水盈眶,痛哭流涕,表达了对这位品德高尚、学问精深的朋友、前辈和老师的不舍之情。当灵车驶离殡仪馆时,我久久伫立,目送灵柩消失在涕泗滂沱的视线之中。我深知,这一别是永诀。往昔那些可以随时请教、可以尽情倾诉的时刻,再也不会出现。师生之间那份早日融入日常的深厚情谊,也只能化为永恒的思念。
老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将永存。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老师看到了弟子们的成长,以及对他的尊重与感恩;而我们也将在悲痛中,带着老师的期许继续前行。
谨以此文,寄托我对朱师最深沉的哀思与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