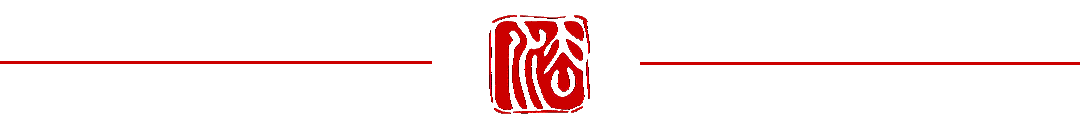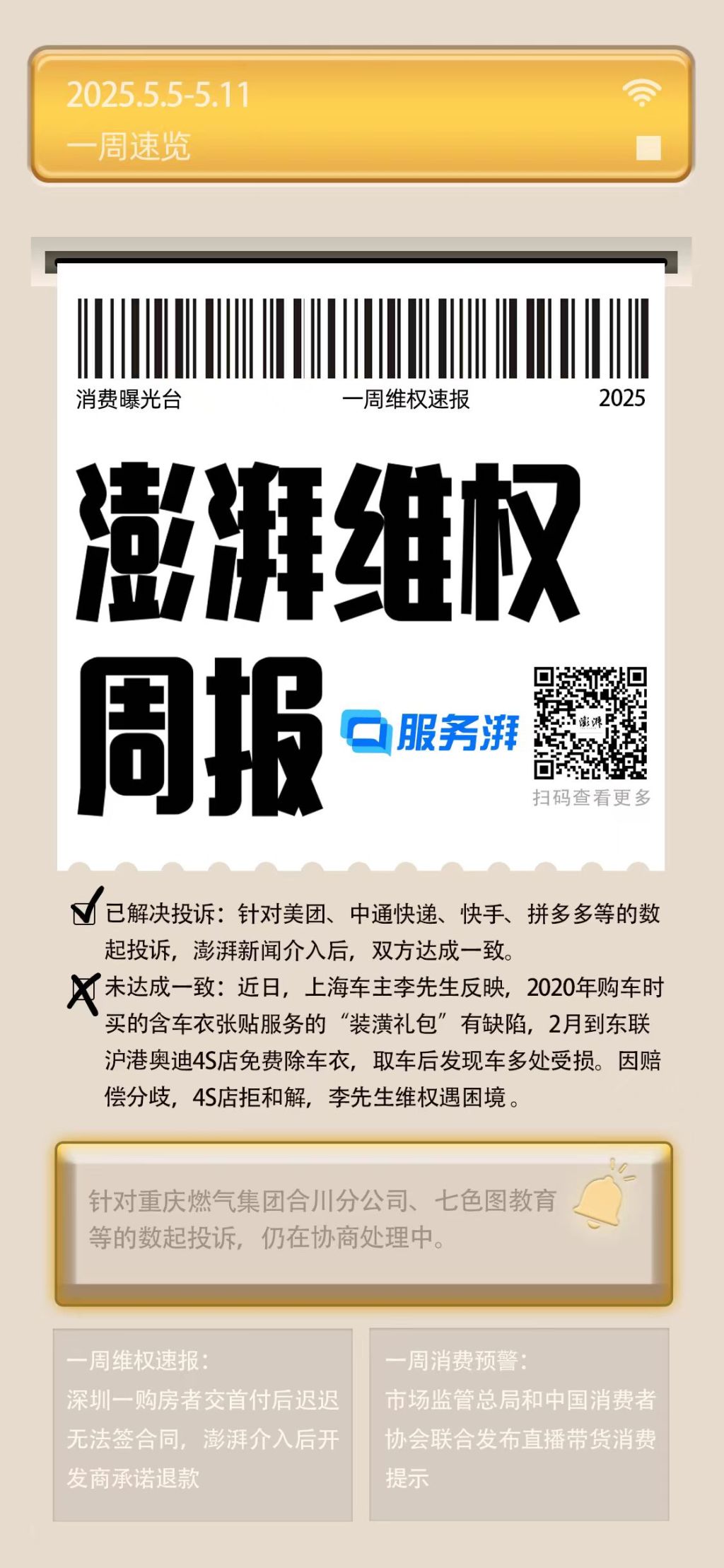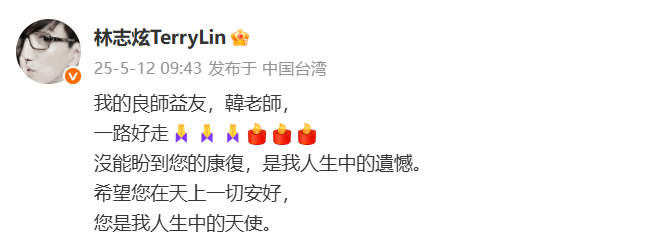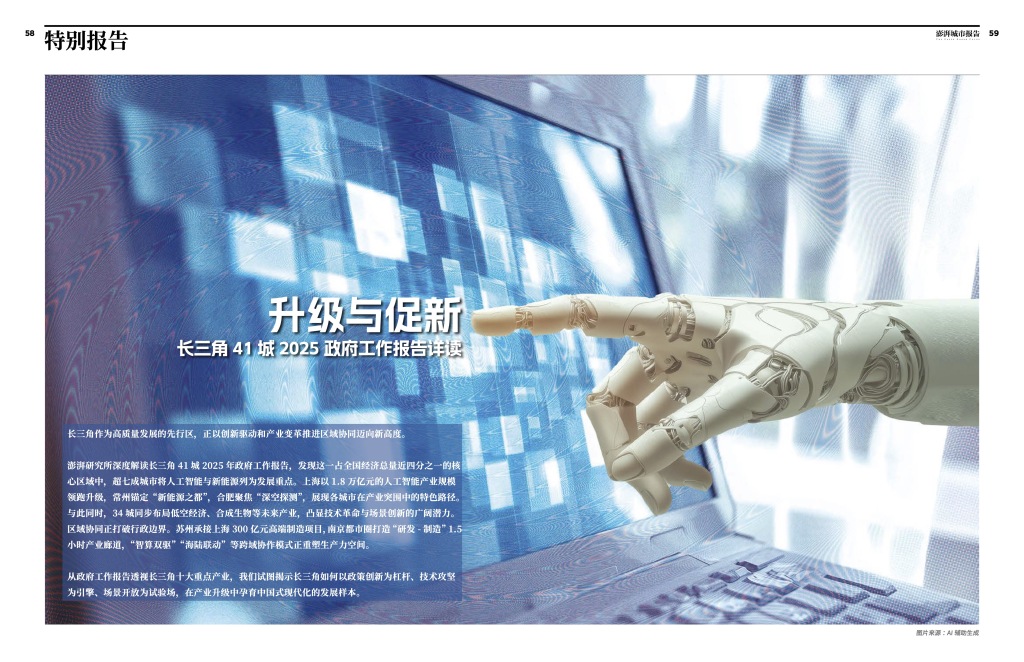左娅︱悼陈昊

陈昊(1983-2025.4),原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副教授
陈昊的突然离世,对我来说是一场时间彻底崩塌的事件。我们是在北大本科念书时结识的朋友,迄今已经相识二十余年。这二十年间,我们分别在世界的两头读完博士、入职高校、写字为生,是共同成长、风雨同灯的好朋友。这么多年来,我们维持着亲切而家常的友谊,对话主要集中于晚饭吃了什么或者吐槽哪篇文章又写不出来。然而这样曾经令人熟视无睹的日常生活,在4月17号戛然而止了。他的突然离世,让我觉得过去的二十年瞬间被抽空了一半,过往的时间里绽露出的巨大空洞,无论如何再也无法填满。而往前看的时间维度也坍塌了。偶尔听到新闻里某某事件人物五十二岁、六十三岁,惊觉我的朋友再也不会活到那个岁数,这些都是与他无关的数字了。一个朋友从你的生命里走过,会把他的步履细密地织入你的时间,他离去时撕去那一缕,你余生的时间就再也无复完整。
然而所有的混乱和悲伤都只不过是属于生者的。陈昊走的很平静,就如同入睡一般,一切都平常照旧,他甚至都没有关上电脑,也没有留下只字片言。“这个人很懒,什么都没有留下”。 他走后的第七天,我家一盆沉寂多年的多肉植物,突然开出了一朵鲜艳的小红花,在春日的阳光里熠熠发光。感谢你回来道别,我的朋友。你走得轻松,获得了解脱,那就比什么都重要。
其实作为多年的朋友,我了解他对生死的豁达。一个义无反顾拿生命燃烧出灿烂的人,就能坦然面对满开而散后的寂静。他的第一本著作,赠书时夹了一张书签,上面题的是刘禹锡的惜春词:
春去也,共惜艳阳年。犹有桃花流水上,无辞竹叶醉尊前。惟待见青天。
我当年都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这次把他的书和文章都找出来一一看过,才发现他在大作付梓的得意时刻,却偷偷夹进了这张惜春伤春的小小书签。他懂得炽烈之后的寂静,甚至还有两分期待。而他在今年3月刚刚完成进入校样阶段的书稿,标题是《膏销雪尽思还生:知识、情志与中国医学史上的“元白时刻”》。在他走后的第二天我再次看到这个标题,觉得有如被一记闷棍击中,膏销雪尽意还生,唯有思君治不得,你让生者情何以堪,情何以堪啊!但是打开书页,看到的是他在销和尽的意象里平静地讲述人世间的羁绊和离别,写的是轻灵的短章,是他一贯的灵巧,而且愈加轻松了。我知道他毫无遗憾了。
而在更年轻的时代,生死曾经只不过是谈资。2014年我俩一起在亚洲研究年会上组过一个专题讨论,题为“醉生梦死”,是把醉、梦、和生死拆开,分别讨论一种转瞬即逝的人生经历。醉和梦是另外两个同事写的文章,我俩主攻生死。我写的是向生而死,宋代文人的绝笔之书;陈昊写的是伴死而生,宋代文人在守丧期间的读书行为。我是在翻出十几年前的会议记录才意识到,当年我居然写的是现时的他,而他写的是今日的我。真的是满箧填箱唱和诗,少年为戏老成悲啊!
但是悼念陈昊,真的没有比读他的书更加合适的方式。他的一生,只痴迷读和写。这些天我也一直在想,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学者?放下学界各种诘屈聱牙的术语不谈,陈昊是一个真正生活在这个时代脉搏深处的历史学家。他珍重这个时代的丰富和厚度,用一支慈悲和带着敬意的笔,深耕着这世间的复杂性。
从二十世纪中期到二十一世纪这近一百年里,这个世界在不断地增加厚度。世界是否有一个清晰的秩序?我们是否能够能确信自己真的了解这个秩序?对这些问题自信的回答已经慢慢成为上一时代的记忆。用以描述世界的每一种大而化之的结构事实上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质疑。历史是线性前进的吗?宇宙是有终极意义的吗?对大结构的追问,带来的是人类经验各种维度上极大的丰富性。首先,人的面孔开始增多,士庶、老幼、妇孺,众生百相的故事都进入了历史叙事。其次,每个人在自己的处境里都看到了自己的视角的不同,随着个人叙事的日渐丰富,这些不同视角的意义也日渐重大,成为了诠释的核心动力。而与此同时,每个人都在追问:我是谁?我与自己的故事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是我活出了故事,还是故事塑造了我? 我与他人之间,是鸿沟还是联结?而世间真有一个恒定的我吗?
这些问题释放出了无数的声音,有的细小,有的洪亮。而人们对于自己发出声音的方式也做出了更多的追问。文字是可靠的吗?辞章和义理的联结是恒定的吗?一个人使用言语讲述了他的故事,还是被故事塑造了他的言语?我们通过文字了解的世界,到底是世界本身,还是另一个不同的世界?不同的答案指向了人与文字不同的关系,有的在追求清晰性的路上一往无前,而有的则戏谑性地打乱清晰,以挑战清晰背后的规则。也有很多人看到了文字的不足。因为人在张嘴说话之前,已有气息、身体、情感等多种手段与他人和世界相通。言语是便利的,但它甚至远远不是最基本的。
陈昊的每一本书,都是在回答一个这样类似的问题,同时顺势而下,纵身跃入一个不断奔涌和扩张的经验世界。他的作品之所以对读者的心力有要求,正因为他对经验的丰富性有很高的敬意。在他的写作中,结构本身的勾勒必须通过对处境的细腻探究来表达;经验为主,脉络为辅,后者必须支持前者的漫溢性,特别是这种漫溢性中失序的可能。正因为这个立场,他能看到的脉络又特别复杂,随时处于涌现的状态。

陈昊已出版的两部专著:《身分叙事与知识表述之间的医者之意》与《疾之成殇:秦宋之间的疾病名义与历史叙事中的存在》
在他的第一本书《身分叙事与知识表述之间的医者之意》里,陈昊探究的中心问题就是:我(“医者”)是谁?我何以言说我所言说?以第五章为例,他提出了一个人人都想知道答案的问题:《诸病源候论》《新修本草》以及《黄帝内经太素》这几本隋唐医学经典,其“撰者”究竟是谁?但是熟悉这些材料的人也都知道,这几本经典,尤其是前两种,其作者的身份都是模糊或者有争议的。带着这个貌似简单的问题——乘着它的模糊性——陈昊迅速切入了几个宽广的空间,把对个人的侦查转为了对社会场域的考察,比如医学知识传承的地域、医学家族与医学官署之间的互动、官修书籍的体系、药政的布局以及医官与非医官在官僚体系中的合作和互动。他所呈现的“撰者”,在这些场域之间腾挪,于是变成了一个具有丰富社会属性和复杂社会行为的存在。所以,既是我活出了故事,也是多维、多重的故事在诸层面上塑造了我的存有。
在他的第二本书《疾之成殇:秦宋之间的疾病名义与历史叙事中的存在》,陈昊以另一个中心问题贯穿全书:一场病痛,是怎样一个故事?这个问题的底层逻辑是,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一种疾病并没有一个确凿不变的实体。比如现代的糖尿病未必就是古代的消渴症,虽然为了方便大家常常做这种简单的联结。“脚气”这个词在漫长的历史里至少对应了三种截然不同的病症。所以一种疾病必须有一个故事,它的存在是“我”与处境协商对话的结果,必然需要一种叙述的呈现。而历史上对病痛的叙事方式无穷无尽,且弥散在各个社会空间里。这种涌现的复杂性,又再次成为陈昊的着力点。拿很多人喜欢的第八章《石之低语》为例,晚唐洛阳地区曾经发生持续数年的疾疫和饥馑,这些灾疫事件力度不小,应该给很多人造成了痛苦和无助,但是现存的史料里却鲜有正面记载。陈昊挖掘了几则墓志,都是这场疾疫的故事,但疾疫本身都弥散在叙事的深处。譬如丧生于这场疾疫的洛阳青楼女子沈子柔,她的情人源匡秀将她的故事铭刻于石,他写了自己对她炽烈的情感,写了她在病痛中仍不忘给予的深情,写了她挣扎中的自救,写了她最后在雷电交加中的猝然离世。但与此同时,他又并未目睹她的死亡,他的叙述中充满了展示自己伤口的渴望。疾疫不仅仅是沈子柔的死因,更是让源匡秀在自己的叙述里失声喊出“火燃我爱爱不销,刀断我情情不已”的深层动因——它正是源匡秀痛失其爱中的漫漶无界的“痛”。而疾疫在历史叙述中的本体正在此处,不在彼方。
陈昊对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娴熟把握来自他不知晦朔、忘乎所以的阅读。他好读书,且对世间的知识有一种赤诚的平等心,不起分别心、物我两忘的汲取。经典、前沿、通俗、晦涩、从隋唐到拉美,从人文到动物,没有他不为之好奇的类目,哪里都可以是令他欣喜雀跃的灵感触发地。作为同时代的八零后,我常常觉得他这样行走天地间的快意阅读也是我们这代人的福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求知渴望,九十年代对开放的热情,千禧年前后对地球村的乐观展望,等到2010年入职高校前后,世界各地区域研究的极大丰富发展,令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互相关照进入更加细致和同情的阶段。几乎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对他者的好奇和热情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陈昊生长在这个敞开双臂拥抱世界的时代并成为它的繁花盛放的一部分。他以惊人的速度读书和学习语言,在书本里跋山涉水,踏遍山河,赏尽人心和美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我常常惊叹简直没有他未涉猎的区域研究——他的见识早已超越所谓中西之分,他的阅读遍及拉美、中东、非洲,带有真正全球南方研究的使命感。就在这几年,他还在学习纳瓦特尔语——墨西哥在西班牙征服美洲前的本土语言。曾经有一个我们共同的拉美朋友赞叹说陈昊真的可以成为我们拉美人,他实在太懂我们的文化了!
陈昊作为学者的平等赤子之心,同样投射到了他行走人间的实际行动。他一生眼里都常有弱势群体,有一种远超他年龄的痛人之痛的慈悲。他还是一个真正的女性主义者。在他职业生涯的每一个阶段——从博士生到教员——他都在默默帮助身边的女学者。陈昊的朋友们应该都了解,他人的苦难他总能看在眼里,而他的出手相助风雨无阻,从不缺席。他去世前几天留给我的最后一番话,还在讨论帮助一个学生的事。然后他说:我要去休息一下了。这一休息,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而他走后,数十位女性学者,从博士生到资深教授,都第一时间给他发来了悼词。陈昊,我们的朋友,你善良、勇敢,有阅读量,我们为你骄傲,我们永远想念你。
陈昊去世消息传来的当天,他曾经教过的一个学生给我写信,问:你觉得陈老师是不是因为累了,所以去参加了什么奇怪的社会心理实验,然后躲起来休息了。我当时呆呆地看着这封信很久,因为我也觉得,这一切都太不真实了。说不定哪天他又开心地钻出来,告诉我们一切都只不过是个玩笑。他在这个世界的停留太短暂了,但他在这个人间留下的光亮却是如此持久而又温暖。对我们生者而言,能与这样一个美好的灵魂相识是多么幸运,感谢你,用光芒划过我们的天空。
我们有缘来世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