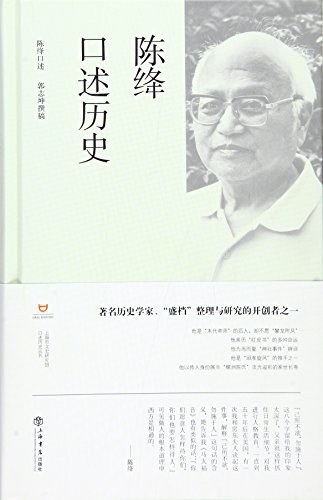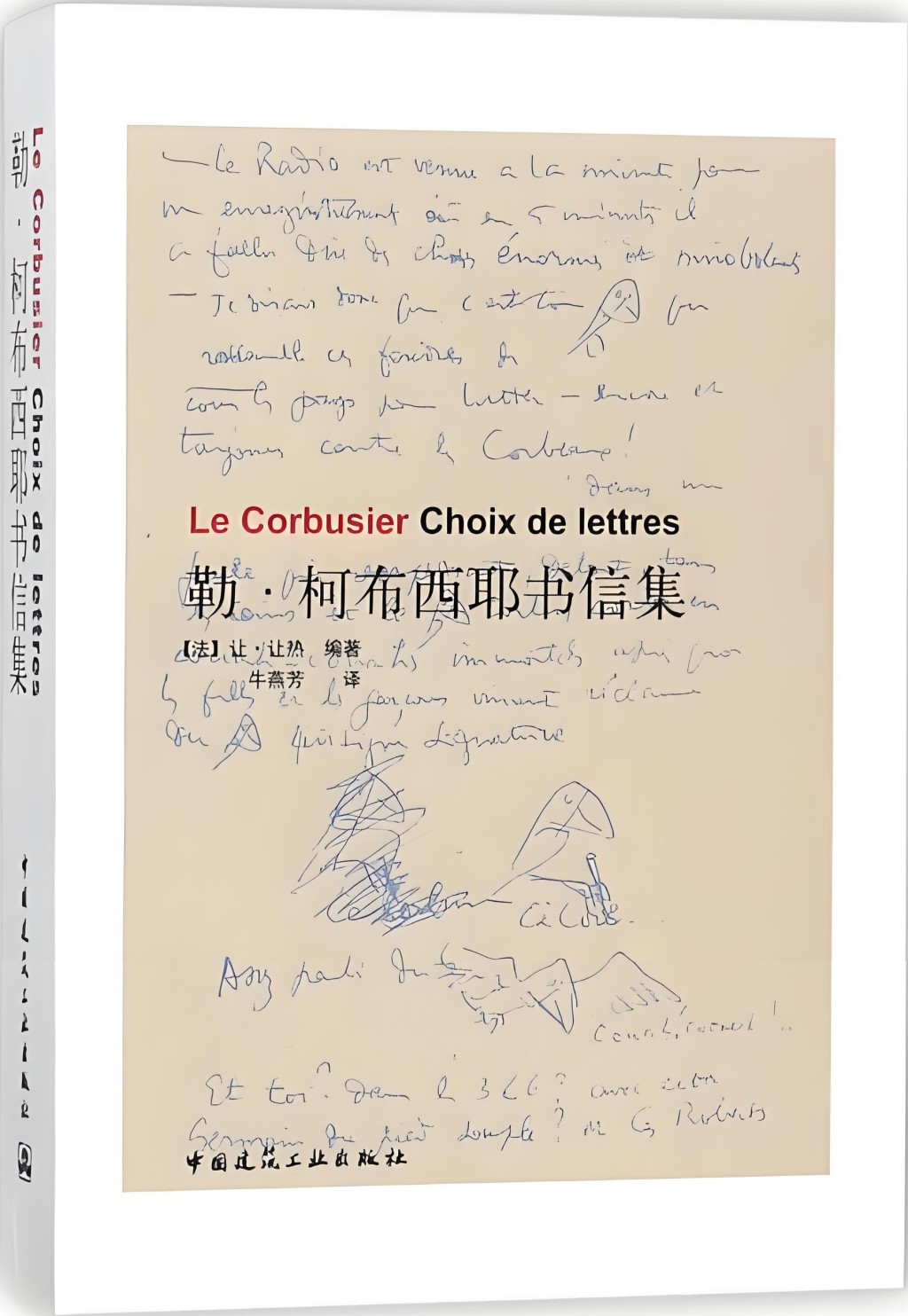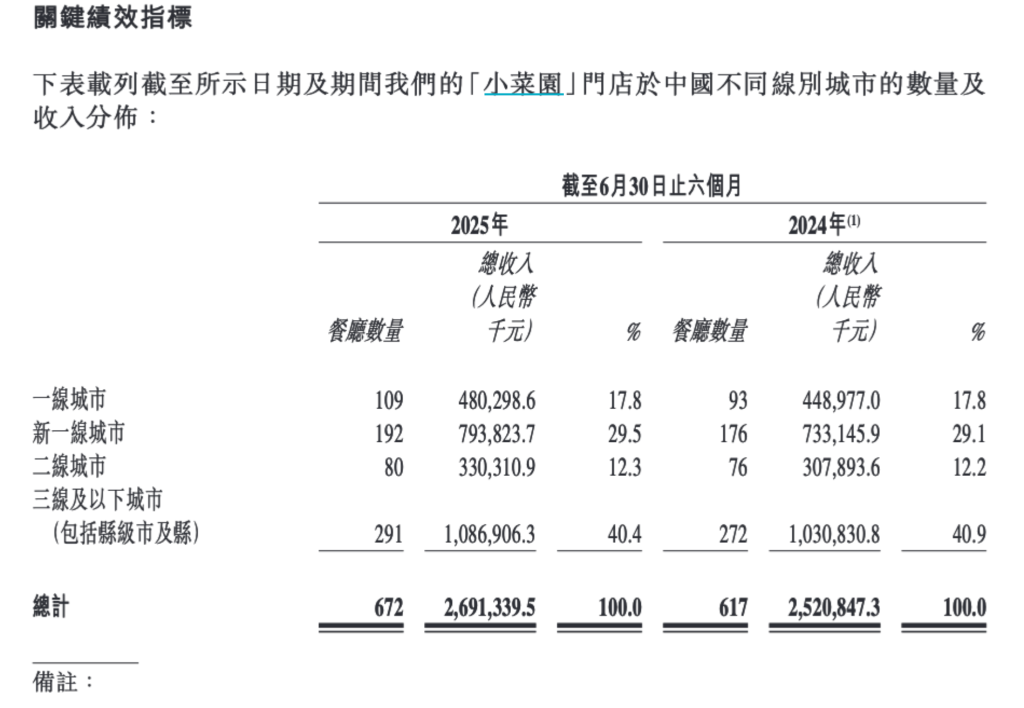王翔|我们可以《对工作说不》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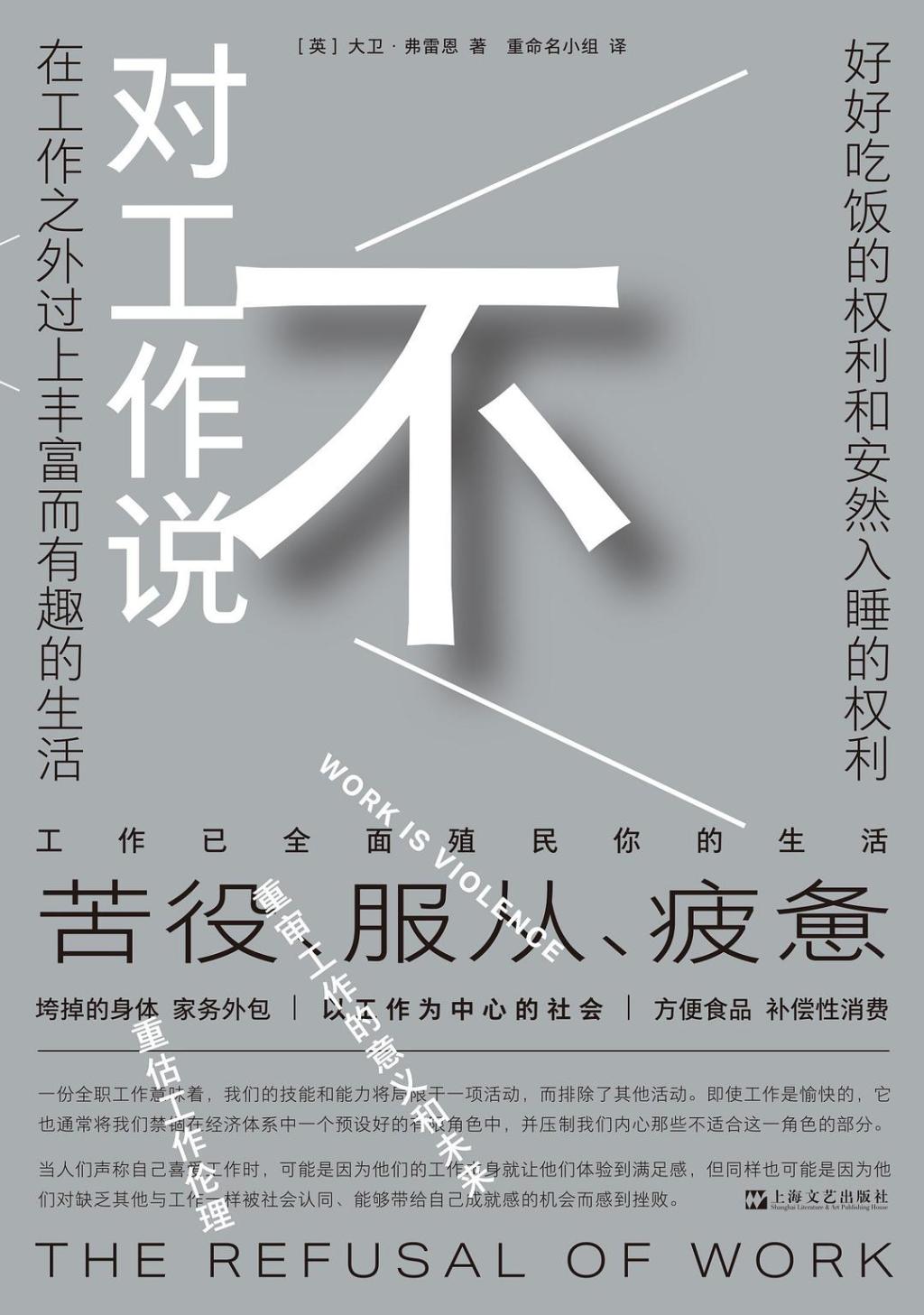
《对工作说不》,[英]大卫·弗雷恩著,重命名小组译,上海文艺出版社|艺文志eons,2025年3月出版,312页,56.00元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依然是全球社会中最常见的社交开场。单位、职位、薪资……像一根看不见的主线,编织着现代人的身份叙事。工位、工卡、加班、周报、KPI、OKR……无数个体的生命被工作之网规训得井井有条。工作赐予我们收入、社交网络、身份标签,也吞噬了我们的时间、想象与健康。即便在下班之后,它也像退潮般带走了我们灵魂中那些本该自由自在的部分。这种被体制化的“惯习”无孔不入地渗透进我们的自我认同与生活意义。而那些主动或被动走上另一条道路的人们——失业者、自由职业者、数字游民、间隔年休假者等等——往往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类”或“失败者”。
然而,“工作”本身真的天然合理吗?它真的是个人成就与社会认同的唯一来源吗?亦或它只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短暂产物——一种现代社会用来组织人口、整合资源、规训主体的机制?大卫·弗雷恩(David Frayne)《对工作说不》就像在滚滚浪潮中一声清醒而高亢的呼喊:我们或许可以选择不把生命完全放在工作的祭坛上。弗雷恩的论述既是思想史的回望,也是田野的记录——它让理论的种子扎进现实生活的土壤,试着把“拒绝工作”变成一件可想象、可落地的个体实践和公共事务。如果不工作的话,钱从哪里来?怎么花钱?怎么过日常?弗雷恩记录了那些开始“拒绝工作”的人,如何在犬儒与鸡血之间摸索出第三条道路,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如果“好生活”不是靠加班熬出来的,那么它可能长成什么样?
“拒绝工作”简史
在年轻人中引起广泛共鸣的日剧《宽松世代又如何》中有这样一段台词,“我这四年来光找工作了。我无数次地深切感受到,自己的自尊心和自我感觉在社会上连一毛钱的价值都没有……我这么努力,却连工作的权利都得不到,你不觉得这样的社会很奇怪吗?不让我工作是不是就意味着不让我生存?”

日剧《宽松世代又如何》海报
不过,工作的中心甚至“霸权”地位其实不过是近两三百年才有的事情。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便将“闲暇”(schole)视为“美好生活”(eudaimonia)的基石,认为真正的自由与德性在于摆脱劳动的束缚,投身于沉思与公共事务。在传统社会,赚钱并不是人的“天性”,人们通常只希望按照自己习惯的方式生活,并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例如买一块地、盖一间屋)而赚取必要的收入。那时候,人是为了生活而工作,不是为了工作而生活。而韦伯发现,近代以来随着新教伦理的兴盛,社会对工作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辛勤工作逐渐被认为是一种“天职”而具备内在的美德,“断绝浮士德式的个人全方位完美发展的念头,而专心致力于一门工作,是现今世界里任何有价值的行动所必备的前提……清教徒想要成为职业人,而我们必须成为职业人”。自从人们被迫成为“职业人”以来,对此怀疑也从来不曾消失。
想象一场在咖啡馆里的思想对话:
马克思指着被机器化为零件的工人,说“劳动被异化了”,人成了“机器的附庸”,“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
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拿出自己写的讽刺小册子《懒惰的权利》,大声痛斥资本主义对工作的狂热,呼吁我们大家应该反对“为工作而工作的愚蠢”,为享乐和闲暇争取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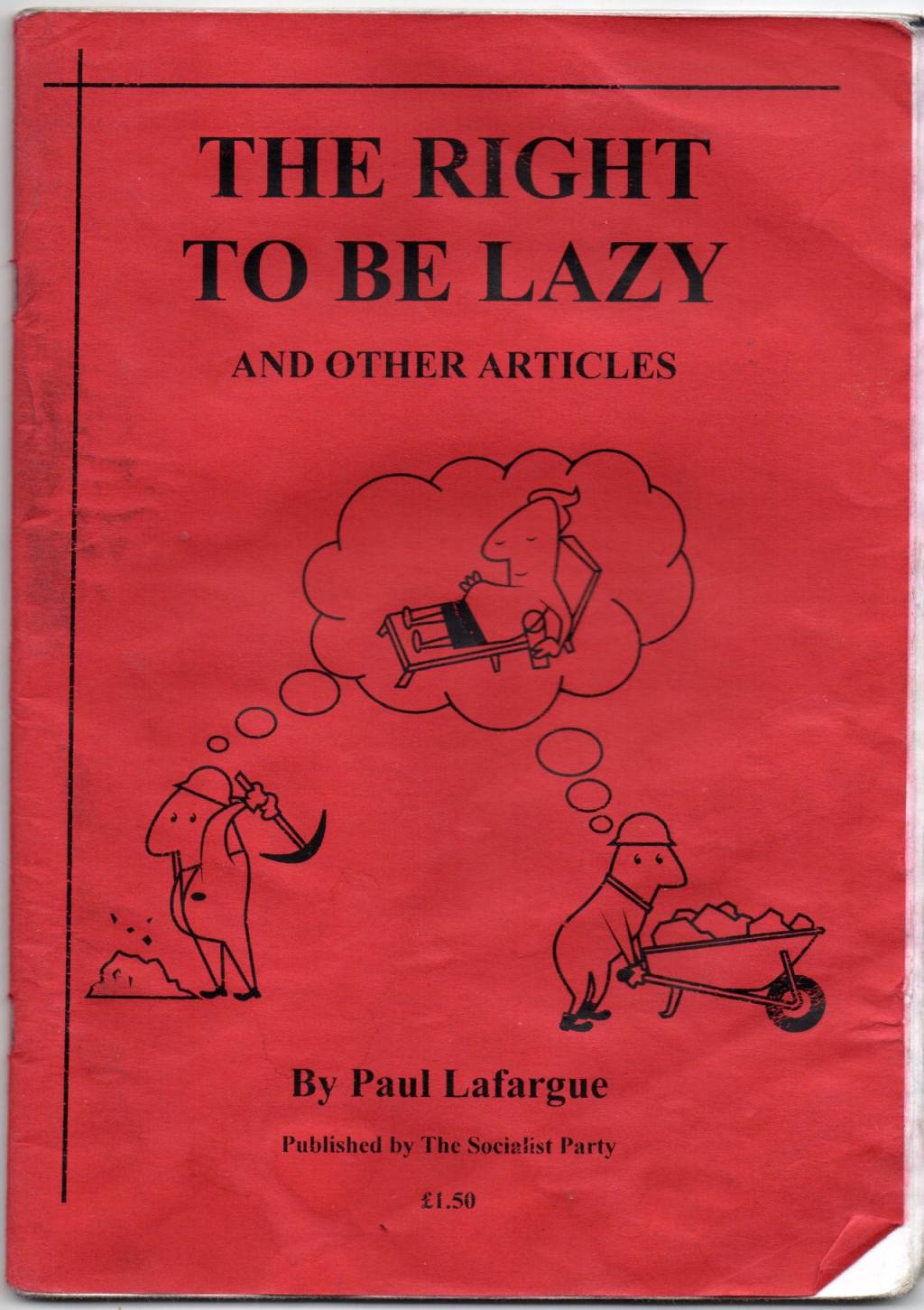
保尔·拉法格著《懒惰的权利》
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则说道,“那好吧,把工作时间缩短,重新分配闲暇”,很多工作其实是对资源和人的浪费,应该让技术进步带来的剩余从资本积累转向全社会的自由闲暇,促进人际关系、社区自治和个体创造力的复兴。
弗朗哥·贝拉尔迪(Franco Berardi)摇摇头:“何止是时间,我感觉身体被掏空了!”工作已经让人陷入“无法呼吸”的焦虑与孤独状态,他主张“灵魂的出走”,即通过诗意、慢节奏、社群共振来抵抗资本对生命的全面占有。对贝拉尔迪来说,资本主义的终极危机不是经济萧条,而是人类社会普遍的“呼吸困难”与情感衰竭。
凯西·威克斯(Kathi Weeks)说道,“别光听男人的,应该听听女人怎么说!为什么‘有工资的工作’才被承认,而家务、照护、情绪劳动等却被视而不见?”我们谈论“拒绝工作”时,必须把性别再生产的结构性不公列为核心议题,“我们女人不光要争取就业权,也要争取‘拒绝工作的权利’!”
不过,尽管思想家们的批判不绝于耳,现实却是工作时间并未如预期大幅减少,反而出现“工作殖民”与社会的两极分化。凯恩斯曾预言“技术进步将让人们每周只需工作十五小时”,剩下的时间可以用于艺术、思考与享受生活。然而,技术红利更多被用来扩张消费与产业,“闲暇社会”并未到来。许多思想家高估了工作衰落的趋势,却低估了现代社会维持工作中心地位的能力。正如C. 赖特·米尔斯指出的,人们总是把某种工作与另一种工作进行比较,却很少对整个工作世界与其他组织方式进行比较并做出判断。
“拒绝工作”不等于懒惰
在这一背景下,大卫·弗雷恩的《对工作说不》以极强的田野感和伦理敏锐性,直击现代劳动体制的“合理性”神话,将“拒绝工作”从激进话语边缘带到学术和公众讨论的中心。弗雷恩继承了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深刻分析,发展了高兹对自主活动和闲暇空间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的探讨。本书有两条主线:一是对“工作”这一概念在思想史话语中的梳理——从马克思对劳动异化的诊断,到各种“后工作”(post-work)或“工作终结”思想的现代变体;二是对现实中那些选择“拒绝工作”的人的质性访谈与生活观察。
弗雷恩沿用高兹的定义,将工作界定为“一种为了工资而从事的活动”。它是在特定的“岗位”上进行的活动,换言之就是“上班”。除了为赚钱而劳动外,还有两种常见的劳动形式,一是“为自己工作”,例如家务劳动、医疗照护、子女教育等;二是“自主活动”,即由人们自主发起的、源于有意识的自我选择的活动。自主活动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或某个特定目标,而是人们自己所定义的“真、善、美”。与保尔·拉法格的观点不同的是,弗雷恩强调,批判工作并不等同于为懒惰辩护,而是希望拓宽自主活动的空间。而现实是,“人们本应用于参与政治活动、沉思、欢聚和庆祝,以及自发享受的时间,纷纷被资本自由对商业生产和消费的狭隘关注所取代”。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抵抗这种宿命呢?弗雷恩把理论的目光下移到具体的人和日常的实践上,去观察那些“拒绝工作”的人——他们为什么拒绝,拒绝之后怎样生活,“拒绝”是否可能构成一种公共性的替代方案。读者可以从他对诸多个案的描写中看到,这并非抽象的反思,而是与身体、债务、情感和社会保障紧密相连的现实抉择。
弗雷恩研究了英国一个“闲人联盟”成员的生活。其中有人选择辞职,去旅行或写作;有人选择做一份收入较少但自主性高的兼职;有人减少工作时间;还有人选择了斯科特式的“日常反抗”,用一些隐蔽的策略来“拒绝”——不加班、不做无偿额外劳动,也许还有当下中国职场流行的“上班恶心穿搭”。当然,失去稳定收入之后,降低消费水平并且依靠家人、朋友、社会福利的帮助以及共居资源的支持,就成了大多数人的普遍选项。
将“拒绝工作”的思辨带回到普通人的日常处境之后,弗雷恩发现,那些自愿减少工时、转向兼职、追求慢生活、选择非典型就业,甚至“躺平”的人,并非我们想象中的“懒惰者”或“逃避者”,他们往往有着清晰的生活理想和自主价值观。他们的经历打破了“只有工作才有尊严和安全”的社会预设,展示了另一种生命可能性:通过主动控制工作时间和内容,获得更多的自我决定与闲暇,从而实现生活的意义感。
把个案拉远一点看,本文开头的几个问题会出现一些共同的答案:
钱从哪里来?光靠“清贫即自由”不现实。有人靠兼职工资、过去的存款或伴侣收入维持;更多人把日子织成拼图:少量临时工、相互帮忙、借贷与国家福利交织。
怎么花钱?降低消费水平,把“体面”改写成“足够”。把愉悦的来源从高耗费的商品型快乐,转向时间丰裕与自给能力带来的安定感与掌控感。
怎么过日常?多出来的时间并非虚无:照护家人、参与志愿活动、发展技能、阅读与学习——这些“非工作”事务重新被他们当成社会性的内容。
从思想史到生活现场
弗雷恩不仅关注个体层面的“拒绝”,还敏锐揭示了这一行动的结构性障碍。工作伦理不仅塑造着“勤劳”“奋斗”的社会评价体系,也通过对“无业”的污名化和妖魔化,维护了社会秩序。一个没有正当工作的成年人往往被贴上“懒惰”“无用”的标签,“这种将人群二元对立从而实现分化的方法,一直是社会规训的常用手段”。工作已经被内化为一种存在方式,它通过制度体系、利益分配、文化规范等渠道进入到人的主观经验中,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有用”或“成功”的重要尺度。如米尔斯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所言,“在科层制度对自由和理性的种种巧取豪夺之中,白领们不过是将社会捆绑在一起的巨大的权威链条上的可替换的一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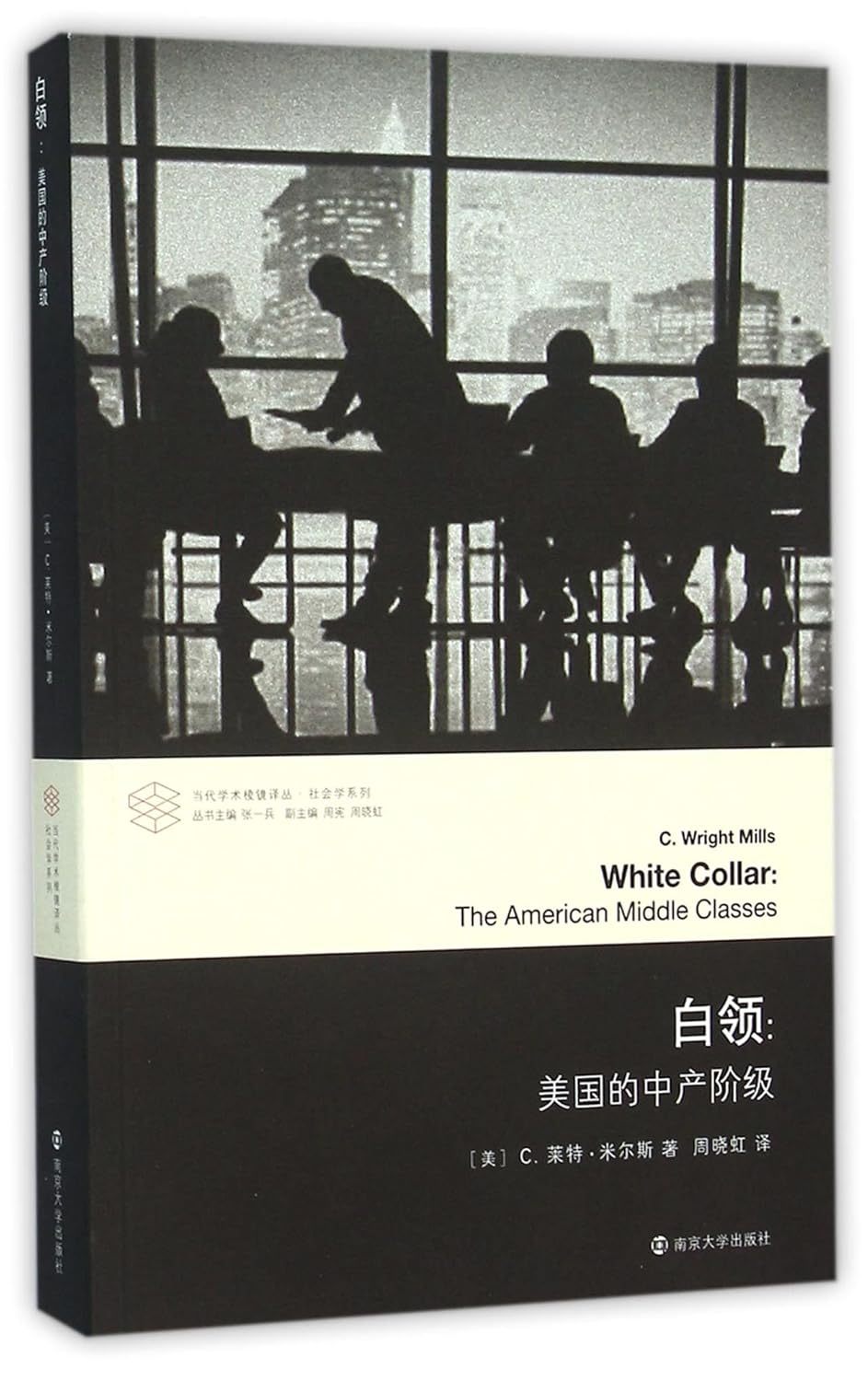
米尔斯著《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
现代社会高度依赖于对工作的崇拜:不仅经济结构、福利制度和社会评价体系都围绕“工作—报酬—消费”而运转,甚至许多左翼话语本身也陷入了“就业至上”的逻辑困境,忙于争取“更多的就业岗位”而非“减少工作对生活的支配”。“拒绝工作”的瓶颈,不仅来自经济层面上的物质压力,更来自深刻的身份焦虑和社会认同危机:离开了“稳定工作”这个标签,个体很难获得家庭、社会的正面评价,甚至面临自我价值的怀疑。
弗雷恩还以高度的敏感性关注到“拒绝工作”运动中的阶级、性别、种族差异。例如,只有具备一定物质资本、社会资源或文化资本的人群才能优先实现“自愿减少工作”,而对于低收入、缺乏社会保障的人而言,被迫不工作意味着失序、贫困、耻感与边缘化。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能看到一条与爱德华·格兰特(Edward Granter)“工作的终结”相呼应的路线:技术进步并不自动带来时间的解放,政治安排才是把解放转化为普遍福利的关键。弗雷恩提醒我们:要让“拒绝”成为公共想象的一部分,需要政策的勇气与文化的迁移。
不过,本书的田野样本以英国中产为主,较少关注被迫失业者和底层劳动者。书中的故事大多来自那些有可能“拒绝工作”的人,他们拥有一定的储蓄、有替代的职业技能,或者可以借助关系网。弗雷恩把“拒绝”作为一种可见的实践来考察,而不是大多数人的即时选项。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细看那些“断点”——疾病、家庭危机、倦怠、伦理觉醒——如何把人推向或拉回工作体系;缺点则是对更脆弱群体的关注不足,例如那些因被剥夺选择而被迫接受低薪长工的人群。应当承认,“拒绝工作”的资格并不均等。中产以上阶层可以把辞职或减工当作自我重整的机会,而底层劳动者的“拒绝”则很可能意味着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这里隐含着一种“可转换性”的不公:当“拒绝”被某些人消费为自我实现的手段时,它也有可能成为另一种象征性资本的展示。
从理论到实践再回到理论,我们会看到,如果把一切与谋生相关或者与亚里士多德式的“沉思”相对的活动都混称为“工作”或“劳动”,可能存在一个分类的陷阱。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提供了一把更清晰的刻度尺:“劳动”(labor)—“工作”(work)—“行动”(a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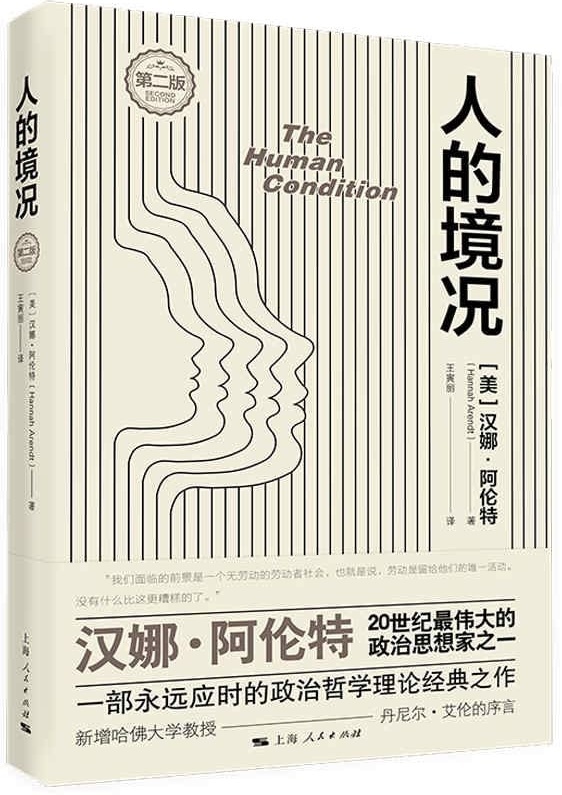
汉娜·阿伦特著《人的境况》
“劳动”是属于生物世界的,服务于生命维持与循环的动物性需要,产出即产即消,主体是被必然性牵引的“动物劳动者”,“劳碌一生……是比死亡更糟糕的命运,因为它使人变成类似被驯服的动物一样的东西”。“工作”是属于物质世界的,面向器物与制度的耐久世界,遵循“手段-目的”的工具理性牵引。在“工作”的场域里,“每个东西都必须有用,也就是,必须让自己成为获得其他什么东西的工具”。“行动”才是真正属于人类世界的,它发生在他者之间,以言说与共同行动在公共空间中开启新的关系与秩序,“去行动,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意味着去创新、去开始,发动某件事”。用一个比喻来说,做饭是“劳动”,制造锅碗瓢盆是“工作”,而在社区大会上说服大家改革伙食制度是“行动”。
阿伦特的区分的重要性在于:近代以来,“社会”逻辑的扩张让工作占据了公共领域——就业率、产出、福利被当作政治的全部,政治被降格为管理,“行动”的场域随之凋敝。与马克思以“解放劳动”为核心的谱系不同,阿伦特把“行动”置于人类自由的最高层次:有了面包与器物之后,仍需公民与城邦。因此,任何“拒绝”的设想,不能仅仅停留在缩短工时、争取闲暇,关键还在于为“行动”腾出空间,让人们成为“彼此中的人”而非“岗位上之物”。
阿伦特的分析为弗雷恩的“拒绝工作”增添了一重尺度。当我们说“不”之后,我们在哪里、如何、与谁共同出场?只有把“行动”的舞台请回来,“拒绝”才不至于沦为私人时间的重排,而能转化为更深厚的公共生活与政治想象。
“拒绝工作”不是口号而是具体姿势
《对工作说不》以极强的现实感召力,点燃了当代青年对于生命意义的重新想象。它揭穿了现代工作伦理的神话,呼吁我们认真思考,“有意义的生活”是否必须以一份正式工作为前提。“拒绝工作”不是反对工作本身,弗雷恩也承认很多工作能给人带来愉悦和趣味,而是拒绝让工作主宰生活。“拒绝工作”不是要让所有人变成懒汉,而是追问“工作为何存在?为何如此重要?为何不由我们自己来决定?”
近年来西方出现的“大辞职潮”(Great Resignation)以及一些国家试行每周四天工作制的探索,表明“拒绝工作”的思潮已从学术理念延伸到现实运动。将这一视角引入当代中国现实,有其独特且更具挑战性的意义。2007年,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刚好赶上工作形态发生戏剧性变化的十几年。平台劳动、零工经济、按需服务与算法管理,既提供了灵活性,也制造了新的依赖。弗雷恩所描述的“被工作的全面殖民”在这个时代找到了新的舞台:不再只是工厂的时间表,而是手机上的提醒、平台上的评分、被算法裁剪的工作窗口。受雇者哀叹下了班也无法放下工作,自雇者则焦虑不安,惶惶不可终日。就像打工人张赛所说的,“在工厂时我老做梦,老是梦到去送外卖,因为送外卖自由……送外卖时又经常梦到自己在做工厂,因为做工厂稳定”。于是,“拒绝工作”的话语在当代中国显得既更加必要也更加复杂。
西方的“拒绝工作”理论往往预设工作和生活的二元划分,而在中国这样的集体主义与家庭主义社会,工作不仅是一种单纯的经济活动,更是家庭、身份、责任、关系网络的复合体。中国社会并未接受新教伦理的洗礼,中国的“工作中心主义”不仅仅是现代性的产物,更与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与儒家伦理密切相关。在中国,对于“拒绝工作”的社会容忍度会比西方社会更加脆弱,反抗者所要付出的社会成本更高。
当下关于“内卷”“躺平”“上岸”的讨论,既是对高昂生活成本与未来不确定性的无声抗议,也可能被简单化为个人态度,而忽视了结构性的深层问题。当大量青年拼命挤进“体制内”,这既是对稳定与安全的渴望,也是对高强度、不确定工作的消极反抗。这种“为了工作而工作”的普遍焦虑,正是弗雷恩批判的“工作殖民”的极致表现——即便工作内容已高度机械、无甚意义,但依然被当作通向社会认同和阶层跃升的唯一通道。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质疑“奋斗叙事”,转向“小确幸”“社区互助”“时间自主”“低欲望生活”等具体的反抗实践。尽管这种尝试经常被批评为“犬儒”“佛系”“消极”,但也反映出对社会主流工作伦理的边界试探与细微触动。当然,直接的集体抗争风险极高,但“拒绝工作”却可通过微观日常的“柔性抵抗”扩散。例如频繁跳槽、打零工、“间隔年”、数字游民,都是拒绝被“单位人”或“996”锁死的尝试。不过,这些实践既是有力的也是脆弱的。去年,我在工作十七年之后决定“对工作说不”,成为一名以研究、写作、翻译为生的独立学者,深刻感受到这种抵抗的代价——既难以获得各种社会保障的基本权利,更会遭遇强烈的认同丧失与社会隔离。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对别人解释“独立社科学者”这样一个在中国几乎不存在的行业。正如弗雷恩提醒我们的,只有当“拒绝工作”成为可被选择的社会权利,而非生存危机或道德污名,真正意义上的“后工作社会”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开始讨论就是改变的第一步
《对工作说不》不仅是对工作崇拜的有力反叛,也是对“何为美好生活”的深刻追问。它将“拒绝工作”从边缘亚文化转化为一场有关身份、制度与意义的公共讨论。思想家们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后工作社会”的轮廓:其中闲暇、照护、创意、公共性、社群关系等将成为新的价值中心。而弗雷恩的贡献则是让这些宏大设想落地到普通人的日常经验,发现那些自觉拒绝“工作殖民”、勇敢追求自我生活的个体其实就是未来社会的先行者。
阅读这本书,是一次思想的散步,也是一次公共想象的起步。对我们而言,理解和吸收“拒绝工作”的精神,并非意味着提倡“躺平”,而是鼓励每一个人敢于追问:“我的时间和生命到底归谁所有?”它呼吁所有利益相关方共同思考和讨论:如何让每个人都能有条件、有尊严地选择自己的生活节奏和价值?如何推动社会文化、工作伦理、经济结构、家庭关系的制度性重构,使“非工作”不再等于“失败”与“危机”,而成为自由与自我实现的组成部分?正如弗雷恩所言,改变的第一步就是“敞开讨论的大门”。他呼吁我们“加入言辞之战”,保卫我们的想象力。这种讨论所用的,“不是责任和义务的词汇,而是自由的词汇”。
弗雷恩强调,这样一种乌托邦式思维的重要性在于“解开当下的束缚”,帮助我们获得一个珍贵的视野,超越那些太过于熟悉的可能性,“这并不意味着要为社会变革提供并强加一种预先设定好的蓝图,也不意味着减少工作是包治社会百病的药方”。读完这本书,我们可能不会立刻辞职,但会更清晰地看到工作如何塑造我们的时间、习惯与价值观;我们也会意识到,只有将个人的觉醒与制度与文化的重塑同步,才能真正让“劳动”和“工作”退位成手段,把“行动”请回到舞台中央。“拒绝工作”——在最好的意义上——不是懒惰,而是对社会如何定义时间、劳动与人的价值提出质问。这样的质问,值得成为公共讨论的一部分,毕竟,“一个无法想象以商品关系之外的方式来实现社会团结和目标感的社会是极其可悲的社会”。
未来的中国社会,或许会越来越多地见证“拒绝工作”的想象与实验。对“工作中心主义”的温和叛逆、对多元生活可能性的探寻,终将成为新一代公共讨论的主题,马克思期待的“以每个人自由时间的丰富为社会财富的尺度”,也许终将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