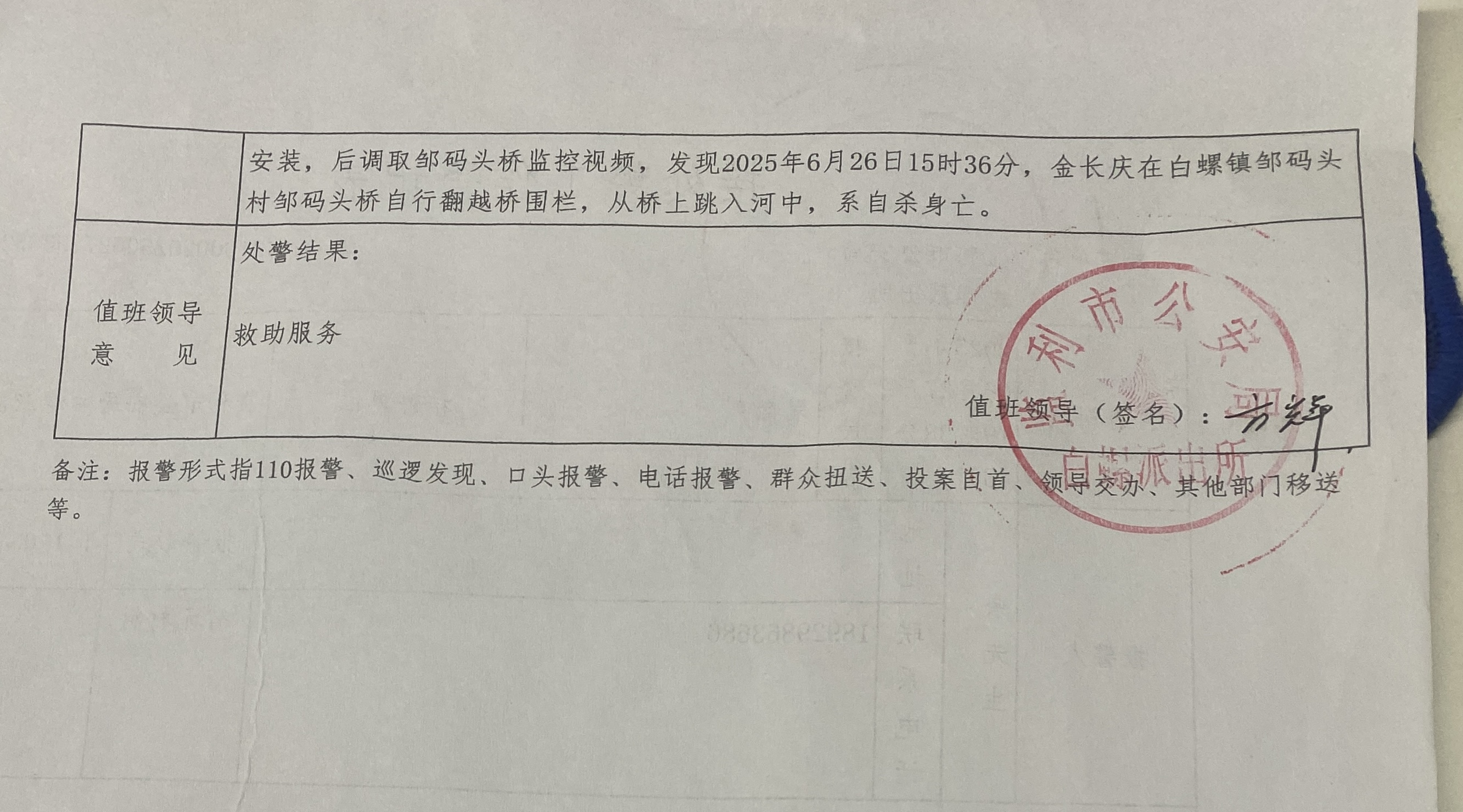蔡萌评《妇女一直在工作》|在历史坐标中审视妇女劳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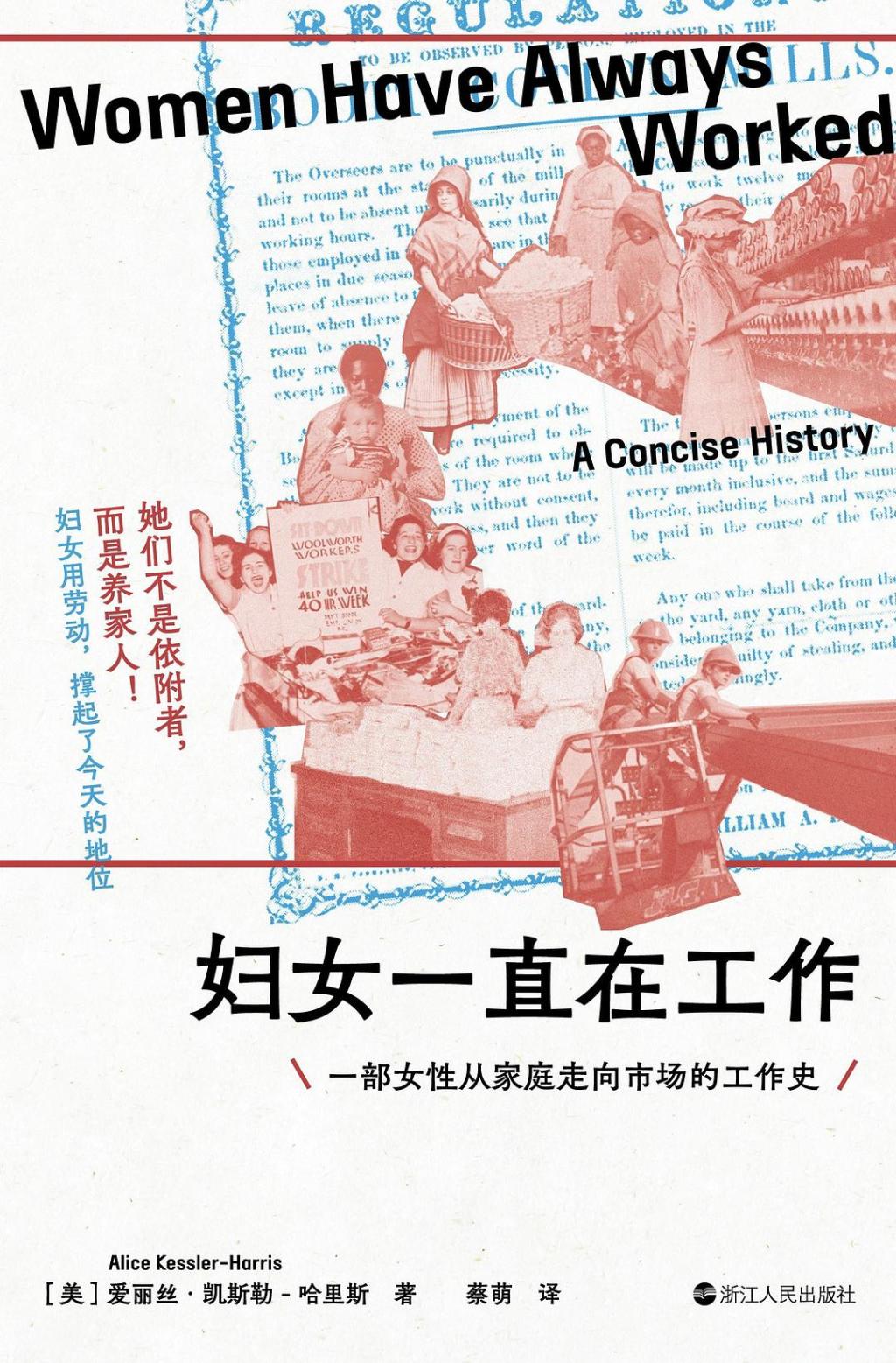
《妇女一直在工作:一部女性从家庭走向市场的工作史》,[美]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著,蔡萌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5年8月,340页,68.00元
在二十世纪美国妇女史与劳工史研究领域,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Alice Kessler-Harris)的名字具有标志性意义。她多年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以及妇女和性别研究中心,曾担任过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AH)主席,还曾到访中国多所高校,极富成效地推动了中美史学界的对话与合作。作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劳工与妇女史研究专家之一,她在1982年出版的《出门工作》(Out to Work: A History of Wage-Earning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一书被公认为该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该书系统梳理了美国妇女从事工资劳动的发展历程,以其鲜明的问题意识、开创性的研究视角和多维度的分析框架,至今仍是妇女史领域的必读经典。值得注意的是,在《出门工作》出版前,凯斯勒-哈里斯就已通过《妇女一直在工作》这部“精简版”通史,构建起其研究妇女工资劳动的核心理论框架。这两部著作在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上保持着显著的连贯性和一致性。相比较而言,《妇女一直在工作》这部“精简版”通史更有助于我们清晰扼要地把握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妇女史研究的学术脉络,理解该领域若干经典议题的演进轨迹。
一、家务劳动的价值
《妇女一直在工作》开篇伊始,作者借由霍利斯·布什内尔的哀叹,精准定位到问题的发轫处:“生产与再生产的割裂”与“家务劳动的无偿化”。前工业化时代,家庭是一个从事生产性劳动的场所,所有家庭成员共同劳动,共同构成家庭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之后,“生产性劳动”转移到在家庭之外,进入了市场,变成了可见的、带薪水的“工作”,从而让男性一跃成为家庭收入的最主要来源;保留在家庭之内的是“再生产性劳动”,包括家务劳动、养育孩子、照顾病人和老人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家务劳动,变成了不可见的、无偿的、妇女专属的任务。
上世纪七十年代,海迪·哈特曼、艾里斯·扬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正是从这两点出发,踏上了批判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旅程。按照她们的解释,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相互强化,构成了一整套压迫系统,其共谋的逻辑在于:一方面,父权制通过将妇女承担的“再生产性劳动”无偿化和私有化,成功地为资本主义转嫁了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资本主义通过将“有酬的生产劳动”划归市场,将“无酬的再生产劳动”归于家庭,反过来又强化了父权制的物质基础。
强烈的批判导向,让七八十年代的绝大多数女性主义文本宛如慷慨激昂的战斗檄文。虽然《妇女一直在工作》的底色也是批判意味的,但从字里行间可以明显感受到,作者在极力收敛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身上的那种犀利锋芒,而是试图站在历史的高度,用一种冷静、克制而又不失温度的方式,讲述劳动形式、家庭形象和妇女职责在进入19世纪以后发生了何等剧变,以及家务劳动在其中发挥了何等重要的社会价值。在这一点上,作者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结论是一致的,认为家务劳动虽然不直接生产产品,但却生产并再生产了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劳动力和社会秩序。因为其一,妇女“开朗热情”,“在家庭中传播幸福”,“负责家庭的平稳有序运转”,为丈夫提供足够的情绪价值和生活服务,保证了他们“生产性劳动”的可持续性;其二,妇女抚养和教育孩子,“既要符合神圣的价值观,也要满足未来在一个不信神的、竞争的世界中谋生的需求”,换句简单的话说就是,妇女通过抚养和教育孩子,在家庭内部实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文化的内化。
二、妇女的公共参与
妇女没有政治权利,不代表她们没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和渠道。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妇女史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她们认为,革命和建国初期的共和主义意识形态强调“母亲”在传承美德、教育未来公民和维系共和国方面的重要意义,从而给妇女的家内行为赋予了丰富的政治意涵。内战前,大量妇女在社会的默许甚至鼓励下,投身到治理犯罪、酗酒、卖淫、贫困等社会问题的改革运动中,因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妇女的某些“专属特质”,使得她们在与“道德”有关的改革领域拥有与生俱来的优势和责任。这些妇女史家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妇女的适当领域”、“专属特质”等传统观念虽然阻碍了妇女获得政治权利和平等,但经过特定的、有弹性的解释后,却能为妇女开辟一条参与公共事务、发挥社会影响力的替代性通道。
本书第四章系统性地整合了七八十年代妇女史家的研究成果。作者先描述了美国内战前的妇女改革者如何在不逾越“适当领域”的前提下,创造性地参与社会问题的讨论和治理。随后,作者把重点放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时代,深入剖析了这一时期妇女活动家的策略突破——她们把“适当领域”概念的弹性解释推向极致,让自己的身份从“母亲”跃升到“社会管家”,让自己的职责范畴从道德改革拓展到“为整个国家谋福利”。这种战略性的身份重构与职能拓展,为妇女的职业发展开辟出现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进步主义时代涌现出大量新职业,这些职业的特征是帮助性的、服务性的、福利性的,包括工厂巡视员、童工调查员、护士、办公室文员、人事专员、图书管理员等等,成为初入职场的妇女的新选择。大学、研究所、医学院、法学院和各种职业能力培训机构也对妇女敞开了大门。然而,正如作者在第四章末尾所提出的,当“适当领域”的弹性被拉伸到极致之后,摆在妇女面前的必经之路就是打破关于家庭、母性、美德的传统预设,勇敢地跨出“适当领域”,真正去攻占男性价值观的堡垒——市场。
三、劳动力市场的性别隔离与分层
继“生产与再生产的割裂”与“家务劳动的无偿化”之后,本书把批判资本主义父权制的视线转向劳动力市场,重点讨论劳动力市场的性别隔离与分层。在第三章和第五章中,作者花了大量篇幅来描述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面临的重重困境:她们从事的工作要在社会公认的“妇女的适当领域”之内,要符合社会对她们的期待;她们被迫接受低工资、低技能岗位,因为社会对她们的定位是劳动力市场中的“次级商品”、“弹性后备军”,她们的收入只能作为家庭的补充,是暂时的、次要的,绝不能成为家庭的支柱;她们大多只能从事护理、教育、服务业等工作,因为这些工作被视为“母职的延伸”,是“妇女的适当领域”;她们在职场晋升中面临“玻璃天花板”,管理岗位占比远远低于男性,因为资本主义父权制将权威角色建构为男性特质,而妇女则早早被预设为只能充当“辅助者”。
在1981年本书的初版中,作者讨论的时间跨度有一百多年,从十八世纪后期工业化最初起步,一直延伸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期间,虽然妇女经历了进步主义时代和民权运动时代的多次赋权;虽然她们在二战期间还曾短暂打破职业隔离,接管男性的工作领域;虽然二战后在经济社会环境、技术革新、家庭规模、生育率等因素的推动下,她们的就业人数迅速攀升,就业机会快速增长,但从1975年的职业结构来看,性别隔离的色彩依然浓厚,妇女集中在文员、服务员、家政工、教师、售货员、打字员、会计、护士、营养师、电话接线员等职业,而这些职业本来就被社会公认是“妇女专属”的。
进步时代的一系列保护性劳工立法,限制了女工的工作时间、最低工资和工作条件,看似改善了女工的处境,然而作者强调指出,其实际效果却是降低了女工的吸引力,使妇女在与男工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更严重的是,这些只保护女工不保护男工的立法,本质上是把妇女归为一种特殊的劳动力类别,助长了劳动力市场的性别隔离和分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紧密出台的一系列公共政策,包括所得税立法、养老保险、失业救济、育儿补贴、单亲家庭补助、儿童福利政策等等,其制定的基础都是预设妇女是家庭责任的主体,宣扬“回归家庭”的价值导向。这些深刻的分析,呼应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对美国福利政策背后“母权主义”逻辑一贯的批判——这些表面“赋权”的经济援助,其实是资本主义父权制的精密装置,它不仅强化了妇女作为“家庭照料者”的社会角色,而且还塑造了一种“受助妇女(福利依赖者)VS.纳税男性(劳动者)”的对立叙事,无助于消除劳动力市场的隔离与分裂。
故事并没有止步于1970年代。在2018年的修订版中,作者特别增补了第六章内容,系统梳理了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的性别平等发展状况。作者指出,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劳动力市场中性别隔离的高墙终于被穿透——传统“妇女专属”职业中的妇女从业比例大幅缩减;在法律、医学、学术等专业领域以及企业管理层中,妇女占比呈现跨越式增长;突破男性堡垒,登上政治舞台的妇女人数也达到历史新高。然而作者清醒地指出,这些进步并不意味着妇女已经摆脱了资本主义父权制的结构性束缚。家庭责任和带薪工作的矛盾仍是当代妇女面临的普遍困境。针对这一难题,作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解决方案,包括推动家务劳动市场化、建立社会化的再生产服务体系(如普惠性托育机构)等制度创新,旨在帮助妇女真正超越“生产性/非生产性”的二元框架等等。这些见解为探讨当代性别平等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指引。
四、妇女之间的共性与差异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妇女史研究的主题,如果用一个词概况的话,一定是“姐妹情谊”。早期妇女史学者关注两性之间的对立和公私领域的分离,强调传统性别秩序妇女的禁锢和压迫,注重探讨妇女的主观能动性,以及由姐妹情谊所构成的独特的人际关系网络和性别文化。她们立论的前提是不同阶级、种族、族裔、地域妇女之间的共性。例如,卡罗尔·史密斯-罗森伯格研究“女性世界”,认为十九世纪的美国妇女是通过共享的日常经验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南希·科特研究1780到1835年新英格兰地区的妇女,也把妇女视为一个拥有共同身份、经历和使命的共同体,强调妇女是按性别分类的,性别决定了她们的情绪、能力、目标和潜在的成就。
然而,本书的论述重点并非妇女之间理想化的“姐妹情谊”,而是妇女内部的巨大差异和分歧。作者想要告诉读者:中产阶级妇女可以顶着“共和母亲”的光环,在备受尊敬的目光中守卫社会道德,而数量更多的农村和城市贫穷妇女而因经济压力被迫率先迈进劳动力市场,从事报酬最低、强度最大的工作;富裕的中产阶级妇女可以享受技术革新带来的便利和舒适,而农村和城市贫穷妇女却因经济拮据而继续承受传统家务的重负;中产阶级妇女可以在职场努力打拼、追求性别平等,而底层妇女可能还要同时与种族歧视作斗争;中产阶级妇女可以通过家务外包给底层贫穷妇女来实现自我解放,而这种转嫁压迫的机制则进一步加剧了底层妇女的生存困境。从美国的社会现实来看,贫富之间的分化往往又与种族、族裔高度重合,因此,作者考察妇女内部的巨大差异,实际上构建了一个涵盖性别、阶级、种族、族裔等多维度的分析框架。
在本书初版问世的1981年,这样的多维度分析框架可谓是开风气之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妇女史研究的关键转型期。在保守政治回潮、黑人女性主义批判白人中心论、多元文化主义思潮兴起的多重背景下,八十年代以后的妇女史学界逐渐开始突破“姐妹情谊”的单一叙事模式,研究重心从妇女之间的共性转移到差异性上,并最终在八十年代末形成“交叉性”这一新的研究范式。从妇女史研究的发展脉络来看,本书在八十年代初就尝试打破单一维度分析,系统阐释性别、阶级、种族和族裔的动态互构机制及其对差异化权力结构的形塑作用,其方法论的创新性和理论前瞻性是不言自明的。
在当下社会,关于妇女劳动议题的讨论往往充满张力。“职场妈妈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35岁女性职场困境”“丧偶式育儿”等话题动辄引发全社会热议和争论。在这种众声喧哗的舆论声中,本书尤为可贵之处在于,它摒弃了当下常见的情绪化表达,通过历史事实的呈现而非价值立场的宣示,为理解当代女性劳动议题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思考维度。它以历史学的视角,系统展现了妇女参与社会劳动的历史进程,还原了不同历史时期妇女劳动形态的特征与变迁,既避免了情绪化的表达,又保持了足够的人文温度。这种学术态度在当前充满情绪对立的讨论环境中可谓一股清流。本书适合所有对妇女问题,以及对劳动历史和社会变迁感兴趣的读者。书中那些普通劳动妇女的真实故事,跨越时空与当代读者的生活体验产生微妙的共鸣。这种共鸣不是简单的情绪感染,而是源于对历史脉络的深刻把握。当读者跟随作者的笔触,在更宏大的历史坐标、更复杂的社会网络中审视妇女劳动议题时,往往能获得超越当下争论的思考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