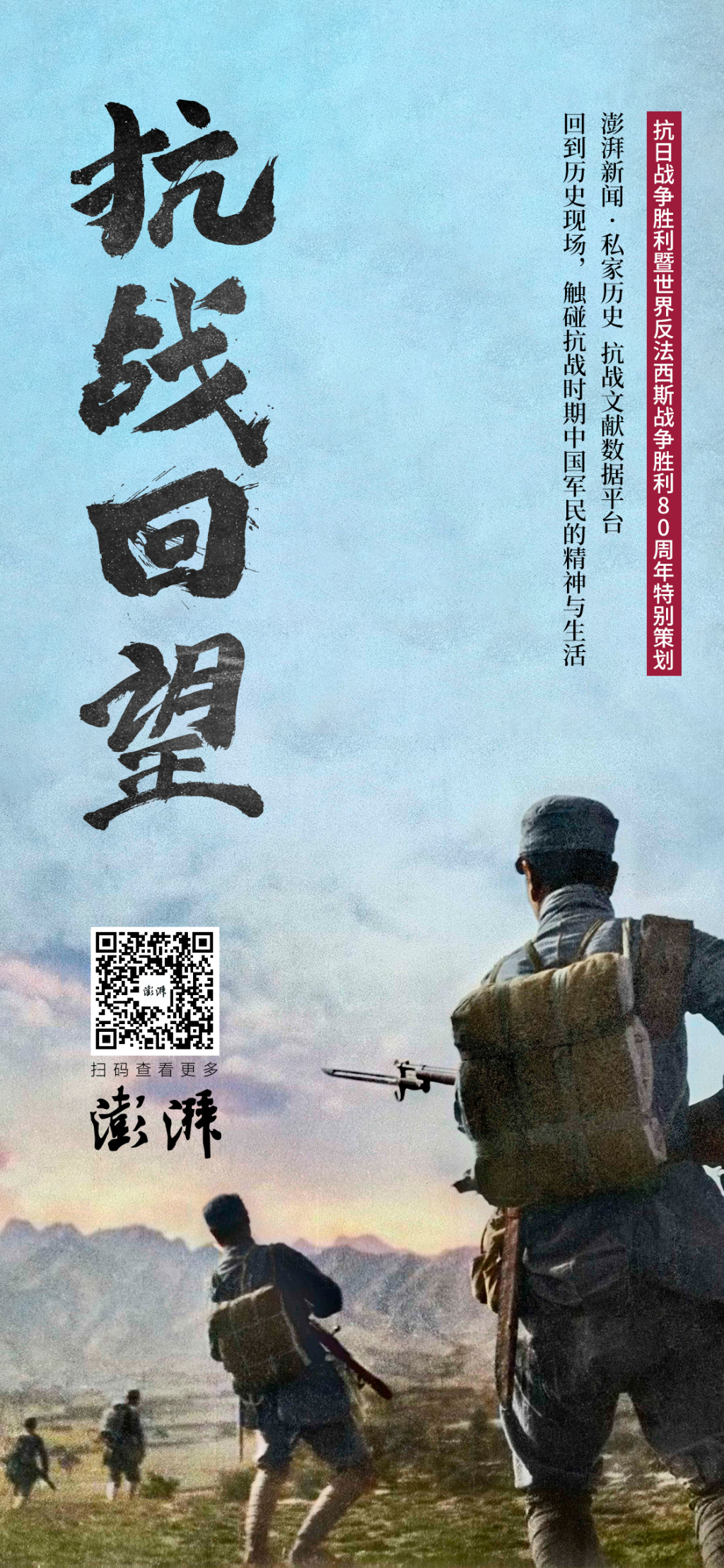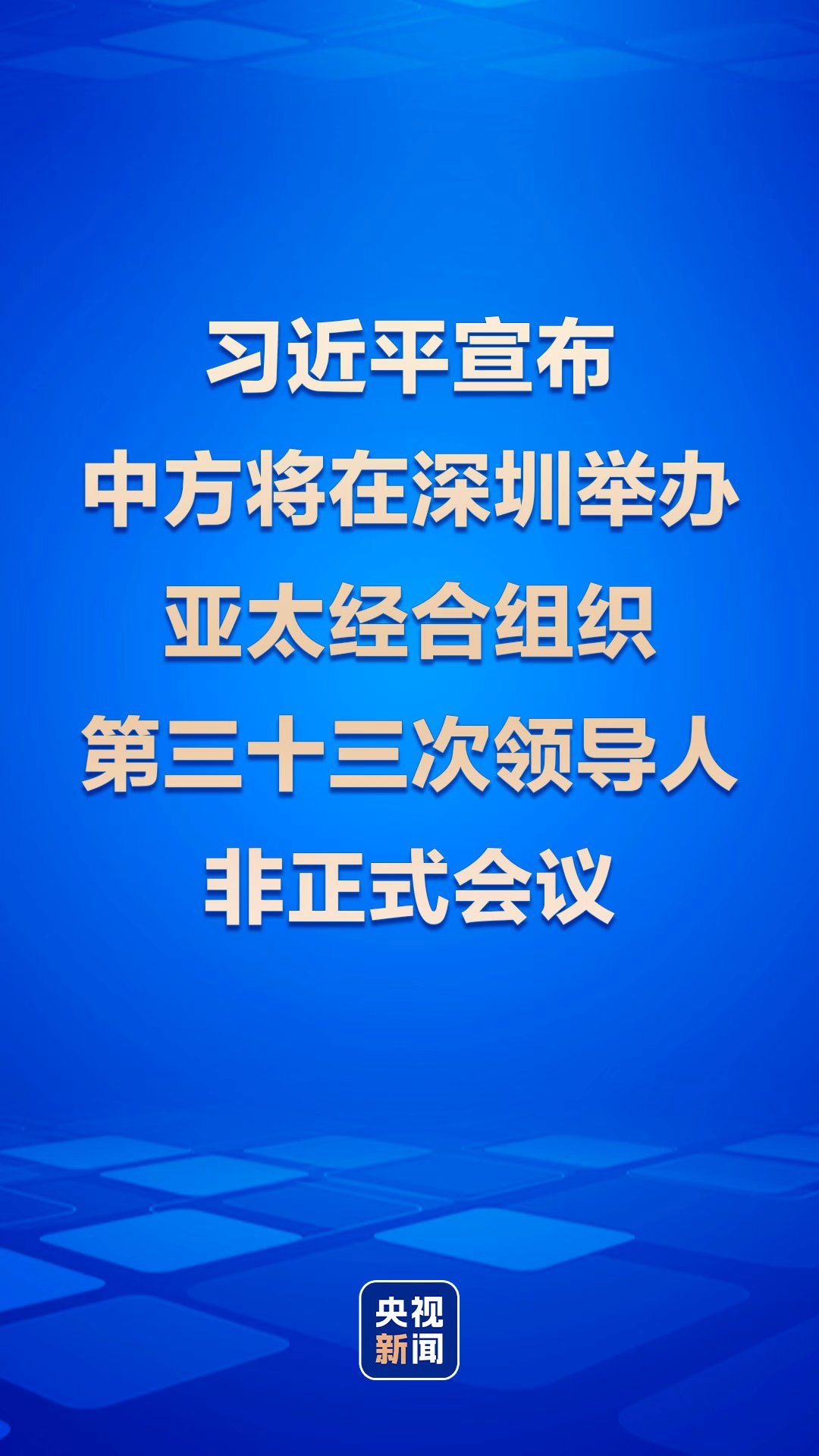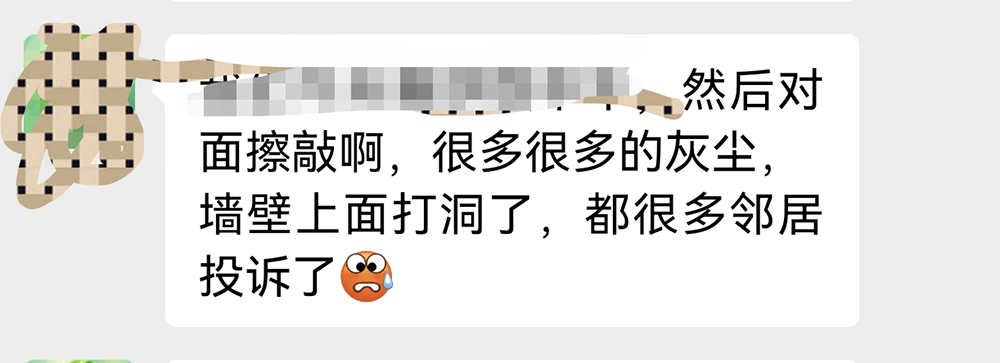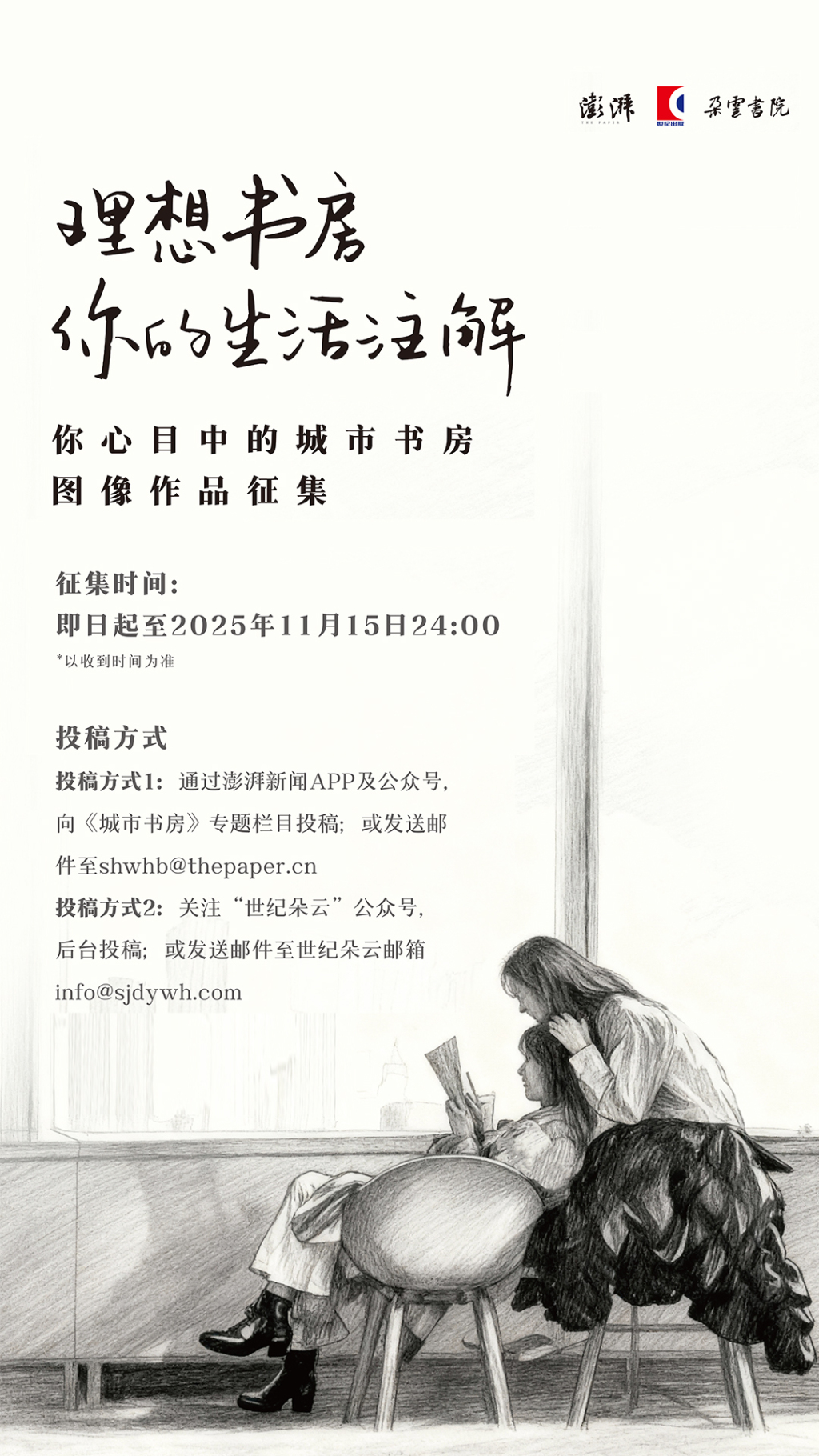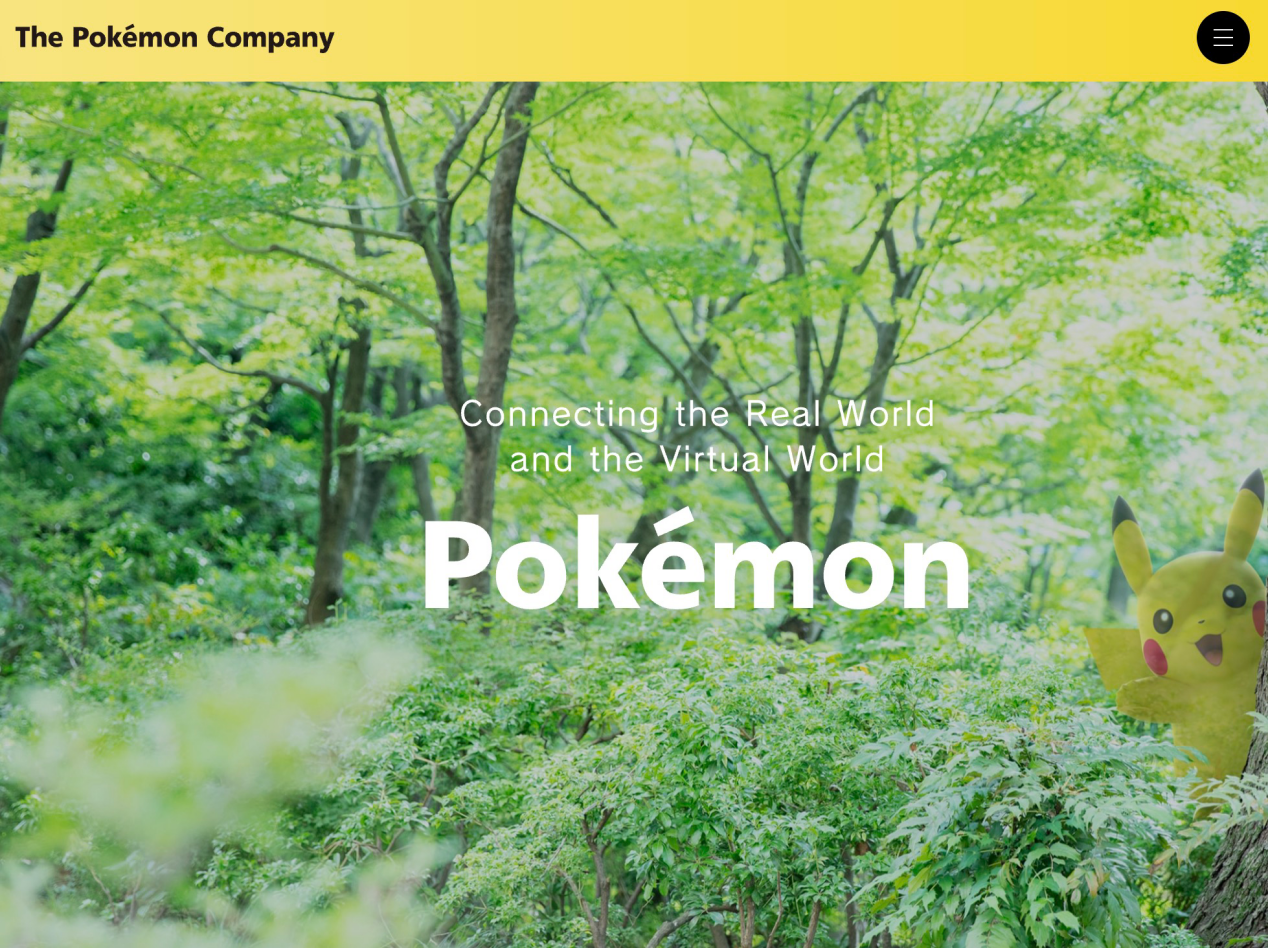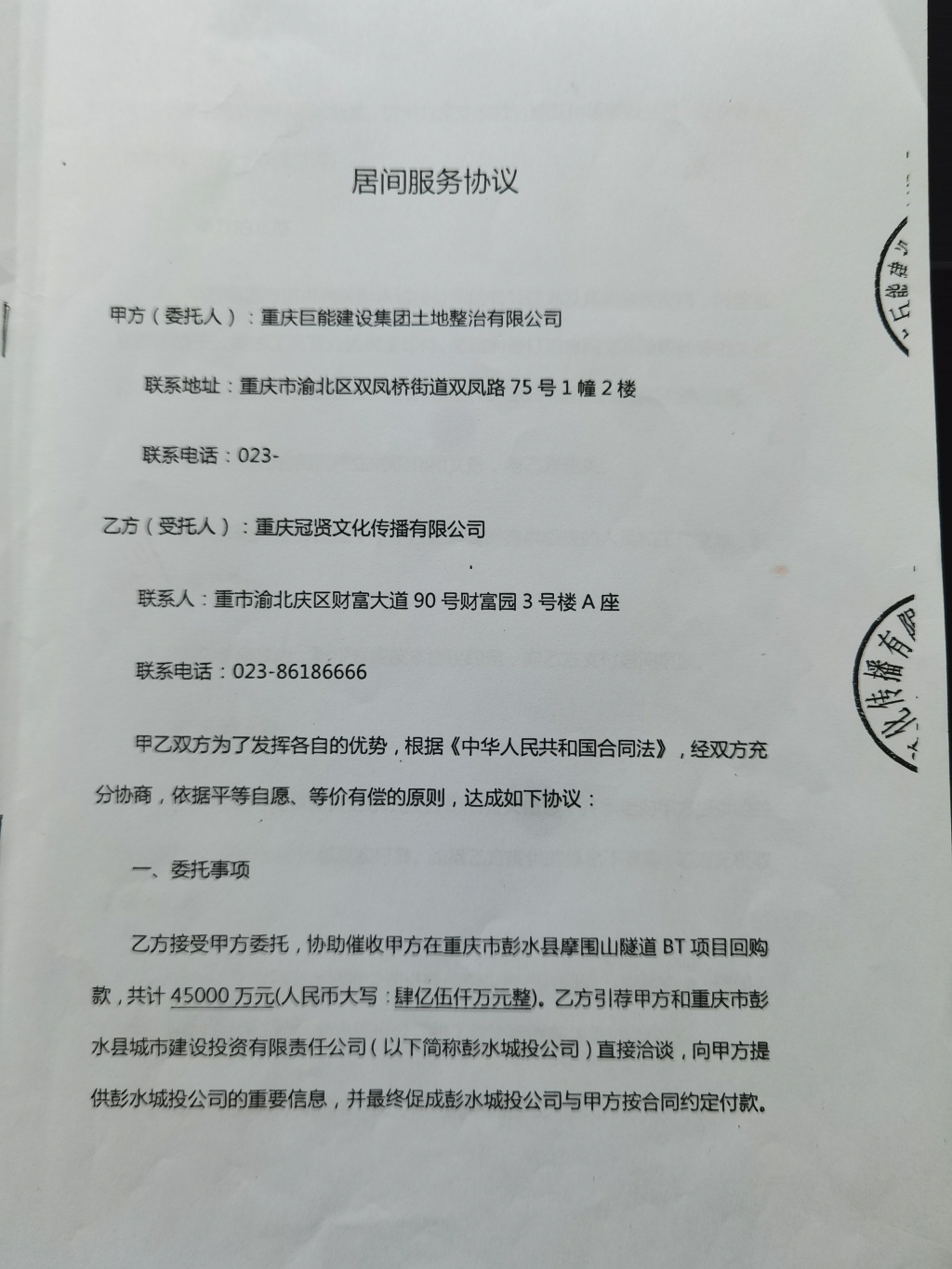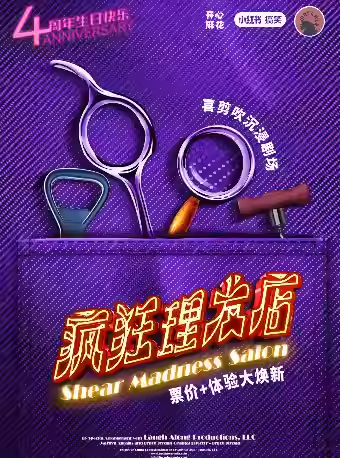《禅师岩记》载二僧率众力抗张献忠兵锋事迹献疑
清同治二年(1863),灌县(今四川都江堰)人陈炳魁写了一篇《禅师岩记》,交代了青城山禅师岩的得名由来,内容是:
禅师岩者,因了空、鉴随而名也。二僧参禅白云洞,明澈心性,慧谙忠义。献贼屠灌时,泰安寺住持僧集众告曰:“贼至矣,寺内数百僧,方隅数千户,非二僧莫保也。”乃延为主席,咸听区画。二僧扼山口,筑垒以御,贼攻之不能入,阴觅间道,毁寺戕僧及居民。二僧闻警急,率众奔山后,奋力击贼者七,今七阵沟其战处也。因众寡不敌,抚膺大痛曰:“负我和尚托矣。”遂触岩死。
呜呼!扼贼山口,智也;击贼山后,勇也;耻负所托而死,忠且义也。设二僧者不溷迹于空门而宣力皇路,不受托夫山寺而擢镇蜀疆,吾知其能据贼、杀贼、必不容贼之入蜀而屠也。且并力击贼,同战同死,较杨展之以倾陷死,于飞之以轻率死,尤为轰轰烈烈,几与唐之张、许媲美焉。予尝稽考遗文,搜览残碣,窃为二僧悲其失传。然营垒故地,历今二百余年矣,而山氓野叟,樵夫牧童尤相以禅师呼之,则二僧忠义之大节,不永辉耀井络哉!后之游息于斯者,亦可观感而兴矣。
禅师岩是青城后山的一处风景名胜,泰安寺是青城山地区佛教寺庙中历史较悠久者,《禅师岩记》中记述的了空、鉴随率众抵抗张献忠军队事迹于他处无载,显出补史之阙、为青城景致增古增色的独特价值,还被论者引为历史上僧兵参战的一个案例。但令人遗憾的是,细究之下,《禅师岩记》所载二僧率众抗张事迹,真实性存疑。

青城山
佛教史籍不见了空鉴随抵抗事迹
由于并未见到记载了空事迹的现存材料,只能从有限的鉴随禅师相关记载入手。目前能见到的最早最详细记载鉴随生平的材料为清代丈雪通醉编纂的《锦江禅灯》,“灌阳鉴随”条载:
灌阳鉴随法师,渝州严氏子,法嗣燕京休尘和尚,得无碍自在定。隐于西山白云洞,四十稔不下山,常受蜀藩隆供。开示偈语,不许纪录。后汉璞密记数则,付剞劂氏,名曰《白云深意》。世寿七十二,于崇祯甲申二月圆寂,塔于太安寺之左。
据此可知,鉴随俗姓严,渝州(今重庆人),嗣法于燕京休尘禅师,曾在西山白云洞修行,四十年不下山。白云洞位于今青城后山地区,地处蓥华山与熊耳山相连的半山弯月形山梁,“岩有三层,层层有洞,大小数约上百”,唐宋时便有僧人依崖架屋在此修行。鉴随常得到明蜀藩王的隆供,说明其应当是明末四川地区较有名望的禅僧,他的部分思想成果,曾由汉璞记下后刻印为《白云深意》,今已不传。传文言鉴随于明崇祯甲申(1644)二月圆寂,世寿七十二,殁后“塔于太安寺之左”。“太安寺”即“泰安寺”,在今青城后山泰安古镇。该寺相传唐代初建,曾历多次毁修,明末再毁于战火后,清乾隆时复修。1986年重新整修,寺旁尚有舍利塔一座,清代碑三通,舍利塔即为鉴随灵塔。因“5.12”地震,鉴随灵塔崩坏,后重修于泰安寺内。鉴随修行在白云洞,灵塔建在泰安寺,两地相距不远,地理位置可简单理解为“山上上下”。冯学成指出“依佛教学修的传统,泰安寺是此地佛教的讲习之处,当僧人学养完满,行持坚固之后,方可到白云洞去闭关”,可对两地之间的关系作出修行角度的解释。
透过僧人们前往白云洞参鉴随的零星记载,也能够部分了解鉴随的影响力。《锦江禅灯》的编纂者、清代初年西南佛教的领袖人物丈雪通醉,二十岁(一说二十三岁)时就曾到白云洞参鉴随和尚。丈雪曾发问:“‘乃至举一手,或复小低头,皆已成佛道’,意旨若何?”。鉴随回答:“我这里不重机锋转语,一味平实商量。”后丈雪“因久慕随和尚道风,就座下圆具足戒”。《锦江禅灯》载鉴随法嗣二人,分别是彭州宝池和了凡刚禅师。彭州宝池“幼工讲席,长伏禅宗。后参白云鉴随和尚……隐于西禅二十余稔”。了凡刚禅师不仅“落发参白云洞鉴和尚”,更因“暗机契合”,鉴随“嘱住上方洞”,即与鉴随同在白云洞参禅,居于鉴随上方一层,丈雪通醉尊称他为“了凡师”。又如眉山灯甫禅师,“初游西山参鉴随,随教观心念佛”;新津正觉寺僧如镇“先拜山西五台幻灭和尚,后回蜀参于白云洞鉴随和尚”。还有丈雪通醉的法嗣端鼻万禅师,“因听《楞严》,疑常住其心。屡求抉择,未有所入。上白云洞参鉴随和尚……”。
细读《锦江禅灯》“灌阳鉴随”条,问题出现了,即传文根本未提《禅师岩记》所说的了空、鉴随率众抵抗张献忠军队事,《锦江禅灯》全书也无一处提及了空和尚,这该做如何解释呢?
第一种可能性是本就不存在鉴随率众抗张事。传文言鉴随于崇祯甲申(1644)二月圆寂,而张献忠攻成都地区在八月,则鉴随逝于张献忠部抵达之前,自然不会发生他率众抵抗事。第二种可能性是编纂者不知此事。但丈雪通醉曾从鉴随学习,时代交集,其长期所在的昭觉寺离灌县青城山地区并不远,部分碑文及丈雪的诗作、信札也透露其与灌县及邻近崇庆州境内的寺庙、僧人保持有一定联系,如确有二僧抗张事,信息传递不难。又丈雪编纂《锦江禅灯》,“搜罗全蜀古今知识”,前后花费二十余年,取诸方口实,如确有二僧抗张这样的“大事”,应不至于忽略,特别是二僧里有他的戒和尚——鉴随。第三种可能性是《锦江禅灯》因讳言僧人与李自成、张献忠等势力的冲突而不载二僧抗张事。但紧接着鉴随,《锦江禅灯》就讲述了鉴随法嗣彭州宝池禅师与李自成军的冲突,并表露出一定的表彰意味。编纂《锦江禅灯》时又已在清,清政府在宣传导向上贬斥闯、献,因此编纂者无需讳言,更不用花功夫编造鉴随亡于张献忠入蜀之前的传文。
此外,不只是成书时间距离鉴随活动时期最近的《锦江禅灯》不载二僧抗张事,清代以来的佛教文献均未记录相关事迹。
乾隆《灌县志》不载二僧抗张事迹
晚于《锦江禅灯》成书百余年,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灌县志·仙释》介绍说:
鉴随,未详何处人,静修太安寺熊耳山白云洞中。崇正(祯)年间得道,有先见之明。凡来谒者预知姓名,叩以吉凶祸福,辄应。蜀王闻之赴访,因移避深山。尝谕僧徒,数年后蜀中大乱,在劫者莫能逃,吾将逝矣。不数日,无病圆寂,时年百旬有余,后果有献贼陷蜀。
与《锦江禅灯》相比较,可知乾隆《灌县志》的文本属另一系统,并未利用到《锦江禅灯》已载的一些信息。乾隆《灌县志》强调鉴随“有先见之明”,言其曾预言张献忠陷蜀,这让鉴随和张献忠似乎发生了联系。但志文明确指出,鉴随在“献贼陷蜀”之前数年已“无病圆寂”,宣称其有百岁之龄则是烘托神异之语,可信度不高。因认可鉴随死于“献贼陷蜀”之前,该志自无一字记载鉴随抗张之事。不同于《锦江禅灯》,乾隆《灌县志》是清朝灌县地方官员主持编修的地方志,如真有老禅僧率众抵抗张献忠部不敌触岩而死之事,只会大大表彰一番,不会有隐藏。同时,乾隆《灌县志》没有像对待鉴随一样为了空列传,如了空确实存在,未免太过厚此薄彼。
记载二僧抗张事迹的灌县(都江堰)地方史志分析
下面按时序对提及二僧率众抗张事迹的灌县(都江堰)地方史志进行分析。
(一)清同治二年《禅师岩记》
在现存材料中,陈炳魁的《禅师岩记》恰恰就是最早提到二僧抗张事迹的记载。陈炳魁是灌县地方名士,中举后两度会试不第,曾主讲岷江书院二十余年,后任眉州学正,现存30余篇诗文作品多与灌县地方有关,论者认为“这些文章可以补史之阙,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通看《禅师岩记》,首段讲述二僧抗张事迹,次段重在表彰,立场明显与张献忠一方对立。陈炳魁提到“予尝稽考遗文,搜览残碣,窃为二僧悲其失传”,这句话表明,他写作时尝试考察二僧抗张事迹,但并没有寻觅到记载二僧抗张事迹的“遗文”“残碣”作为佐证,因此“悲其失传”。从“然营垒故地,历今二百余年矣,而山氓野叟,樵夫牧童尤相以禅师呼之”的表述来看,陈氏的信息来源很可能是“山氓野叟”的口头传说,那么《禅师岩记》的说法就更值得怀疑了。
(二)清光绪十二年《增修灌县志》
清光绪十二年(1886)《增修灌县志·人物》“鉴随”条内容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编纂者明言抄自乾隆《灌县志》,接着附上了另一种说法,“一说,献贼寇至青城山下,鉴随同了空率众御之,闻后山破,触岩死,详古迹禅师岩下”。
检《增修灌县志·古迹》“禅师崖”条,载“相传昔有了空、鉴随二僧参禅在白云洞,献贼至,扼山口,筑营御之,闻贼由间道毁寺,戕僧及居民,急率众奔山后奋击,今七阵沟即其处也。因众寡不敌,触崖死”。又《增修灌县志·武备》“戎事”下载:“僧了空、鉴随御贼于青城山下,闻贼由偷营沟袭破太安寺,忿极触崖死。今禅师崖绘像祀之。”
如单看《增修灌县志》的记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光绪十二年以前,已有二僧率众抗张事迹在民间流传,二僧之死已与禅师岩地名“挂钩”,流传广度已足够引起县志编纂者注意,甚至有人在禅师岩绘像祭祀。但必须提起十分警惕的是,其一,《增修灌县志》和此后灌县(都江堰)地方史志的编纂者都已可以读到陈炳魁的《禅师岩记》,这些文献中的记载在未交代来源的情况下,是否采自《禅师岩记》难以明确,例如《增修灌县志》“禅师崖”条的文本在行文、用词上就高度同于《禅师岩记》;其二,《增修灌县志》使用了“一说”“相传”的谨慎表述,只是采录说法而已,并未明言二僧抗张确有其事;其三,在《增修灌县志》刊刻之前,二僧抗张事迹虽已有一定流传广度,民间已出现绘像祭祀行为,但这很有可能是《禅师岩记》问世二十多年间带来的新影响;其四,《增修灌县志》也没有像对待鉴随一样为了空列传,了空依然是一个不具体的人物。
(三)清光绪十三年《青城山记》与《灌记初稿》
光绪十三年(1887),灌县人彭洵“检阅群籍,就所见录为一册,名曰《青城山记》”,他还在此年纂辑了针对乾隆《灌县志》删繁补遗的《灌记初稿》,二书有多处提及禅师岩、泰安寺、二僧抗张等内容。《青城山记》卷上言:“禅师岩……明季太安寺僧了空、鉴随率众御贼触崖而死难,乡人义之,绘像崖间以祀。今山民婚丧凡鼓吹过境,必祭而后可行,盖英灵所致云。”《灌记初稿·大事记》载:“明太安寺僧了空、鉴随,不知谁氏子。献逆扰青城,合谋举义,率徒侣及乡人扼险御贼,贼莫越,用密谍出偷营沟,焚其寺。二僧闻警急,转斗不利,触崖死,乡人今称禅师崖云。”综合来看,《青城山记》《灌记初稿》只选择了《增修灌县志》“鉴随”条所载两说中的“二僧抗张”说,并删去了“相传”等谨慎表达,内容没有超出《禅师岩记》《增修灌县志》。
(四)清光绪三十三年《灌县乡土志》
光绪三十三年(1907)《灌县乡土志》“太安寺”条载:“明末有了空、鉴随二僧,率僧徒数百御献贼于山口,兵败死禅师崖下。”内容简略,未超出《禅师岩记》《增修灌县志》及彭洵二记。
(五)1930年《青城山记补正》
1930年,罗元黼成《青城山记补正》,他是距离二僧抗张事迹所谓发生地不远的崇庆州街子场人,因认为彭洵的《青城山记》“取材惜俭,抉择未精”,遂作补正。但《青城山记补正》“禅师岩”条内容同于《青城山记》,“太安寺”条只补“清初重建”数字,亦未就鉴随、了空及二僧抗张事对《青城山记》作出增补。
(六)1932年民国《灌县志》
民国《灌县志》“禅师岩”条内容与《青城山记》同,记“鉴随”则照抄了光绪《增修灌县志》,另作出了三处重要增补。
其一,在《故实记》中专记二僧抗张事,把这一传说直接当作了“故实”,言“明崇祯末太安寺僧了空、鉴随者,不知谁氏子。张献忠扰青城,合谋举义,率徒侣及乡人扼险御贼,贼莫越,用密谍出沟壑,焚其寺。二僧闻警,转斗不利,触崖死。乡人称其沟曰偷营沟,崖曰禅师崖云。《蜀破镜》《蜀碧》”。比对可知,这段文字大体上同于彭洵《灌记初稿·大事记》对应内容。特别的,民国《灌县志》给出了《蜀碧》和《蜀破镜》两书名,意为所据文献。但经查检二书中并无二僧抗张相关记载,反而都记载了南充七宝寺僧晞容率乡勇抵抗张献忠军队事。
其二,民国《灌县志》第一次在《人士传》中为“了空”单列一条,言“了空者,青城太安寺僧也。献贼之乱,民多避入山中,了空率众扼险御寇,触崖死,乡人义之,绘像崖间以祀。又有鉴随者,与了空同志,贼焚其寺,亦战殁焉”。不难看出,这段话只是将一事换主角叙述,内容、细节不出《禅师岩记》《增修灌县志》,且仍然对了空生平细节无一字涉及。
其三,民国《灌县志》附《灌志文征》收录《禅师岩记》(共收陈炳魁诗文作品31篇),要说县志编纂者在撰写相关条目时未受陈氏此文影响,可能性极低。
(七)建国后灌县(都江堰)地方史志
建国后灌县(都江堰)编纂的《青城山志》《灌县宗教志》《灌县志》等地方史志均提及二僧抗张事,但无新说亦无细节增补。王纯五《青城山志》记泰安寺僧与张献忠部对战时,只提及泰安寺僧和了空,并只言了空触岩而死,不提鉴随,叙述也是以“相传”起笔,体现了一定的谨慎态度。
余论
“献忠遣使四出,趋地方官兵及乡绅朝见……蜀府宗支,多在灌县,乃发兵围之,不论宗室细民皆杀之”。从留存的相关记载来看,张献忠部确实到过灌县,并有杀戮。在青城山地区有不少与明蜀藩王府关系密切的寺观,包括泰安寺在内的不少宫观寺庙也确实在明末清初时段毁于战火。历史上是否曾有了空、鉴随率众抵抗张献忠军队事,与泰安寺是否曾被张献忠部所毁、是否曾有泰安寺僧众护寺抵抗并不冲突。
经考证,《禅师岩记》之前编纂的《锦江禅灯》、乾隆《灌县志》均不载了空、鉴随率众抵抗张献忠兵锋事,且明言鉴随死于张献忠陷蜀前,《禅师岩记》就是最早记载二僧抗张事迹的材料。从陈炳魁的叙述来看,二僧率众抗张事迹极可能来源于他听到的民间传说。《禅师岩记》问世二十余年后,光绪《增修灌县志》首次将二僧抗张事迹作为“一说”采录,并提及禅师岩下已出现绘像祭祀情形。《增修灌县志》以后编纂的灌县地方史志,均无视乾隆《灌县志》和《增修灌县志》提供的另一种说法,只保留了“二僧抗张”之说作为“鉴随”“泰安寺”“禅师岩(崖)”等条目的主要内容。民国《灌县志》将“二僧抗张事”写入《故实记》,标志着“二僧抗张事”在辗转传抄中,已逐渐失去“传说”属性而成为“故实”。另综观可供分析的文献记载,尚未发现能证明了空和尚确实存在的材料。可以说,《禅师岩记》所载二僧率众力抗张献忠军队事迹,并不可靠。
那么为何鉴随、了空二僧成为了抵抗故事的主角呢?鉴随,恐怕是因为他是明末该地区有数的高僧,受明蜀藩王崇敬,且隐居在与泰安寺有密切关联、属于“高一级”修行地的白云洞,卒年又接近张献忠攻陷成都地区时。至于了空,目前并没有材料可证明确有其人,但可以做个猜测,“了空”是鉴随法嗣了凡刚禅师“了凡”之名的讹传。《禅师岩记》提到“二僧参禅白云洞”,而了凡正好曾住在鉴随上方洞内参禅,隐逸白云洞的二僧易让山民留下深刻印象,口耳相传。当然,传说或故事的真假并不会有损禅师岩等青城景致的古幽,数百年间山氓野叟的口耳相传、文人墨客的观感而兴早已成为其历史风采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龙显昭主编:《巴蜀佛教碑文集成》,巴蜀书社,2004年
严耀中:《佛教戒律与中国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丈雪通醉编, 吴华、杨合林点校:《锦江禅灯》,中州古籍出版社,2019年
灌县《泰安乡志》编写领导小组编:《灌县泰安乡志》,内部印行,1985年
王路平、龚晓康:《丈雪禅师语录诗文》,贵州大学出版社,2018年
性统:《续灯正统》,《卍续藏经》第一四四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
孙天宁:《灌县志》,清乾隆五十一年刻本
王燕飞、喻芳、张婷婷著:《巴蜀文学与文献研究论稿》,吉林文史出版社,2021年
庄思恒、郑珶山:《增修灌县志》,清光绪十二年刻本
彭洵:《青城山记》,清光绪二十一年刻本
彭洵:《灌记初稿》,清光绪二十年刻本
徐昱、高履和:《灌县乡土志》,清光绪三十三年刻本
罗元黼:《青城山记补正》,1930年铅印本
罗骏声:《灌县志》,1932年铅印本
王文才:《青城山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灌县宗教志编辑组编:《灌县宗教志》,内部印行,1987年
四川省灌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灌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
王纯五主编:《青城山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顾山贞:《客滇述》,《中国野史集成》第30册,巴蜀书社,1993年
灌县《青城乡志》编写领导小组编:《灌县青城乡志》,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