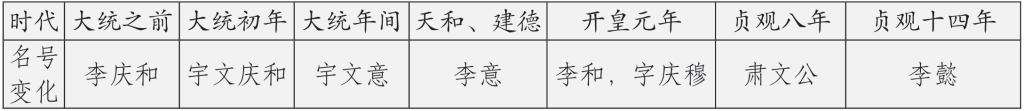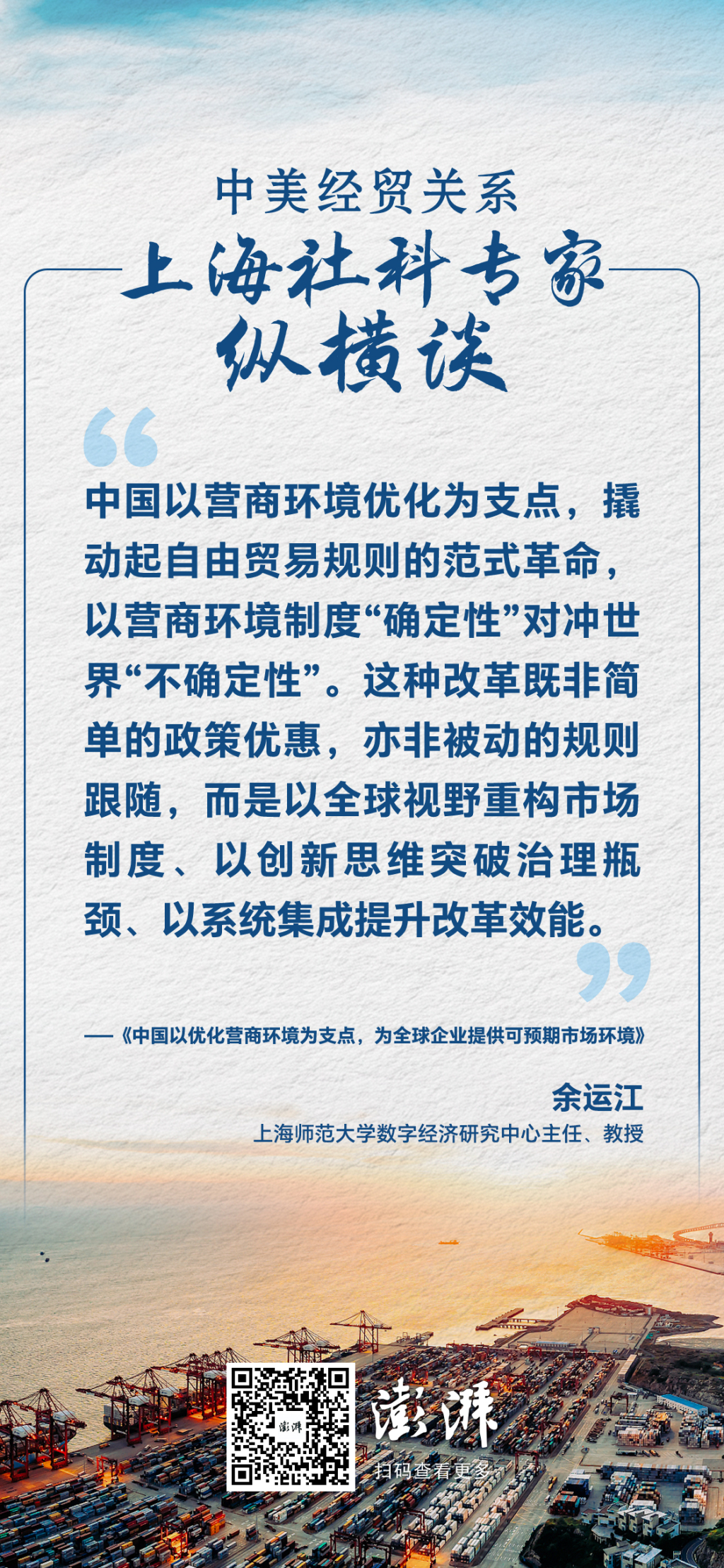东洋学人|滨田青陵:近代日本考古学第一人
滨田耕作(1881-1938,号青陵)早年在一篇题为《风弦录》(题目源自白乐天的“风弦自有声”)的文章中指出,“大凡人物有大小三类。一曰,其人生死无关世间痛痒者,凡人也。二曰,生前其名甚显,死后渐为人所忘者,世间英雄也。三曰,方其生时名不甚高,殁后其人愈受追慕者,洵真伟人也。”(《滨田耕作著作集》第七卷)不过,滨田大概属于第四类,生前就享有盛名,死后仍受到爱戴,“洵真伟人也”。
对日本考古学史极为熟稔的斋藤忠(1908-2013)认为,大正时期的考古学界有三大主流:一为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人类学教研室和东京人类学会,二为考古学会及成为其地盘的东京帝室博物馆历史部,三为率先在文学部开设考古学讲座的京都帝国大学考古学教研室。(斋藤忠:《日本考古学史》,200页)滨田耕作正是京都帝大首位考古学讲座教授。追溯日本考古学史,滨田是绕不开的人物。

滨田的前半生
看滨田耕作的年谱(结合其他材料),有几个地方印象较深。
其一,小学阶段几乎年年转学。明治十四年(1881)滨田生于大阪府古市村(现羽曳野市古市),是家中的长子。原籍为同府岸和田市并松町。滨田家代代是岸和田藩士,也就是武士出身。滨田的父亲源十郎曾在小学任职,后转任堺市警官。或许跟武士的出身有关,源十郎身上流淌着“反抗”乃至“反骨”的血液,为此经常与上司发生冲突,频频调动工作岗位。因此,幼小的滨田耕作也经常转校。六岁,在大阪中之岛的小学入学;七岁,转入山形市寻常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九岁,转入米沢市兴让小学;十岁,移居香川县丸龟町;十一岁,转入德岛县寻常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十二岁,转入大阪府寻常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十三岁时,源十郎到大阪朝日新闻社任职,一家迁居大阪府西成郡今宫村(现大阪市南区今宫),滨田为上学方便,独自寄寓于豫章馆。十四岁,滨田自大阪府寻常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高等科毕业。滨田在文史方面成绩优异,但算术、修身等科目甚是一般。
其二,因反抗教师,中学转学。小学毕业后,滨田进入大阪府立第一寻常中学(现北野高等学校)。中学时代的滨田很喜欢在畿内参拜陵墓、寻访神社和古寺。十八岁时,滨田因在体操课上为同学鸣不平,被视为“不敬”,遭学校开除(《放校处分前后之事实报告》,《滨田耕作著作集》第七卷)。这起事件对滨田未始不是一件好事。同年,滨田转入东京的早稻田中学,进入第五学年的学习。这是滨田首次踏上东京的土地,在早稻田他受到了坪内雄藏(逍遥)等人的熏陶。坪内逍遥(1859-1935)是日本近代的小说家、评论家、翻译家、剧作家,对日本近代文学的形成、话剧改良运动有着很大的影响。滨田生性敏感,热衷文艺,爱好绘画。在早稻田中学时期,原本没有记日记习惯的滨田却留下了日记,去世五十年后由岸和田市图书馆整理出版(《滨田耕作(青陵)日志》)。从日记中可以看出,滨田并不是勤奋型的学生,他好恶分明,对数学尤其讨厌。早稻田中学毕业后,滨田原想继续到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就读的,但考虑到自己的学力及家庭的经济状况,便改变了主意,考入京都的第三高等学校。(滨田敦《谈父亲——〈青陵青春日记〉后记》,《滨田耕作(青陵)日志》)
其三,七年的东京生活。明治三十五年(1902)七月,三高毕业,同年九月滨田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文学部)史学科,专攻西洋史。大学期间,滨田充任《国华》编辑,同时参与《史学杂志》编辑事务。三年后,滨田毕业,毕业论文的题目为“论希腊式美术之东渐”。继而进入研究生院,研究方向为“日本美术史,特别是与外国美术的关系”。而后在母校早稻田中学担任历史科讲师。明治四十二年(1909)九月成为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讲师。这七年间,滨田在美术史领域深造自得,为他此后的京大时代奠定了基础。滨田的弟子藤冈谦二郎认为,东大史学科、理学部人类学、工学部的建筑史对滨田的东京时代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关于东大史学科时代的滨田,后来在京大成为同僚的时野谷常三郎有细致的描写。两人“一起上西洋史学课——西洋史成为史学科的一个分科,是滨田君毕业后才开始的。……桌上放着坪井九三郎博士的史学研究法、白鸟[库吉]博士的塞外民族史的讲义……其时,滨田君出任史学会机关刊物《史学杂志》的学生委员,[明治]三十九年毕业,按惯例推荐我担任学生委员,一年后,滨田君任学士编纂委员……如所周知,滨田君禀有文才,和他主编的汇报栏一样,在史学界的杂志中显得格外出色……滨田君才气焕发,斗志昂扬,倘对其他杂志上的论说不满,立马援笔疾书,以新颖的论调击中对方的心扉……尽管笔锋辛辣,却因其间流露出的温情恳切之状而变得柔和,反倒引发对方的好感”。(转引自藤冈谦二郎《滨田青陵及其时代》,32-33页)
悠长的京大时代
滨田耕作一生活了57岁,而他在京都帝大待了29年。也就是说,他的后半生是在京大度过的。从明治四十二年(1909)到昭和十三年(1938),滨田在京都帝国大学由讲师而助教授、教授、文学部长,最后出任校长,并死于任上。滨田的学生角田文卫认为,滨田业绩最显著的时期应为他的少壮教授时期,即大正六年(1917)到昭和五年(1930)。据此,或可将滨田的京大时代分作三个时期,即初入京大、留学欧洲时期(1909-1916),少壮教授时期(1917-1930),晚年(1931-1938)。
1909年,滨田出任京都帝大讲师,在哲学科讲授“日本上古美术史”,并设置文科大学史学科陈列馆。赴任前,28岁的滨田在东京与21岁的野村琴寿结婚,而后定居京都府爱宕郡田中村。翌年新学年讲授“日本美术史”和“考古学概论”。同年,与内藤湖南、狩野直喜、小川琢治及富冈谦蔵等一同赴北京调查敦煌文书,又和小川一同赴河南洛阳,归途又到辽宁调查遗迹。这是滨田第一次到中国旅行。1913年3月,滨田经西伯利亚踏上留学之途。由于不喜欢繁琐的考证和抽象的理论考辨,滨田比较排斥德意志的学风,因此选择了英国。他起初主要待在牛津,向皮特里(W. M. Flinders Petrie)、塞斯(Archibald Henry Sayce)两位教授学习考古学研究法。而后在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地游历。1916年3月回到日本,9月京都帝大设置了日本第一个考古学讲座,在二战前也是日本唯一的考古学讲座。欧游归国的滨田成了日本考古学的学科带头人。
少壮教授时期,滨田意兴风发,筚路蓝缕,留下了沉甸甸的业绩。1970年代,有光教一(滨田的弟子)负责编《日本考古选集·滨田耕作集》,为此他撰写了《学术史上滨田耕作的业绩》。该文开门见山:“滨田耕作在考古学界留下的业绩,离开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后来的文学部)考古学讲座是不可能言说的。”作为滨田的业绩,首先不得不提厚重的《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考古学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几乎是学界共识,比如藤冈谦二郎在列举滨田的学术成绩时,也率先提到《报告》。(《滨田青陵及其时代》,130页)穴沢咊光也认为,滨田将皮特里的考古学方法引入日本,由京大考古学研究室加以实践,再通过《报告》公诸学界,提升了日本考古学的水平。(穴沢咊光《梅原末治论》,角田文卫编《考古学京都学派》,229页)
该《报告》第一册出版于1917年,最后一册即第十六册出版于滨田去世后的1943年。第一册到第十册,以及第十三、十四册,滨田的著述占了相当部分;第十一、十二册虽没有滨田的署名,但也是他指导下的调查研究的成果;第十五册(梅原末治、小林行雄执笔)、第十六册(末永雅雄、小林行雄、藤冈谦二郎执笔)也是他生前规划指导的调查。由于京大考古学讲座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日本独一无二的考古学讲座,所以《报告》具有强烈的示范性,成为学界的共同财产。在藤冈谦二郎看来,《报告》有两个特点,一是它的内容并不局限于滨田本人擅长的领域,而是涉及广义的考古学;二是为配合遗迹的发掘调查,经常参考相邻学科学者的意见,有时还请他们参与执笔。除了《报告》,滨田还参与发起朝鲜古迹研究会、东亚考古学会,并积极推动考古发掘调查报告的出版。
在滨田的指挥下,京大考古学研究室几乎每年出版一册《报告》,这种速度是极为惊人的。除了对被任命为考古学讲座的感激,以及对考古学研究的热情,也跟滨田强烈的责任感有关。滨田经常告诫年轻的研究者:考古发掘,如果只是发掘,那就是破坏,而破坏遗迹是有罪的。为了免于这种罪责,必须迅速地将发掘经过精确地记录下来,并尽快公之于众,便于其他学者自由利用。正由于秉持这样的信条,滨田及其团队才留下了十六册内容丰赡、图版众多的《报告》。
作为一个机构的领导,特别是教育机关,滨田最大的才能是营造氛围。凭借着个人的才智和素养,滨田时代的考古学教研室吸引了京大内外的才俊,形成了自由开放的学风。据专攻考古学的第一届毕业生长广敏雄回忆,滨田常常和好友羽田亨(东洋史家)、小川琢治(地理学家)、新村出(语言学家)等出现在考古学教研室,同年轻的学子一边喝咖啡,一边自由讨论。当时的每日新闻京都支局局长岩井武俊看到这幅场景,不由得称赞京大考古学教研室搞的是“咖啡考古”(coffee archeology)。长广敏雄清晰地记得,与陈列室相邻的三间考古学研究室,滨田教授室在中间,左手边是放有书架的助手室,教授室里边是文物整理室。考古学教研室师生一般要穿过滨田教授室、助手室,才能进入文物整理室。也就是说,滨田教授室是开放的,他猜测那是滨田本人的设计方案,这样他可以将三间研究室都当作工作的场所,同时也是教研室全体人员的研究场所。在滨田那里,不存在私人的研究室、秘室的概念,也不容忍狭隘的想法。因此,研究室挂着他手书的“以和为贵”的匾额。尤其使长广敏雄感动的是,每天一到傍晚五点,滨田就会离开研究室,这是由于,滨田觉得老师一直在场,助手和学生会感到拘束,所以研究室需要没有老师在场的时间和空气。(转引自藤冈谦二郎《滨田青陵及其时代》,176-178页)
另一方面,滨田身上流淌着“武士之子”的血液,也带有“反骨”精神。早稻田中学时代,滨田曾围绕前方后圆坟的起源问题,在东大人类学教研室举行的学术会议上,向八木奘三郎(1866-1942,号静山、冬岭)的观点提出质疑。其时,滨田才十八岁,八木已是著名的考古学者,两人还有书信往还。这个故事后来被滨田的好友清野谦次(1885-1955)写入《日本考古学·人类学史》上卷,题为“八木静山与滨田青陵”。在大学时代,滨田也曾围绕北海道阿依努的小人传说(也叫コロボックル),与“日本人类学之父”坪井正五郎发生论争,滨田由此为学界所瞩目。或许如滨田的次子滨田敦所指出的,“与其说父亲反权力,不如说他‘天邪鬼’的性格”来自祖父的遗传,不过“不仅父亲如此,京大文学部创设时的各位教授,多多少少恐怕都是这种性情”。他们当中很多人出身于东大,所以比其他大学出身的人更反东大,内心深处就有努力养成东大所没有的、崭新的学风的意气和精神。(滨田敦《谈父亲》,载《滨田耕作(青陵)日志》)
在制度建设、学风养成之外,作育人才当然也是滨田对日本考古学的一大贡献。梅原末治、末永雅雄、森本六尔、小林行雄、角田文卫等日本考古学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都离不开滨田的栽培和提携。因此,滨田时代的京大考古学教研室,真可谓人才济济,争奇斗艳。
昭和六年(1931)到昭和十三年(1938)可以算作滨田的晚年。其间,滨田先后成为京都帝大文学部长、帝国学士院会员、京都帝大校长,晋升为正三位勋二等(瑞宝章),学成功遂莫过于此。与此同时,滨田还担任各团体的理事、顾问等,各种事务缠身,虽有研究的意愿,恐怕也难以专心致志了。
1938年7月25日,缠绵病榻数月后,滨田在昏睡中去世。据说,临终前三天,他觉悟到死亡,对夫人说“人生如朝露,似梦若幻”(人生朝露に以て夢の如し)。这让人不禁联想起丰臣秀吉的临终感言:“生如露死亦如露,浪速浮生犹梦中之梦”(つゆと落ちつゆときえにしわが身かな浪速のことも夢のまた夢)。与滨田晚年成为亲戚的小川琢治(滨田长女精子与小川环树结为连理)写了题为《梦青陵博士》的汉诗送别故友兼亲家:
曾游巩洛共连林,欲语当年空断肠。
踪迹分明犹记得,邯郸客舍梦黄粱。
(藤冈谦二郎《滨田青陵及其时代》,第43、60页)

书比人长寿:滨田著述扫描
著名西域史专家羽田亨是滨田在三高、东大的校友,京大的同事,滨田去世后他接任了京大校长职位。羽田亨为滨田的《考古学研究》作序时写道:“著述等身是自古以来学者理想之所在,如将此等细小活字排版的论著以旧式的木版刻印,恐怕超过了著者的身高。何况所论开拓宇域,海内外罕有人及,东亚考古学一科本就奠基于此等论述。此书与其他姊妹篇一同达成著者作为学者的理想,并成为黎明期我国考古学一大跃进之印迹,可谓传之久远的纪念塔。此塔由承传衣钵的梅原博士搭建完成。易箦后一年整,自行留下的材料由接受熏陶的弟子整理,奉于墓前,九泉之下,著者莞尔之貌,仿佛就在眼前。”(藤冈谦二郎《滨田青陵及其时代》,第152-153页)
如羽田亨所述,滨田确实留下了等身的著作。考古学者坂诘秀一著有《日本考古学文献解题》,对重要的考古学论著加以介绍,于初学者甚为便利。其中,滨田是入选著作最多的学者之一。不仅如此,著述体裁也各式各样,研究方法有《考古学通论》(1922年),入门、概说类有《考古学入门》(1941年),论文集有《考古学研究》(1939年),译作有《考古学研究法》(蒙特柳斯著,1932年)、《阿道夫·米海里司美术考古学发见史》(1927年)。由此亦可想见滨田在日本学界,乃至普通读者中的影响力。
在滨田众多的著述中,如果只能选一种代表作,那无疑是《通论考古学》。该书大概也是滨田所有著作中版本最多的一种。大而言之,迄今已有六个版本。1922年7月由大镫阁初版,此后有1929年刀江书院版、1947年全国书房版,1974年《日本考古学选集·滨田耕作集》上册收录了初版全文,然后是雄山阁2004年版(初版影印,附有角田文卫的解题),最近的一版为岩波文库2016年版(春成秀尔解题)。顺带一提,关于滨田耕作在中国的影响,可参阅徐坚《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第九章。
《通论考古学》是日本第一部系统的考古学通论类著作。它将考古学定义为“根据人类的遗物研究人类的过去的学问”,英文可译作“Archaeology is the treatment of the material remains of the human past”。全书主体由序论(何谓考古学;考古学的范围及目的;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资料(考古学资料的性质;考古学资料的所在与收集;遗物及其种类;遗迹及其种类)、调查(考古学发掘;发掘的方法;调查方法一、二)、研究(资料的整理与鉴别;特殊的研究法;断代;考古学与文献)、后论(考古学成果的出版;遗物、遗迹的保存;遗迹、遗物的修理;博物馆)等五部分组成,内容相当全面,行文简洁明快。
该书问世已有百年,但迄今尚未出现超越此书的考古学概论类著作。京大考古学讲座第三任教授有光教一在讲授“考古学概论”时,日本学者写的教科书只列了《通论考古学》。这跟他是滨田的弟子或许有一点关系,但决定性的因素还是该书本身的品质。有光教一认为,滨田此书“排除了古老的偏重古物的风气,阐述了对出土遗迹的有组织的发掘调查和科学研究”,“虽多次提及彼特里的《考古学研究法及其目的》,但两相比较,说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并非溢美之辞”。(《学术史上滨田耕作的业绩》,载《日本考古学选集·滨田耕作集》)藤冈谦二郎、角田文卫也认为此书独步天下,无与争锋。
坂诘秀一的《解题》选了滨田《考古学研究》,这是滨田著作集的一种。实际上,历史上出过两版“滨田耕作著作集”。第一版是滨田生前计划选编,死后由梅原末治统筹完成的滨田耕作著作集,座右宝刊行会发行,共四册,分别题为《考古学研究》(1939年,羽田亨作序)、《日本美术史研究》(1940年,泷精一作序)、《东洋美术史研究》(1942年,池内宏作序)、《青陵随笔》(1947年,新村出作序)。第二版是滨田耕作先生著作集刊行委员会(末永雅雄任顾问,角田文卫任委员长,委员有长广敏雄、有光教一、斋藤忠、澄田正一)编辑的七卷本,同朋舍出版(1987-1993年)。
这个七卷本的滨田著作集并不是“全集”,比如《考古学通论》就没有收入在内。不过对这个著作集略作介绍(参考了相关解说),或有助于加深对滨田学问与人生的理解。
第一卷《日本古文化》(1988年,东伏见慈洽解说),收文24篇。其中,开头的两篇(《淡路国鸟饲村的洞穴》《和泉的石器》)均为早稻田中学五年级时在《东京人类学会杂志》上发表的作品。第三、四篇(《山城原史时代的遗物遗迹》《京都附近的古坟》)是在京都第三高等学校踏访遗迹的结果。十余年后的1914年,滨田写了《日本古坟与西洋古坟之关系》,显示出其广阔的学术视野。《考古学所见九州的古代民族》《日本文明的黎明》等文则是滨田自中学时代以来考古学兴趣落实在日本古代史研究上的初步结晶。关于从远古到上古的日本文化,滨田撰有《日本文明的起原》《日本原始文化》《日本文化的源泉》等长文,指出日本可能存在旧石器时代,展示出其深邃的历史观察力和想象力。
第二卷《日本的古美术》(1988年,岛田修二郎解说),收文41篇。岛田修二郎认为,考古学与美术史兼收,是滨田学问最显著的特色,这种学风传给门生,于是有水野清一(1905-1971)和长广敏雄(1905-1990)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研究,再则是樋口隆康(1919-2015)的佛教遗迹研究。滨田的日本美术史研究大致有两个特点,一是所涉范围甚广,从史前时代到安土桃山时代,后来又转向奈良时代前后,均曾著文论述。二是讨论时代大势的文章较多,这从篇名即可略窥一二,如《天平时代的雕刻》《佛教以前的日本美术》《镰仓时代的美术》等。
第三卷《东亚古代文化(一)》(1989年,有光教一解说)和第四卷《东亚古代文化(二)》(1990年,长广敏雄解说)是姊妹篇。第三卷收文18篇,分作两辑,上辑为概说和图录的解说(《东亚古代土器概说》《中国古铜器概说》《陈氏旧藏十钟解说》《中国古玉概说》《中国古明器泥象图说 总论》),下辑则涉及土器、铜器、货币、鼎鬲以及印度最新的考古大发现等。第四卷收文17篇,分作三辑。上辑为《东亚古代美术综说》,共十一章,将近90页。长广敏雄指出,最后四章(即第八章《汉六朝的建筑与法隆寺的建筑》、第九章《东亚佛教美术的源流》、第十章《犍陀罗与中亚地方的佛教美术》、第十一章《中国最早的佛教美术遗迹》)论述关联度很高,体现了滨田对整个东亚(包括日本)古代美术的综合把握。中辑主要涉及艺术传播与文化交涉的问题,即使像《汉代绘画》《西魏四面像》《六朝土偶》等看上去“纯中国”的题目,实际上也包含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内容,更不要说《希腊印度式佛教美术的东渐》《犍陀罗雕刻与六朝泥象》等文了。下辑主要跟辽宁、朝鲜的考古调查有关。
第五卷《基督教文化》(1991年,斋藤忠解说),主体是曾出过单行本的《天正遣欧使节记》,长达300余页;附有一篇《日本基督教遗物》。斋藤忠指出,在滨田众多著作中,有两本书不太为世人所知,一为昭和七年(1932)刊行的《庆州的金冠塚》,这是朝鲜考古学的专门读物;另一本即为本卷收入的《天正遣欧使节记》,该书于昭和六年由岩波书店刊行。所谓“天正遣欧使节”,又称“天正少年使节”,是指天正年间(1573-1592)四位少年出访欧洲,完成大任并回到日本的故事。滨田在东京帝大学习西洋史时在村上直次郎教授的课上听过这个故事,十分感动。大正五年(1916)滨田留学归国途中,通读了《日本西教史》,并获得《日本使节考》,由此对这段历史更感兴趣。昭和二年(1927),滨田有机会再赴海外,获知《使节记》《布教史》等资料。因缘凑泊,滨田遂执笔追踪这段“使节之迹”,其后在《历史与地理》杂志上连载。该书有三个特色,其一,少年使节访问过的场所,滨田也亲自探访、观察,并附有写生。其二,滨田充满感情的叙述,堪称美文。其二,全书随处可见详细的注释。另外,《日本基督教遗物》是滨田为《天主教大辞典》撰写的一个条目,介绍了日本保存的、与基督教(日文汉字写作“切支丹”或“吉利支丹”)有关的绘画、铜版画、雕像、信教用品、墓碑类文物。
第六卷《西方古典文化及其遗迹》(1993年,角田文卫解说),收录了《罗马考古学》《罗马的雕刻》《南欧游记》《希腊纪行》等四编。《罗马考古学》是滨田1920年在京都帝大文学部史学科讲义的草稿,续编《罗马的雕刻》是1926年的讲义。这两册讲义都是滨田家寄赠给奈良县橿原考古学研究所的。角田文卫指出,《罗马考古学》主要参考了英、德学者的研究成果,它的一个显著特色是滨田为相关的遗迹作了写生。滨田在京大讲述罗马考古学之时,沢木四方吉(1886-1930)在庆应义塾大学讲授希腊的古典考古学,可谓东西辉映。
前两编为讲义,是首次刊行;后两编为游记,属于稀见书再版。大正三年(1914)四月底到五月中旬,滨田和同在欧洲留学的市河三喜(1886-1970)从罗马出发,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探访古迹,而后回到罗马。翌年早春过后,两人又去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寻幽访胜。这就构成了《南欧游记》的三章:《南意大利之旅》《西西里岛巡游》《法兰西内的意大利》。同年五月初到六月中旬,两人又在希腊本土和克里特岛参观博物馆,踏访遗迹,慨叹人事兴衰、国运起伏,遂有《希腊纪行》。《希腊纪行》是滨田最早的单行本,1918年由大镫阁发行;《南欧游记》同样由大镫阁出版,时间晚了一年。
第七卷《青陵随想》(1987年,角田文卫解说),收文70篇。有学者认为滨田本质上是文人,是美术史家,《青陵随想》大约最能体现滨田的这一面向。该卷收录了滨田家秘藏的《放校报告》(“放校”即被学校开除之意)及滨田夫人的《回忆》,这都是了解滨田的珍贵材料。作为“著作集”的最后一卷,本卷还制作了“年谱·著作总目录”,卷首载有滨田的画作和照片(包括数帧合影)。角田指出,《风弦录》反映了大学时代滨田的人生观、社会观、基督教观。《希腊与日本》一文,是大学毕业论文《论希腊式美术之东渐》的概要,体现了宏阔的视野。《金色堂与凤凰堂》指出平泉与平安京地形的相似,显示了非凡的眼力。短文《有马大友大村三侯遣使纪念碑》表明滨田很早就对天正遣欧使节一事颇有兴致。从《彼特里氏》等文可一窥早年留学生活的样貌。《我国考古学的将来》《我考古学界的新气运》是学术史上的重要文献,可视为滨田考古学的行动纲要。《蟋蟀》充满理趣,自是滨田的随笔名篇。
此外,滨田还有《桥与塔》《百济观音》等俊逸多彩的作品。限于篇幅,恕不一一介绍。
作为一名学者,滨田的著作比他短暂的人生要长寿得多,这应该是一桩幸事。当然,滨田之所以为人怀念,也跟他的人格有关。他曾在《我的塞斯老先生》这篇悼文中诚恳地说:“对我而言,比起学问上的影响,我更深切地感受到先生人格上的感召力。”同样的,滨田的弟子藤冈谦二郎由衷地表示,在滨田那里,为学与为人是不可分离的,因此他在老师故去四十年后著书《滨田青陵及其时代》以为纪念。藤冈强调,书名没有用“耕作”,特意选了“青陵”,是希望藉此更多呈现滨田作为“人”的面向。为此,本文也仿效了这个作法。
参考文献
1、有光教一「学史上における濱田耕作の業績」、有光教一編『日本考古学選集・浜田耕作集』、築地書館、1974年
2、藤岡謙二郎『濱田青陵とその時代』、学生社、1979年
3、濱田敦「父を語る」、岸和田市立図書館編『濱田耕作(青陵)日誌』、1989年
4、『濱田耕作著作集』第一~七巻、同朋舎出版、1987-1993年
5、穴沢咊光「梅原末治論」、角田文衛編『考古学京都学派』、雄山閣出版、1994年
6、斎藤忠『日本考古学史』、吉川弘文館、1974年
7、坂誥秀一『日本考古学文献解題』1・2、ニュー・サイエンス社、1983・1985年
8、徐坚:《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科学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