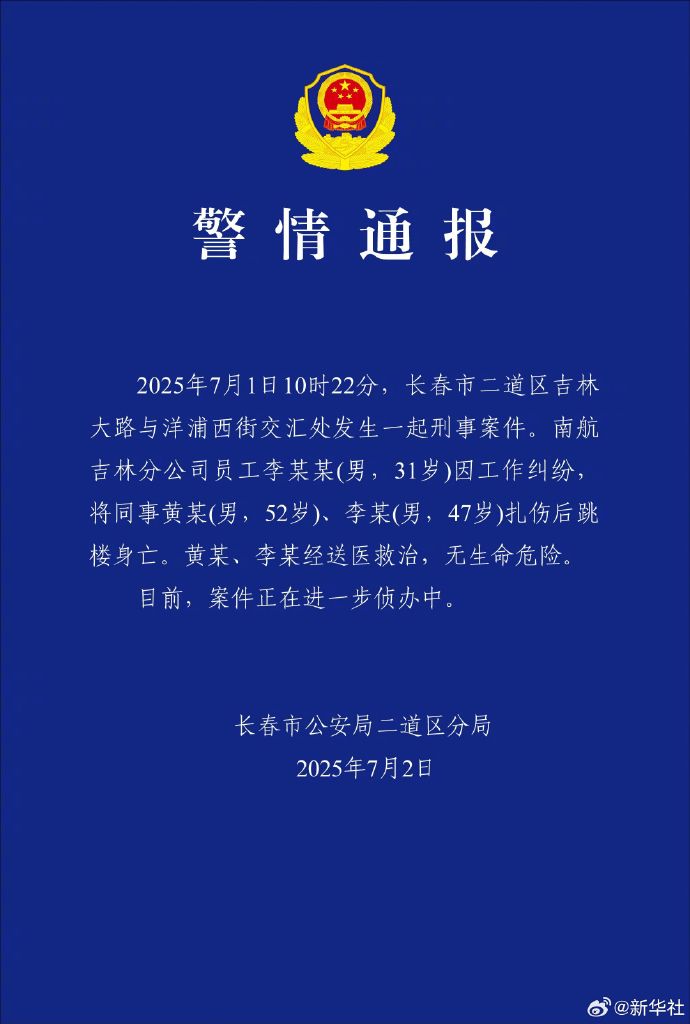在安宁疗护病房,我们不再忌讳谈死|健康有方FM
当生命进入倒计时,我们还能为彼此做些什么?
近日,电影《好好说再见》在全国公映,它讲述了一位身患癌症的单身母亲,在临终之际与父亲和女儿展开告别。而在真实的安宁疗护病房,医护人员每天都在目睹这样的告别发生。
面对死亡,恐惧是常态,安宁疗护,照亮生命终点。本期节目以电影为契机,借安宁疗护病房医师田虹与《好好说再见》导演张弛的对话,探寻安宁疗护背后的专业与情感。
在本期节目,你将听到:
• 电影《好好说再见》中所展现的安宁疗护,专业医师怎么看?
• 安宁疗护到底是什么?如何帮助患者减轻痛苦、留住尊严?
• 当疾病无法治愈,医生还能做什么?家属又能准备什么?
• 一线医护人员如何面对一场又一场“终点”?又如何安慰活着的人?
以下为文字节选,更多讨论请点击音频条收听,或【点击此处前往小宇宙App收听】,效果更佳。
【本期嘉宾】
田虹 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疗护病房主管医生。全科主治医师,上海觉群文教基金会特邀讲师,主攻安宁疗护方向,擅长肿瘤晚期止痛等缓和医疗,为患者及整个家庭提供身心灵的全方位照护。
张弛 电影导演。执导作品《好好说再见》获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周“优选观众喜爱影片”,《记忆囚笼》入围第26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入围“亚洲之窗”单元。
【本期主播】
雅婷 ·湃客编辑。

为什么我们要聊“死亡”这件事?
如果死亡不可避免,我们能否有尊严地离开?这是影片《好好说再见》试图回答的问题。
该片讲述患有绝症的单亲妈妈,如何与女儿和父亲面对生命终点将至的时刻。故事设定在宁波社区,老街区里,有着孩子们最爱的旧滑梯与传统糕团店,穿插的宁波话对白将死亡话题拉回生活本身,在平实的镜头中,激发普通人对“临终关怀”的思考。

《好好说再见》剧照
作为安宁疗护病房主管医师,当片尾灯光亮起,田虹在观众席里沉默许久。
在观影过程中,她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出她与癌症抗争了16年的父亲,还有无数像他一样在病房里逝去的生命,以及在最后生死关头所经历的那些悲欢离合。
在田虹看来,这部电影准确再现了安宁疗护病房的日常。药物剂量如何根据疼痛等级微调、如何帮病人用香薰缓解焦虑,如何完成“生前预嘱”,如何让病人在最脆弱时仍保有人格尊严......这些细节,在银幕上一一浮现。
“与其说它是一部艺术作品,不如说它是我们身边的故事。它呈现出的,几乎就是我们的生死观和安宁疗护的照顾模式。”
导演张弛说:“拍这部电影其实还是挺忐忑的。我们曾担心影片是否‘过于传统’。但也许恰恰是这种温和的讲述,让大家能够放下苛刻的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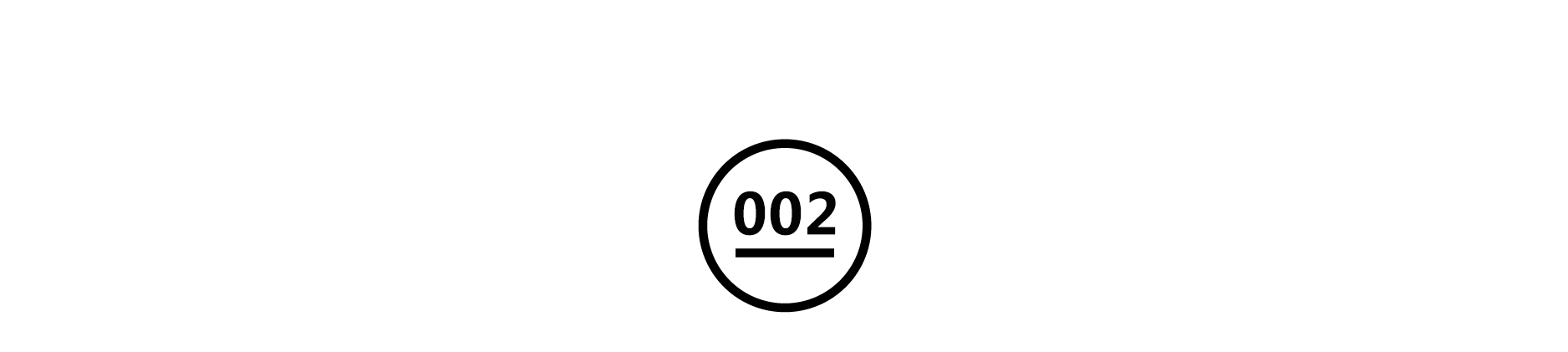
安宁疗护如何帮助患者减轻痛苦、留住尊严?
田虹介绍,在中国,安宁疗护整体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目前已经有三批国家级的安宁疗护试点,现在已经覆盖到全国185个市区,上海是第一批试点城市。
2022年,安宁疗护被纳入了上海市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这项普惠制的民生工程基本上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依托的服务模式。
田虹所在的宝山区月浦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日常工作中不仅要服务好本院的患者,还要建立全区患者的信息网络,向上承接二三级医院没有治愈希望的晚期患者;向下深入到社区,开展多种生死教育,传递“优生优死”的理念。
安宁疗护病房入住标准很清晰:当临床医生诊断患者已进入临终期,并且现有医疗水平无法治愈,预计生存期不超过三个月。患者本人和家属如果接受安宁疗护的理念,即不进行插管、不进行心肺复苏等有创伤性的抢救措施,就可以申请入住病房。
服务形式方面,包括门诊、住院和居家三种方式联动,为患者提供全场景、全病程、全人关怀的连续性服务。当患者在上级医院的治疗结束后,由于医学的局限性无法继续治疗,就会无缝转接到社区医院,做到全病程、全场景的连续关怀。也就是说,在人生最后的这一段时间,能够获得全方位、无缝衔接的关怀。
照护方案方面,安宁疗护强调减轻患者痛苦和不适症状,实现舒适照护。同时还要关注患者整个家庭的需要,这一点在传统医疗中常被忽视。“其实,整个家庭在面对这种情况时也会承受巨大压力,要为他们提供心理支持和人文关怀。”田虹说,“这些措施,才是我们对生命尊严最深刻的捍卫。”
而疼痛,是许多终末期患者无法回避的难题。据调查显示,中重度疼痛在晚期患者中的比例高达80%。“如果躯体的痛苦无法缓解,心灵的安宁就无从谈起。”田虹介绍,她所在的安宁疗护病房组建了一支跨学科的团队,联合中医师、康复师、治疗师等为患者提供常规药物之外的联合止痛方法。例如针灸、穴位敷贴、耳压豆、五音疗疾等技术,有效减轻疼痛和焦虑。

《好好说再见》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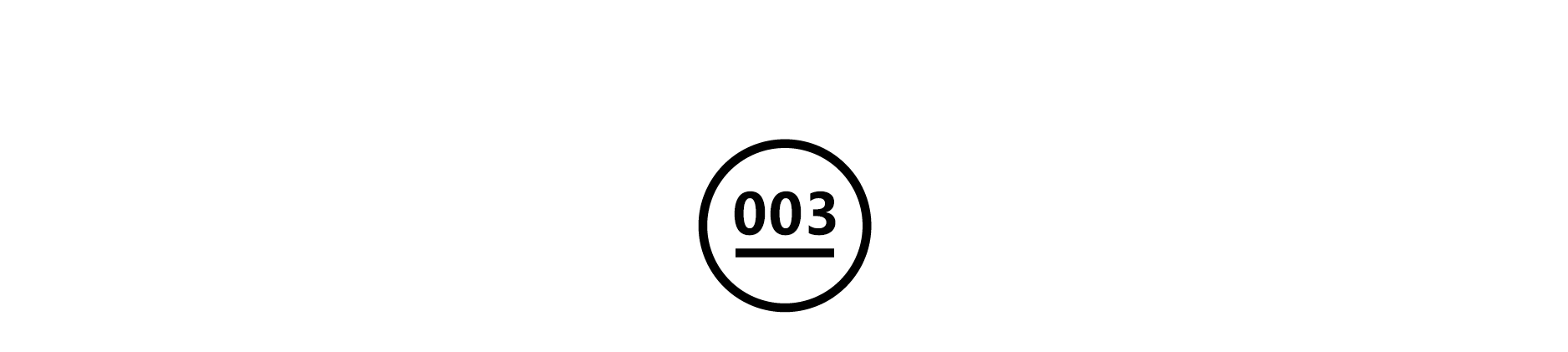
如何放下对死亡的恐惧?
《好好说再见》里,女主角应诺第一次进入安宁病房后,情绪失控地逃出走廊。那种崩溃不只是恐惧引发,更是内心对“终点”这两个字的拒绝。这样的场景,同样是现实中患者和家属普遍会经历的心理状态。
“人来到这个世界是没有选择的,但是如何面对死亡却需要学习和选择。”张弛分享到,“电影里有一位计算机教授,他年纪还比较轻,内心充满不甘。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找到了自我,也开始慢慢接受,给母亲留下了自己的AI形象。”
在田虹的工作中,也遇到过很多患者说自己“不怕死亡”,这里的不怕并不是看淡生死,而是不再逃避,勇敢直面死亡。他已经安排好了一切,也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不再害怕了。
对于儿童患者,田虹介绍,他们会注重家庭的支持和情绪的表达。由于孩子无法理解死亡,会通过游戏或绘画,引导孩子描述自己的情绪,以童话的方式建立积极信仰,比如让孩子相信,他只是比父母早一步去了更美好的地方,而且将来必定会和父母再相会,让他们的心灵有所寄托。
对于年轻的成人患者,常常因为人生的突然中断有更深的痛苦和愤懑。这时候,安宁疗护团队通常借助心理治疗师运用意义疗法,帮助他们重构生命的价值。

《好好说再见》剧照
此外,对生者进行哀伤抚慰也是重要的一环。“曾经有一位26岁的大学生在病房去世,我们团队对其母亲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心理辅导和安慰,因为女儿是她唯一的亲人,她的丈夫也去世了。”田虹说,“直到现在,我们还经常上门看望她。”
在这部电影中最令人难忘的镜头之一,是父亲应大海走进病房,在女儿床前插上一束鲜花,在他多次拒绝踏入“顶楼”看向窗外。这一刻,他终于学会放下。
安宁疗护的温暖就这样,从逝者到生者完成了整体善终的闭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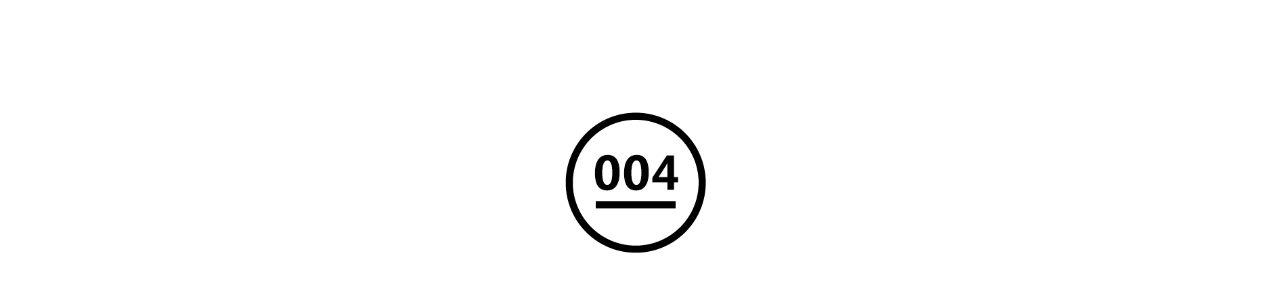
生者,如何疗愈自己?
安宁疗护医护人员面临高情感投入与压力,尤其年轻护士。在张弛对宁波社区医院的前期调研中,他同样发现,大部分医护工作人员比较年轻,由于病人害怕、情绪不稳定,常常遭受很多委屈。
田虹表示“不能离患者的悲伤太近”,太贴近,会被对方情绪所牵引,无法兼顾自己的专业部分,但也不能太疏离,这样会无法与患者共情。
日常中,安宁疗护团队会定期接受心理疏导和减压训练,以专业态度疗护他人。“没有一颗慈悲心,是做不好这份工作的”,田虹强调这种心态的平衡需要多年工作的修行。
告别需要距离,却不失温度。是最后一次爱的守护,而不是与痛苦共融。
回忆起身边的死亡,张弛提到自己两位大伯的离世——一位在医院里毫无准备地走了,另一位在寺庙助念中,有准备地走了。他们离开的过程恰好发生在他创作的阶段,让张弛变得更加“达观”。
“我的父亲也是四年前在我的病房里去世的。”田虹说,“就像大多数中国家庭一样,我们忌讳谈论死亡。我不敢问他想把墓地选在哪里,还有什么心愿,葬礼上想穿什么衣服,只能把对他的爱与纪念写成信,放进他胸前的口袋。”
如今,她的心中不再有悲伤。“我常常想,父亲的陪伴,可能是就是母亲窗外树梢上的一抹新绿,哥哥上班途中落下的一场春雨,或者是我坐在安宁疗护办公室时,吹进来的一阵微风。”

《好好说再见》剧照
死亡终将降临,但在它来临之前,每一个人,都有权利知道如何“好好说再见”。
【时间轴】
01:33 《好好说再见》里,令安宁疗护医师最动容的是哪一幕?
02:15 电影里那些“像极了真实病房”的细节处理
03:20 为何要拍一部关于“死亡”的作品?
06:51 宁波这座社区医院的顶楼,成了影片的锚点
08:41 用绿色,呈现生命的轮回
11:50 去到这个特殊的病房,就离死很近了
14:10 安宁疗护在中国发展到了何种水平?
19:15 安宁疗护病房的收治标准和诊疗方式
21:20 愤懑、不甘、无法理解......年轻人和儿童如何面对死亡?
24:45 缓解终末期疼痛:若身体痛苦无法缓解,心灵安宁则无从谈起
28:39 在死亡来临前,你还能做这些事情
30:00 生者,同样需要哀伤抚慰
31:05 安宁疗护一线工作者,该如何自处?
35:05 见证父亲离世,安宁疗护工作者的自白

策划、主播 / 胡雅婷
监制 / 徐婉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的观点或立场,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