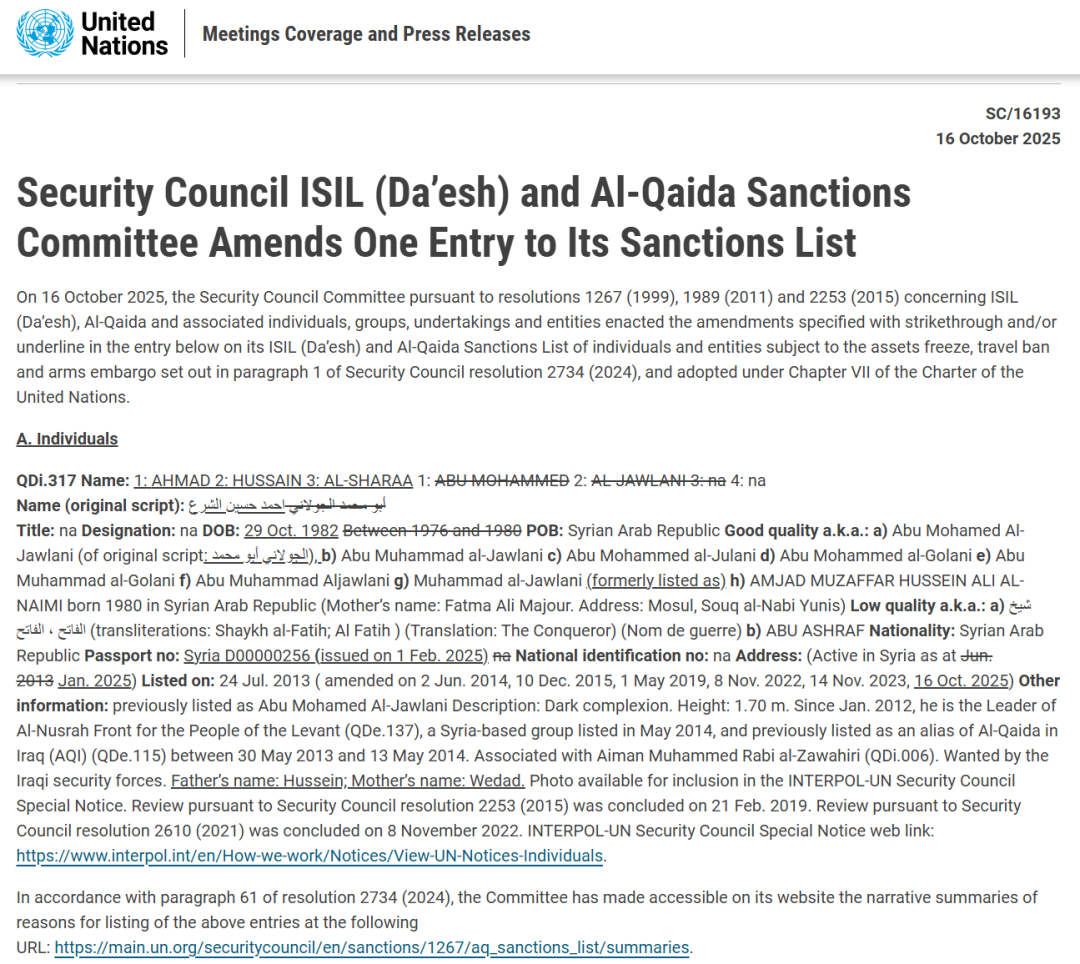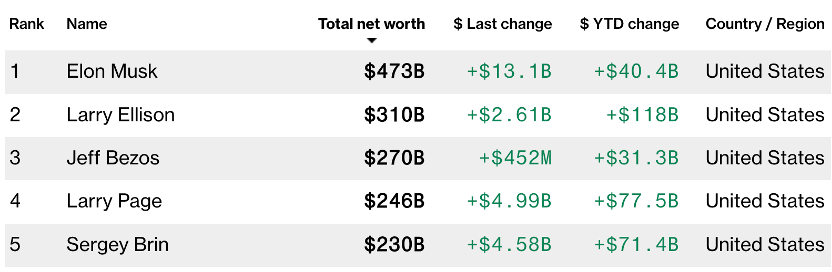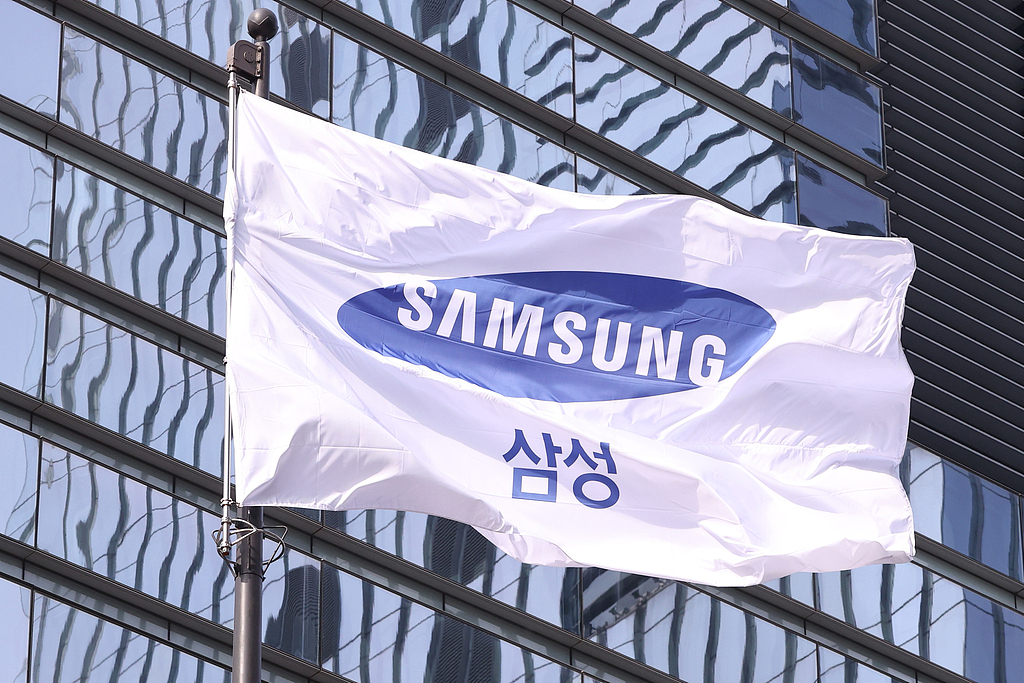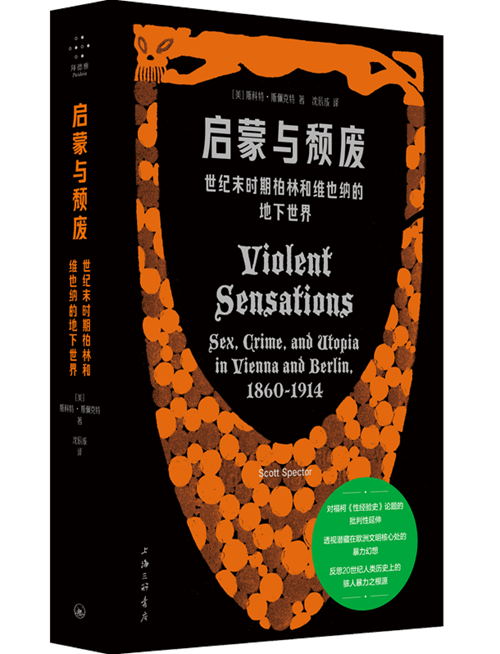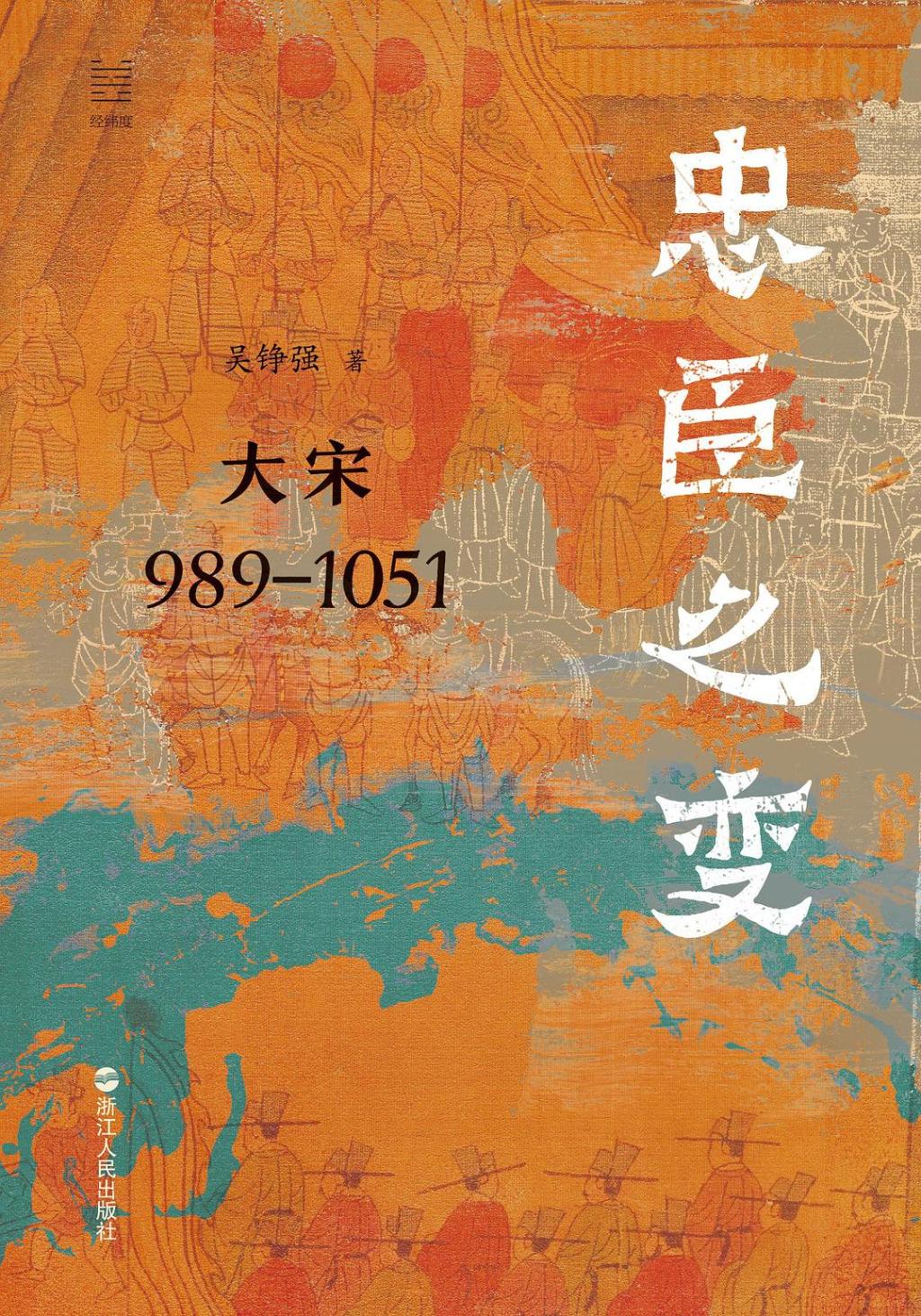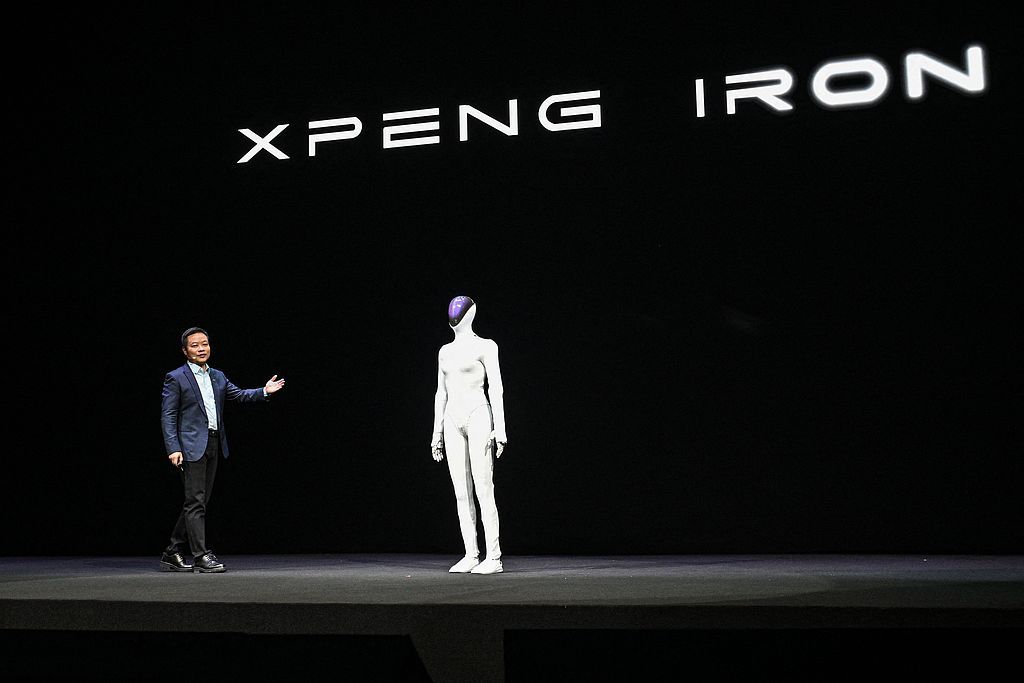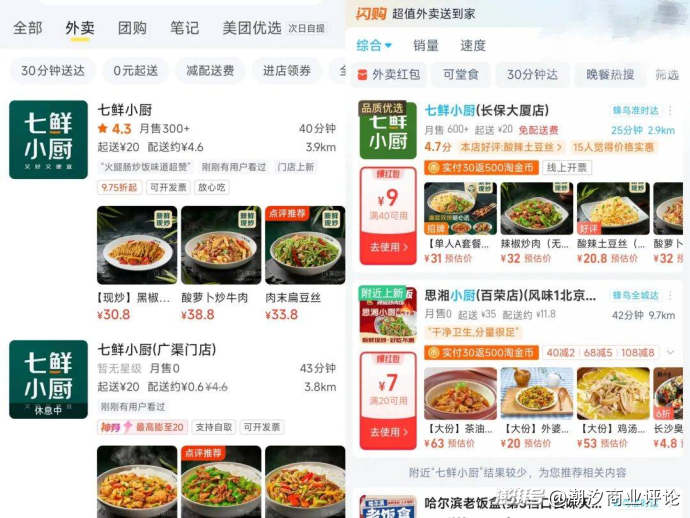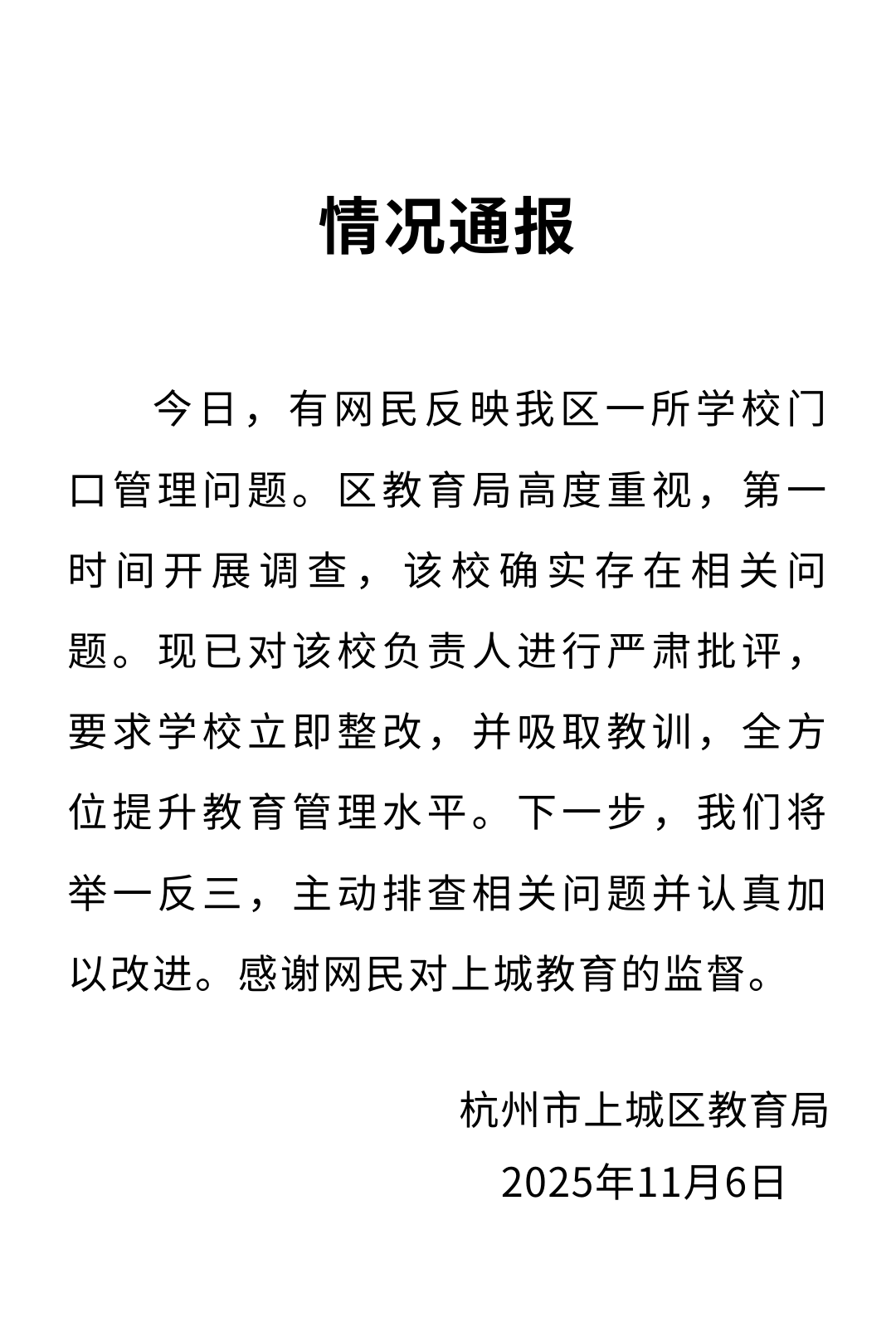历史数据如何驱动城市史研究
2024年11月10日,恰逢顾廷龙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上海图书馆分别在本馆、东馆举办展览,组织学术研讨会,并出版研讨会论文集、书法墨迹选、古籍题跋集等,与此同时,山东大学何朝晖教授主持编印了《为前贤行役——顾廷龙诞辰120周年纪念文集》一书。在图书馆学界,像这样纪念一位前辈,于今来说已不多见。中华书局在此之际,出版《顾廷龙年谱长编》,其意义不言而喻。此前,2004年《顾廷龙年谱》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公开出版,这是沈津先生为了纪念顾老百岁诞辰,匆匆赶编而成的一本大书。时隔二十年,《顾廷龙年谱长编》的出版,自然是对顾老一生最好的回顾,也是献给他一百二十岁生日最好的礼物,
一
近二十年来,年谱长编类著作的出版如雨后春笋,形势十分喜人,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质量上难免良莠不齐。之所以会出现这个局面,既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观的原因。十多年前,沈燮元先生就不止一次告诉我,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写传记、编年谱,早就有十分精到的论述,但真要动手做起来,年谱却也并不容易。他早年就是为了磨炼自己,尝试编了一部《屠绅年谱》,很幸运得以出版。彼时知道屠绅的人很少,但却是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点过名的人。编年谱的难点,主要在史料,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谱主材料多的,编者的主观剪裁很重要,有些年谱长编摘抄谱主日记数十年,一味重复,无新材料,不如直接看日记,气息贯通,更为自然生动。反之,谱主材料少的,客观条件所限,编者虽多方搜罗,将诗文、笔记全部抄入谱中,枝蔓过甚,本末倒置,不如整理成诗文集,以年表作为附录,反而眉目清爽。更有甚者,谱主本人材料少,而友朋中一二人日记、书札留存极完整丰富的,编者抓到救命稻草,悉数收入,使得友朋反客为主,谱主反而边缘化了,这种偏枯的现象,在年谱长编中,也时有发生。
顾廷龙先生一生的行事,在《顾廷龙年谱》中早已呈现出清晰的脉络,毕竟当时已是七十万字的篇幅。《顾廷龙年谱长编》的篇幅,较之《顾廷龙年谱》几乎翻了一倍,这不仅让我们看到一个更近距离、更立体的顾廷龙先生,并且间接揭示了二十年间相关史料的不断揭示与发现。
就顾老本人的一手材料,原本一巨册的《顾廷龙文集》,变成了七卷十册的《顾廷龙全集》,这无疑为《年谱》的补订提供了最直接的支撑。尽管《顾廷龙全集》内容已经相当丰富,但没有收《顾廷龙日记》,2016年11月中旬,我与同事去北京顾诵芬先生家接受《复泉井阑题字册》捐赠时,顾院士当面表达了这一遗憾。之后,在师元光先生全力支持下,我接手了《顾廷龙日记》的整理工作,终于在2022年初由中华书局出版。最初,在师先生交下的《日记》初稿中,除了《顾廷龙日记》中收录的内容之外,有一部分顾老晚年日记片段,我选择了割爱。主要原因是,这部分是师先生从《顾廷龙年谱》中摘录出来的,内容当然很好,却没有底稿可供校对。我曾专门问过沈津先生这部分日记底稿的情况,他告诉我这是从一批顾老随手用的大大小小的笔记本里搜集而来的,事过多年,原稿恐无法逐一找到,令人深感遗憾。因此,《顾廷龙年谱》中收录了《顾廷龙日记》中的大部分内容,而《日记》反而缺少顾老晚年的那些片段。这是使用《顾廷龙日记》、《顾廷龙年谱长编》时,读者应当注意的。
关于《顾廷龙日记》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日记》初稿中最初是没有1932年《平郊旅记》这两个月内容的。在我接手《日记》整理工作后,忽然有一天师元光先生告诉我,顾老应该有一册1932年的日记,名为《平郊旅记》,早已捐存上海图书馆。于是,我写Email给上海图书馆,并请顾院士联系上图,拿到了这一本手稿的扫描件,补入《顾廷龙日记》,同时将这部分内容分享给了沈津先生,补入《顾廷龙年谱长编》,使得1932年的纪事丰满了一些。
《顾廷龙年谱长编》中吸收了近二十年中面世的新材料,如与顾老交往密切的顾颉刚、潘景郑、陈乃乾等的日记、书信之类。尤其是体量庞大的《顾颉刚日记》,从1921年开始,补充了很多顾老早年的事迹,尤其是他们同在北平期间的一些细节。以1932年为例,《平郊旅记》仅存十月、十一月两个月,《顾颉刚日记》中的记录,不仅可以与这两个月相互参证,另又补充了一月至九月、还有十二月的相关内容,比对《顾廷龙年谱长编》与《顾廷龙年谱》,不难发现顾老早年在北平的活动《长编》详明了许多。这一阶段,顾老正在撰写《吴愙斋先生年谱》,若据《顾廷龙年谱》加以考察,只能看到一个粗线条的脉络;再看《顾廷龙年谱长编》,仿佛给高度近视配了眼镜,另外还给了一个放大镜,所见、所得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潘景郑1929年、1933年日记的利用,效果与《顾颉刚日记》差不多,对早年顾老回故乡苏州的活动,作了细节上的补充。可惜,潘先生日记尚有很大一批没有整理,这给《顾廷龙年谱长编》的增订,留下不少余地。在《年谱长编》面世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新出版《杨仁恺日记》、《刘九庵日记》中,也存有零星关于顾老的记录,可供采撷。
事实上,纵览《顾廷龙年谱长编》,不难发现在谱主本人与他人材料的处理上,颇为克制,折中繁简之余,兼顾相互印证,力求允当。对《顾廷龙全集》中已收内容,把握尺度,不缺不滥,更有一部分溢出《全集》之外的材料,是《全集》出版后的新发现材料,为未来增订《全集》提供了诸多线索。
二
从《顾廷龙日记》出发,可以看到青壮年、中年时期的顾老;从《顾廷龙年谱长编》出发,可以看到顾老的一生,他始终都在发光发热。青年时代的顾老,是一个极具天赋的学者,他在学术研究上的几部代表作,基本上都是在三四十年代完成的。学术上的天赋与敏感性,难能可贵处,在于来自跨学科的赞扬。举个很简单的小例子,前段时间读北京大学荣新江先生的新书《满世界寻找敦煌》,意外见到他称赞顾老。在《从羽田亨纪念馆到杏雨书屋》一章中,他提到李盛铎收藏的432号敦煌卷子,被羽田亨买去日本,资金出自武田家族。国内关于这批敦煌卷子,只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了一本《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有所记录。后来,荣先生在上海图书馆发现“藏有顾廷龙先生抄的一个李盛铎藏卷目录,也是432号。顾先生也是很厉害的,他大概是从李盛铎家抄来的,或者在琉璃厂买的。这些学者,他们只要知道哪儿有资料,就赶紧弄一份”(页152)。顾老在敦煌学上,并没有令人瞩目的成果,正是他对文献的高度敏感,才为后人留下了无数的学术盲盒、学术彩蛋。这种例子,在上海图书馆的书库里,应该有很多,不少像家谱、朱卷等已经成了著名的案例,但我相信,还有很多尘封数十年的宝藏等着我们去发现。
毫不夸张地说,《顾廷龙年谱长编》不仅向我们展现了顾老的一生,更时我们了解中国近百年、尤其是新中国成立来图书馆事业发展、特别是古籍事业发展的重要角度与线索。在七十多年的时间线上,《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续修四库全书》都早已耀眼的亮点。
而在此之前,从1939年到1953年十四年里,顾老在上海主持私立合众图书馆工作,历经抗日战争、孤岛时期,一直到上海解放,苦苦支撑,不断壮大。合众图书馆可以说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从无到有,由小变大,成为当时上海著名的文化机构之一。《日记》无疑是最直接的实录,却只是从他本人角度做出的记录,若加上他人的材料,或许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最近,中国人民大学的吴真教授写了一本《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讲述郑振铎在孤岛时期的上海所做的抢救文献活动,颇受好评。之前整理《顾廷龙日记》时,我隐隐觉得,当年顾老因不了解内情,对郑振铎在上海抢购古籍善本,似乎印象不太好,可能是与合众图书馆形成了竞争关系,有些顾老想保存的文献,由于抢购价格升高,没有帮合众买下,让他深感遗憾。而《顾廷龙年谱长编》结合多方史料,重新回顾这段往事,历经岁月的沉淀,立体式的记述,显得多源而客观。
有时我不禁会想,若以顾廷龙先生作为主角,是不是也能写一本类似于《暗斗》的作品呢?个人觉得,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只不过我没有那样的才华与文笔罢了。依我的浅见,《顾廷龙年谱长编》给我们提供了几个可供深入挖掘的点,一个是孤岛时期的上海合众图书馆,目前谈馆史的多,谈人、谈书的少,背后的暗流涌动,一旦揭示开来,必定十分精彩;一个是《中国丛书综录》的编纂出版,在短短一两年时间里,跃进式的成果,经受了历史的考验,无法想象,那一段热血澎湃的往事里,主角竟是一群长期身处故纸堆、习惯坐冷板凳的学者;一个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出版,举全国之力,前后持续近二十年的浩大工程,背后的甘辛,非亲历其事者无法言说,可惜全程参与者生前惜墨如金,没留下太多的记述,而今大半凋零。好在这些题目,《顾廷龙年谱长编》都为我们提供了大纲和线索,至于细节仍有待后来者细细琢磨。
三
说到细节,这次我也注意到了两个,这是之前读《顾廷龙年谱》没想到的。巧合的很,这两个细节,都和《顾廷龙日记》有关。《顾廷龙日记》中,我最遗憾没收的有两部分内容:一个是1963年十一月、十二月顾老作为中国书法家访日代表团成员赴日本访问的日记,一个是1989年二到三月他赴美国参加编辑“全美中文善本书联合目录”国际顾问会议的日记。前者题为《访日游记》,已收入老版的《顾廷龙文集》,但至今没看到底稿;后者是沈津先生摘自“先生小笔记本”,并未全文发表。我一直对“先生小笔记本”深怀好奇,却始终无缘一见。
言归正传,顾老访日期间,有一个非官方的任务隐藏在《访日游记》背后,之前《顾廷龙年谱》没有显现出来,那就是寻找流散到日本去的《永乐大典》。二十年前读《顾廷龙年谱》,之所以没有注意及此,主要还没看到1964年三月十日顾老写给陈乃乾的那封信,信一开头他便说“想公必在盼望《大典》情况矣”,然后逐一说明在日本期间,到京都博物馆、人文研究所等处,寻找上野精一旧藏《永乐大典》,查到人文研究藏书目录中有一个隆庆中吕鸣瑒抄本。《顾廷龙年谱长编》中全文收录了此信,信中所述,和《访日游记》互为表里。据《日记》记载,十二月七日,在今井凌雪、金翚陪同下,顾老参观天理图书馆,在善本书库见《永乐大典》七皆一册。十二月十二日,顾老又有托小野和子找日本藏《永乐大典》目录。十二月二十一日,参观东洋文库时,馆长岩井大慧赠其所著《永乐大典收藏情况表》。两个多月后,忙完手头工作后的顾老,给陈乃乾回信,并将《永乐大典收藏情况表》寄给陈乃乾参考,并告知“属访《大典》经过如此,恐不足以厌所望,乞谅。仓石武四郎、长泽规矩也两君均曾晤,但未谈及《大典》”。
彼时陈乃乾已调任中华书局,主持影印《永乐大典》。据张忱石《<永乐大典>的收集和影印》一文称,中华书局“1960年把当时收集到的七百三十卷影印出版。影印本为三十二开朱墨两色套印线装本,凡二十函二百零二册。这是《永乐大典》诞生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刊印”。陈乃乾托顾老到日后查访《永乐大典》,据《顾廷龙年谱长编》应是1963年十一月十九日晚上七点三刻在北京访陈氏时事。
至于访美,是距访日二十六年之后,顾老以八十六岁高龄第二次出国,这次他与周一良同行。先后参访了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地,前后共计二十天。在纽约期间,由郑培凯先生陪同、照料,沈津先生告诉我,这是他拜托郑先生的。据美籍华裔历史学家谢正光在《钱遵王诗集校笺》后记中回忆,他获悉顾老到美,曾偕夫人专程到纽约拜望:
及返美后不久,得闻顾先生有美东之游,急携绛云飞往纽约叩见。时逢一旧交设盛宴为顾老洗尘,获邀作陪。是夕,绛云与顾老并坐,以苏州话对谈。席上有一原籍吴中之国际知名学人,则自始至终操英语,夸夸其谈,旁若无人。此平生唯一至难理解、至难忘怀之事也。
谢正光夫妇参加在纽约为顾老接风洗尘的晚宴,这个细节,《顾廷龙年谱长编》中没有记录。但对照《年谱长编》,推测谢先生所说设盛宴的“旧交”应该就是郑培凯,这似乎并不难。更令人好奇的是,那位在席间操英语,夸夸其谈,旁若无人的“原籍吴中之国际知名学人”是哪一位?谢正光先生并没有明说,《顾廷龙年谱长编》从头到尾没有提及他的名字。结合纽约、苏州人、英语流利以及东道主等几个关键词,不免让人猜测,“国际知名学人”会不会是夏志清(1921—2013)?留下谜团的谢正光先生已于去年12月在美国去世,或许只有问三十五前那场盛宴的东道主郑培凯先生,才能知道正确答案。
匆匆又经年,去年十一月初,我因事去苏州大学老校区,寒风冷雨中,撑着伞经过十梓街的望星桥堍,一抬头便看见顾廷龙先生的故居——复泉山馆,屋顶的黑瓦不再陈旧,大门紧闭,院墙直接外扩到马路边。之前挡在宅前的一排楼房悉数被拆去,与几年前隐蔽、局促的老房子相比,气势完全不同了。上个月,沈津先生自美返国,十月十八日来苏州,约我在乐桥见面,随后一同重游顾老故居,行抵望星桥堍时,天忽然下起了细雨,去年清冷的场景,再次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仔细回想,七年前的暮春时节,我们和沈燮元先生一同来过这里,彼时老宅闭门谢客,大家只能悻悻而返。而今我们终于得偿所愿,登堂入室了,只是沈燮元先生已于两年前谢世,忆昔同游少一人,高兴之余,不免又令人怅怅。
沈燮元先生曾对我讲起,在北京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期间,他曾和“冀大姐”(冀淑英)等商量,约顾老一起到法源寺吃顿素斋,想着请赵朴老打个招呼,本就有名的素菜,庙里做得肯定更好。结果他向顾老说起这个提议时,没想到顾老说了一句“老沈啊,素菜没有荤菜好吃”,素斋自然也就没吃成。这件小事,《顾廷龙年谱长编》当然没有记,却让我想起《年谱长编》里有顾老晚年在北京,托人给他带福建肉松、玫瑰腐乳。一种熟悉的味道,透过文字,带着江南人家泡饭的米香,混合着肉松丝丝口感和腐乳的红糯咸甜,一下子让人觉得,顾廷龙先生的形象又鲜活了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