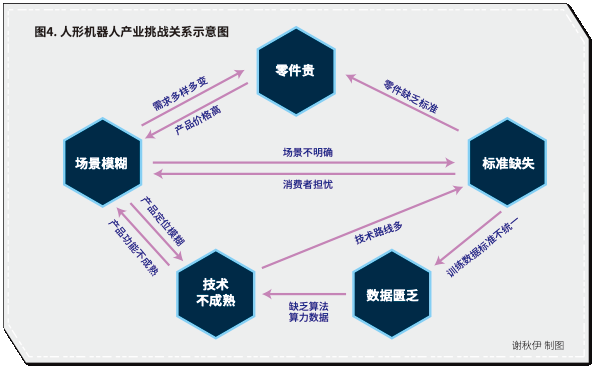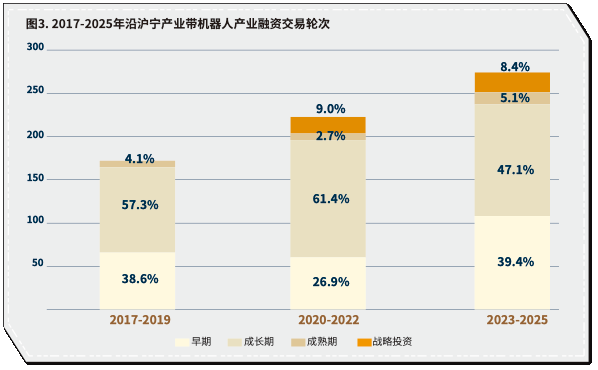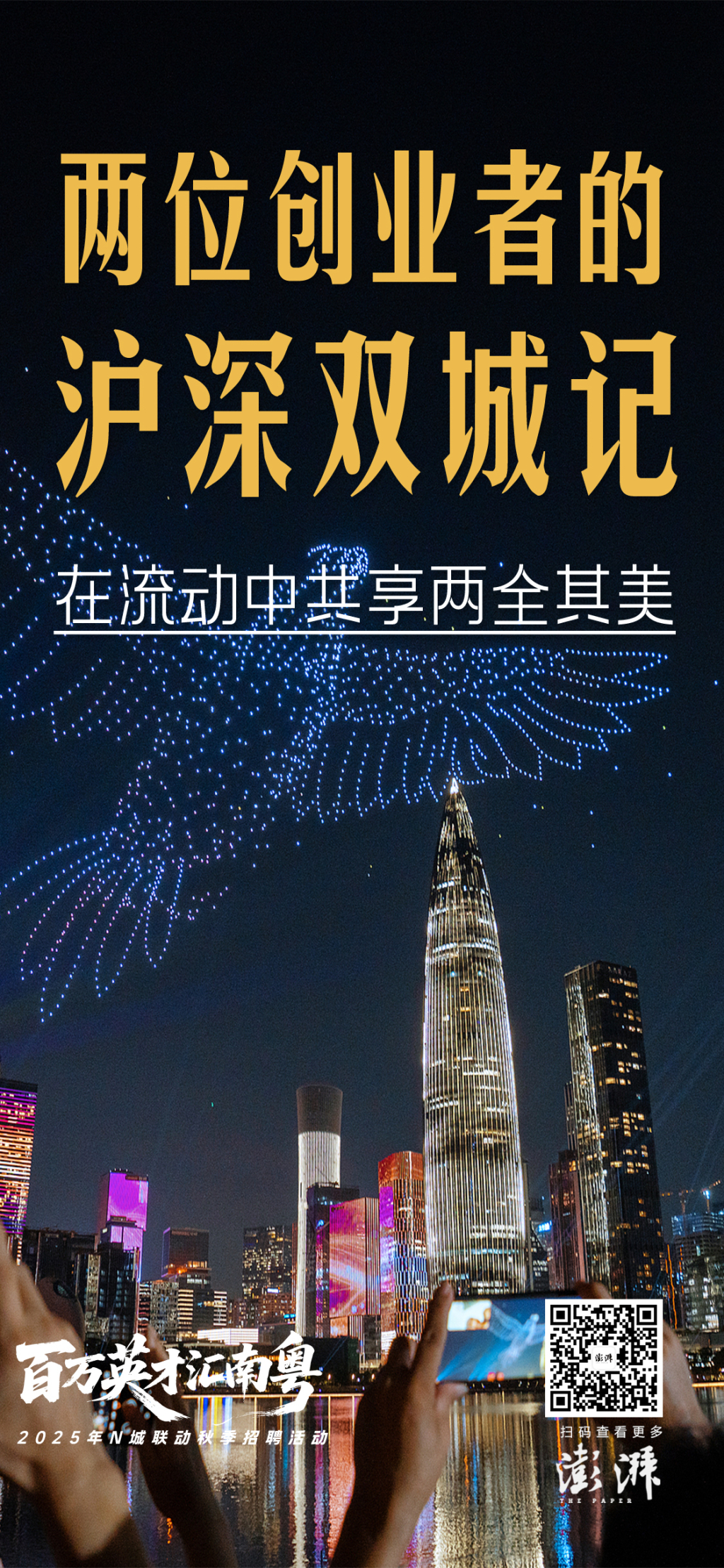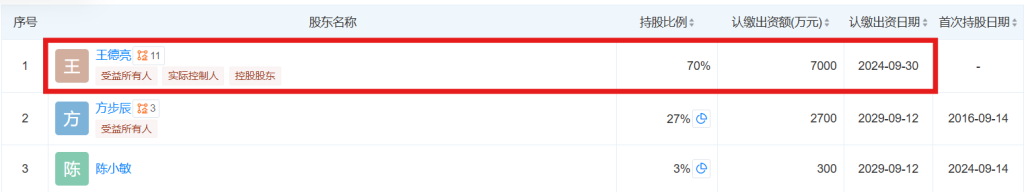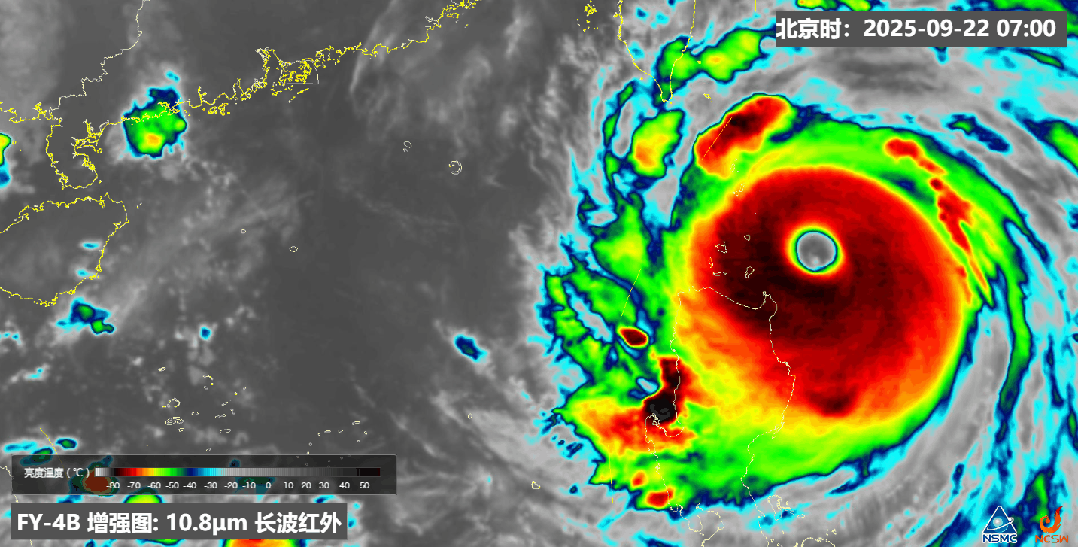交易成本节约:中国式统一大市场的政策逻辑
统一大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一环,有利于将中国经济国内大循环中的“规模但不经济”症结充分“解锁”,并通过本土市场效应转换为国际大循环竞争中新的比较优势,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跃上新台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统一大市场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进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交易成本是理解中国式统一大市场及其历史进程的一把钥匙。这是因为,影响全国范围内市场“连成片”的因素无非是运输成本带来的自然分割与地方保护等交易成本带来的行政性分割。考虑到中国“铁公基”建设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前,行政性分割日益成为统一大市场进程中的主要矛盾。换言之,交易成本节约本质上可视为中国式统一大市场进化的底层逻辑,交易成本下台阶,市场统一程度就会上台阶。
一、交易成本是理解中国式统一大市场的一把钥匙
效率是经济学的中心概念,人类对经济效率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开篇,就论述了分工是效率提升和增加国民财富的关键,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带来规模报酬。规模报酬带来的经济效率提升依赖于以下三点:一是产业的不断分工和专业化是实现规模报酬递增的基础;二是报酬递增取决于劳动分工的发展;三是市场规模的扩大将进一步促进劳动分工。
统一大市场本质上也是对更大范围、更加专业化的分工提升经济效率的追寻。中国式统一大市场可理解为全国范围内基于价格信号分工协调并“连成片”的开放性共同市场。具体来看,市场的本质是由价格信号作为分工协调机制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全国”框定了分工协调的市场范围,市场从特定行政区向周边拓展直至在全国范围内“连成片”,“统一”意味着开放性共同市场的形成,带来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与规模报酬,从而释放中国1.8亿户市场主体、4亿多人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规模市场内需潜力,并通过“本土市场”效应转换为国际大循环中新的比较优势。
全面地认识全国统一大市场,需要简洁有力的经济学分析工具,交易成本是理解中国式统一大市场的一把钥匙。在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形下,统一大市场意味着同一产品或要素在不同地区的价格是相同的,即“一价定律”。真实世界中,不仅存在运输成本,也存在着交易成本,特别是地方保护带来的市场壁垒等制度性交易成本。运输成本造成市场的自然分割,交易成本则带来市场的人为分割。自然市场分割短期内难以改变,一定意义上也无需完全改变,因为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远远超前了,统一大市场的症结主要在交易成本。交易成本若能够通过相应的改革实现有效节约,市场的统一程度就会相应提升。
直观地看,交易成本节约涉及地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以价格信号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机会成本是政府通过行政命令配置资源。政府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边界取决于交易成本,谁的交易成本更低,就应该由谁来配置。通常情况下,政府配置资源较为有效率的是提供信息、基础设施等具有外部性的公共产品,而没有外部性的私人产品通常是由市场配置更加有效。如果地方政府过度配置要素资源,从公共产品延伸到市场配置更加有效的土地、劳动力、资本等公共产品以外的领域,交易成本必然偏大,带来较大的潜在效率损失,且不同地区差异也比较大,使用这些要素的企业也就面临着一个行政分割的要素市场。
进一步看,要从根本上推动交易成本节约,涉及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即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问题。因为地方政府与市场关系实际上是中央和地方关系所内生的。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对地方的政绩考核机制决定了地方政府及其主官的政治激励,而财税体制则决定了地方政府的经济激励。地方政府“制造”交易成本的激励内生于央地关系。然而,地方政府打破市场分割面临着囚徒困境。虽然所有的地方政府都破除地方保护,相互之间都是受益的;但在其他地方政府进行地方保护的情况下,某一地方政府破除地方保护,将是受损的。
二、阶段性重点:从产业下游的产品市场到产业上游的要素市场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地方政府从“直接的生产者”转变为“间接的征税者”,角色转变重塑了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地方保护带来交易成本提升的重点领域也从产业下游的产品市场转向产业上游的要素市场;相应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交易成本节约的阶段性重点,也应从产品市场转向要素市场。
改革开放之初,短缺经济叠加分灶吃饭的格局下,地方政府以所有者身份大办国企和乡镇企业,产品不愁卖,能够获得可观的财政收入,但外地产品的流入则会带来不利影响。这一阶段,地方保护带来的交易成本突出表现为地区市场封锁带来的进入成本,各地鼓励“抽本地烟、喝本地酒”,阻碍甚至禁止外地产品流入。中央政府相继出台《国务院关于在工业品购销中禁止封锁的通知》(1982年)、《国务院关于打破地区间市场封锁,进一步搞活商品流通的通知》(1990年)等政策文件,但收效甚微。
上世纪90年代产能阶段性过剩后,地方政府作为“直接的生产者”的效率低下问题日益显露,加之1994年分税制改革导致地方政府进行产品市场保护的激励弱化,地方政府的角色逐步转变为“间接的生产者”,即开展招商引资竞争来吸引流动的制造业企业获取新的财源。要素市场分割成为地方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压低工业用地和劳动力等要素价格,持续追加要素投入,形成价格竞争优势,伴随2001年加入WTO后国外市场的充分开放,助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需要指出的是,市场分割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高速增长阶段对应着倒U型曲线的前半段,这一阶段国外市场的拓展并非国内市场自然扩张的延伸,而是地区间市场分割导致国内贸易严重滞后的产物。要素“一价定律”的国内资源配置效率无法实现,从而使得国际资源配置过程缺乏国内资源配置最优化的支持,客观上致使各地区将更多注意力转向对外贸易,不同程度地形成了“对外贸易偏好”,即以对外贸易替代国内贸易,客观上加剧了国内市场分割程度,呈现出“大国贸易规模”和“小国贸易条件”的双重特征。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意味着进入倒U型曲线的后半段。国外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强,继续追加要素投入的边际报酬快速递减,国内市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要素市场分割造成的“规模不经济”成为主要矛盾,新的经济增长点主要来自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组合优化产生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跃升。要素的组合优化以要素的自由顺畅流动为前提,要素市场也就成为当前阶段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中之重。
历史地看,全要素生产率的跃升通常与巨大的制度红利相对应。2001年加入WTO带来面向国际大循环的出口红利,全要素生产率在2001-2007年间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26.6%。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四万亿刺激计划使得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弱化,2008-2012年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骤降至2.4%。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回升至19.7%,但仍显著低于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亟需进一步释放国内大循环的市场规模经济红利,必然要求劳动力、资本、数据等要素在更大范围内更加顺畅地流动,以便利要素组合优化带动全要素生产率跃升。
企业家是要素使用与创造性组合的主体,企业家精神向生产性活动的涌流实际上也倒逼制度性交易成本节约。高质量发展是创新驱动的发展,比以往任何阶段都需要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配置到创新等生产性活动中时,1%的企业家精神增长便可以带动约3%的经济增长;但企业家精神也可以配置到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中,影响企业家精神配置的关键变量是基础制度规则。如果市场的基础性规则,在本地外地企业之间、在本国外国企业之间、在国有民营企业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企业家精神配置到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的激励便会明显增强。统一的、公平竞争的市场基础制度规则,有助于消除规则间的寻租激励,引导企业家精神更多地配置到创新等生产性活动中来,有效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以统一的基础制度规则降低交易成本
通过央地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产业上下游关系的适应性调整,以自上而下的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实现交易成本节约,特别是要素市场的交易成本节约,是中国式统一大市场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
强化中央政府对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主导权,弱化地方保护的激励。需要明确统一大市场建设是与国防、外交、国家安全等并列的中央事权。以市场取向的自上而下的基础性规则,作为统一大市场建设激励约束指南,激励有突出成效的地区从而实现有效引领,识别并动态规范不当市场干预与不当竞争行为。中长期内,则应改革地方政府及主官的目标函数,将高质量发展与统一大市场的关键指标纳入政绩考核,弱化地方保护的政治激励。将统一大市场建设与新一轮财税改革联动,转移支付与交易成本节约挂钩,使得地方打破分割的收益大于进行保护的收益,渐进式弱化地方保护的财政激励。
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以统一的产业政策底线规则规范地方招商引资。加快推动土地、劳动力、数据等上游要素的市场化改革,统一土地、税收优惠等产业政策底线标准,更新《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2006),并严禁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进行“超常规优惠”,加快对存量政策进行摸排,设置过渡期,到期后一律废止。以城市群或都市圈为单元,进一步降低大城市落户标准,引入“教育券”“租房券”等政策工具助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统一基础性市场制度规则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严格落实“全国一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严禁各地区各部门自行发布具有市场准入性质的负面清单。推动能源、交通、通讯等现代社会重大基础设施标准统一与高效联通。基础性规则与标准之外,积极发挥团体标准的支撑作用,通过行业自律缓解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相关问题,避免政府标准定得过细挫伤市场主体创新积极性。
提升基础性规则执行的透明度与公平性。在中央层面建立统一的规则与标准的基础上,明确各地区、各部门的执行边界,弱化监管部门和执法人员自由裁量权。建立地区间、部门间执法信息共享机制与市场主体的投诉反馈机制。
(作者王瑞民系经济学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本文首发于《清华金融评论》2025年6月刊,刊发时有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