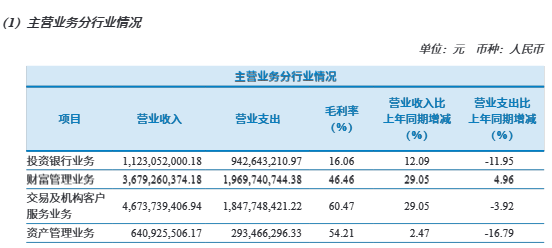七夕节|走过爱情的“窄门”
你要努力进窄门。
这句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的箴言,据载是耶稣讲述的关于灭亡与生存的两道门与两条路。行走向灭亡之道的人多,因此那便是一道“宽门”,而能走入永生之门的人少,所以那便是“窄门”。在两千年的时光里,这句话被无数寻求救赎的灵魂奉为圭臬。它指向一条艰难、孤寂却通往永生的道路。这条路,要求信徒舍弃世俗的欲望,以纯粹的信念去追寻那终极的神圣。
《窄门》同样也是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创作的爱情小说,因此在纯粹的宗教思考以外,“窄门”也成为了提及爱情时的经典象征。它似神秘而危险。它将宗教中关于“牺牲”与“德行”的追求,嫁接到了人类最复杂、最本能的情感之上,从而开启了一场注定走向悲剧的、以爱为名的精神苦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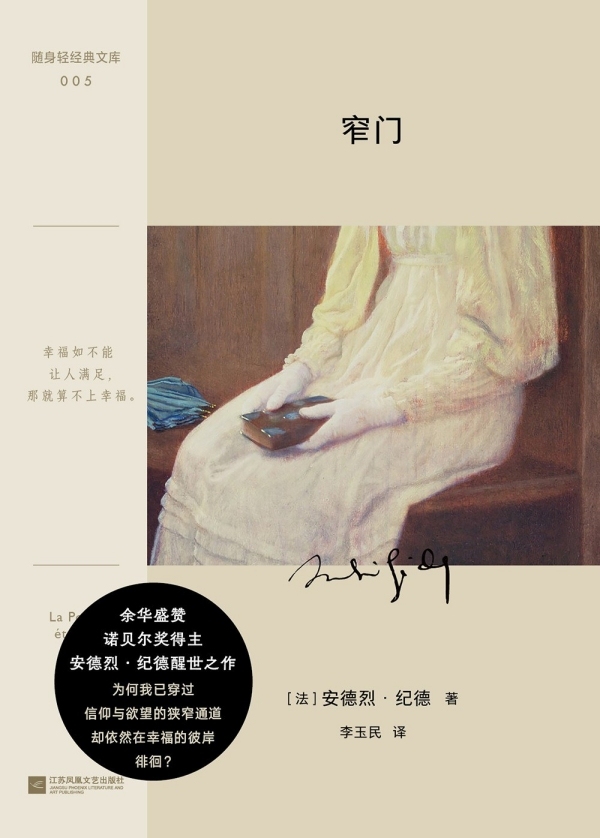
《窄门》,【法】安德烈·纪德/著 李玉民/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新流文化,2024年10月版
故事围绕着一对恋人:热罗姆与他的表姐阿莉莎,他们自幼青梅竹马,拥有着共同的信仰、智识与品味,他们的爱恋,从一开始就奠基在一种纯洁无瑕、充满精神性的土壤之上。在热罗姆眼中,阿莉莎是引领他走向“德行”的灯塔;在阿莉莎心中,与热罗姆的结合,本该是上帝应许的尘世幸福。然而,正是这份看似完美的、两小无猜的感情,却又暴露了它的脆弱。
我们出于爱情而彼此期望对方得到比爱情更高的东西,从那时起,我们就来不及了。由于你,我的朋友,我的梦想上升到那么高的地方,以致任何人间的满足都会使它跌落下来。我常常想我们在一起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一旦我们的爱情不再是美满无缺时,我就再也忍受不了它……
这段话,是理解阿莉莎内心世界的钥匙。它精准地描绘了一种致命的、属于完美主义者的爱情心理。在阿莉莎心中,她与热罗姆的爱,已经不再是普通男女的感情,而被她亲手塑造成了一件悬于高空的艺术品。她既是这件艺术品最忠实的守护者,也成为了它最偏执的囚徒。
她恐惧的,是“人间的满足”这种不可避免的“重力”,是完美无缺之后的瑕疵。而那句神圣的经文,则为她这种恐惧提供了最高尚的理由,将其从个人选择,升华为了一种神圣的使命:
你还记得《圣经》上这段话吗?它曾使我们不安,我们害怕没有看懂:“他们未得到所应许的东西,因为上帝给我们预备了更美好的事。”
这句经文,成了阿莉莎全部行动的最高纲领。她将尘世的爱情与婚姻,定义为那个“应许的东西”,而她要追求的,是那个凌驾于其上的、“更美好的事”。这让她获得了一种崇高的、不容置喙的理由,去拒绝唾手可得的幸福。
这几乎成为了一种堪称危险的力量,一种以“圣洁”为名的力量,它允许阿莉莎将自己最深的恐惧——对现实的恐惧、对不完美的恐惧——最终理解为一种对上帝的虔诚。这种力量让她心安理得地推开热罗姆,因为每一次推拒,在她看来,都是在帮助彼此的灵魂向着那个“更美好的事”上升。她没有意识到,当她把目光执着地望向天国时,她脚下的人间乐园,正在寸寸枯萎。这种力量,最终异化为一种温柔的残忍,一种以爱为名的、最彻底的伤害。她写给热罗姆的信,充满了这种矛盾的情感:
相信我:当你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不能更多地思念你。我不愿意使你难过,可是,现在我不希望你来。要我说心里话吗?我要是知道你今晚来……我会逃掉的。
啊,请求你,别要求我向你解释这种……感情,我知道我一刻不停地思念你(这足以使你幸福)。而我这样也感到很幸福。
这段话完美地诠释了她的悖论:真实的热罗姆的存在,会干扰她对那个“理想的热罗姆”的思念。她的爱,在距离中才能保持纯粹,在想象中才能抵达完美。现实的靠近,对她而言,是一种“污染”。于是,她选择将爱人禁锢在思念之中,并把这种禁锢,当作是彼此的幸福。
阿莉莎几乎是以殉道的姿态走向了她生命的终结。我们并不能得知那是否是她通向“更美好的事”的道路,这份感情也以破碎而告终。

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
在故事中,阿莉莎的妹妹选择了“宽门”。朱莉埃特,那个同样爱过热罗姆,却在被拒后迅速拥抱现实的女孩,成为了阿莉莎选择的对照组。她结婚、生子,拥有了一个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或许有瑕疵但却充满生命力的家庭。纪德借由朱莉埃特,向我们展示了那条被阿莉莎鄙夷和抛弃的道路——那是一条通往世俗幸福的宽阔之门,它接纳人的欲望、软弱和不完美,它通往的是“生活”本身。而阿莉莎,则决绝地走向了另一条路,一条通往“圣洁”,却也通往“虚无”的道路。
阿莉莎的选择,呈现出了一种复杂的样态:她爱上的是“爱情”本身,而非具体的人。抑或说,她以具体的人开始爱起,但将这份具体的情感,一步步抽象化、概念化,最终变成了一个与现实中的热罗姆无关的、纯粹的精神图腾。当热罗姆远在天边时,她可以在想象中将他美化成完美的圣徒,他们的爱在书信往来中圣洁无瑕;可当热罗姆回到她身边,带着一个真实男人的气息、欲望和不完美时,她感到的却是恐惧和疏离。那个真实的热罗姆,会玷污她心中对于过往纯洁无瑕的爱情,玷污她对于崇高爱情的构想。
所以,她在以一种极致的切断换取一种永恒。她恐惧的是“爱的熵增”——任何炽热的情感,在时间的冲刷下,都不可避免地会趋向复杂、无序和温吞。她害怕这份初始完美的爱,会在日常的消磨中变得面目全非。她无法接受幸福最终会趋于平淡,激情会归于温和,神圣的恋人会变成需要面对生活琐事的伴侣。于是,她选择在爱情最巅峰的时刻,亲手将它终结,以一种最决绝的方式,让他们的爱永远停留在了那个“未完成”的、充满可能性的、最纯粹的阶段。她切断了所有的未来,以此换取了一个永不褪色的过去。
阿莉莎追求的或许是宗教的信仰,也或许是一种偏执的对于爱的信仰。她感到了无法承担后果的脆弱,她也不想放弃这份感情。表面上,她不断地向上帝祈祷,将热罗姆推向所谓的“德行”高处,似乎是在追求一种宗教上的圣洁。但她无法承担的“后果”,就是爱情进入现实之后必然的不完美。她不想放弃的,也不是热罗姆这个人,而是“爱着热罗姆”这件能让她感受到自身圣洁与伟大的事情。
在阿莉莎这场盛大而孤寂的“殉道”中,热罗姆扮演了一个极其微妙且关键的角色。他是这场悲剧的亲历者、受害者,但同时,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同谋”。
热罗姆是这个故事的叙述者,却在这个故事中显得无言而沉默。他的叙述冷静、克制,充满了对往昔的追忆,却缺少了主动参与。他更像是一个事件的记录员,而不是一个局势的改变者。他忠实地记录了阿莉莎如何一步步将他推开,记录了自己如何一次次地困惑与服从,但他很少发出过自己的声音,去质疑、去制止这场以“德行”为名的精神苦旅。他更像一个忠实的观众,看着心爱的人走向悬崖,却只是站在原地,为她的“圣洁”而感叹。
他对阿莉莎的爱毫无疑问是忠诚的,直到结尾,当阿莉莎提到他未来将和别人娶妻生子,他还在悲伤地回应:“你明明知道我只爱你”,然而他的一切选择都由阿莉莎的选择而被动做出:他在这段感情中也在一定程度上迷失了自我。这正是热罗姆最致命的软弱。他的忠诚,变成了一种被动的顺从。阿莉莎将爱情定义为一场通往窄门的求索,热罗姆从未想过要去改变规则,他只是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陪同贯彻的人。他缺乏一种强悍的、充满生命力的激情,去击碎阿莉莎病态的幻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沉醉于这种充满高级趣味和悲剧美感的爱情模式中,享受着自己作为“忠诚受难者”的角色所带来的道德优越感。他对阿莉莎的精神追求,有一种近乎崇拜的、软弱的顺从。
人是否可以逃离自己可选择范围内的悲剧?她听上去追求的是更本质的爱,但她又违背了爱的本质。他们的爱成为了一场悖论。阿莉莎追求的,是一种抽离了肉身、日常和不完美的“本质”,但爱的本质恰恰在于接纳一个完整的、立体的甚至有些粗糙的现实。她的爱,是一场盛大的单人祭祀,而非双向奔赴的双人舞。它引诱我们相信,最伟大的爱,是通过放弃爱本身来达成的。这既是这本书的核心悲剧,也是无数情感困境的寓言。
最终,他的性格完美地“配合”了阿莉莎的病态。阿莉莎需要一个愿意陪她玩这场“圣洁游戏”的对手,热罗姆从未拒绝;阿莉莎需要一个足够“高尚”,以至于让她觉得世俗婚姻会“玷污”他的人,热罗姆努力成为了这样的人;阿莉莎需要一个足够软弱,不会强行将她从自我毁灭的幻想中拉出来的人,热罗姆恰好做到了。他用《圣经》中的比喻为自己的选择做了注解:
阿莉莎就像是福音书中那颗无价的珍珠,而我是卖掉一切以得到珍珠的人。
可以说,是阿莉莎亲手建造了这座通往毁灭的窄门,而热罗姆,这个忠诚的信徒,则是在一旁默默跟随的人。他的终身未婚,是他作为“同谋”最终付出的代价,也是这场悲剧的尾声。
“你希望很快忘记吗?
我希望永远不忘。”
然而,搁置阿莉莎与热罗姆最终走向极端的悲剧,这本书也非常真实地道出了在所有感情之中都存在的困境:我们都渴望永恒,但生命与爱的本质却是变化——越没有距离越容易溃败。这是一种现代人愈发能够感同身受的恐惧。当浪漫爱的叙事不再被广泛地接纳,人们都害怕“感情”“关系”中的美好会被时间、被现实所磨损和玷污。于是,我们陷入了“刺猬的困境”。爱情的理想是“零距离”的融合,但现实却是,靠近彼此会放大瑕疵、侵蚀边界、产生无尽的摩擦。
阿莉莎和热罗姆的悲剧,在于阿莉莎对“窄门”的诠释:她以为那是一道需要独自通过的、通往圣洁的门,为此不惜舍弃彼此的爱。但或许,真正的“窄门”,恰恰是需要两个人携手,才能勉强挤过的、通往真实生活的那道门。它需要放弃对完美的执念,接纳彼此的尖刺,在日复一日的磨合中,寻找那个虽不完美但却温暖安全的距离。
七夕节,喜鹊搭起跨越天河的鹊桥,供牛郎与织女穿越困住彼此的“窄门”。如今想来,这一则中国的浪漫故事却也不约而同地和《窄门》的故事有所呼应:当一年只能见一次面时,生活中的琐碎便不会再被提及,而彼此在想象中都被美化成了最完美的模样。距离,成全了爱情的神话。然而,这毕竟是神话。凡人无法生活在一年一见的神话里,我们必须面对日复一日的真实。
走过爱情的窄门,其真正的意义,不在于抵达某个没有瑕疵的永恒天国,而是在布满荆棘的现实之路上,学习面对并接纳另一个不完美的、真实的灵魂,这或许是凡人的爱情中,最接近神性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