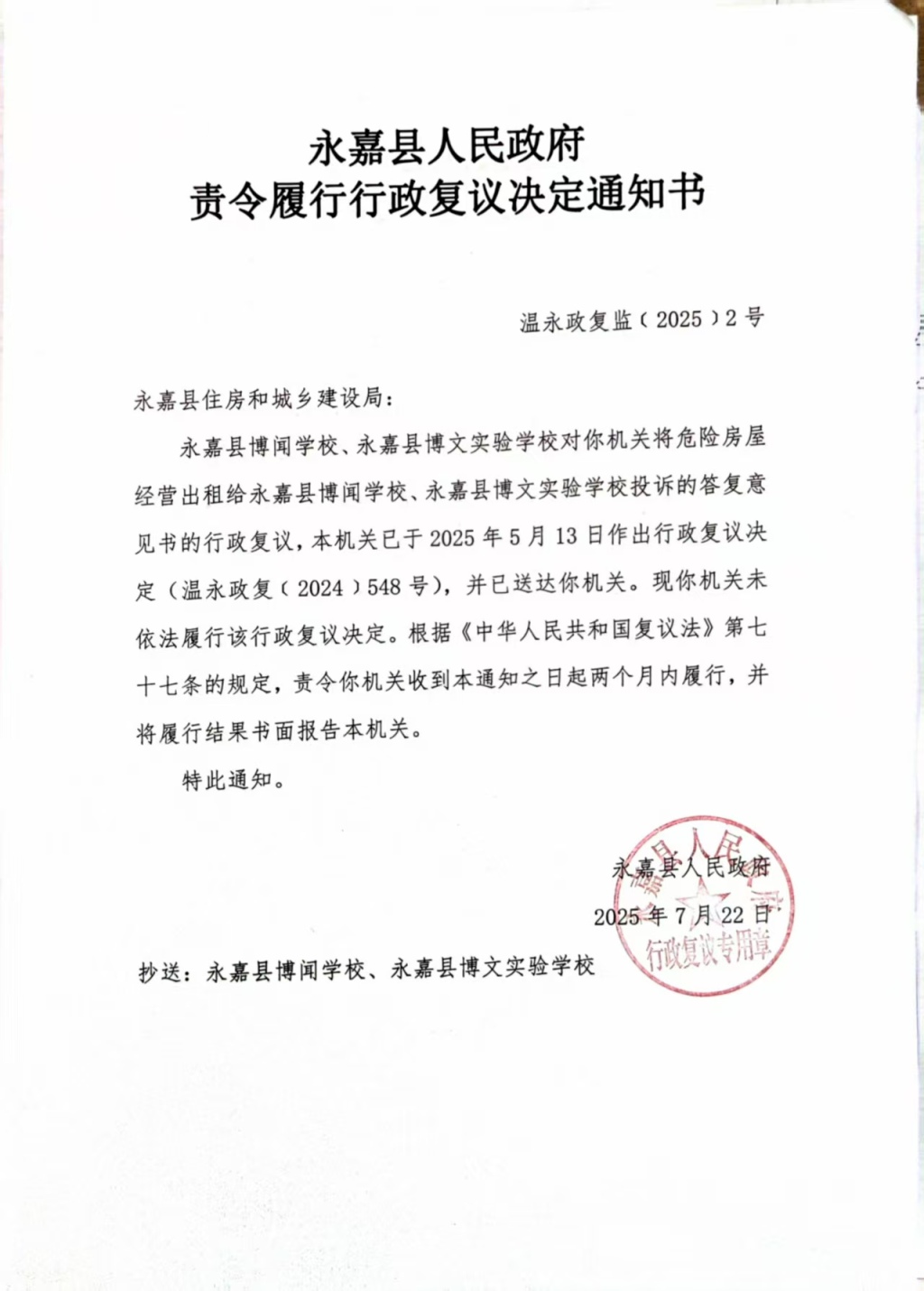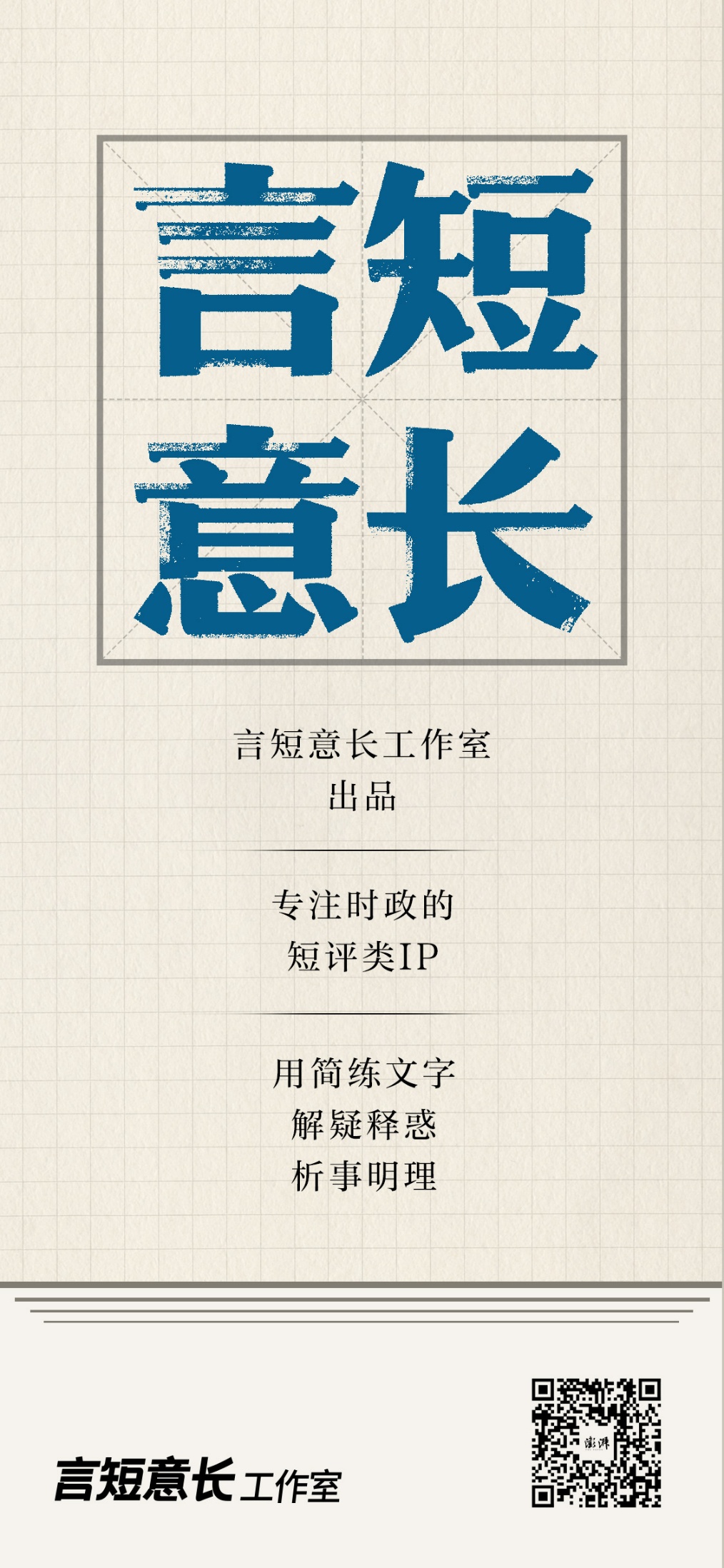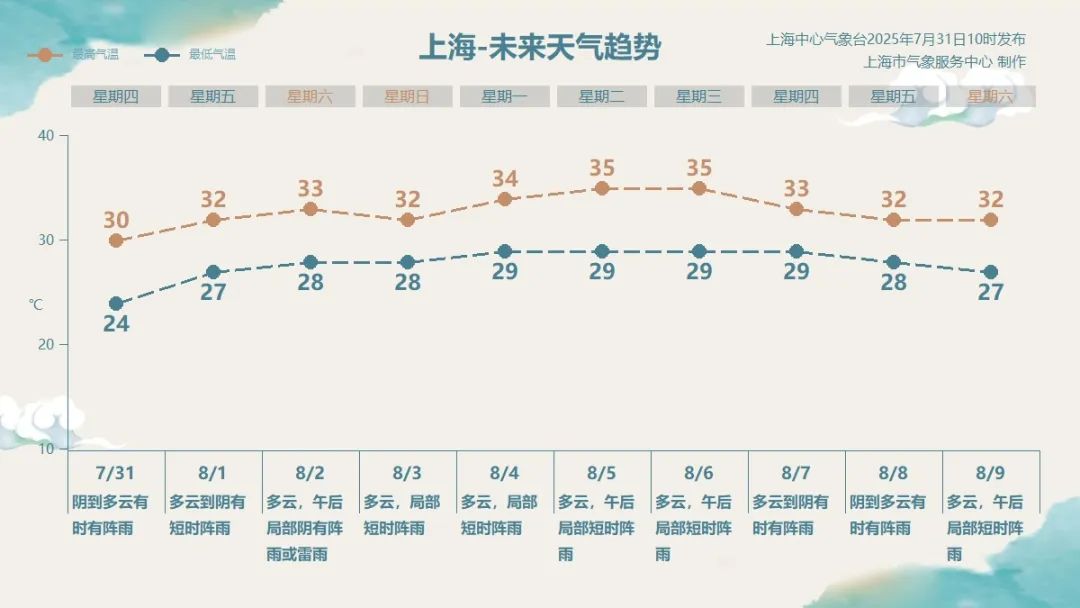在南边“大展鸿图”:今天的年轻人为什么开始重新怀念广东感
今年以来,一首魔性神曲《大展鸿图》席卷各大短视频平台,作者“揽佬”硬是以一己之力,把全国年轻人拽进了“广东阿叔”的茶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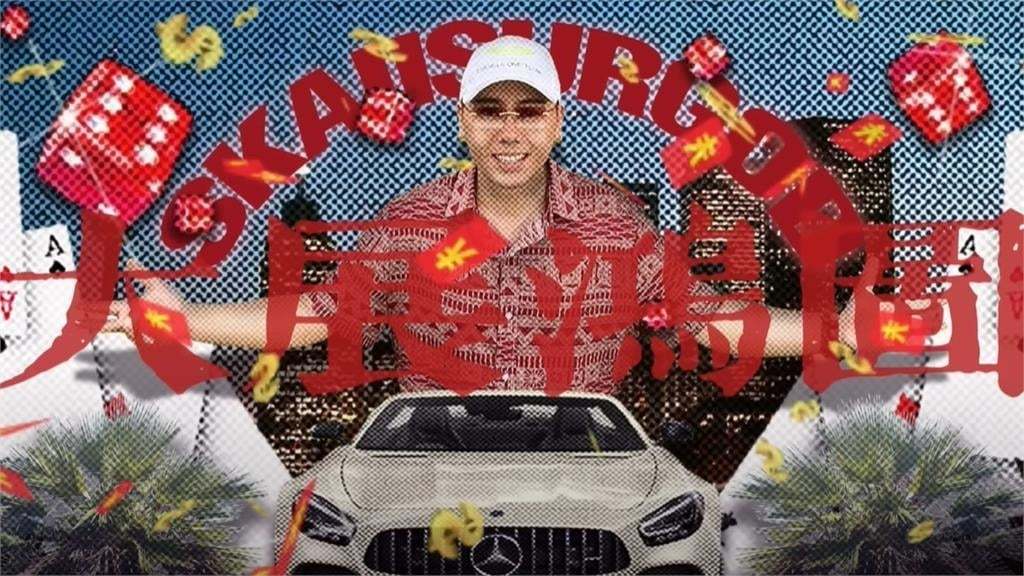
《大展鸿图》歌曲封面
这股热潮似乎并非偶然,反而更像是这几年“广东文艺复兴”的最新一棒。从文学界开始关注华南、岭南、海南乃至“南洋”这些江南之南的“新南方”,到马伯庸连写《长安的荔枝》和《食南之徒》两部关于广东的畅销小说,再到诸如《狂飙》和《扫毒风暴》等以广东为背景的影视剧。一股强烈的“广东感”正在席卷文艺圈。
在这场复兴中,“广东歌”的复兴无疑扮演着核心角色。自2021年起,各大主流电视台开始承办“湾区生明月”的中秋歌会。与此同时,2019至2023年间,现象级音综《乐队的夏天》先后让广东的小众乐队取得全国性的影响力。芒果TV更是非常有意识地用《声生不息》的“港乐季”和“大湾区季”将今日的广东文化复兴和昔日的港乐黄金年代勾连在一起。
不过,与当初粤语主导的港乐黄金时代不同,如今的“广东歌”尽管有粤地诸方言的要素,但主体仍以普通话为基底。更重要的是,“广东”作为一种独立于香港的文化概念,正在出现。发生在广州、深圳、惠州、东莞、海丰、河源等广东城市的生活成为“五条人”“揽佬”“九连真人”“广东雨神”“蛙池乐队”等音乐人的创作灵感。
这就意味着,这种自2020年左右开始兴起的“广东感”自出现起,就有意识地和港乐盛世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从政治经济的大背景看,这场复兴无疑和2019年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有关。不过,这似乎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当代年轻人如此自发地迷恋某种“广东感”。
年轻人所沉迷的“广东感”到底是什么?它的背后是否有着更大的精神寄托?带着这些疑问,我想对这些有关广东的歌词进行一些“文本细读”。
南方无摇滚和困在摇滚里的南方
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涌现出两种具有极强生命力的音乐形式。其一当然是港台的“靡靡之音”。它们在内地的流行,通常被认为和改革带来的经济活力有关。人们从中找到了一种被禁锢的情感和欲望的解放感,也获得了一种“爱拼才会赢”的希望。与此相对的,乃是北方的摇滚乐。虽然摇滚乐也歌唱自由和解放,但困住北方摇滚家的恰恰是物质生活所带来的虚幻和迷惘。
崔健告诉周国平,他为什么使用“新长征”这样的意象:“长征是以少打多,小米加步枪打你飞机大炮,很过瘾的,人性超越物质的那种感觉。我们土八路打你怎么样,所有那些讲大道理的人,或有权有势的人,或那些每天生活在蜜罐里的人,唱甜歌蜜曲的人,你大红大紫,我们摇滚乐就是捶你这帮人”。在他看来,在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团体,任何两个团体的结盟,都是对另一个团体的削弱。60、70年代是政治和文化的结盟,故而经济被轻视;而80、90年代则是政治和经济的结盟,文化就遭了殃。(《自由风格》)。似乎,文化天生地就不会和经济结盟。一旦结盟,文化就丧失了生命。就连崔健的摇滚乐,在人文学者看来,也有结盟的风险。汪晖在《<具体的敌人消失以后>,我们如何歌唱》中写道:“崔健的歌声是在‘革命’与‘后革命’的关口发生的、既是告别又是召唤的自由和解放的旗帜。然而,一旦这个旗帜成为在市场流通的领域中闪现的商标,自由和解放就会从这个旗帜上褪色”。
北方摇滚对南方的经济生活始终抱有一种警惕性。在1991年北京发行的《红色摇滚》的专辑里,侯牧人想象自己成为了一只小鸟,飞到了一个“热闹的地方”:
那眼花缭乱、五彩缤纷旋转舞台 ,像鲜花盛开的村庄。 那汽车、电车、电车、汽车自行车 , 像河水一样流淌……抽洋烟、喝洋酒、吃洋饭,穿上真的假的名牌衣裳。玩霹雳、玩摇滚、玩新潮——嘿!就是让你觉得很西方。学习外语提高身份,说话总是带着广东腔。(《小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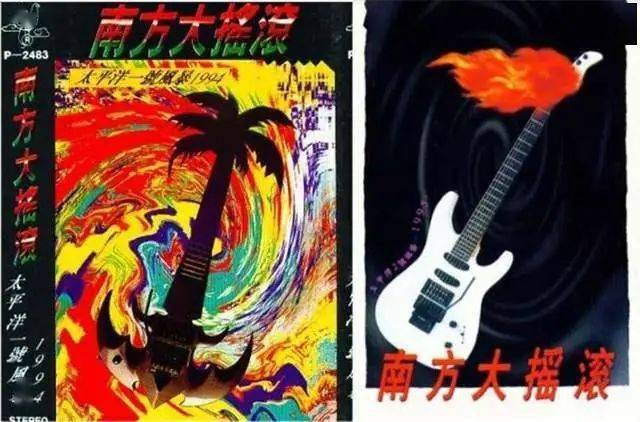
《南方大摇滚》专辑
两年后,具有标志意义的《中国大摇滚》专辑发行,其中未曾收录一首南方乐队。据说张萌萌因为一句“南方无摇滚”而赌气,在1994年就组织发行了《南方大摇滚》的专辑。然而,这种看似对北方的反叛,仍旧没有脱离北方所定义的摇滚精神。张萌萌和捞仔自己的歌仍旧是扭扭捏捏地想表达出那种对物质生活的批判:“变化的年代,你是否学会忍耐;变化的年代,你是否服从安排;变化的年代,给自己留点空白;给自己留点色彩”。(《变化的年代》)倒是有一首啫喱乐队的《炒股票》,唱的是深沪的股市热潮:“炒炒炒炒炒股票,刺激的东西是否太少,所以才要玩个心跳;古老的民族看似发烧,这样的生活你说好不好;大团结的钞票,你是我的目标,今天和未来究竟是哪个重要?想要明天,就别怕摔跤”。
可以说,在那个年代,身处港台和北方的夹缝之间,广东并没有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化声音。但或许,广东那时恰恰不需要这种表达。正如1986年《东方之珠》最初的粤语版所唱的那句“无言地干,新绩创不断”——广东正在迅速地积累财富,热烈拥抱物质生活,至今仍矗立在深圳蛇口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牌就是它的无言之声。
小贩、走鬼、女工和流浪歌手
冯仑《野蛮生长》曾对民营经济做过这样一个分期:1978年到1990年代初是一个“跑江湖”的时代,个体户和“倒爷”是主要的经济参与者。随着1992年《公司法》的颁布,90年代到世纪初,经营活动开始以公司为单位,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全国超过10万体制内人员下海创业,形成一批所谓“九二派”的企业家。2001年后开始进入所谓资本市场的创富时代。
如今的这批“广东歌”的创作者大多出生于90年代的广东。这也意味着他们大多听闻甚至目睹过“跑江湖”和“资本积累”时代的风火,也在本世纪初有过自己的广东故事。相比于上一代“无言地干”的广东人,这一代人有更强烈的表达欲望。
不过,如果我们仔细分辨。这批“广东歌”里其实仍旧体现着广东故事的两条支线。一条是珠三角地区的“阿叔经验”,另一条则是从粤东、粤西、粤北乃至其他地方去广州、深圳、东莞等地的“打工经验”。
“九连真人”乐队的创作核心阿龙来自粤北河源市的连平县,十分贫困,去外地大学后,选择去深圳闯荡。所以,在他的歌里,并没有别墅、银龙鱼、玉牌这些“先富起来的”意象。相反,仍是一种“通往富裕”的渴望:
求神冇用,民古兼窘,ィ厓阿民,一定会出人头地,日进斗金(求神没用,阿民矫情 ,我阿民,一定会出人头地,日进斗金)(《莫欺少年穷》)
阿公、阿叔、阿婆、阿伯还有阿姆,係人出来做事都会有赢有卑(《莫欺少年穷》)
望唔到哦,望唔到哦……做事囊来翻身(《北风》)
我们看到,虽然阿民唱的也是一无所有,但是他没有歌唱什么“生来孤独”—— 他有四叔婆、阿伯公、阿太、太爷和一大家子人;他也不歌唱什么“彷徨无助”—— 他有很明确的目标,去深圳搞钱,日进斗金;他也不歌唱什么“莫名愤怒”—— 出来做事就是有输有赢。
来自粤东汕尾海丰县的阿茂高考失利后到广州摆摊卖打口碟,和同乡的野生画家仁科组成立“五条人”乐队,写了大量来广州打工挣钱的人的生活。

2023年10月11日,山西晋中,五条人乐队亮相第七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并演出。
风吹过石牌桥,我的忧伤该跟谁讲……她来自梦幻丽莎发廊,她说她家里很穷、很乡下,只有山和河,没有别的工作。年轻的时候她被别人骗,被卖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事情有点复杂,我说简单点。后来她终于离开了那个鬼地方,可忧伤一直写在她脸上,但对未来还是充满希望。她想让我带她去海边漫步,在那柔软的沙滩上,让风吹走所有的忧伤……可是我家里也很穷,很乡下,除了捕鱼和种田没有别的工作……我离开了梦幻丽莎发廊。(《梦幻丽莎发廊》)
一个打工仔,没有信用卡,没有她,也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难道本不是应该坐在寂寞的春天里,想象着老无所依地死在异乡吗?但这并不是广州。在广州有24小时热水的发廊,还有同样过得很惨,但仍旧“充满着希望”的洗头妹可以聊15分钟的人生和爱情。尽管他目前带不走她,但说不定哪一天就搞到钱,日进斗金了呢?
除了打工仔,广州街头还有大量的城市漫游者。不过他们可不是巴黎闲逛的诗人,也不是上海文艺的city walker——他们是“走鬼”,城市的淘金者。仁科在《通俗小说》里就写过一个来自粤西湛江的走鬼,成日穿着米老鼠的衣服在发传单。他曾经在家乡工厂打工,但因为爱上工友老婆,不但被工友发现还被告强奸,就决定到广州来讨生活。还有一位粤东惠来县的走鬼阿兄,和老婆一起在天桥上摆摊。他时常与隔壁卖盗版书的谈文化——“读书很重要,一个人如果不读书命运会很悲惨,一个国家如果不读书就会落后,落后就会挨打。有本书叫《人性的弱点》真的很好,你一定要去看”——但是每次批发盗版碟的“花姐”一出现,这位阿兄就陷入了人性的弱点。
在仁科的笔下,盗版书商是最熟悉广州城里人们心思的人。他们“背着一个大背包,里面装着满满一箱的畅销书,有《水煮三国》《血酬定律》《潜规则》《细节》等等”。这些出版于2003年前后的书籍之所以被走鬼们青睐,恰恰是因为这个城市里有一群渴望通过参透人性规律来实现阶级跃升的读者们——他们混迹于各色歌厅酒局之间,在醉话里听商机,于狼嚎中闻密码。
除了广州之外,其他珠三角的城市,也吸引着各地的淘金者。东莞“蛙池乐队”的主唱依依从小生活在东莞周屋工业区,家里有厂,自己也在厂的流水线上打过工。蛙池《孔雀》就描述了女工,虽然也会穿着松糕鞋、挎着漆皮包去女人街,但心里仍旧挂念着北方城市月经初潮的女儿。她为了赚钱无法回去,就在短视频广告里下单,买了竹纤维内裤,寄到许昌中学。广西“瓦伊那”乐队的成员“十八”在《大梦》里也写过一个决定去深圳打工的年轻打工人心态:“我已十八岁没考上大学,是应该继续,还是打工去,该怎么办?我来到了深圳,转悠了些日子,没找到工作,钱花得差不多,该怎么办?”
深圳不相信眼泪,所以海丰人仁科在《深圳的街头》里唱:“我很想很想亲吻你的脸,就在深圳的街头;我的世界,我的青春,我们可以一直唱歌到天亮,就在深圳的街头”;所以陆丰人卢大雨在《广东爱情故事里》唱:“笑的多一些,改变要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
我们可以说,这种以笑代泪的精神,和邓丽君1983年的粤语歌《漫步人生路》中所唱的“愿将欢笑声,盖掩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每天找到新发现。”一脉相承。只不过,在港乐盛世,巨星歌手们迫切地希望去除这些经验的地方性,将其表述为一种可以全球流行的普遍经验;而这批新声代的广东歌手,则更自觉、更自信地为这些经验打上“广东制造”的标签。
四十年过去,广东歌不再是那个被困住的“南方摇滚”,而是找到了一种自己的歌唱方式。广东的年轻人们不歌唱孤独、彷徨、痛苦和一无所有,而是大方承认对世俗意义的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如年轻的惠州本土乐队“右侧合流”在2020年《人生四重奏》的专辑介绍中所写:
这是对我们现阶段的人生来说最重要的四项“俗事”:家庭,爱情,理想和金钱。
阿叔经验
惠州的揽佬在MV里唱歌戴着茶色墨镜,穿着鲜艳的西装或具有热带风的衬衫,或在香港跑马地赌马,或是在别墅的茶室里打麻将。与此同时,又大量使用类似关公像、香炉、玉牌等广式“求保佑”的元素。这显然是想捕捉广东故事中的另一条支线——那批先找到钱的人。
别墅里面唱k,水池里面银龙鱼,我送阿叔茶具,他研墨下笔,直接给我四个字:大展鸿图。(《大展鸿图》)
阿叔到底谈了什么人生经验?揽佬在《大展鸿图》和《八方来财》所戏仿的无疑是两个方面:
(1)赚钱胆子要大:要玩就要玩的大,贼船越大,老鼠才做的下;揽佬没钱也要搏命揾;宗旨利滚利,好运八方来,散了才能聚。你不出手?说聊斋。
(2)做生意要讲道义、信神仙:得罪小人没关系,得罪君子我看不起;关公都点头,鸿运不能总是当头;我们这里的憋佬仔,喜欢脖子上挂玉牌,香炉、供台上摆,虔诚拜三拜,钱包里多几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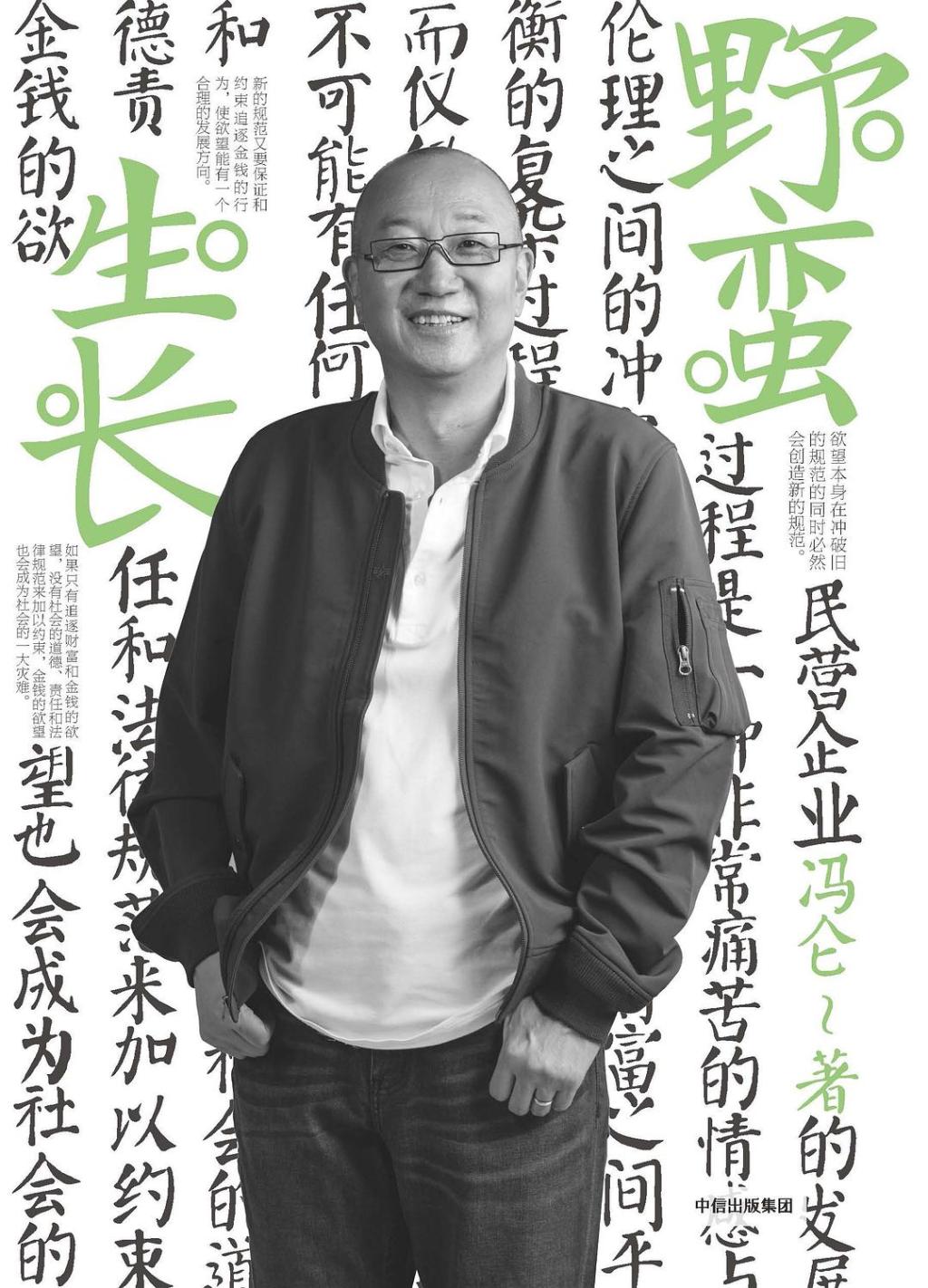
《野蛮生长》书封
冯仑在2013年的《野蛮生长》里把1999年开始学界以及政府对民营经济原始积累阶段的“原罪”讨论带到公众面前。他在书的开篇说:民营的发展是正义和财富之间平衡的复杂过程,并且反思了“做得大”所带来的问题:
我们当时扩张得非常快,主要通过杠杆收购和连环控股的方式,在房地产、 商业、零售以及高科技等许多行业投资并购……在扩张过程中,财务负担日益加重。当时,用于投资的资金都是以将近 20%的年利率短期拆借来的,如果没有 60%以上的毛利,投资肯定是亏的;越投,口袋里的钱越紧, 越紧就越加摧残手中的金融机构和向更多的人与机 构去高息拆借 ,结果雪上加霜,饮鸩止渴。
2010年,《中国企业家》在潮汕商圈震动之际,曾发表文章《绝地潮商》,感慨潮商在新世纪的沉浮:
十几岁外出闯荡,由小商小贩变身亿万身家的商贾大户,堪称潮商的标签之一,李嘉诚、朱孟依等皆是如此。你不能不折服于这一群体对于商业拜物教式的执着,以及为此不惜代价的努力。“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商”,“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潮汕人”,正是这种对商业无孔不入的精神,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富可敌国的巨贾。其间,潮商所爆发出的霸气、魄力、胆量、想象空间,自然令人震撼,但也掺杂了唯利是图、漠视法律、不择手段、任人唯亲等的复杂因素。
进入新千年后,与走私、骗税、假货猖獗相伴,潮汕信用危机的爆发,非但令潮汕企业名声扫地,还被曾与潮商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温州商人(两者同被称为“东方犹太人”),迎头赶超。
揽佬歌词中的“阿叔”极有可能是经历过这些商海沉浮的人。一方面,他还保留着年轻时那种“没钱也要搏命揾”“做事囊来翻身”的劲头;另一方面,他深谙欲望贪婪的可怕,以及时运的重要性。所以,这位阿叔酒醉般地颠来倒去地给年轻的“阿民”说:大展鸿图,也得记着鸿运不能总是当头,要讲道义,要多拜神。
相比较于广东内陆,广东沿海城市受到香港更直接的影响,在炒外币、炒股、炒楼等各种搞钱的新花活儿上,最为活跃。“五条人”在2009年发行的《倒港纸》里就描写了一个倒外币的表叔公:
那一天我经过东门头的时候,我看到古巴的表叔公,他摆张凳子坐在路的旁边,浑浑噩噩。他看见我走来,便猛然站起来喊,“靓仔啊,你有没有港币呀?”…… 来我去广州北京路逛街的时候,又看见古巴的表叔公。我走过去问他,还做兑港币这行吗?他两眼发亮惊讶地瞪着我说:“靓仔啊,我认得你呀。你有没有美金呀?”
这位表叔公显然比卖书的走鬼更加机敏。从汕尾倒卖港币到广州兑换美元,每一步都在踩外贸变化的节点。但他的这种机敏到底来自哪里?“五条人”为何非要刻意强调他“来自古巴”?
我在芝加哥遇见过一个叫Carmen的华裔女孩。她说自己的曾祖父是古巴人,娶了位广东媳妇。这个家族后来辗转广州生活,最终又到美国谋生。Carmen回忆童年时,常因混血面孔被同学叫作“鬼妹”。因此机缘,我才了解到,19世纪中叶大量广东“契约华工”曾远赴古巴,而20世纪美国排华法案又迫使许多广东移民转道哈瓦那。表叔公和Carmen的家族,或许就是其中一员。他们像候鸟般追逐着商机,凭借海洋赋予的迁徙本能,在全球化的夹缝中寻找每一次出人头地的可能。
“五条人”的另一首歌讲述了另一个全球迁徙而致富的故事——不过,这只叫“刘德龙”的候鸟,羽毛上沾着人血。
在县城地下赌场一直输钱的刘德龙,借了高利贷希望翻身,但实在还不清,就出手伤了追债人,逃到其他县城。在另一个县城旅馆的洗手间杀了一个妓女并抢钱,随后又谋害一个银行取钱的人。之后,他骑上摩托,跨越中缅边境,消失不见。直到十几年后,中国警方在泰国曼谷的中餐馆抓获了一个有钱人——这个“泰国人”笑着对警察说了一句:“Sawadika!”仁科说这是根据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真实案件改编:主人公“王x球”在广州增城在追讨高利贷时杀人,后逃亡南洋成为过千万身家的著名华侨,最后被缉拿归案。
“五条人”为这首歌取名为《热带》,这个歌名堪称神来之笔。季风、海洋与潮湿空气刺激着人们对甜蜜生活的向往。那些茂盛的宽叶植物极富生命力,但又为树根下的恶之花提供了阴凉。
在南方之南,发财梦和霉菌一起疯长。
内卷和躺平之间的“广东感”
2020年,“内卷化”一词破圈流行,横扫神州大陆,成为描述当代各界年轻人生活的主流叙事。为了摆脱生活的不稳定感,年轻人在竞争“稳定生活”的赛道上疯狂赛车。2025年的高校毕业生达1222万人,而高校的扩招仍在继续。大学招聘的人数完全赶不上博士毕业的人数,让高校成为“内卷”的重灾区。
2021年“躺平”作为一种反抗叙述强势出现,和“内卷”平分天下。此后,淡人、断亲、摆烂式社交、低电量模式、退休预备员、全职儿女……年轻人开始疯狂发明概念,以求对抗生活的现实。
人们似乎陷入到一种精神生活的两难困境:要么在过度竞争的焦虑中消耗自己,要么在低欲望中消磨自己。这个主流叙事的结构和“广东文艺复兴”在时间上是重叠的。这也意味着,这场对上世纪80、90 年代经济上行期的广东的集体怀旧,很可能是在“内卷”和“躺平”之外寻找精神寄托的又一次努力。
“广东感”不是低欲望的生活,而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命力并非建立在抽象的理想或愤怒之上,而是扎根于有烟火气的“俗事”。 “广东感”又象征着一种对变动和不确定的拥抱。与如今努力“上岸”的氛围相比,1990年代的广东正是“下海”的热潮,人们对“做事囊来翻身”抱有巨大的希望。
2004年汪峰在他的成名曲《飞得更高》里唱:“现实就像一把枷锁,把我困住,无法挣脱”。2025年了,他的新歌《人海》还在唱:“生命是不断的离去,留下孤勇的等待,那就疼痛着自由吧”。在痛苦中的人们可能并不想痛苦再被歌唱,而只是想听听——
“来财,来!来财,来!来财,来!来财,来!”(《八方来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