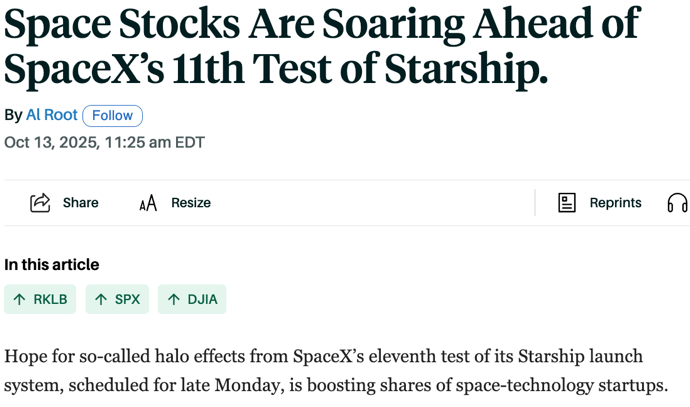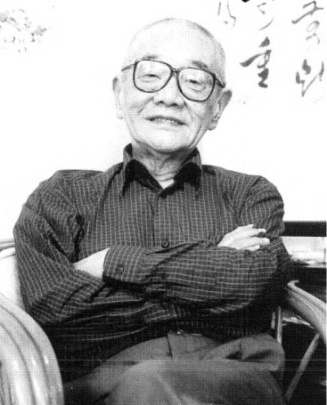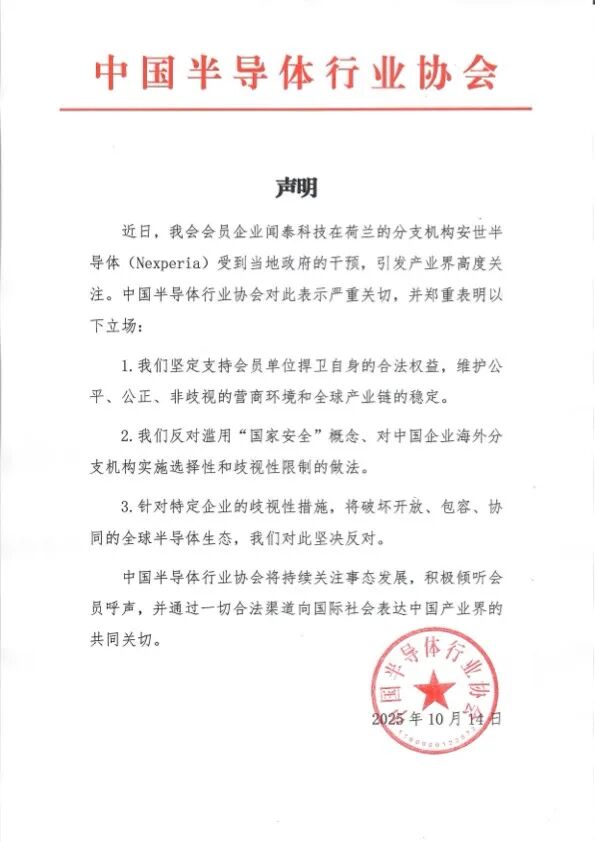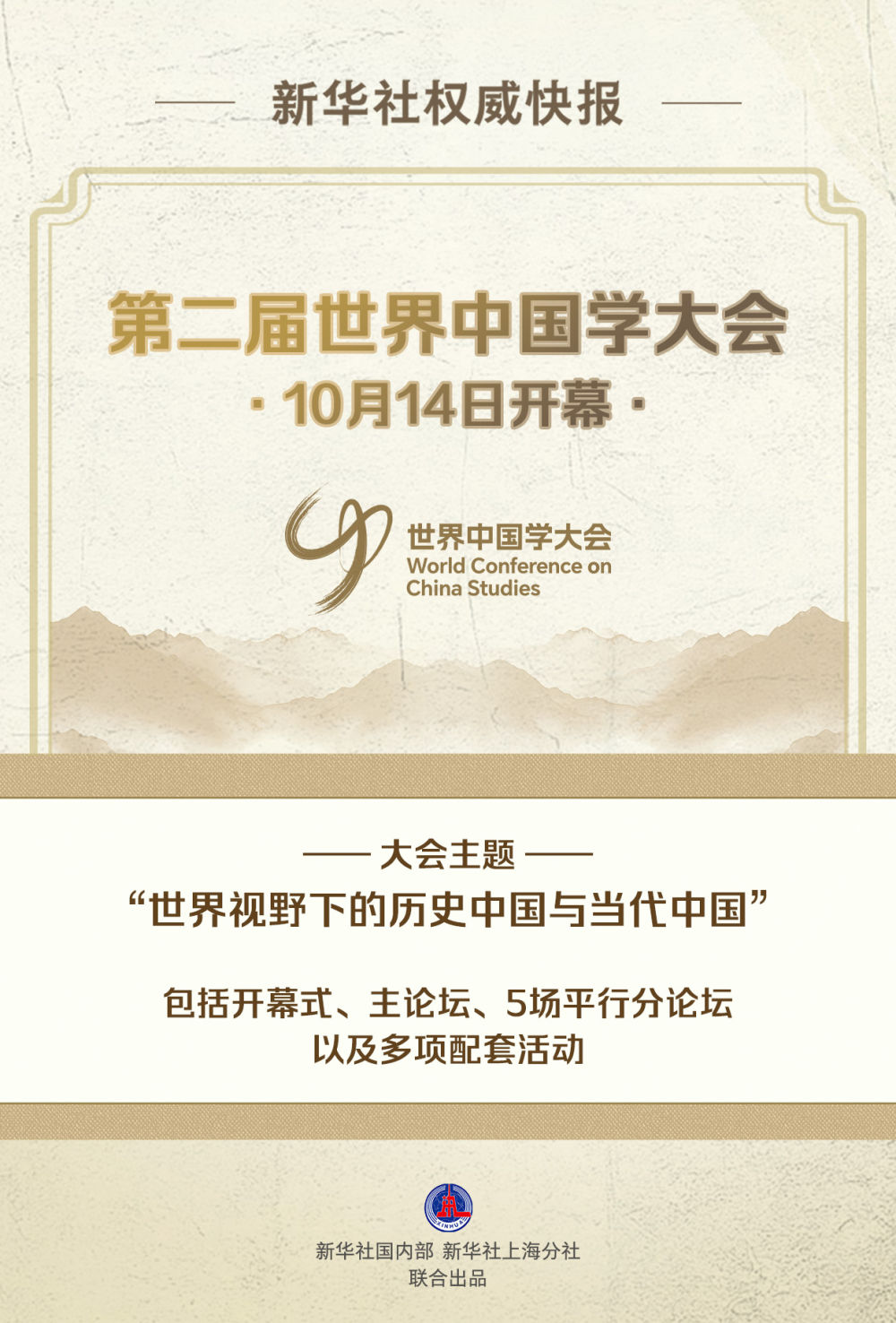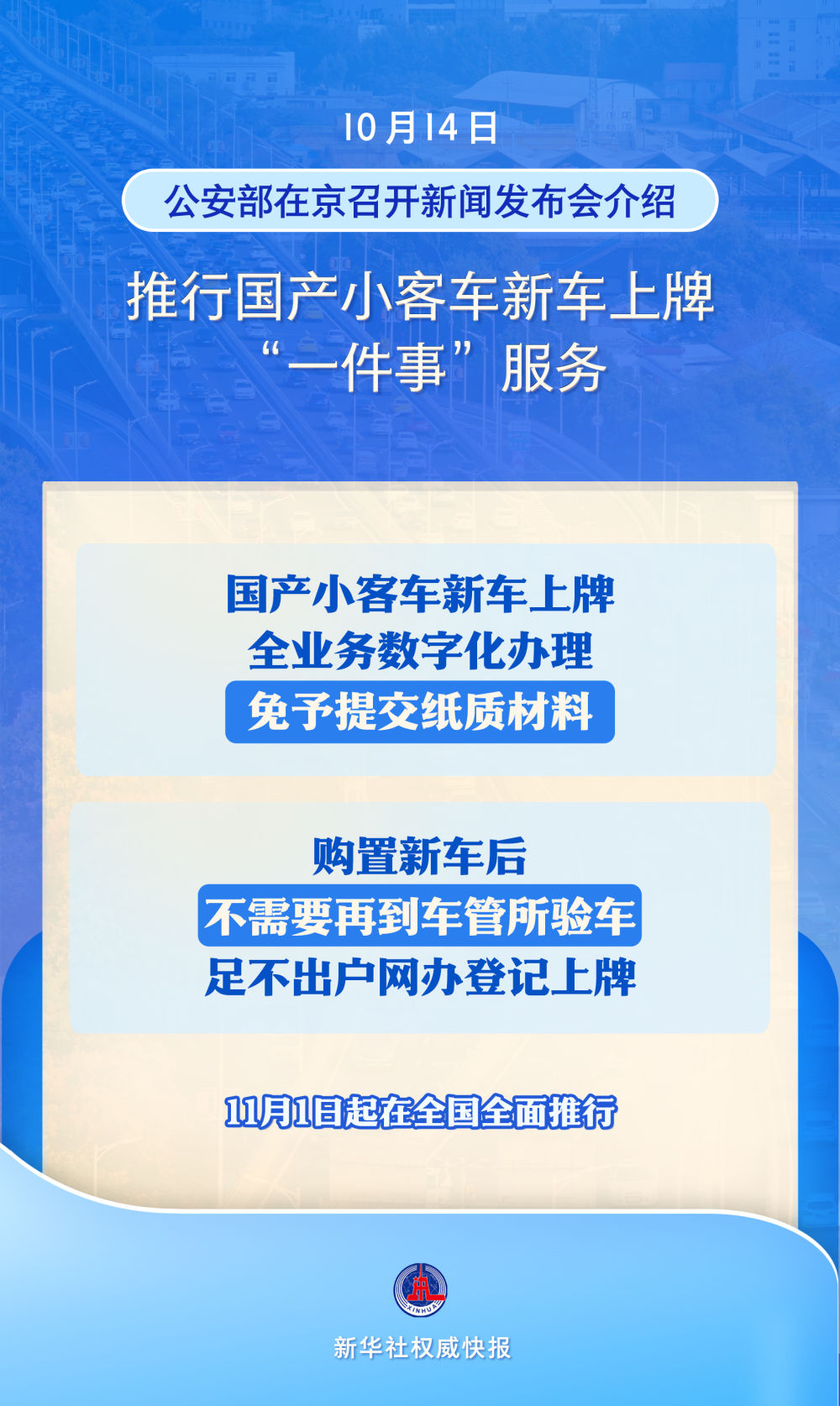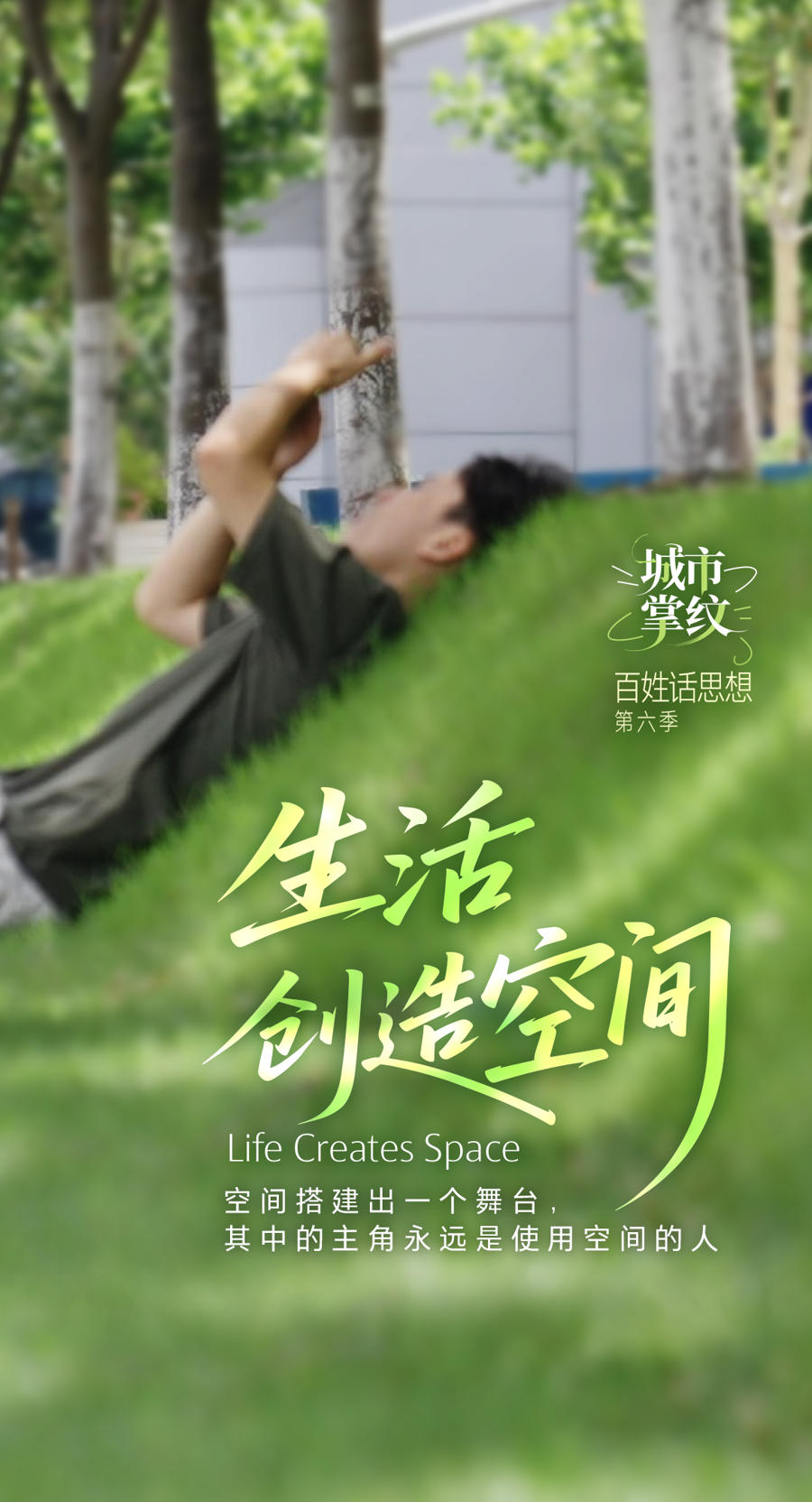那些考不上的读书人,最终都去哪儿了
【编者按】在中国古代,科举考试是平民阶层改变命运的主要途径,但成功者永远是极少数。当我们今天翻开史书,看到的多是状元、进士的风光故事,却很少听到那些考不上的人后来怎么样了。当主流的成功之路走不通时,人们如何维持生计和尊严?那些考不上的读书人,最终都去了哪里?他们找到了怎样的出路?这些问题不仅关乎历史,更关乎每一个在竞争中感到疲惫的现代人。本文摘自《我在古代当考生》,陆蓓容著,湖南美术出版社·浦睿文化2025年8月版。经浦睿文化授权刊发。

《我在古代当考生》书封
差生到底都去了哪儿?失败者的心声其实也沉淀在历史的海洋中,只是比成功者的更隐蔽,也更零散。到了进士也要讲名次的时代,大家都难,而平民比士绅更难。新的思路正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内卷的游戏,要么迎头而上,要么彻底退出,两间徘徊只会搞毁心态,得不偿失。乾隆五十一年(1786),杭州黄家有一个小孩,爱学习,肯努力,在府试中位居前列,眼见得就能考上秀才,却又落了空。有位何琪老先生写信给他叔叔说:孩子虽然志气可嘉,但是现在这个时代,谋生为要,没必要把秀才的头巾当作人生追求。而且显然,这顶头巾什么都证明不了,并不完全与你个人的能力相关。
有些人自己上了岸,转头对别人说岸上也不好走。何先生并非如此,他自己就没有参加考试,甚至受到荐举都决定放弃,终身布衣。但他能写诗,书法不坏,和金石篆刻家玩得很好,在当时的杭州城里,像这样受过良好教育,却没能在科举道路上通关的中下层知识分子为数相当不少。城里人连块田地都没有,从正经史料上看,简直难以想象他们怎样谋生。有些人似乎天天赏花饮酒,泛舟西湖,很少叹老伤贫,也没有怀才不遇的庸劣感慨,令人怀疑他们是否家境优渥,有房有钱,一看成功无望,就及时放过自己,与这个世界和解了。如今,饥荒的阴影已经从发达地区的历史记忆中淡化,没有突发事件的时候,吃饱穿暖还不是问题。你若是生活在好地方,考学考编找工作失败,也有机会放过自己,做一个全职晚辈——所谓“虚假的啃老是在家混饭多双筷子,真实的啃老是出门打拼掏空六个钱包”。
但是多数人没有这样的条件。他们得另外找方法,把漫长的一辈子混完。那究竟能干点什么呢?
一种循环是,当你拥有了秀才的资格,就去“菜场小学”里教新的小朋友考秀才,如同一个纯艺术领域的学生,毕业后立刻成为儿童艺术培训教师;又像最近常见的新闻,清华、北大毕业生选择回到家乡重点中学任教。教育系统的自体循环简直像一个永远重复的关卡游戏,原来它确是常见的社会现象,古已有之。如果学问好一点,你还可以到官僚的幕府中去帮忙编书、校书、代笔写书,赚取薪水,但这需要积累一定的名声。否则,张三识字,李四也识字,凭什么请你不请他?

汪中像
仍是乾嘉年间,扬州有一位饱学青年汪中先生,他家境极为贫寒,早年丧父,家中只有母亲与姐妹,住的房子连板壁都不完整。即便如此,他还是不到二十岁就成了秀才,以擅长骈文知名一时,但考不中乡试,家累又重,只好开始了颠沛的打工生涯,先后为太平知府、安徽学政、宁绍台道做幕僚。那是一个文章学问受到尊重的时代,大家为了给他谋求一个职位,都伸出过援手,写过推荐信。到了乾隆四十二年(1777),他正在南京打工,江苏学政谢墉又将他荐为拔贡,从此解决了出身问题。可是汪先生的条件和境遇让他势难向上发展,仍旧为官僚和豪家服务,弄笔为生。
艰辛的童年与青年岁月深深影响了汪中的性情。探讨清代中期上升困难的读书人心态史,很难绕开他在南京写作的《经旧苑吊马守真文》。旧苑与江南贡院隔秦淮河相望,是明代著名的声色场所。马守真别号湘兰,为晚明秦淮八艳之长。汪中前去凭吊她,说:你虽然香消玉殒快两百年了,画的兰花还长留天壤。禀性聪慧,一望而知。沦落风尘是命运的玩笑,色笑侍人,谅非所甘。总而言之,你的遭际不是你的错误。而我,一个卖文为生的穷读书人,和你又有什么分别呢?我每打一次工,就要迎合一位新老板,揣摩他们的性情,陪他们的笑,就像你每换一位服务对象,都要重新打扮自己,整顿心情,明明遇见过称心的君子,却无法和他偕老。将文字工作与卖笑等量齐观,至少说明他并不歧视女性。并且,这也侧面说明了幕僚生涯的尴尬之处:社会声誉不足以换取工作中的自由。清代学人游幕是突出的文化现象,境由心造,欣于所遇者也不在少数。可是,对敏感多情而自尊心高的个体而言,看人眼色的痛苦实在太过于强烈了。

《幽兰》(传)明 马守真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然而社会深不见底。层层下视,更多的读书人连秀才都没有考上,无从获取被人注意的机会。入幕、教馆这样听来辛苦委屈的职业赛道,甚至很难对他们开放。今天,在老师的笔下,“二本学生”群体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学观察对象。即便本意只为定义,但标签一旦被提取出来,总会起到某些导向作用,让人隐隐感到不适。其实,如果给社会做切片,普通本科生绝非中下层级。真正的中下层级,多数时候根本没法连片切。当我们问考不上秀才还能干什么,就会面临这样的困境,严肃史料很难提供完整而有效的答案,只能借助一些没有作者的集体创作来进行想象。
社会观念制造出了“三教九流”这样粗糙的分类。随着时代的发展,“九流”被戏曲小说家们演绎出了一丝贬义。究竟怎么排,各家版本不一,但差异并不很大。一种口诀说:“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流堪舆四流推。五流丹青六流相,七僧八道九琴棋。”从读书人往下数,世上还有中医、风水师、画家、算命先生、宗教从业者、演艺家等工种。这些工作者都得具备一定文化知识和读写能力,可以看作“举子”队伍里的外溢人员。于是,这个清单也就能够说明“读不出书还能干什么”。这样的顺口溜,就像“二本学生”的标签一样令人难受,这和你在考试世界里被排名支配的恐惧异曲同工。它们背后都有一种以等级和规则来描述人、筛选人的认识方式。
其实,令人唏嘘的历史现实还在更后头:一方面,考试失败让你注定与“上层”无缘;另一方面,隐约被贬低着的九流之中,也出现了人们事实上能够接受的好工作。以我最熟悉的绘画行业而言,早期它曾是工匠的事业,倍遭歧视。到了明清,随着某些固定风格占据审美价值高地,文人卖画变得不再可耻。而且,社会稳定的时代,上升的几率固然变得稳定,世人对书画作品的需求倒也同样能保持稳定。你若下定决心,把孔乙己的长衫一脱,转身制造孔乙己们喜爱的文创产品,没准就能游进一片蓝海。如果在地方上画出成绩,日子更加好过,不用像秀才朋友们那样,要么在“菜场小学”里生熊孩子的气,要么在各大城市间飘荡,每隔几年换一个阔东家,写一本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