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W·大卫·马克斯:地位是由他人赋予,再多的资本也无法改变
【编者按】LABUBU、Jellycat、玲娜贝儿;潮流服饰、球鞋、配饰......潮流圈层的风向不停变化,身处圈内的人也在不断追随潮流的过程中确立自己的地位。但流行来得快,去得也快,最终似乎什么都没有留下。在流行转瞬即逝过后,一切都显得空洞无聊。为什么在互联网文化中,所有东西都没有以前那么酷了?《地位与文化:身份焦虑如何塑造审美与潮流》的作者W.大卫·马克斯表示:互联网改变了“地位信号”(status signaling)......人们以前要求的地位,都需亲身临场,而如今在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上,则不间断上演着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炫耀盛会。互联网上的时间流逝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反而感到它根本没有流动;而超高速的网络时代,反而让我们陷入了文化停滞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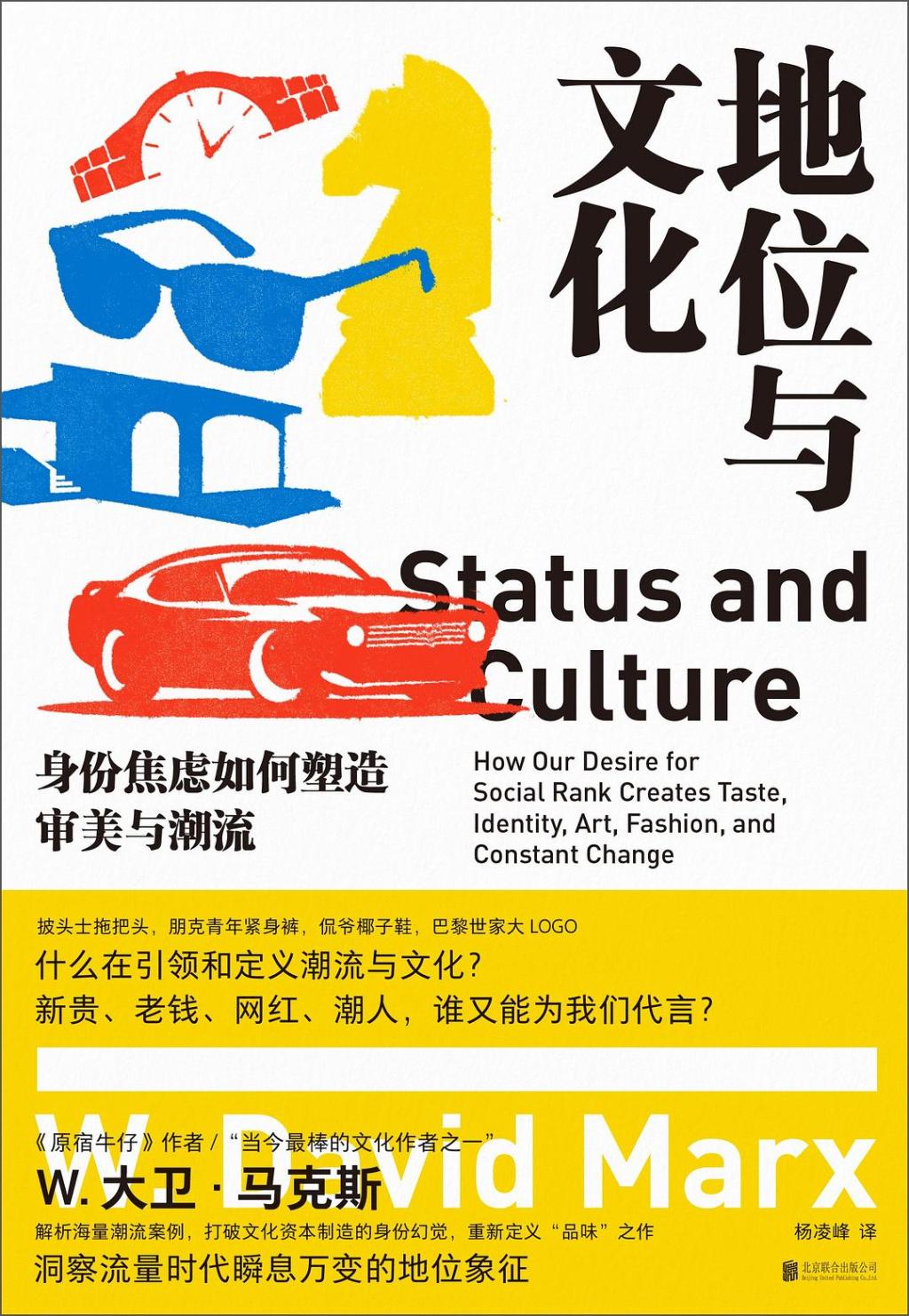
《地位与文化:身份焦虑如何塑造审美与潮流》书封
:在引言中,您提到随着人们的认可,以前的激进行为在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产中获得一席之地。披头士的“拖把头”发型曾被视作离经叛道,但之后又成为具有文化地位的符号。当反叛、小众的元素被大众发掘后,是否必然会经历从被排斥,再到被接纳,最后在人群中普及的过程?
W.大卫·马克斯:并非所有激进的创新(radical inventions)都能成为集体惯例的一部分,但在上个世纪,有太多的流行文化发源于边缘群体和非主流社群。当这些文化变得过于普及时,往往会遭到其他边缘群体的否定和改造。这解释了文化变迁背后的许多原因。那些最终被接受的激进创新,其自身确实具备值得采纳的特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最激进的部分会被“钝化”,从而更容易被广泛接受。
:最近的LABUBU潮流离不开明星佩戴的作用,再到几年前一系列的潮流:Supreme、Bearbrick……正如书中所写:位于社群顶层的名人、有权势的和受尊敬的人通过彰显品味,让大众争相模仿。人们抢购明星同款,是否也在模仿明星的品味,试图在物质上与他们实现地位对齐?
W.大卫·马克斯:这一点总是存在争议,因为很少有消费者认为自己在“模仿”,更不会觉得自己只是被带有“地位价值”的事物所吸引。他们看到LABUBU时只会想:“这很酷,我想要!”但如此多的人在同一时间发现同样的价值,说明背后一定有社会机制在起作用,而我认为地位价值最能解释这一点。当具有更高地位的人群开始独家采用某物时,它就具有了“声望”(cachet),这让我们的大脑觉得它更美、更有趣,即使我们并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想。
:为什么在互联网时代,所有东西看似都没有以前那么酷了?我们了解新鲜事物的成本是否更低了?我们不需要再想尽办法去搜寻特定事物(游戏、服饰、球鞋等)的蛛丝马迹。我们不再和同好交流喜欢的东西,因为算法不停地在猜测我们的喜好,推荐我们新产品。购买商品也不再需要线下排队,到店抽签。一切都更方便,但缺少了努力研究的过程,似乎也让一切都变得更无趣?
W.大卫·马克斯:互联网本质上是一个打破信息和实物流通壁垒的引擎,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些壁垒是精英阶层用来构建“信号成本”(signaling costs),维持其身份地位符号(status symbols)价值的关键方式。互联网让一切变得可知、可查、可购,这意味着物品的整体价值降低了。同样,我们可能无法通过理性的方式去理解这一点,但我们却能切身感受到。在过去的时代,我们之所以格外珍视某些东西,正是因为它们稀有且难以获得。而今天,那些仍然稀有之物(可能是因为它们不在线上销售)依然更有价值。

W.大卫·马克斯
:在阅读第一章关于地位的内容时,坎耶·韦斯特的例子时不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伴随着他出格的言论,这位昔日文化名人的地位似乎已经降低。在您看来,他违反了哪些准则?我好奇的是,他是否违反了与自身地位对应的权利和义务?而随着他持续发表歧视性言论,他是否也失去了社会层面的尊重?
W.大卫·马克斯:我们允许最受尊敬的艺术家打破某些社会惯例,因为他们是天才,不应受到传统道德的束缚。起初,人们接受了坎耶的傲慢之举和醉酒后的无礼行为,比如他在2009年打断泰勒·斯威夫特的获奖感言。他因此受到谴责,但并未被排斥。他的下一张专辑被称为“21世纪最佳专辑”。然而,当他开始谈论纳粹思想时,这已经突破了美国普遍的民主和反种族主义政治规范。尽管如此,他仍然拥有一定规模的事业,许多小公司依旧渴望与他合作各种项目。
:您在讨论地位时提到了教育资本、社会资本、职业资本和经济资本,这些对于地位提升都非常重要。我好奇的是,地位是否具有某种排他性?即便满足上述条件,个人是否仍会被排除在某个圈层之外?似乎J.D.万斯就在有意向人们证明,他是一个被排除在上层精英之外,代表自己阶级的政治家。后文中关于老钱和新钱的区别,也暗示了圈层的壁垒?
W.大卫·马克斯:J.D.万斯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名义上拥有职业、经济和教育资本,但仍然不受其他富裕精英的欢迎。这凸显出文化资本的作用:他不知道如何融入精英中,无论是行为举止还是政治意识形态上,他都不清楚应该如何表现。尽管如此,右翼精英阶层如今如此庞大(且政治影响力极强),以至于他获得了巨大利益,甚至成为副总统。地位最终是由他人赋予的,如果他们不喜欢你,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你都会缺乏地位。再多的资本也无法改变这一点。
:书中对于惯例的影响力有精彩的分析,支持惯例会获得社会认可,违反惯例就会遭到抵制和反对。但越来越多的声音在让人们“做自己”,选择与众不同、有自己风格的生活方式。问题在于,对于一出生就被文化规范和惯例包围的人们来说,真的存在某种完全属于我的生活方式吗?
W.大卫·马克斯:我认为“个人品牌”的原创性很像语言。除了极少数情况,我们不会自己创造词汇,而是从集体中继承它们,但可以通过新颖有趣的方式排列语言,成为伟大的诗人。同样,我们可以用消费品和已知的行为来构建身份。独特的排列可以产生独特的身份。然而,对许多人来说,“做自己”可能只是意味着喜欢他们喜欢的东西,而不考虑这些选择对地位的影响。
:在阅读“品味、真实性与身份”的过程中,我不断想起“搏击俱乐部”,一连串的商品看似赋予了主角身份,而幻想出来的布拉德·皮特则对此不屑一顾;与之相对,“天才雷普利”里马特·达蒙最初伪装自己身份的方式,恰恰是穿上裘德·洛的衣服。在您看来,我们能否通过商品构建身份?我们又为何对此感到厌倦?
W.大卫·马克斯:在21世纪,消费品是我们构建身份的主要方式,尤其是因为文化产品大多是为消费市场创造,在消费市场中获取的。与此同时,这很容易让人感到矛盾,因为这些商品的目的不是帮助人们成为独特的个体,而是为了盈利。如果每个人都为了“独特”而购买同样的东西,最终只会和别人一样……
:精英们获得自己地位象征需要稀有之物、新奇商品与技术创新产品。在互联网时代,这些事物在多大意义上依旧能让精英获得特殊地位?随着信息流通的速度越来越快,曾经特殊的商品是否也变得更加容易获得?
W.大卫·马克斯:昂贵的商品和服务仍在将精英与大众区分开。例如乘坐私人飞机对普通人来说是不太现实的。然而,信息和品味作为信号成本的作用已经被消解,这意味着几乎所有的身份地位符号都建立在金钱之上,其象征意义极其单一。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可谓相当无聊。
:您在一则采访中表示:互联网固有的超高速,意味着时尚周期更倾向于推出速生速灭的短暂潮流,而不是定义时代的趋势......许多人都觉得我们已经进入了文化停滞期,互联网上的时间流逝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反而感到它根本没有流动。但您也在书中畅想互联网时代更为平等、更能激发创造力的未来。其中是否存在矛盾?
W.大卫·马克斯:我的新书探讨了这一矛盾,但我认为,互联网本应成为一种让人们更好地表达自我的途径,但它在这方面已经彻底失败。网络上的多数创作——尤其是流行的创意作品——并不聚焦艺术创新,而是出于 功利性的盈利目的。
最优秀的创作者都擅长“符号操纵”。这是一项真正的技能,标志着陈词滥调和诗意表达的区别。这意味着,并非每个人都有同等的艺术创作能力。我们应该建立一种推崇此类技能的文化,像赞美熟练的战斗机飞行员、神经外科医生或手工匠人一样赞美这些技能。不同的是,许多未经训练的人最终也能成为符号操纵的专家,这意味着这项技能天生比其他技能更为民主。因此,当我指出:“我们应该赞美最具创新性的文化”,这并不精英主义,因为我并没有宣称“创新只能来自特定群体”。但大多数人目前并不这么认为:我们的文化仍然深陷在某种“民主”思维中,最受欢迎的内容获得最高赞誉,而遗憾的是,这些内容往往缺乏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