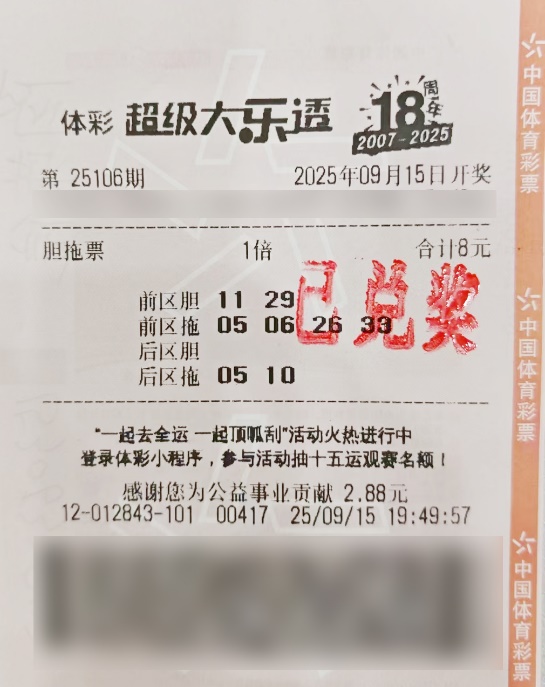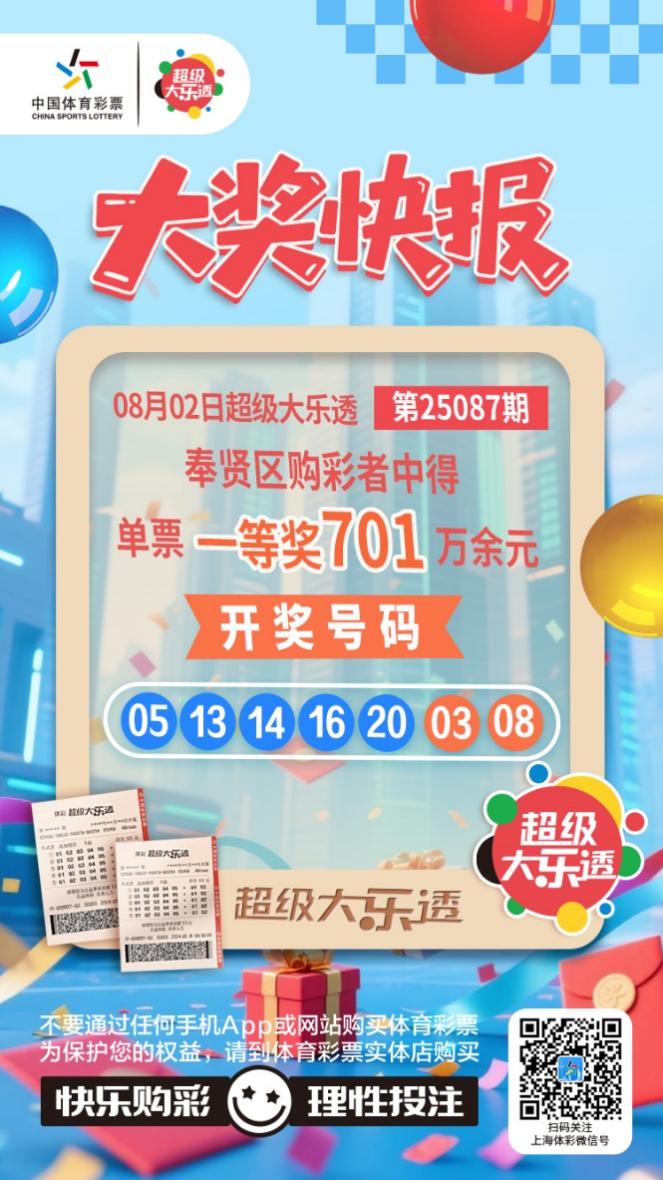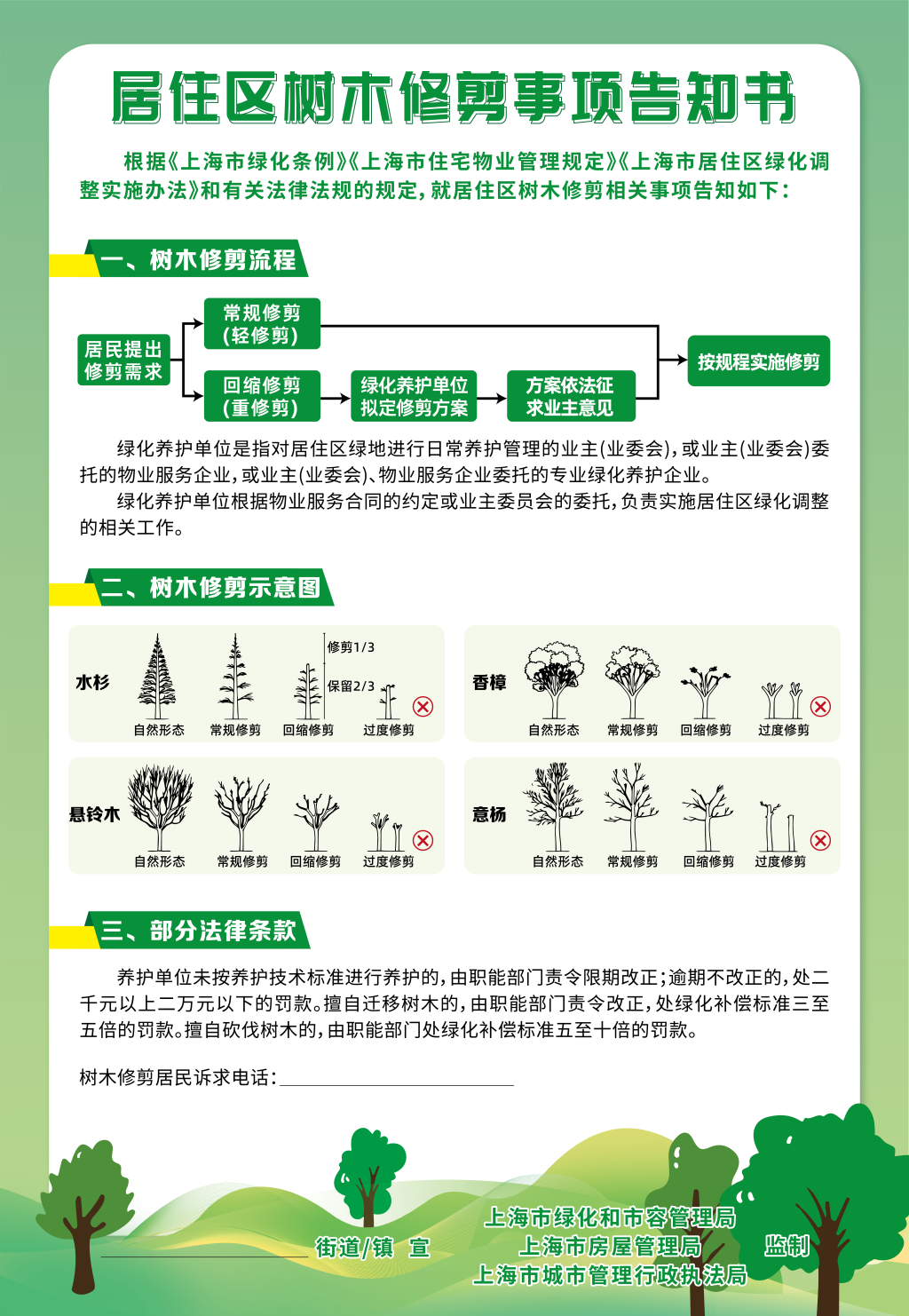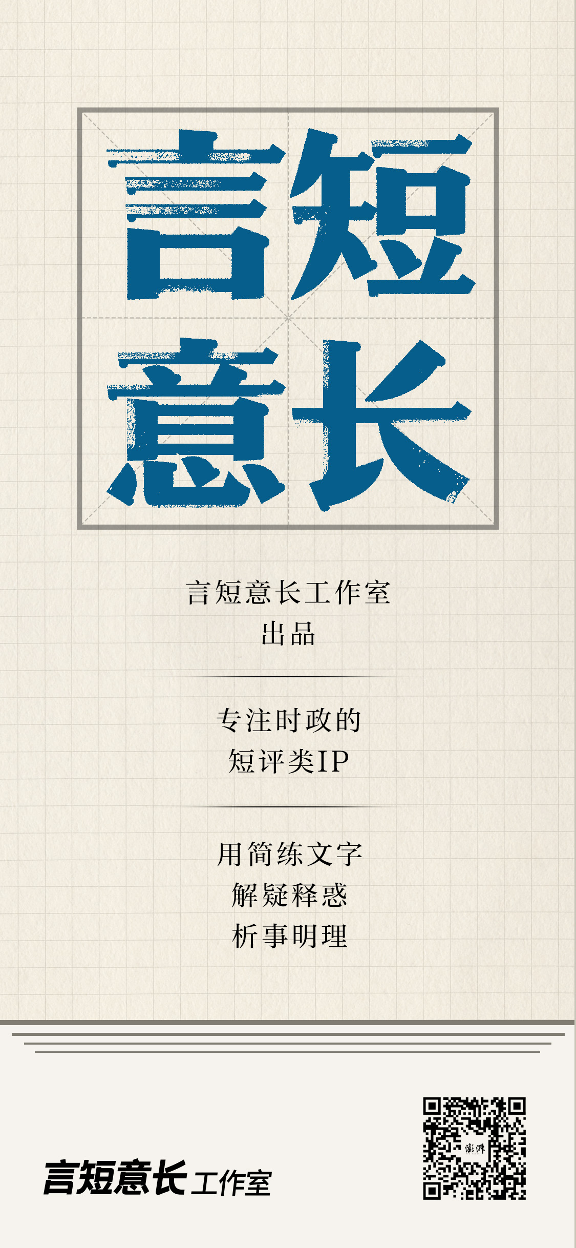复旦史学百年︱章巽与中西交通史研究
一、家学渊源,慈母启蒙
章巽,亦名丹枫,祖籍浙江金华,生于1914年4月23日。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尤其是外祖父汪志洛,乃是清末民初的有名诗人。其母汪芙卿,曾任义乌县立女子小学校长及金华县立中学国文老师多年,极具才学。他幼年失怙,家境贫穷,母亲的培养为其日后的治学和为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年,为了帮助年幼的儿子阅读《通鉴纪事本末》,曾撰写了《读〈通鉴纪事本末〉诗》,归纳《本末》所载的重要史实,各成七言诗一首,共计150首。诸诗不仅富有学术价值,更对章巽先生产生了终生的影响。对于先生来说,母亲的这150首诗是其刻骨铭心的优秀启蒙作品,也是对慈母的最佳怀念。因此,他在33岁之时就已把它们编成三卷本的小册子,意欲刊印出版,留传后世;数年后,并请顾颉刚先生撰写了一篇《读后记》。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20世纪50到70年代诸多“运动”和其他客观原因的干扰,此事始终未能付诸实施。直到晚年,他还曾对其学生感慨地说道,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达成这个心愿。足见先生对于此事是如何地重视。
为了聊以弥补先生的遗憾,趁撰写本《传记》的机会,抄录先生为此小册子所撰的《弁言》如次:
巽二龄失怙,家贫,先母抚孤守节,以舌耕自给。当时授徒乡间,常苦失业,纵能免此,亦往往一岁之内,一再易馆,或称小学,或即私塾,因陋就简,多无校舍,祠宇家庙,狐鼠窥窬,皆吾母子寄身之所也。先母日授诸生书,夜则课子,及巽稍长,令读《通鉴纪事本末》,恐其不易记识,因即就袁氏书原题,或一节为一诗,或数节合为一诗,命巽背诵之,以助领会,即此册是也。沧桑多变,其本尚存,敬加校订,朗然在目。每一开卷,当年母子相依之情,与夫慈亲吟哦之声,仿佛犹在耳目间。然而幽明永隔,欲舞莱衣,唯能求诸梦境,每一念及,不觉涕泪之交流也。昔胡曾成咏史诗一百五十首,为上中下三卷,今读通鉴纪事本末诗适亦一百五十首,遂亦分作上中下三卷。原诗间或附有小注,兹亦仍旧保留,未加变动云。
一九四七年初冬,章巽谨记。
二、奋笔赴国难,昭显记者良心
章巽先生天资颖悟,又秉承良好的家庭教育,因此在十岁之前就已小学毕业,并在十岁时考入位于金华的省立第七中学(后来改名为金华一中)。先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旋即就学于杭州的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随后转学至南京的中央大学历史系,二十岁时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后,先生相继担任天津南开大学教师、《大公报》社驻上海、香港、桂林各分部的编辑、编辑部主任,以及中华书局编辑和《新中华》杂志的主编等职,历时十年。在此期间,正是日人侵华,国难当头之际,而报刊、杂志正是唤醒国人,共赴国难的重要阵地,故而先生尽其才智,发挥特长,撰写了大量的政经短论、形势研判、新闻报道、知识译介,频繁闪现思想火花,充分展示拳拳之心。它们分别载于《大公报》《国闻周报》《新中华》等刊物上;先生之子章嘉平近年将这些文字编辑成册,题为《老报人章丹枫(巽)先生旧作》,虽然并不完全,却也达百余篇之多。
关于这类文章,在此选择二例,略作介绍。第一,谈谈《论战后新都》一文(刊于1943年第12期的《新中华》)。当时,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已露胜利曙光,故国人对于战后重建的问题越来越关注,新都的选址也成为热门话题之一。但章巽先生的文章却并非“赶时髦”之作,而是持有独特的见解,指出关键因素所在,乃至对于任何时代而言,都是永恒的真理。
该文的最精彩之言是文末数语,指出最为关键者并非首都设在何处以及地理形势如何,而是在于治理国都(国家)的“人”到底如何:“国民努力,则危地可安;人谋不臧,则险峻何用!”“人”之素质,最为根本,诚为金玉良言也!
第二例则谈谈先生采访印度圣雄甘地的“传奇”经历。1944年,章巽先生赴美留学,预期搭乘印度孟买5月8日启航的轮船,从而来不及实现采访甘地(其居地离孟买不远)的设想。然而,一个偶然事件达成了先生的心愿:轮船因故耽搁到11日仍未启航,甚至要求旅客返岸,无限期地等待。于是,先生趁这机会积极联系、落实采访甘地之事。期间虽遭殖民当局的阻挠,但先生毫无惧色,与之据理力争,最终得以成行。
先生于5月17日下午访问了巨河镇(在孟买近郊)的甘地居所,虽然甘地因健康原因遵照医嘱而不能与人交谈,但是其亲密助手,印度妇女界的最高领袖奈都(Sarojini Naidu)夫人会见了先生。接着,先生又与朋狄脱夫人(尼赫鲁的妹妹)等国大党要员交谈了许久,并随众人与甘地一起作了20分钟的祈祷,并在祈祷结束后被引见给甘地,向他致意。最后,先生通过致甘地短信的形式,获得了他的答复,甘地请先生转告全体中国国民,他“对于中国人民在战争中所受的苦痛,无时不在怀念;对于日本现在的军阀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行动,像对于其他的法西斯主义及帝国主义一样,极表厌恶。中国和印度,是兄弟之国。印度的人民,永远愿为中国之良友,互助互济,共谋幸福”。
先生的这份采访报道分上、下两篇刊载于1944年7月4日和5日的《大公报》上。这次略带传奇色彩的采访既为中印友谊增添了美好的内容,同时也展现了先生的忧国忧民之心和赤诚的记者良心。
三、历史地理和海交史的早期研究
1944至1947年期间,章巽先生在美国先后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和纽约大学,以文学硕士毕业。在此期间,他还兼任《大公报》的特派记者,因而学习、工作都很繁忙。1947年回到上海后,一度兼职于南京的中央大学和上海的复旦大学,频繁奔波于两地。数年后,则因健康原因辞去南京的工作。当时,正逢顾颉刚先生和丁君匋先生在上海开办“大中国图书局”,他遂被聘为特约编辑,从而有机会与顾颉刚先生合作,编绘了现代中国学术界最早的历史地图集。
由顾颉刚、章巽合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在1955年由地图出版社出版。此书虽然篇幅不大,内容不够详尽,却是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之学科建设的重要成果之一,是综合性历史地图集的开先河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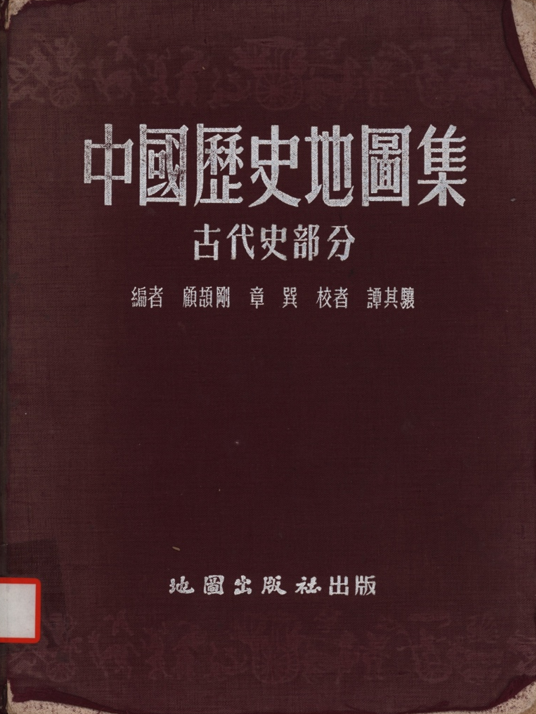
《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
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有关历史地图的作品尚不止于《中国历史地图集》,其他如《世界历史地图》(章巽编译,张志云绘图)也是当时颇受欢迎的一种读物。这是根据苏联出版的历史地图编译绘制的,不过在“古代亚洲图”(第六幅)中增添了见于汉文古籍的资料。原书由苏联国务院直属测量及制图总局出版,中文版则由上海大中国图书局出版。这套挂图充分重视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交通路线,并尽量展示历史的发展进程。最后附有文字说明和地名索引,十分便于阅读。
章巽先生于1956年5月正式出任复旦大学教授,随后,他的学术研究领域除了历史地理外,还扩展至古代中外交通史。在该领域的第一本著述为《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是中国古代航海史综论的“开山之作”。在此之前,先生相继撰写了《从远古到战国时代的海上交通》《秦汉三国时代的海上交通》《隋唐时代的海上交通》和《宋元时代的海上交通》四篇论文。不久后,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将四文合编成《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一书出版;继而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刊印以后,国内外学界和社会的反映都十分良好,因此在数年之后由格列可夫(Г. B.Гpeкoв)译成俄文出版(苏联国家科学出版社,1960年)。
1986年,商务出版了该书的修订版。先生在原书基础上,添入晋、南北朝、五代、明、清(迄于鸦片战争前)各时段的海上交通发展情况,使得全书更为充实和完整,这可以视作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海上交通的简史。
四、《大唐西域记》研究的设想与实践
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降,先生将学术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唐代佛僧玄奘的名著《大唐西域记》上。该书撰成于公元7世纪上半叶,记录玄奘从陆路西行,前赴印度求法,经历十七年后返回中土的旅行见闻。书中除了记述中亚、南亚的宗教(主要为佛教)外,还谈及各地的地理、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被国际学界誉为古代中外交通史、佛教史和印度古代史的重要著述。
据中华书局资深编审谢方先生的回忆文章称,早在1959年4月,章巽和范祥雍二位先生便致函中华书局,建议高质量地整理出版《大唐西域记》,并附上整理的计划书;此议与最早设想整理该书(1958年)的向达先生的想法不谋而合(见谢方《二十六年间——记〈大唐西域记校注〉的出版兼怀向达先生》,载《书品》第1期,1986年)。虽然嗣后此举因某些客观原因而未能立即付诸实施,但是章巽先生却丝毫没有放弃研究《大唐西域记》的意向和工作。这从先生遗作中的几篇亲笔手抄稿上可以看出来。
以下是先生认真抄录和初步校刊的四部古籍,皆涉及玄奘的事迹及《大唐西域记》,在此略作介绍。
一是《〈大唐西域记〉考异》的手抄本。原书在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出版于日本,收录于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丛书的第一辑。
二是《〈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考异》的手抄本。原书当是昭和七年(1932年)由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撰写出版。抄录本的最后一页上题为“庚子十月廿四夜录毕”,是知此本录成于1960年12月12日。
三是《寺沙门玄奘上表记》的校勘手稿,封页题为《玄奘法师表启》,当是手稿撰写者所拟的缩略名。《上表记》原刊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卷,编号2119。在手稿中,“寺沙门玄奘上表记”之下的括号内有“原本:唐时代写小泉策太郎氏藏本”和“甲:奈良时代写京都知恩院藏本”的字样,则知此手抄本是以《大正新修大藏经》所刊者为底本,并用小泉所藏唐本及知恩院所藏奈良本校勘之;校勘文则使用红笔。由于手稿上未见校勘者的姓名,故此稿似是先生使用日本收藏的两个珍本校勘《大正藏》的版本。
四是《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的校勘手稿。其底本出自《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0的《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编号2052),由冥祥撰写。底本的文字用蓝笔书写,校勘的文字则用红笔,出自所谓的“原本”和“甲本”;前者为“平安时代写观智院藏本”,后者为“平安时代写宝菩提院本”;二者均为日本收藏的珍本。手稿的最后有“一九六○年九月三十夜至十月二日上午抄”的蓝笔字样。
以上所列先生的手稿有两份都标明成于1960年;余者虽然未见确切日期,但就其内容而言,亦当成于相近时期内。可知先生至少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就着手《大唐西域记》的研究。惜乎他仙逝后,家中曾惨遭邻居火灾殃及,许多遗稿付诸一炬,否则或能发现更多的研究手稿。《大唐西域记》点校本于197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它所提供的原文的权威性和正确性颇获学界的肯定。
五、老骥伏枥,壮心未已
在1980-1990年的短短十年内,先生一方面精心培养硕士、博士生,学生们继承先生之学术传统,并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为将先生之学术理念、风格发展壮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则相继编撰出版了四本著述,为其学术研究成果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1980年3月,先生的《古航海图考释》由海洋出版社出版。此书是继《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后,先生有关古代海交史研究的又一部重要著述。这份古航海图是先生在上海汉口路的来青阁书庄偶然发现的。在此后的许多年内,先生对这份资料进行深入的研读、辨识,最终确认它是一份极为难得的古代民间航海图。又经历多年的考释,最后于1980年正式付梓面世,为中国的古代海上交通史研究贡献了一份重要的原始资料。

章巽著作《古航海图考释》
1985年2月,先生的《法显传校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法显传》是东晋及南北朝时期的高僧法显关于自己十五年间赴天竺求法取经的亲笔记录。先生对于这部珍贵的古籍早就予以重视和研究,他积多年之功,以南宋刊印的《思溪圆觉藏》本为底本,参考了多种《法显传》的最早印本和古钞本,充分汲取了19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此书的研究成果,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法显传校注》一书出版后,甚获学界赞誉,被称为当时集法显研究之大成的、最有影响的力作。
1986年12月,《章巽文集》由海洋出版社出版。此书收载的文章主要为先生自20世纪50年代以降的学术研究作品,研究领域则集中于历史地理、古代中外关系等方面。

《章巽文集》
除了完成上述的三部著述外,更值得一提的是,先生奋力拓展《大唐西域记》专题的研究领域,旨在形成该专题的研究系列。首先,他接受了巴蜀书社“古籍导读”系列中的《〈大唐西域记〉导读》的稿约。然而,由于身体状况不佳,先生勉力完成了该书的前半部分,在实在无法继续的情况下,委托其学生芮传明博士接续此事。能够获师信任,继续这一任务,对于学生而言,当然倍感荣幸。于是他立即尽其所能,积极撰写。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先生竟然“暗中”与出版社发生了龃龉:他要求与学生联合署名,而出版社则倾向于先生独立署名。数度往返之后,在先生的“最后通牒”——否则就毁约作罢——之下,出版社才接受了此议。学生得知此事后,大为惶恐,直接致函出版社,请求维持原议;但是当时“木已成舟”,只能听从先生的意见了。这场“风波”不仅展示了先生在名利方面的高风亮节,还体现了他提携学界后辈的良苦用心。
以先生为主导的努力在数年后获得了成果,《大唐西域记导读》于1990年1月正式出版;2009年1月则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发行了新版。

《大唐西域记导读》
先生对于《大唐西域记》专题研究的贡献并未至此为止,因为当1991年贵州人民出版社策划古典名著的《全译》大型丛书时,先生在身体稍见康复的情况下,又毅然接受了《〈大唐西域记〉全译》的稿约。显然,他想利用其人生的最后阶段,再为《大唐西域记》的专题研究贡献一点力量。然而,这部书对于工作量的要求较诸《导读》更高,它不仅要求白话文的全文翻译,还要求对全部内容进行详细的注释和辨析。所以,当先生着手实际撰写时,已深感力不从心,况且此时的健康状况又再度恶化。万不得已,先生只能改用原则指导的方式,交办其学生芮传明完成文稿的撰写。
先生在学术和资料方面的全力支持,使此书的撰写得以顺利地进行,从而在他在世之时交出了书稿。不无遗憾的是,《大唐西域记全译》正式出版于1995年11月,距先生之仙逝(1994年12月)已有一年。不过,此书凝结了先生在其人生最后阶段的心血和期望,则是显而易见的。此后,该书在学术界的口碑尚属不错,故经修改后更名为《大唐西域记译注》,由中华书局新版于2019年。先生对于《大唐西域记》专题研究的设想和规划,以间接的形式得到了部分的实现。
六、严于治学,淡泊生活
章巽先生严于治学,一丝不苟的精神为学界共知,其例证不胜枚举,在此不赘。但是先生对于自己的名、利却并不苛求,向来淡然处之。正是这种坦荡、淡泊的生活态度,使得先生即使在最艰苦的客观环境中也能最大限度地享受到生活的乐趣。
先生在1983年赠送复旦大学郑宝恒教授的两首诗,便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特色。其一《七十》云:“岁月如流去不还,行行又到古稀年。病须书卷抛身外,老喜儿孙绕膝前。家室平安已是福,命途否泰尽由天。寿登耄耋生同寄,识得无求自泰然。”其二《偶成》则云:“平生羞带折腰心,鱼爱江湖鸟爱林。自解寂寥吟短句,春兰秋菊即知音。”先生淡泊名利和坦荡胸怀之态跃然纸上。二诗的手迹为郑先生所收藏,确为万分珍贵之物。
先生另一首小诗《漫笔》也反映了类似的高尚情操:“深杯酒满心宜足,小圃花开意亦舒。莫笑衰翁贫且老,传家尚有五车书。”(引自吴琅璇、郑宝恒《缅怀奠祭章巽教授》一文)先生不以钱少为耻,而以书多为傲,这才是顶天立地的“真知识分子”!
综观先生一生,自幼熟读书诗,长则认真治学,擅长历史地理,尤精中外关系。谨遵圣贤之道,修身齐家救国。终生与书为伴,清名永传后世。附图为先生晚年摄于书斋的近影。

章巽先生晚年撰于书斋的近影
(为纪念复旦大学历史学科创建一百周年,特推出“复旦史学百年”专栏,刊载关于谭其骧、周予同、顾颉刚、杨宽、章巽、耿淡如等大师、名师的研究性文章。本文是系列文章之六,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姜力丹摘编,完整版收录于《承百年学脉,开史学新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学术传统》一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25年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