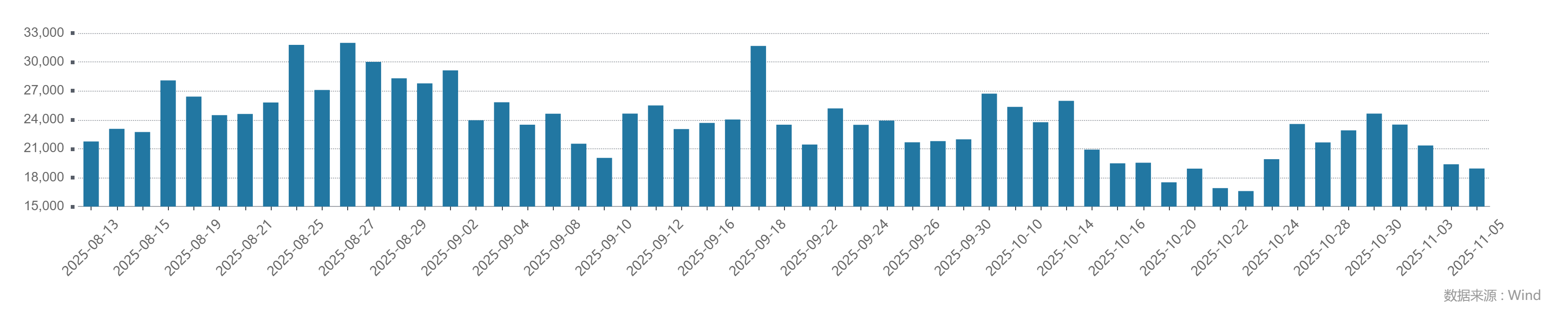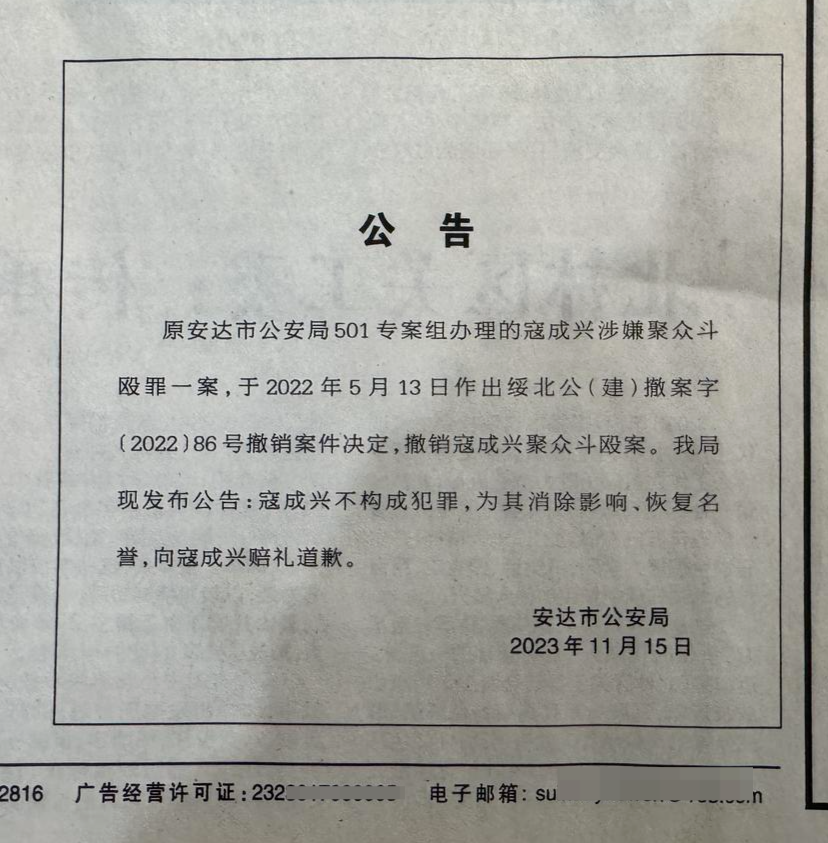夜读|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天气还是有点热,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坐在咖啡店的户外,看着太阳慢慢落到红砖红瓦的屋顶后面,时不时擦一擦额头上冒出的汗。
那几天好像正值什么假期,偶有游客从我们面前经过。刚给我看完侄子小时候的可爱照片之后盯着对面屋顶发呆的朋友突然问我,家乡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自己不觉得自己有“家乡”。
我说我也不知道。
这类问题大概可以用那个古老的哲学命题来概括,“我从哪里来”。再不济,就按照福山的理论,我们这是遇到了身份危机。
说不清是什么具体的原因,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避免回忆小时候,避免回忆“家乡”。人的大脑也是有“肌肉记忆”的,当可以忽略某一部分的记忆调动足够长时间之后,就真的很难再主动想起。
如果不是看到《都灵之马》,我大概不会再记起幼年时期的深秋。
长满枯草的野外,石砌的房子和水井,狂风卷起枯枝败叶撒向空中。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有那么大的风,吹得世界一片死寂。我记忆中的人只剩下老人,灰色的脸上布满沟壑,他们说着过去的人和事,更多的时候是坐着、发呆、沉默不语。他们的表情并不麻木,而是若有所思。那表情是属于过去的,而他们仿佛也不活在当时当下。
我想起来,那时候我对他们的谈话充满好奇:他们说的很多年前到底是多久之前,那个时候真的有土匪吗,土匪长什么样子,那个时候真的吃不饱饭吗,人为什么会吃不饱饭,那谁家去了很远的南方的孩子我见过吗,他为什么很久才回来一次,南方有多远,南方跟我们这里很不一样吗。
夏天过完之后,我回去了几天。朋友在微信里说,我没去过那里,你能不能多拍些照片给我看看那里是什么样子。
那里是什么样子?那里没有春天。天气好像是一下子热起来的,树和草好像是一下子就变得绿油油了,很少看到花。
那里夏天很亮,到处都能听到蝉鸣,杨树的叶子被太阳光照得发白,有风的时候发白的杨树叶子哗啦啦响,一闪一闪的。那里深秋和冬天大概就是贝拉塔尔电影里一片萧瑟的匈牙利平原,天空很高,白色的墙、灰色的瓦。这样的景色看多几天之后,人们的眼神就变得空洞,不知道是在绝望着什么还是在期待着什么。
那里除了夏天之外的三个季节每天都在刮大风。大风平等地卷起它遇到的每一个尘土,把它们从一个角落带到另外一个角落。风停了片刻,水泥路面看起来一尘不染的样子,如镜子般反着光。但是下一秒,大风依然从路面上卷起了细如烟的尘土。真的令人困惑,这马路竟然这么脏吗,吹了几个月的风都没能把它吹干净。
“就只是一个不知名的、毫无特色的北方小城而已。北方的小城镇千篇一律。”我回复他。
但非常感谢这位朋友,让我突然对那个地方产生了一点兴趣——我要去看看那些我曾经很熟悉的地方。
我去看了我至今都不太喜欢的高中老校区。正值假期,所以它看起来有些冷冷清清,但那装模作样的大招牌和保安亭依然非常不讨喜。我没有透过铁栏杆往校园里面看,更没有要走进去看看的欲望。
学校的隔壁是一个已经倒闭很多很多年的国营单位的家属院,已经破败不堪,很少人住,原本的空地全部被开垦成了菜园子。那栋已经存在了很多年的两层高的宿舍楼里,几户人家装了新的门窗。一位年轻的女人抱着孩子站在自家门口远远看着我。
路边有不少卖小吃卖菜的摊贩。超市里人声鼎沸,不知道是因为促销的广播还是因为人太多。
经常有车几乎是横着停在马路并不很靠边的地方,你以为是临时停车吗?不,这是他们在心里给自己划的车位。
我第一次在这里启用了我日常生活里的习惯——观察周围的人,在等红灯的时候、等奶茶的时候,包括走在路上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的面孔和姿态,各种各样的、很鲜活的。然后我不由地思考这个地方这些人的生活具体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们如何上班、几点下班,他们应该和我父母去的同一个地方买菜,他们应该还是在那条老街的那几家店里吃早餐。
我猛然发现,不管承不承认,客观上,自己跟这个有点熟悉又比较陌生的地方是有关系和关联的。我很快接受了这一点。这让我更加坦诚地观察和审视自己。
后来偶然在书里读到哲学家布拉德雷德有关个体与环境的关系的一段阐述:“……他内心中的灵魂被普遍的身后所浸透、浇灌和限定,他吸收了普遍的生活,由此形成了自己的本质,并把自身建立起来。他的生活与普遍的生活是同一的,如果他反对这种生活,那他就是在反对自己。”所以,如果人生是一条曲曲折折的线,那故乡大概就是其中一个坐标点吧。
这当然并不是问题的答案。我也依然不知道答案。看到《永恒和一日》里安德烈对着沉睡的母亲问,“为什么我要过着流亡的生活,为何我不认得归程,在这个讲着自己语言的地方,却感觉不到信心”,我依然痛哭流涕。
朋友看了我发的照片之后回复说,小城镇果然千篇一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