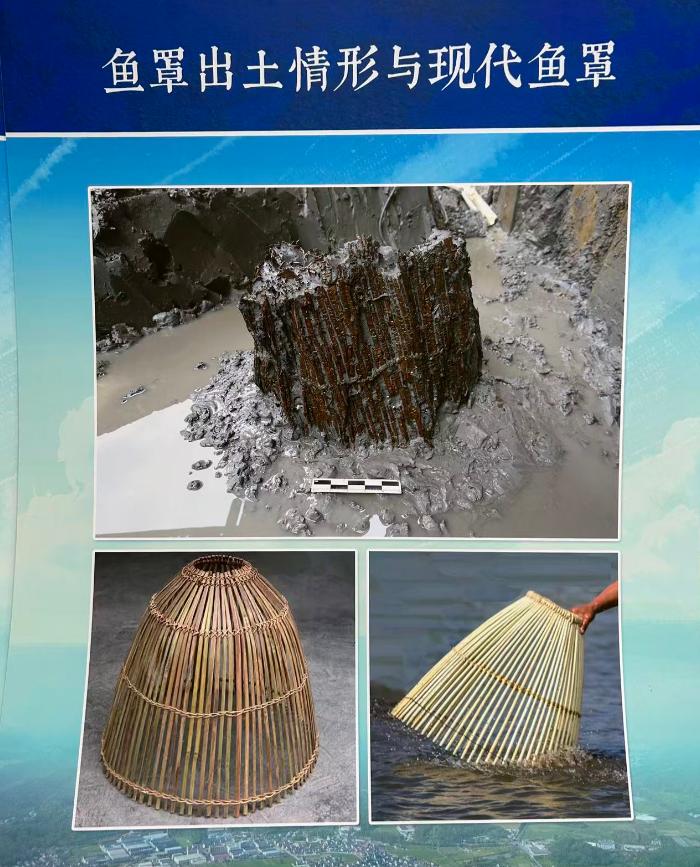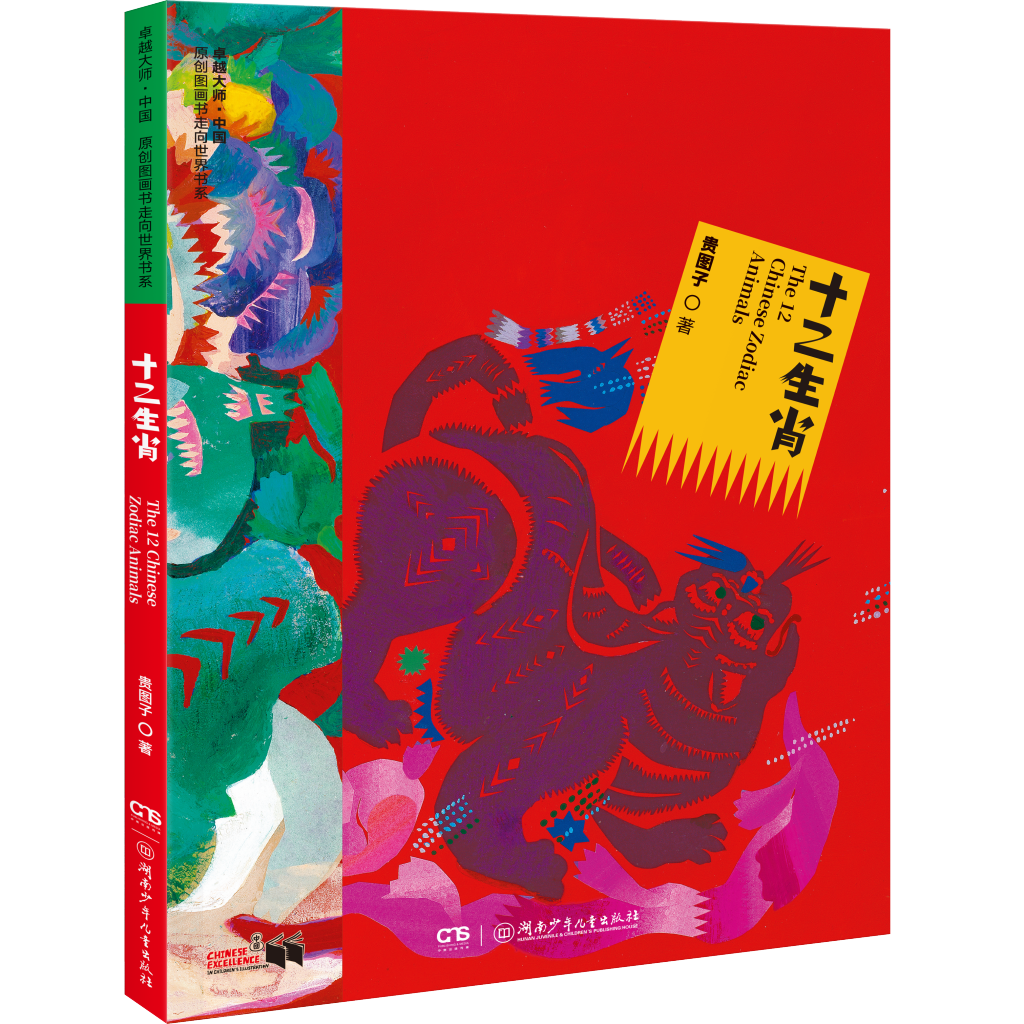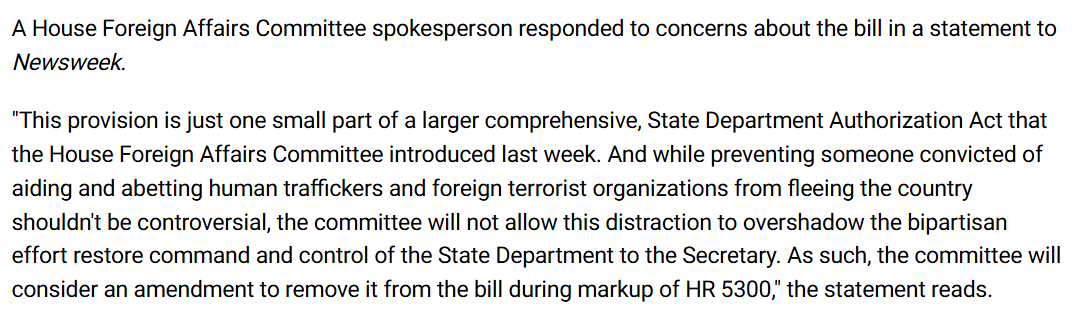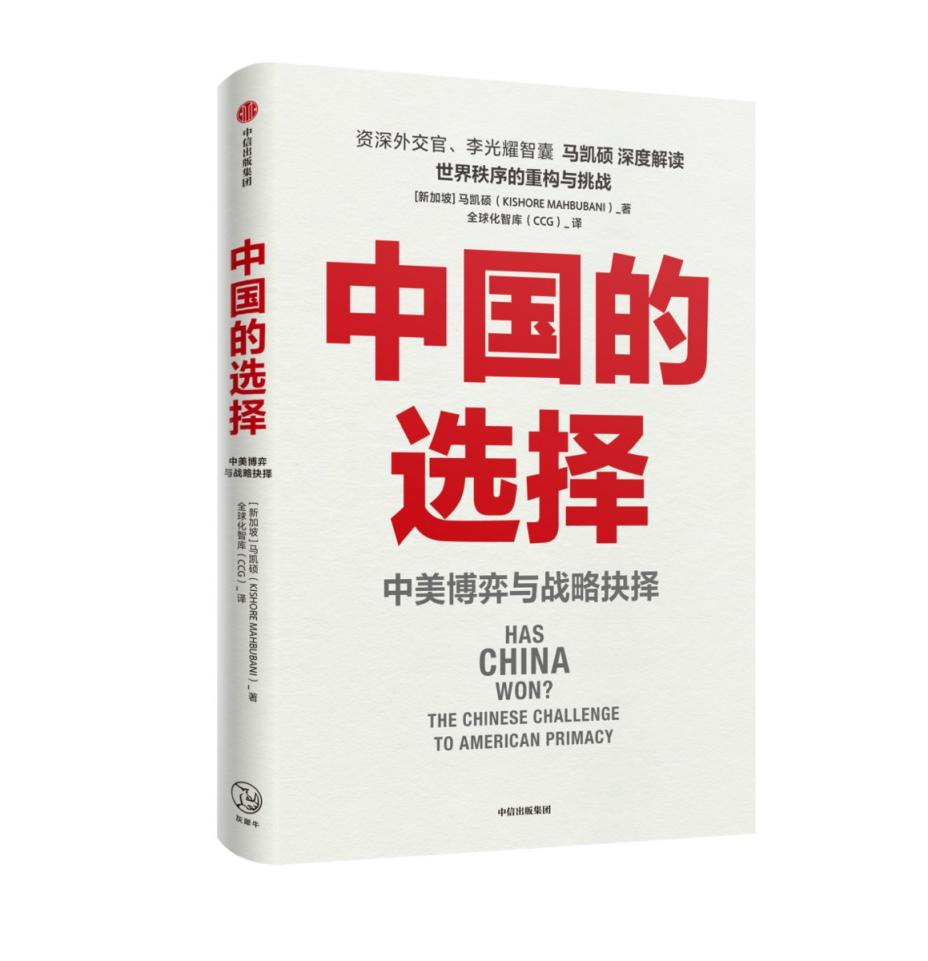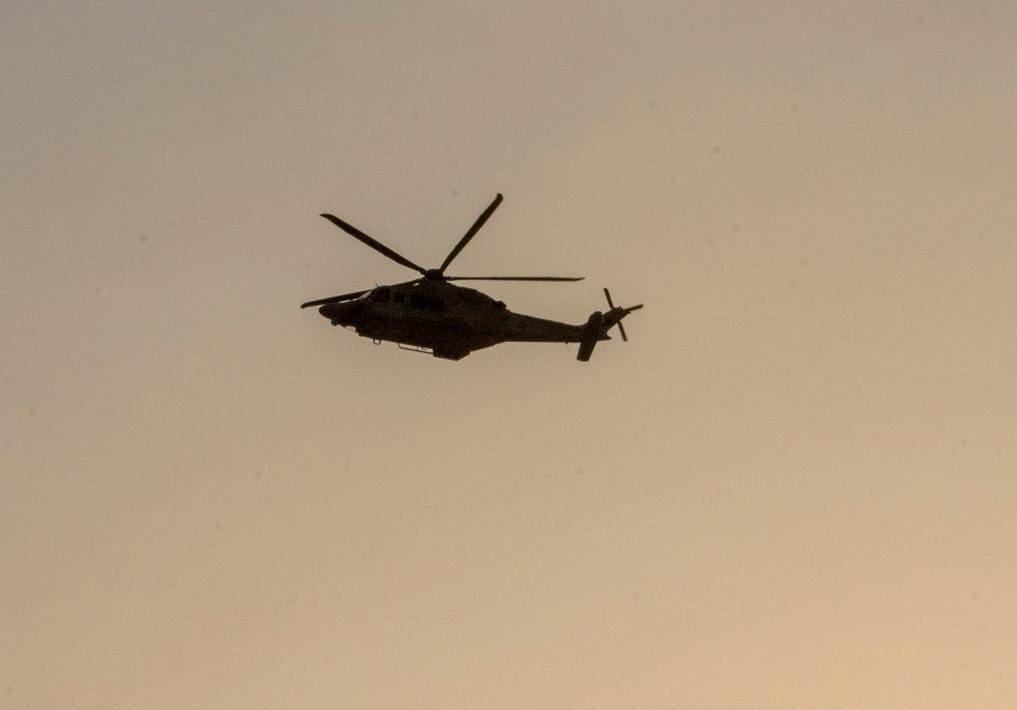宋耕 重木|从屈原到贾宝玉:探寻古代中国的男性气概
8月23日,《文弱书生:前现代中国的男性气概》作者、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宋耕与书评人重木在上海古籍书店举行对谈。两位学者从书籍的写作缘起与学术脉络,延展至对中国古代男性气质、性别话语与文化传统的探讨。从屈原到《红楼梦》,从文武之辨到情教的兴起,他们不仅追索“文弱书生”的历史踪迹,也将之放入现代性与西方理论的视野中重新理解。以下是本次对谈的文字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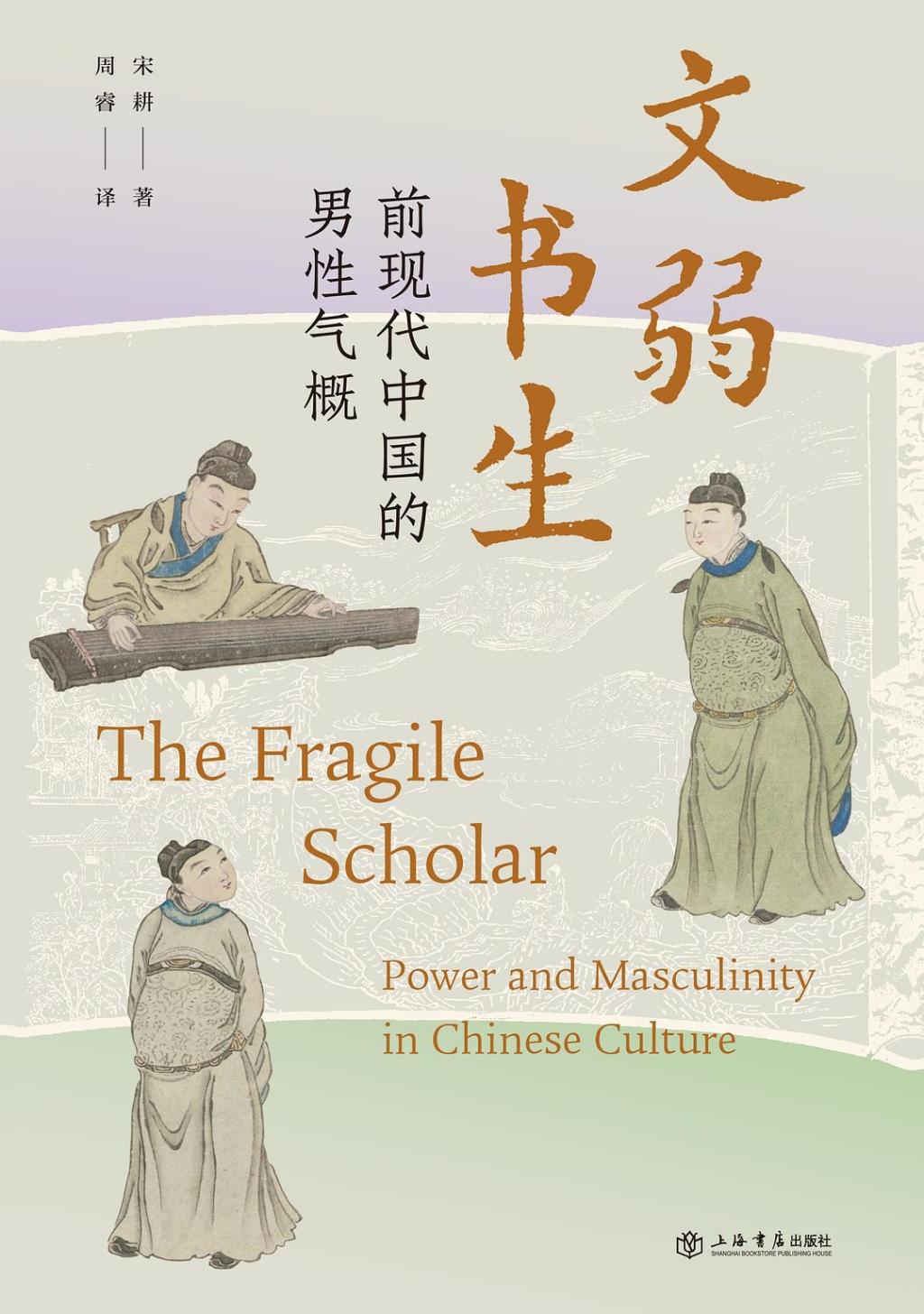
书籍缘起与理论框架
宋耕:本书由我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写作时间比较长。从1995年到2000年,我在香港大学读博士。我一开始想做中国古典戏曲研究,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研究中国戏曲。在这个过程中我有一个很感兴趣的问题,就是“小生”这个形象,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的观众,都会觉得好像是一个很女性化的形象,没有胡须,唱腔也很假嗓子,舞台形象没有所谓的阳刚之气。但是才子佳人爱情故事里的男主角,都是这样的小生形象,比如《西厢记》里的张生,他是我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所以我就从张生入手,研究在受西方文化影响以前,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的男性形象是怎样的。
2004年,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本书的英文版,由于本书是学术著作,其影响力主要限于学术圈内,之后有做中国男性气质研究的学者,对本书多有引用。2024年港大社出版了本书的繁体中文版,2025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简体中文版。
重木:我得知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候是很开心的。因为我的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与宋老师相似。宋老师研究的是在受西方影响之前的中国古代士人的性别气质,而我研究的刚好是在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之后的中国古代士人。所以我论文的前一部分需要讨论中国古代是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我当时在查找文献的时候,宋老师的这本书就出现在我的视线中,而且关于本书,我看过三个版本。
我最先看到的是宋老师的博士论文版,后来又看了英文版,对比这两个版本,我发现宋老师做的改动还是比较大的。宋老师在前言里提到他受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男性研究的影响。当他在1995年开始写本书的时候,刚好有一大批人开始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我认为本书和当时一大批书,都属于中国古代性别气质研究的开山之作,在学界如果要进行相关研究的话,必然要参照这些著作。所以本书能译成简体中文版,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另外就是对我写论文以及对我的一些理解很有帮助的是,宋老师在书中虽然主要围绕明清时期的才子,但是他以才子为核心进行延伸的时候,整成了一条很有意思的线索,而这条线索即使是在当时也没有被过分讨论。宋老师整理的这条线索,从屈原开始,考察整个男性机制的变化,那么后来出现的话语流变,即所谓的女性化话语的流变,是怎么发生的呢?当下我们说的“娘娘腔”“女性化”这些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在非常短暂的历史时期里诞生的一个关于性别趋势的模板,如果把线索拉长了看,会发现这个事情非常复杂。
宋耕:一提到性别研究,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女性研究。所以在性别研究领域,男性研究可以说是一块还没有开垦的土地。关于它的重要性,我在书的前言里也有讲到。只有把男性也作为性别的个体来进行研究,才能真正地在平等的意义上来看待性别问题。性别本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男性研究中用得最多的就是“霸权男性气质”,否定它的对立面,就是不女里女气。所以男女是互相定义、互相依存的,只有对男性进行了深入研究,才能更好地理解作为性别个体的女性。
另外在研究男性的过程中,我们也面临着一个问题。性别话语,它是一把双刃剑,在对女性造成压迫的同时,也使男性面临社会压力和期待。所以男性能否实现所谓的男性解放,这也是一个课题。再有一个就是研究男性的意义不局限于男性本身。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男性是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就像我们说“东亚病夫”而不说“东亚病女”,它是跟国家的命运、形象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通过男性形象、男性气质的研究,看到性别话语是如何影响国家和民族想象的。
本书从屈原讲到《红楼梦》,好处是可以梳理出男性气质发展的脉络或者说是中国古代男性气质共通的特点,但这样做必然也有局限性。它不能够充分地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做研究,因为它的跨度比较大。所以我很期待能有这样的作品,它可以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去分析。
重木: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文献综述时,会涉及中国古代士大夫对于自身男性气质的感受,以及他们所产生的感性生活。在宋老师这本书以及我自己的研究中,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一种理论性的框架。我后来借助了福柯的一个方法。福柯晚年在法兰西学院有一份法兰西讲稿,其内容转向了古希腊世界对自我伦理修养的关注,这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会很有启发。德国汉学家何乏笔就用福柯的这套理论来研究中国古代儒家的功夫论(相关研究参见《修养与批判:跨文化视野中的晚期傅柯》,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我发现福柯也面临着这个问题,即如何理解古希腊男性对于自我的关注,其中涉及身体以及他们的情爱。
福柯后来做了一个理论归类,总结出了两个原则,第一个叫同构性原则,宋老师在书里对此也有指出。我觉得中国古代男性气质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古代的男性气质,它不是一个自在的场域,而是一个完全受制于权力的问题。你的社会身份是什么,决定了你能展演出怎样的身体形象以及性别形象。福柯把这一类叫作同构性,即身体、性别和社会地位在权力、伦理、政治中被安排的位置是息息相关的。
福柯总结的另一个原则叫主动性原则,它其实和同构性是一样的,如果你在整个同构性原则中占据上位,那么你必然是占据主动的一方。主动性并不是自然的本质属性,是权力赋予你的,是在这段关系中以及在性行为中必然占据的姿态以及整个身体的表现。这就是福柯总结的两点。
中国古代性别观念的特殊性
宋耕:其实所谓的男/女二元对立在西方社会也不是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的。它实际上伴随着“个体”的兴起。这种思想在晚清至五四时期传入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接受了这种思想,把它作为现代性的一部分,并用来全盘否定或者修改传统中国的性别话语。
关于中国古代男性气质,主要有两种理论框架:一是文武,二是阴阳。雷金庆的《男性特质论:中国的社会与性别》一书,主要讲的就是文武。他认为中国古代有文、武这两种男性气质,都可以作为理想男性气质的标志。理想的状态是文武双全。而在宋代以后,我们的传统成了重文轻武。重文轻武的原因就是“规训的身体”,不过福柯讲的“规训的身体”主要谈的是资本主义下的现代社会,但我觉得他的思路也可以放在前现代中国社会上。为什么才子或者文弱书生的形象是理想的男性,因为这个跟科举制度是相联系的。科举是统治阶级用来规范社会秩序的制度。在备考科举的过程中,你的身体就会化为一个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在我看来,文和武是有阶级性的,不识字的人没有资格被纳入探讨范围。而武也并非光有力气或者是武功高强,还有道德层面上的武,只有服务于正统的统治者才是武的要求。另外文武只存在于公共空间,没有涉及私人领域,所以本书中我主要的理论框架就是阴阳。如重木所讲,阴阳是流动的,不以身体性别作为划分。我们现在一般都理解为男性就是阳,女性就是阴,其实不是这样的。男女可以放在阴阳的框架中,但是阴阳的内涵比男女广阔得多,而且它是一个流动的概念。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不同意用“同性恋”这个概念,因为它也是西方现代社会思潮进入中国后才出现的概念。在中国古代是没有这样一个身份的,至少作为个体是不存在的。中国传统社会对同性关系态度相对包容,因为它完全可以放在阴阳的框架里面,并不对性别秩序造成破坏或者颠覆。
而在西方基督教文化里面,由于上帝创造男女,然后让男女结合,繁衍后代。而两个男人结合在一起,是违背上帝旨意的。这个是罪。在中国社会的认知体系中,阴阳本就有上位者和下位者之分。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中,前者为阳,后者为阴。任何的所谓同性关系都有一个阴阳,有一个地位高的、年龄大的和地位低的、年龄小的,这就完全符合阴阳这样的性别秩序。当然在中国历史中也有禁止这种行为的,比如清代。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情况,但是总的来说人们没有把这个当作颠覆性的或者对社会造成非常大破坏的行为,最多叫作癖好。有这类癖好的人不是很好,但也无伤大雅,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所以我觉得刚才讲到的福柯理论能很好地对此作出解释,本书也用到了一些西方的理论,当然这也存在争议,很多学者会觉得福柯讲的是西方社会,而我们现在讲屈原、张生,能否把福柯的理论套用在上面呢?我觉得阅读古典的过程是一个对话式的阅读,我们不可能穿越回去,而我作为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学者,肯定是在西方理论的影响下,跟古代文本进行对话式的阅读。所以我希望这个是本书的一个特点,也是我现在一直想要继续做下去的方向。
文本帝国与阶级属性
重木:我想就着宋老师说的雷金庆谈论文武的《男性特质论:中国的社会与性别》谈下去。这本书我在很早之前看过,我觉得雷先生在这本书中给了一个框架,文武可能是韦伯认为的理想型,但其实我觉得还是有挺大问题的,就像宋老师在书里讲到屈原。我们当下在中国内地看到的关于屈原的研究,一般情况下都是政治史的研究,或者是关于屈原作为“慈父”形象的研究,很多人忘了屈原在《离骚》中对于自我形象的展演。
屈原一开始上来就说“帝高阳之苗裔兮”,然后又说“又重之以修能”。他上来就提到了自己的家世,来表明其高贵血统。血统高贵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儒家所继承的礼仪制度,规范的是周王朝下的贵族子弟,而春秋时期的各国君主,也都是贵族子弟,所以他们的身体从小就被一套所谓的礼仪制度所规范,而这也就是对思想的规范,以及对感性生活的规范。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屈原表明他血统的高贵就来源于他的贵族出身。贵族这个概念后来由孔子对其进行了改造。贵族一开始关乎血缘,但是孔子将其改成和道德修养有关。屈原反复地说他的衣服上粘了好多香草和花,他的目的就在于表现其身体本身。其身体本身作为一个外在形象,是他内在品质的表现,我的身体就是我内在德性的展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宋老师的书里看见荀子说了一句话,叫“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就是儒家对个人德性的反复锤打。它在某种程度上会在你的外在身体形象上展现出来。它不是一个内在的、不可见的品质。当你见到一个君子的时候,你可以从他的外在形象上了解这个人。这一点直到魏晋时期还是很重要的。《世说新语》中就专辟一章,讲了当时的人们有多么注重外在的仪容仪表。所以我们现在嘲笑中国古代男性过分注重外表,其实大家是没有理解这种对外在的注重和我们当下所谓的被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逼迫之下形成的美是不一样的。当时的美是一种修能,是人的内在品质的外化表现。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古代“文”的本质。陆威仪在其研究中认为,中国是一个文本帝国,中国古代产生了这么多的文本,而且还在文本里套文本,对文本进行注释,对注释的注释再进行注释。我们如果要看古代文本的话,会发现很难懂,就像现在网络上的超链接。由此就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文本帝国。“文”在某种程度上被赋予了一种特权。真正为汉朝奠定文化基础的是早期的儒家思想,且在两汉时期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儒家体系,最后更是构建出一个庞大的群体。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后来能被看到的文本以及对于文本诠释的决定权。所以当下我们做研究的时候经常会被质疑,就说这些研究都是有很强阶级属性的,研究都是上层贵族或者是士大夫群体,而对贩夫走卒都不大了解。
但请注意,我们做研究,必定要涉及所研究的具体时代背景。不能说当下是民主的社会,人人平等,要求古人也这么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无论是男性气质还是女性气质,会发现其实是很难研究那些被排斥在文本之外的群体的。你无法研究那些贩夫走卒。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活在自然之中的,虽然身体是无言的,但他们有日常生活,以及对自身情感的感受。只是如果这种情感无法进行外在化的表现,尤其是在中国古代,“文”是这么强势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如果你的感情不能进行外在的物质化流转,无论是当代人还是后代的人,都是很难被看到的。所以我们会看到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清小说,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看到了一些贩夫走卒的形象。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写这些小说的作者,即使是底层的士大夫,也是士大夫。他们也不属于一个落魄的阶级,在明代,秀才是有特权的。这一点为何不会妨碍我们对于中国古代男性气质研究的理解,因为我们研究的是一个显现的东西,即使是那些贩夫走卒,他们的理想也是由这些士大夫等主流群体所塑造的。
晚清到民国的时候,好多学者进行社会学研究和人类学研究去采集竹枝词,他们觉得竹枝词可以普遍表现百姓的状态,但我觉得其实这里面能看到的东西也挺少的。我之所以说这一点也就涉及另一点,就是后来对于中国的男性气质研究中有一类,是从《水浒传》拉出来的这条线索,认为《水浒传》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历史上和我们主流理解不同的男性气质。他们更强调“武”,更强调兄弟情谊,大家会在里面看到强烈的所谓的厌女症。但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忘了《水浒传》的这些英雄。他们是一群社会边缘人物,且他们的领头人宋江也并不是一介武夫。所以我们会发现中国古代由士人群体所组织的庞大文本以及流入文本底层的欲望,无论是身体的、写作的,还是言说的欲望,它背后都有一个强势的群体外在表现。 即使是《水浒传》也没有逃脱这个大框架。《水浒传》中文武双全的人都是文质彬彬的人。儒家一直讲“文”和“质”是同等重要的,其实“武”的气质在儒家看来就是“质”的问题。“质胜文则野”,如果一个人的外在形象是过分“质”的,他就不是一个君子的形象。在本书中,宋老师也有讲从“君子”到“才子”的形象的变化。
才子佳人与男性欲望投射
宋耕:我们现在看到的古代文本的作者,都是士大夫阶层。从性别角度来讲,我们今天所讨论的理想男性形象,是不是真的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妇女们的理想男性形象呢?我们不知道,也没有办法知道。因为古代的妇女声音是被湮没的,她们没有书写的权利和能力,那么文弱书生和才子佳人的作者是什么人呢?就是像张生这样的人,落魄的知识分子或读书人。他们把自己的欲望投射在才子佳人的作品里面,所以这个才子一定是去进京赶考的书生,而小姐也一定是出身高贵的,不是相国的小姐,就是大家闺秀。小姐一定是爱上书生。她不可能爱上像张飞、李逵那样“武”的男人。小姐一定是青睐书生,然后书生去进京赶考一定是高中状元,奉旨成婚回来大团圆。所以它反映的是一个男性欲望的投射或者想象。
所有的才子佳人戏曲小说实际上都是由男人书写的,是男人写给男人看的作品,因为当时的女人基本是没有阅读能力的。像《红楼梦》里面的薛宝钗、林黛玉这些人是很少的。即使有,恐怕也是占很少比例的。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网络小说,比如男频小说、耽美小说,都是男性作者写给男性读者看的幻想和欲望,或者相反。关于阶级的问题,我的同事,香港大学中文学院的吴存存老师现在做的一个研究,就是去欧洲的博物馆、图书馆,找当时传教士记录下来的底层老百姓特别是底层妇女的说唱文学和她们写的故事。这些故事并不是士大夫写的,这些东西的文字质量是很低的,但它记载了劳动人民的声音。而我这本书它的副标题是“Power and Masculinity in Chinese Culture”,在出版简体中文版时就改成了“前现代中国的男性气概”,将它的读者面扩大了。前现代中国社会和其他同时期的文明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我们是一个文本社会。
在《西厢记》中,张生的才能和男性气质表现得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他对于“文”的能力。《西厢记》里有关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部分。张生在进京赶考的路上住在普救寺,恰逢崔莺莺与母亲和弟弟带着父亲的灵柩回乡安葬。张生看上了莺莺的美貌,但此时两人都没有逾越封建礼教的界限。当时有个叛将名叫孙飞虎,他听说崔莺莺长相很美,就带领叛军把寺庙围了起来,要求崔莺莺成为他的老婆,否则就杀掉所有人。这时候,崔莺莺的母亲就站出来说谁能够解普救寺之围,就把崔莺莺许配给谁。这时张生跳出来说他可以。众人都觉得张生是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是没有对抗的能力的。而张生的能力就在于“文”,他给在附近驻扎的一位将军朋友修书一封,用他“文”的能力写了一封信,让一个和尚连夜突破重围把信送了出去,然后将军马上就带兵来解普救寺之围。这样一来从道德上来说张生就合理地成了崔莺莺的丈夫,只不过老夫人后来由于张生是穷书生的原因悔婚了,让张生与崔莺莺以兄妹名义相称。经此一事的张生就病倒了,而崔莺莺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为了报恩,以身相许。事情败露后老夫人十分生气,红娘却说:“非张生小姐之过也,乃老夫人之过也。”并且用儒家的道德说教她,于是老夫人就决定给张生盘缠,让他进京赶考,如果能够考中状元就回来取莺莺,如果落榜就不要回来了。所以这里的“父母之命”,也就是普救寺之围,是很重要的一个情节,因为在这里,张生占据了道德上的合法性。他作为一个士大夫和读书人,只有他有这个能力写这封信,而“媒妁之言”就是红娘在其中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
还有一点我想说的是,我们现在歌颂这样的爱情故事,实际上“爱情”这个概念也是随着现代性进入中国的,包括《红楼梦》,这些我们很难用现代的爱情观念去解释,比如说贾宝玉跟林黛玉是不是爱情?这里面张生他只是“君子好逑”,只看到莺莺的美貌,但重要的是这些才子佳人小说中都不是一夫一妻制的,很多都是双美共侍一夫,尽管《西厢记》里面没有明确说,但是也说了一句“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的暗示,这也说明了红娘如此积极的原因。红娘有自己的私心,她陪小姐嫁过来的同时,实际上自己也就变成妾了。所以情跟爱情的区别,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情教的兴起与文化变革
重木:我顺着宋老师的话说一下情的事。在明清的时候,情教产生了,在某种程度上说,它重新塑造了儒家伦理,让它焕然一新了。文弱书生形象的出现,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和情教的出现也息息相关。以前传统的君子形象是一个“文”的形象,通过整个内在的道德修养,再由外在形象变成一个文质彬彬君子的形象。“文”和“质”是两个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先秦儒家探讨的事情都是双面性的,比如君臣伦理就是双向伦理,从不讲君对臣能干什么,也不讲臣对君能干什么。孔子和孟子都反复强调,君和臣的关系是双向关系。所以当孔子在谈及君子的时候必然是“文”和“质”同时讲的,所以我们都知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句话。但其实到了后面,尤其是汉儒,它结合阴阳家、法家,双向伦理变成了单向伦理,就变成了等级制。上位者如果让下位者干什么,下位者其实是很难反抗的,当然可以以死抵抗,后来出现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很晚才出现的。我们会发现先秦儒家是君要臣干什么,臣不一定会干这个事情。当时的君臣关系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还有一套外在的秩序在制约君臣。但是在编户齐民后就不一样了。我们都知道中国所谓的帝制晚期,整个皇权是很集中的,所以儒家就出现了一套作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它的问题和修不修身没关系,就是皇权用来统治的一套手段。
一直到宋儒以及后来的明儒,他们都致力于重构儒家。尤其到了心学这一脉后就变成了关于情的问题,开始注重人的内在感受。之前早期的中国古代的伦理规范是一个外部的规定,它规定君要怎么做,臣要怎么做,丈夫要怎么做,夫妻要怎么做。在某种程度上,它和内在想不想这么做是没关系的,自己不需要考虑自己。
但是其实情教出现后,我们就会发现,人的内在是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情感的。在先秦儒家是有讨论过这个问题的。所以它就想以人自身的情作为一个规范的原点,这个规范不再是外部的规范,而是来源于内在情感的规范。情在诞生的时候是具有一定激进性的。我们看到冯梦龙、汤显祖的情在某种上有破掉儒家五伦规定性的趋势。明代之后的才子佳人作品,里面有极强的破坏性,已经完全不见“媒妁之言”,而且其中出格的事情非常多,大家去看柳梦梅和杜丽娘在梦中完成的事情以及在实践中完成的事情和传统儒家的整个意识形态的规范格格不入了,所以情一旦开始具有内在爆破性的时候,整个伦理要重新对它进行整合。明清小说里面有一个变化,就是从情和欲的二元辩证渐渐地开始合一,也就是说情渐渐地从一个内在想爆破意识形态的东西,变成了儒家新的伦理规范的一环,它成了奠基的东西。我们后来就发现,其实在《红楼梦》里一直讲情的问题,但其中“情”和“淫”是对立的。但在情诞生的早期,我们发现性欲是内含于情的。所以我觉得对文弱书生而言,一旦小姐们不同意他们的感情,他们就病了,或者说这是一种因情内在的发作而带来的外在症状。无论是身体的虚弱还是外在的这种矫情,这些形象其实都是情的表现,所以我觉得这些才子在某种程度上,尤其在明清的时候,他们其实是被情化了。
宋耕:我们现在所说的才子佳人可以说是一个母题,是有很长的演变脉络的。母题里的一些基本要素,比如翻越墙壁、私订终身等,在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以及《世说新语》中都有显现。之后便是唐传奇和元杂剧。那么我之所以选择《西厢记》作为分析文本,是因为作为一个文化话语,在元杂剧时期,它已有了固定的模式。到明清更是如此,才子佳人小说的文本,可谓是千篇一律。刚才重木提到了情,讲得很好。情既有颠覆性,也有被正统文化收编的部分。元杂剧中有不少“暗合姻缘”的情节,比如两个人落难之后私订终身,发现绕了一圈,他们在小时候就被父母指腹为婚了。这些描写是用来淡化或者收编文本中有关情的颠覆性的。所以仅从才子佳人小说这个脉络来讲,我认为情的颠覆性,尤其是到了晚明,是个很重要的文化现象。与此同时,才子佳人小说在士大夫阶层中的流通,其实和我们现在看网文和爽文是一样。这种流通是受到限制的,存在被正统文化收编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