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节|关于痴迷之爱的幻想
【编者按】
无论在哪个时代,人们都可能被爱情的幻想所俘获,有时“痴迷之爱的假象比真实的人能够给予的爱更加美好”。这种对完美爱情的向往是人类情感的永恒主题,但也可能带来危险的后果。本文摘自《关于爱的五种幻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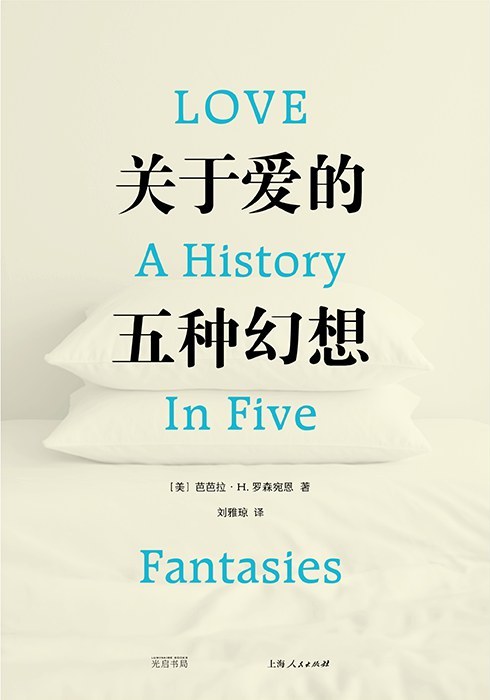
被仪式化的痴迷
在安德烈亚斯的作品中,痴迷之爱已经成为一种“风格”,一种向女士求爱,然后她回应他的方式——没有人真正感受到太多的东西。这成了一场游戏。事实上,在安德烈亚斯的时代,将爱情视为男女之间的有趣斗争的想法非常普遍,它在《爱情城堡》中被刻画(图5),有时还被表演出来。

图5:《爱的城堡》(法国,约1320—1340年):在这个可能是盒盖的象牙小圆盘上,一座由淑女居住的城堡被情人骑士包围。女士们用鲜花和花枝保护自己。
另一种游戏在“爱的法庭”中举行,它由女士主持。安德烈亚斯声称,玛丽伯爵夫人是所有法官中最为重要的。如果真有这样的法庭,他们一定没有审判权。然而,根据安德烈亚斯的说法,他们宣布专横的决定,剥夺美好爱情的自发性,还用规则来阻挡它,使得每一个动作都变得具有仪式感。在这里,美好的爱情模仿,甚至超越了当时围绕婚姻所制定的一丝不苟的教会法律。法庭判决的一个简短例子就能说明这段历史的味道。“如果一个女人不与她的爱人拥抱……除非她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他对她不忠,否则她就违背爱情的本质。”如果两位绝对平等的求婚者在差不多的时间内提出他们的爱,“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优先考虑先求婚的男人;但如果他们的求婚似乎同时进行,让女人来选择也不失为一种公平”。“任何想得到世界赞美的女人都必须沉浸在[与爱人的]爱情之中。”
似乎法庭的判决还不够,安德烈亚斯列出了“爱之王”颁布的三十一条规则,其中包括:
1.结婚不是不爱[别人]的真正借口……16.当一位情人突然看到他心爱的人,他的心怦怦直跳……26.爱无所不爱。27.情人永远不会满足于他心爱之人的慰藉……30.一个真正的爱人会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他的爱人。31.没有什么可以禁止一个女人被两个男人所爱,或者一个男人被两个女人所爱。
在规则的束缚下,在谩骂式的责备中,在“情人节时,每只鸡都来选择自己的伴侣”的感伤中,美好爱情席卷一切的激情在其源头就被驯服了。当然,它一直都受到控制——美好爱情从本质上来说就是通过纪律、服务和淑女的美德进行净化的爱情……
因此,在乔万尼·薄伽丘的《十日谈》(Decameron)中,他在佛罗伦萨的瘟疫期间创造了一个井然有序的聚会。十位高贵、聪明、有礼貌和机智的年轻人逃离城市到乡下住了十天。在帕姆皮内娅或其他人的组织之下,他们轮流讲故事——有的粗俗,有的温柔,有的批评神职人员,这些故事都非常有趣。他们一起唱情歌,一起跳舞,然后回到各自的房间。尽管其中一些人陷入了爱河,他们仍然保持着“遥远的距离”,这是在仿效彼特拉克对劳拉无望的爱。
薄伽丘幻想中的宫廷仅仅持续了几天。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Baldassare Castiglione,卒于1529年)在他的《廷臣论》( The Book of the Courtier )中意图描述一个真实的宫廷,即乌尔比诺(Urbino)公爵和公爵夫人的宫廷。这个宫廷拥有擅长“格斗、比赛、骑马、使用各种武器,以及狂欢、游戏和音乐表演”的人。他们在那里供公爵娱乐;15和16世纪真正的战争是由带着枪炮的雇佣兵进行的。宫廷的氛围颇具竞争意味,但是,正如卡斯蒂廖内所说的,公爵夫人使激烈的竞争变得温和。“每当我们来到公爵夫人面前时,一种至高无上的幸福感都会油然而生。而且,这似乎是一条将我们所有人联系在一起的爱的链条。”他说,宫廷里的男人就像兄弟一样。与女士在一起时,他们可以自由地打交道,却没有对爱情的渴望。在公爵夫人面前,宫廷中人群的“游戏和笑声”中有很多“诙谐的玩笑”,但最重要的是,它们是“以一种高尚、清醒的尊严”进行的。
17世纪到19世纪初,沙龙在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兴起。这些沙龙由富有且多才多艺的女性主持,她们精于生动的谈话,使得“交际”成为一种艺术。这些沙龙吸引了著名的作家、哲学家、艺术家、音乐家和外交官。在混合的人群中,或者在英国的女性聚会中活跃地交流思想是礼节的需要,半隐蔽的爱情也是如此。正如达尔马提亚作家米霍·索科切维奇(Miho Sorkoˇceviˊc)对博学的威尼斯女主人和作家伊莎贝拉·泰奥托奇·阿尔布里齐(Isabella Teotochi Albrizzi)的描述,她“的美丽动人被高贵的礼节所中和”。事实上,泰奥托奇·阿尔布里齐当然已婚,与此同时,她发展了许多情人。像她这样的沙龙,是试探和测试社会、情感和政治规范的边界的地方。它们与俱乐部、剧院和咖啡馆一样,是革命思想和被历史学家称为“感伤主义”的强烈情感表达的孵化器。然而,泰奥托奇·阿尔布里齐的爱情故事并没有赞美痴迷的爱。这种幻想结束了吗?
重新获得的痴迷
完全没有。因为与此同时,当泰奥托奇·阿尔布里齐正在招待、指导和资助国际才子的小圈子时,浪漫主义文化正在孕育之中。尽管浪漫主义时期所颂扬的爱情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中世纪浪漫主义的复兴,它并没有对自己进行轻松愉快的嘲弄。它的痴迷超越了格律和韵脚的限制。相反,它们成为了一种较新的文学体裁——散文小说。这些作品探索了当时,也就是作者和读者所处时代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感受。正如夏绿蒂在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对她的追求者维特所说的:“我最喜欢的作家是那些能够帮助我进入我自己的世界的作家,他作品中描写的事情应该就像发生在我周围一样,故事要亲切有趣,好像发生在我家一样。”
当夏绿蒂提到一本小说的名字,即哥尔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的《韦克菲尔德的牧师》(Vicar of Wakeffeld)时,维特有一种“完全忘我”的激动感。维特是一位年轻的诗人,他在夏绿蒂(即绿蒂)的身上只看到了善良。他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一个田园诗般的家庭环境中。她的母亲最近去世了,她承担起了母亲的角色照顾弟弟妹妹。自从那次会面之后,维特在给他朋友的一封信(这封信构成了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中写道:“对我来说却再也没有白天和黑夜之分了。”和绿蒂在一起,“我在那儿非常自在,并体验到了一个人所能体验到的一切幸福”。每当这两个人偶然接触时,他都会被一种“我快要晕倒了”的说不出的感觉折磨:“好像我已经神魂颠倒了。”无论早晚,他都会在床上伸手去找她,他梦见自己在她的手上“印上千百个吻”。当他第一次和绿蒂见面时穿的衣服穿坏了,他制作了一套一模一样的衣服:青色蓝燕尾服、黄坎肩和黄裤子。当他爬上果园里的梨树,把果实递给绿蒂时,他找到了幸福。她出现在他的祈祷里,栖居在他的想象中,“我看到我周围世界的一切都与她有关”。没有哪位吟游诗人会比他更加着迷、更加乐意为她服务。
但是,维特身上却没有吟游诗人的戏谑。他试着离开绿蒂一段时间后,又跟随他的心回到了她的身旁。与此同时,她已经嫁给了阿尔贝特,也就是她母亲让她保证要嫁的那个人。维特想象着取代阿尔贝特的位置将是多么幸福的事情。他说:“有时我真不理解,怎么有另一个人能够爱她,敢去爱她,殊不知只有我爱她爱得最真切,最忘情,除了她,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有呀!”
维特身上有一些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影子。他的“激情也和疯狂相差无几”,他相当自豪地承认这一点,因为他认为疯狂是非凡之人的标志。绿蒂结婚之前,他随身带着荷马;之后,他带着奥西恩(Ossian),这是一种口头凯尔特史诗和书面的凯尔特史诗拼贴的诗体,在歌德的时代非常盛行。他特别喜欢诗中的一个女孩,她在她死去的情人的墓前“悲痛欲绝”。维特陷入了凄凉的抑郁之中,最终借来阿尔贝特的手枪自杀。
这本书的影响力令人震惊。它被翻译、改编,也受到了嘲笑。男人们穿上了维特套装的复制品,女人则用上了“维特香水”。弗兰肯斯坦的怪物十分敬仰维特,认为他“比我所见过的,或者想象中的任何人都更加完美”,并将主人公的不幸处境投射到自己身上。许多人模仿维特自杀,以至于社会学家大卫·菲利普斯创造了“维特效应”一词来描述模仿者的自杀。尽管歌德后来声称他并不希望维特成为一个英雄,但他的书一开始就由虚构的“编辑”给读者写了一个前言:他已经收集了维特的所有信件,“知道你会感谢我,他的思想和性格将使你由衷钦佩、热爱,他的命运将使你潸然落泪”。歌德知道,他的小说可以在现实世界产生影响。
这种浪漫小说的创新之处并不在于爱情是痛苦的,荷马很清楚这一点,也不是说爱情会变成一种痴迷,奥维德对此已有良方,更不是说人们可能死于单相思,这就是为什么像盖伦这样的医生被要求治疗相思病。不,尽管建立在长期存在的传统之上,歌德浪漫小说的新颖之处在于:陷入爱恋的人将不惜一切代价,也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如果他真的陷入爱恋。维特在给绿蒂的遗书中写道:“这不是绝望,这是信念,我已决定要为你牺牲。”那么女人呢?她应该有类似的感觉吗?最后,当“编辑”讲述维特与绿蒂的最后一次相遇时,答案是明确的。是的!他们将在“[上帝]永恒的视野中、在永恒的怀抱中”相遇并永远相爱。因此,如果歌德说得没错,女人也会不惜一切代价,至少在感情上是这样的,尽管对她来说,为了她持续的幸福,她无法摆脱像婚姻这样的社会安排的束缚。在19世纪的歌剧中,女人和男人一样因爱情而疯狂——于是有相应的悲剧性的结果。
《维特》和其他浪漫主义小说、戏剧、歌剧和诗歌提供的教训,正是福楼拜笔下的艾玛·包法利(见第三章)在危险中学到的一课。艾玛认为最具有影响力的故事是雅克-亨利·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Jacques-Henri Bernardin de Saint-Pierre)的《保尔和弗吉尼亚》(Paul and Virginia,1788年)。小说的背景设定在远离欧洲腐朽文明的小岛(这是对卢梭思想的模仿),小说中的两位主人公一起长大、相爱,并且渴望结婚。但是,他们纯洁无邪的爱情被文明社会物欲横流的价值观所破坏。弗吉尼亚被残忍、富有的姨妈叫到法国,这位姨妈破坏了爱情的自然结局。她终于摆脱了姨妈的可怕要求,可是在回家的路上,弗吉尼亚的船遭遇了风暴。她因为羞怯的“天性”,拒绝脱掉衣服,最终溺水而亡。保尔很快日渐衰弱,离开了人世。艾玛的思绪仍然停留在他们更快乐的日子,那时保尔爬上附近的树,给弗吉尼亚摘取美味的水果——就像维特为绿蒂摘梨一样,在他们的温暖仙境中,他永远给予她甜蜜的爱情。这些男人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女人的一切需求。当这样的事例成为浪漫的典范时,艾玛会自杀也就不足为奇了。早在我有这个想法之前,福楼拜就知道,幻想可以塑造希望、思想和期待,有时是有益的,但有时也会给我们带来危险。
现实生活中的幻想
对于19世纪70年代生活在意大利南部的一些不快乐的意大利妇女来说,这当然是事实。想想乔瓦尼·法达上尉(Giovanni Fadda)与感情不和的妻子拉法埃拉(Raffaella)。当马戏团来到镇上时,她与马戏团的明星杂技演员彼得罗·卡尔迪纳利(Pietro Cardinali)陷入了爱河。我们知道这两个人和其他的人的故事,因为彼得罗谋杀了法达,对他的审判成为一个轰动的讼案。
那时,每个人都期望为爱结婚,但是,对于那些家庭严密地保护着她们的贞洁、限制她们与男人见面的年轻女性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拉法埃拉这样回忆她的恋爱经历:法达“被介绍到家里,我们彼此都喜欢对方”,接着,他向她求婚。就这样,她加入了19世纪意大利不快乐的家庭主妇军团。
不管她和法达的家庭不幸福的具体细节是什么,拉法埃拉并没有在外寻求浪漫。彼得罗·卡尔迪纳利是马戏团的明星,这个马戏团的表演精彩纷呈,表演者的身体时有暴露。马戏团所到之处,许多富裕的家庭对他赞不绝口。几个女人爱上了他,并认为他也爱她们。或者至少,她们在信中(主要是匿名的)似乎倾诉了她们的感情。这些信对卡尔迪纳利来说肯定是有意义的(可能是感情上的,也可能是敲诈的理由),因为他把这些信装在一个上锁的箱子里。它们为妇女提供了一种“尝试”和探索是禁忌情感的方式。
有一封信显然是为了回应他结束他们的婚外情,一个女人写道:“亲爱的彼得罗,我知道很多女人都爱过你,但她们中不可能有人比我更爱你。”另一封来自不同女人的信中说:“我最亲爱的爱人,十三天后我终于收到了你的信……你知道我有多爱你,你自然知道,得不到你的消息[即不寄信]对我来说,就和死亡一样。”一个女人给他寄了三十八封信。她希望有一份永恒的爱,她想象“上帝会用一个神圣的结使我们幸福,这样直到死亡都不会再被分开。我将永远忠诚。告诉我,我的爱人,你爱我,你将永远不变”。然后是瞬间的怀疑:“我应该对你的承诺有信心吗?看在上帝的份上,告诉我真相吧。”不久,他向她要钱,她犹豫着要不要给他。当他停止给她写信时,她的责备直接来自从吟游诗人到她的时代所阐述的痴迷之爱的剧本:“我对你有什么错,让你这样对待我?当你真正爱的时候是不会这样的。你一直向我承诺的是永远爱我。”
*
今天,西方世界很少有女性被父母宠爱到无法结识很多男性,她们会经历一些情事,分手,备受折磨,接着继续前进。不幸福的婚姻可以结束,人们可以找到新的伴侣或者伙伴。在这种新的氛围中,夏绿蒂和阿尔伯特的婚姻几乎不会成为离开他并与维特结婚的障碍;保尔也不会因为哀悼拒绝脱掉衣服的弗吉尼亚而日渐消瘦。那种“如果我真的爱他/她,我就会为他/她着迷”或者“如果他/她真的爱我,他/她就会为我着迷”的幻想似乎已经成为过去的遗迹。
然而,恋爱关系的破裂是自杀企图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爆发点。虽然没有用歌德式的激情语言来表达,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伴侣在恋爱关系中越投入,越有可能在关系破裂时陷入抑郁并试图自杀。一些专门研究脑化学的科学家把强烈的浪漫爱情比作物质滥用:两者都会上瘾,两者都涉及大脑的奖励通路。“最有特点的是,恋人痴迷地想着心上人。”这些科学家专注于思考恋爱成瘾的解药,结果,他们与大约两千年前盖伦提供的良方相似:即转移注意力,如保持忙碌、锻炼身体、寻找爱好等。但是,如果有些人不寻求治疗,如躺在沙发上的贝丝·戈尼克、痴迷于信件的维特、在痛苦中欢欣鼓舞的伯纳特·德·文塔多恩、落泪二十年的佩内洛普,他们的疯狂可能有一个解药:大脑的奖励系统。
《纽约客》曾经刊登了凯特·福克( Kate Folk)的短篇小说《在那里》(“Out There”)。在这篇小说中,叙述者正在寻找一位浪漫的伴侣。她尝试了一些在线约会应用程序,但她担心找到的不仅是一个变态,而且是一个“讨厌鬼”——一个机器人,一种能触摸的假象:他看起来像一个英俊的男人,很有魅力、有同理心、性能力强,一旦他得到一个女人的个人信息,就会一溜烟地消失。“讨厌鬼”受雇于俄罗斯的一家公司,“以脆弱的女性为目标”。我们的叙述者很高兴,因为她在Tinder上匹配的男人山姆有一些明显的缺陷。他并不英俊,没有什么同理心,不是很有魅力,而且性能力也不是特别强。太好了!但是,她与山姆相处的几个月都非常无聊,几个月之后,叙述者中止了这段关系。他也许不是一个“讨厌鬼”,但他不是她生命中的爱人。
过了一会儿,在金门公园散步时,她看到“五个一模一样的男人”坐在一张野餐桌旁边。其中一个男人看到了她,并且开始了一段迷人的、奉承的高谈阔论。她充满感激地和他一起坐在桌旁。一个像保尔或维特一样的完美的“讨厌鬼”满足了她的一切需要——这一点胜过了一个真正的男人。尽管他一旦拥有她所有的信息,很快就会一溜烟地消失。对于我们的叙述者来说,痴迷之爱的假象比真实的人能够给予的爱更加美好。也许对佩内洛普来说同样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