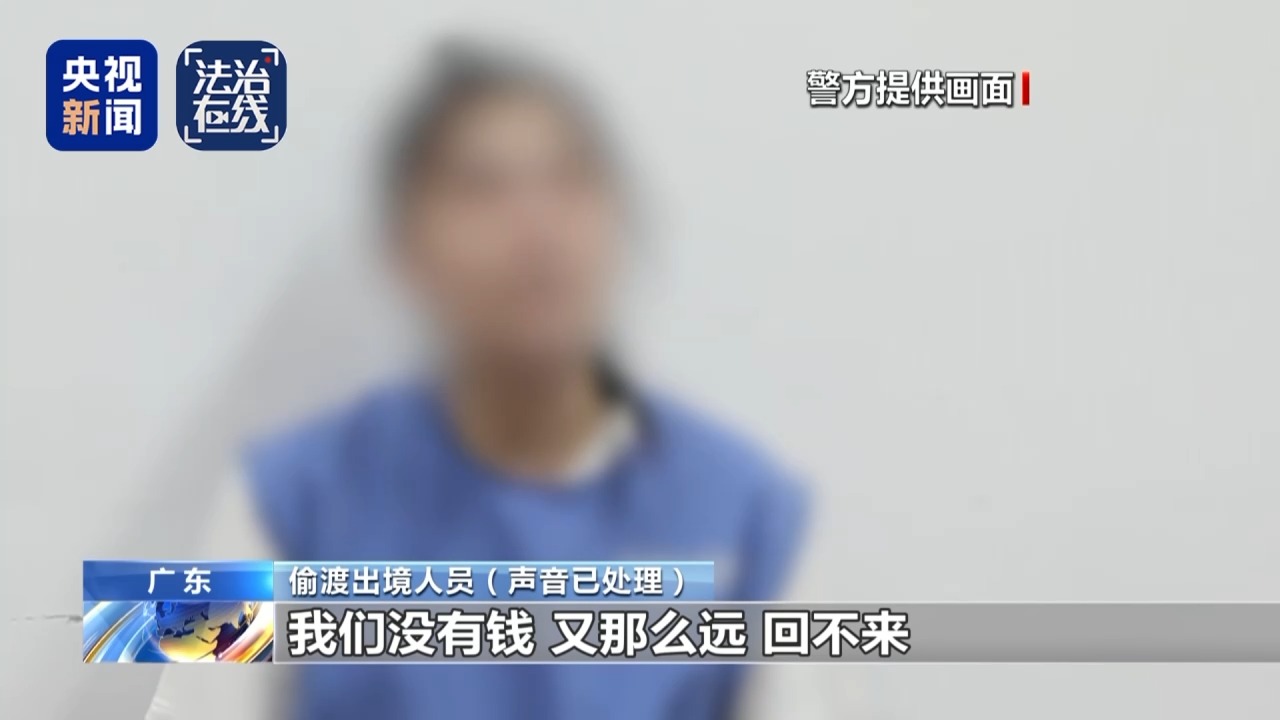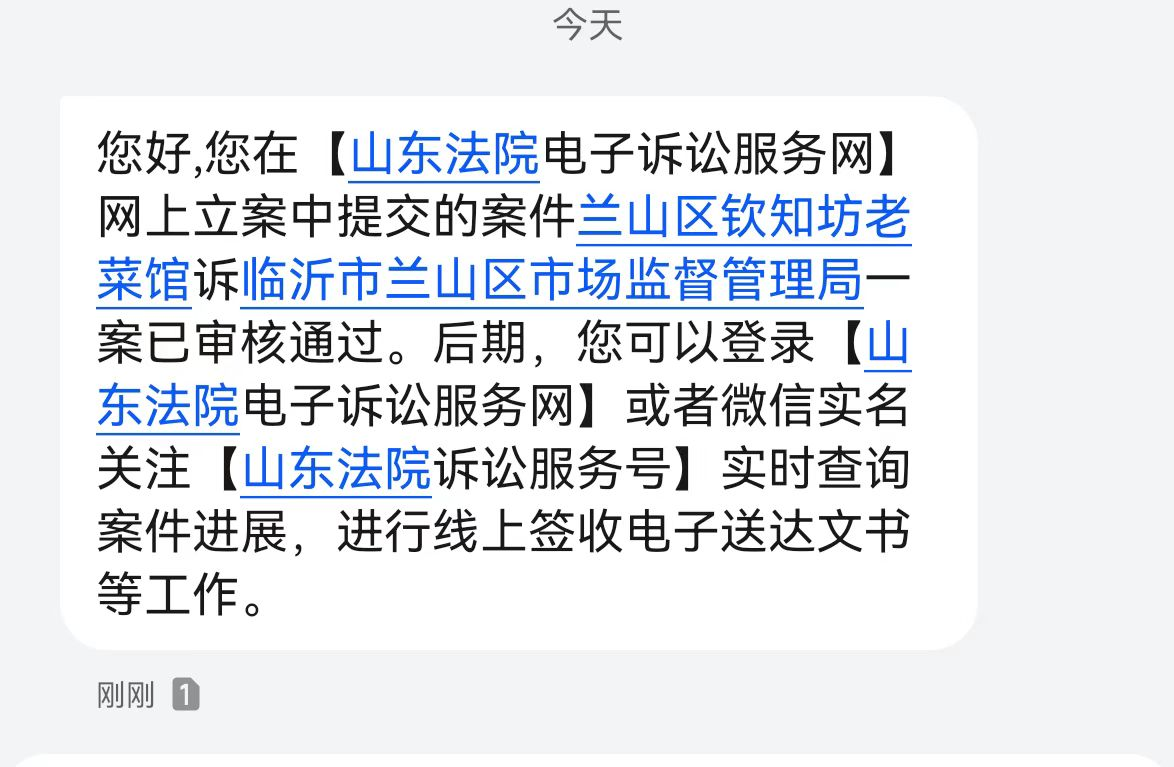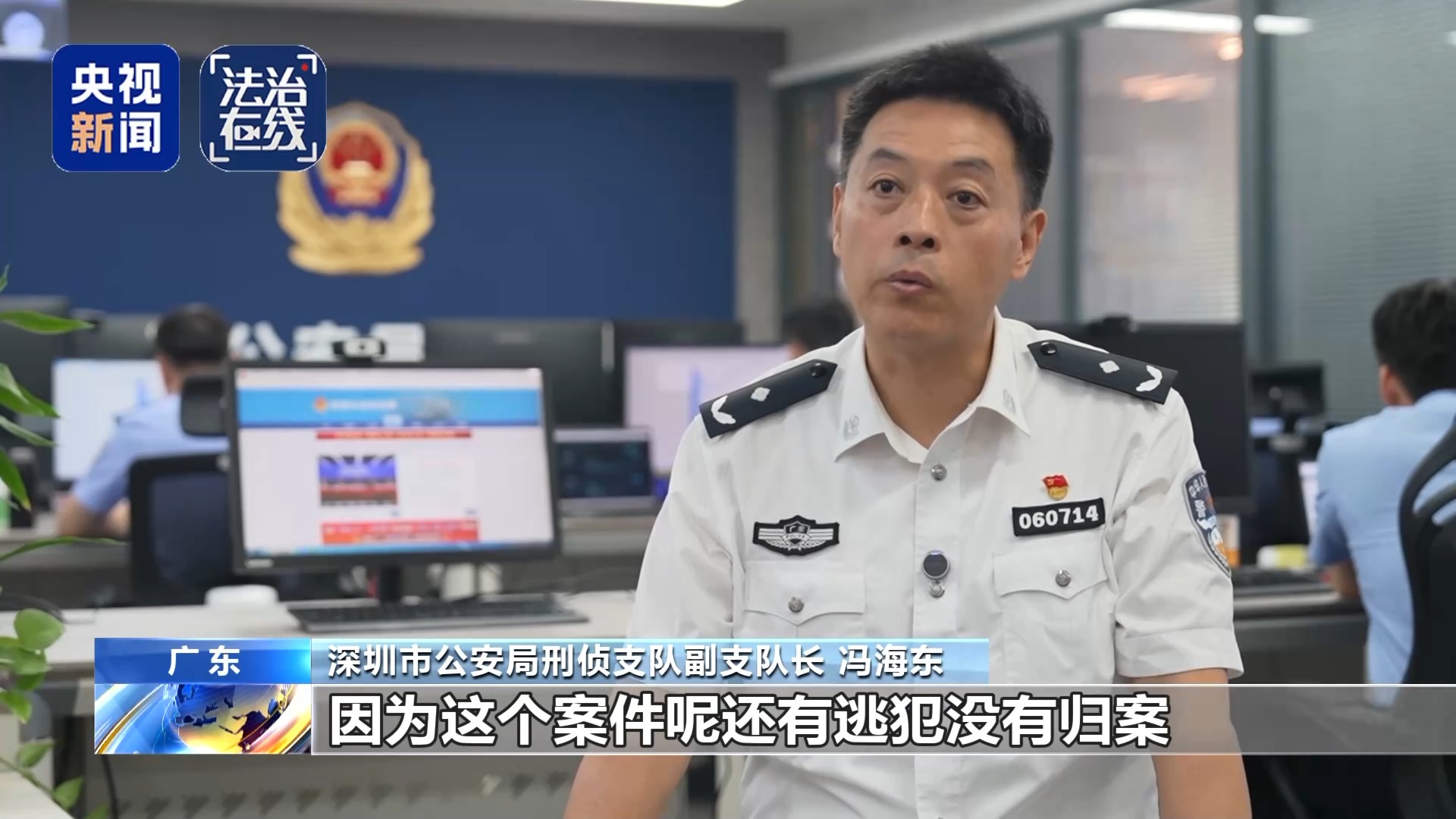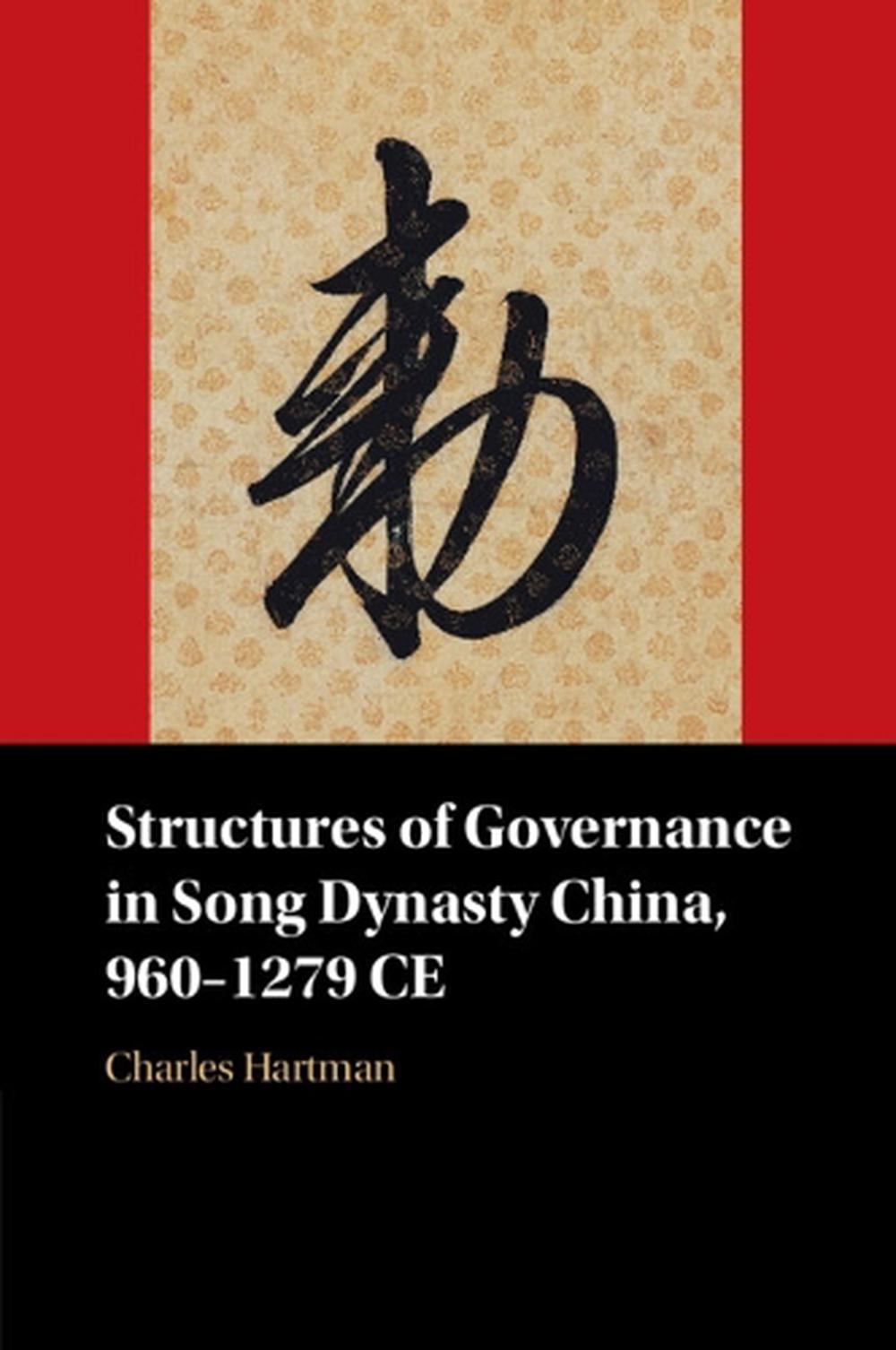殷企平:文化即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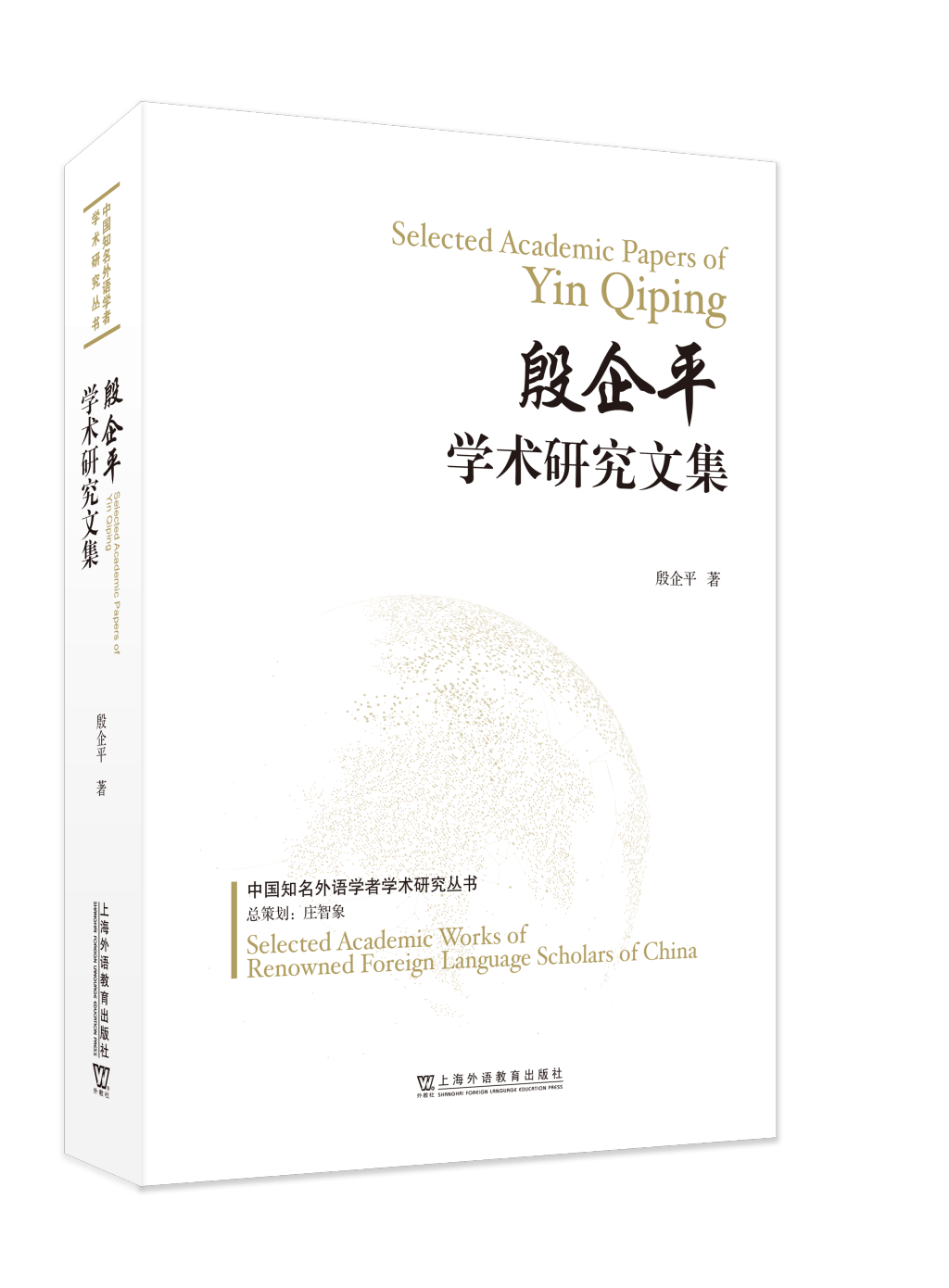
《殷企平学术研究文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
在过去的四五十年中,文化批评逐渐化身为“显学”。几乎在所有的人文、社科领域里,都能见到它的身影。
“文化批评”这一术语的重心是“文化”。更确切地说,文化批评的性质从一开始就被文化的本质规定了:文化即批判,即对“文明” 弊端的批判。“文明”弊端五花八门,体现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分裂”。早在18世纪末,弗里德里希·冯·席勒就曾指出,现代文明的特点是“无限众多但都没有生命的部分拼凑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一个机械生活的整体……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永远不能发展他本质的和谐”。针对这一特点,文化批评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即用“整体”来抗衡“分裂”。换言之,文化意味着和谐性、整体性(无论就个人的发展而言,还是就社会的发展而言),意味着对片面性、机械性和功利性的批判。真正的文化批评,其具体对象可能会不同,批评方式可能会更迭, 涉及的理论和领域可能会变换,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 它必然以反对 “分裂” 为宗旨, 反对那种使人类社会的整体性或和谐性遭受侵蚀的异化现象。
下面以文化批评史上几位杰出代表为例来说明他们都是以维护 “整体”、抗拒“分裂”为宗旨的。
阿诺德是文化批评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他在《文学与科学》一文中发表了如下论断:“科学一劳永逸地摧毁了关于世界的 ‘神秘观’,让诸多正宗的宗教变得不堪一击,因而危害了人类与周围世界的整体性。在这种情形下,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诗歌,这是因为诗歌持开放态度,它把人类所有经验都融为一体,就连古老的宗教冲动也被包含在内”。阿诺德生活在一个科学事业蒸蒸日上的年代,正当大家都在为科学进步拍手叫好(也就是在为“文明”叫好)之际,他却看到了事物的另一面:一味强调科学进步,会让人与周围世界的整体性受到危害。他写文学/诗歌与科学的关系,其实就是倡导人类社会整体性发展,反对呈“分裂”状态的单向度发展。罗斯金曾这样评论工业革命进程中大规模生产的分工方式:“分工劳动可真是伟大文明的一大发明。近来我们把它又研究并完善了一番,只不过我们给它取了一个虚假的名字。说实话,我们并不是在分工,而是在分人——人被分成了一个个片段——分解成了生命的碎片和细屑。结果,一个人的智力所剩无几,甚至不足以制造一枚别针或一颗钉子。仅仅制造针尖或钉子头就耗尽了一个人的智力”。罗斯金此处所谈,表面上跟阿诺德的上述话题风马牛不相及——罗斯金谈的是分工劳动,而阿诺德却是在谈文学和科学的关系;然而,他俩关注的问题在实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反对 “分裂”,倡导“整体”。事实上,他们所关注的“分裂”现象是多种多样的。仅以罗斯金为例:他把批评矛头指向了形形色色的“分离”,包括“思想与感受分离,时间与空间分离,肉体与灵魂分离,行动与意图分离,计划与实施分离”。这就应了我们在前文强调的观点:文化批评的具体对象可以千变万化,但是主线只有一条,即反对“分裂”。
同样的主线延续到了20世纪,这在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那里就颇具代表性。艾略特无论是在从事文学创作/批评时,还是在从事文化批评时,都十分强调“整体”和“部分”的辩证关系。说起艾略特的诗艺,许多人首先会把他作为现代主义的鼻祖,而很少有人会察觉他的灵感首先来自17世纪以及此前的诗坛,就像他在《玄学派诗人》一文中谈到的那样——他强调这一点,其实是从文化整体观出发的。在他看来,17世纪早期的英国,哪怕是一位次要诗人,也能作为文化的表率,这是因为他在那个时期发现了“人类经验的整体性”;他发现那时人的思想和情感、高贵和平凡、精神和肉体都不被看作互不相关的,因而不需要用不同的话语来加以表述。让他感到悲哀的是,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人类渐渐被不同话语——如科学话语、宗教话语、社会学话语等等——分割了,或者说正在经历一种愈演愈烈的“感受力解体”过程。正因为如此,艾略特积极倡导“整体感受力”,主张人类在认知/体验世界时应该兼收并蓄, 或以兼容并包的态度去拥抱世界(Collini2008:263)。
艾略特常常被看作新批评的先驱,这不无道理,不过他对新批评的首要影响与其说在于诗艺,不如说在于文化批评层面。英国学者斯蒂芬·科里尼曾经把艾略特的“整体感受力”和英国新批评代表人物艾弗·阿姆斯特朗·瑞恰兹的“联觉”、美国南方重农派观念中的“南方”以及利维斯的“有机共同体”相提并论,指出“它们都作为完整的形式而受到珍视,它们所对抗的是片面化、碎片化、专业化和工具化”。这一评价颇有见地,它指出上述批评家的主张和活动(实为文化批评活动)看似不同,可是都遵循了一条主线,即反对分裂,捍卫整体。须特别一提的是瑞恰兹的“联觉”——人们通常把它看作一种修辞手段,或者说一种技巧,但是科里尼指出了它的实质:联觉本身就暗示 “联通”和“联合”,因而彰显了一种整体文化观。
艾略特的文化思想尤其在弗兰克·雷蒙德·利维斯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在《共同的诉求》一书的前言中,利维斯借用了艾略特关于文学批评的定义,即“对真知灼见的共同诉求”,以此强调文学批评是一种“合作性劳动”,亦即一种体现整体性的劳动。在他的著述里,“合作性”“集体性”和“创造性”是高频词,而且常常一起出现,这跟他的文化观和语言观有很大关系。就像英国沃里克大学教授迈克尔·贝尔指出的那样:“利维斯那兼容并包的文学观、文学史观和文学批评观都以他的语言观为支撑点。……利维斯明确关心集体的创造过程,这一过程源自无数个人的努力——这些努力未经协调,但都汇入了语言,从而成为未来言说者的资源。利维斯特别强调,个人存在于语言……”这里,利维斯的整体文化观清晰地呈现在了我们面前——个人通过语言与世界实现了连接。利维斯谈语言,谈文学,然而他分明又在批判“文明”的弊端。他的如下论述对此表现得痛快淋漓:文学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因为它本身很重要,而且还因为它蕴藏着创造性的能量;后者在现代“商业化”的社会中到处都处于守势。在文学中,或许只有在文学中,一种鲜活的、创造性地运用语言的感觉仍然显而易见,这与“大众社会”里语言和传统文化的贬值和庸俗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个社会的语言质量是其成员个人和社会生活质量最有说服力的标志:一个不再珍重文学的社会是一个致命的、封闭激情的社会,而激情创造并维持了人类文明的精华。此处,利维斯把语言、文学和人类社会创造力之间的整体关系阐述得十分透彻。这一思想还贯穿于他的具体文学批评实践。例如,他在评论查尔斯·狄更斯的 《艰难时世》时,针对小说中葛擂硬先生只用“第二十号”来称呼西丝·朱浦,导致后者在慌乱中反应迟钝这一情景,做了如下鞭辟入里的分析:西丝“对教育的迟钝反应,乃是她身上那至高无上而无法根除的人性的必然流露:正是她的美德使她不能理解,也不能默认把她当作‘二十号女生’的那种时代精神,使她无法把一个人想象成一个算术上的单元”。透过这层分析,我们可以再次看到尖锐的文化批评:19世纪的英国一味追求“进步”,其代价之一就是把生活简化;西丝这个有血有肉的小女孩被简化成了一个干巴巴的数字。这样的简化,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分裂”,就是“文明”的弊端。
同样的文化批评主线在利维斯之后仍然不断地延伸, 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本文节选自《殷企平学术研究文集》之“文化批评的来龙去脉”章,文字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