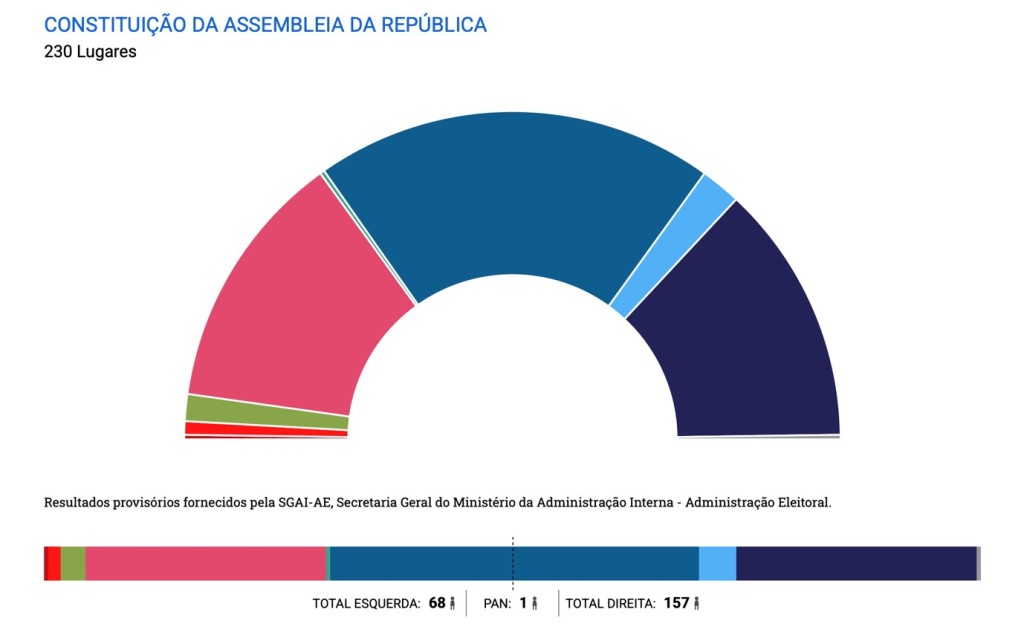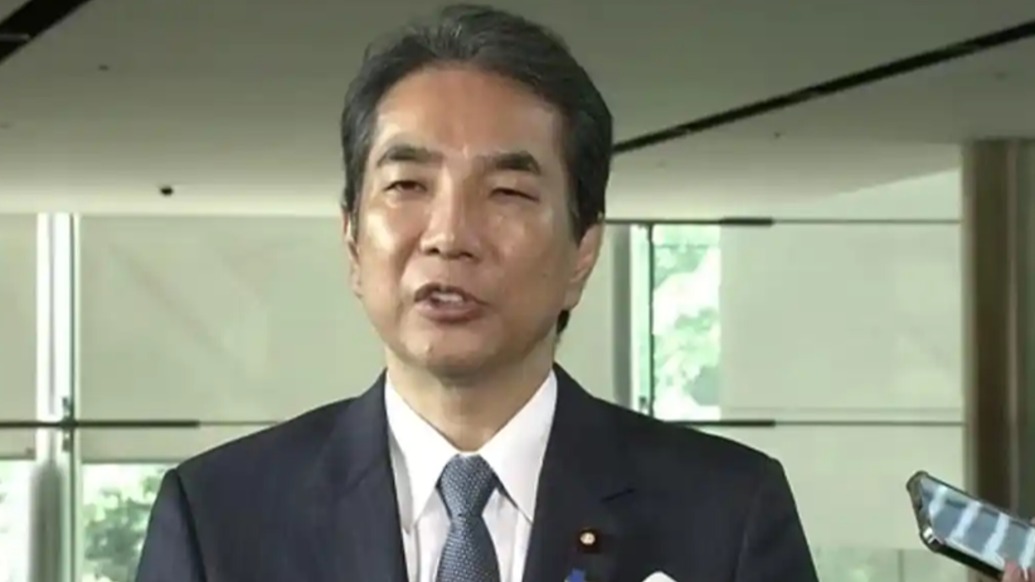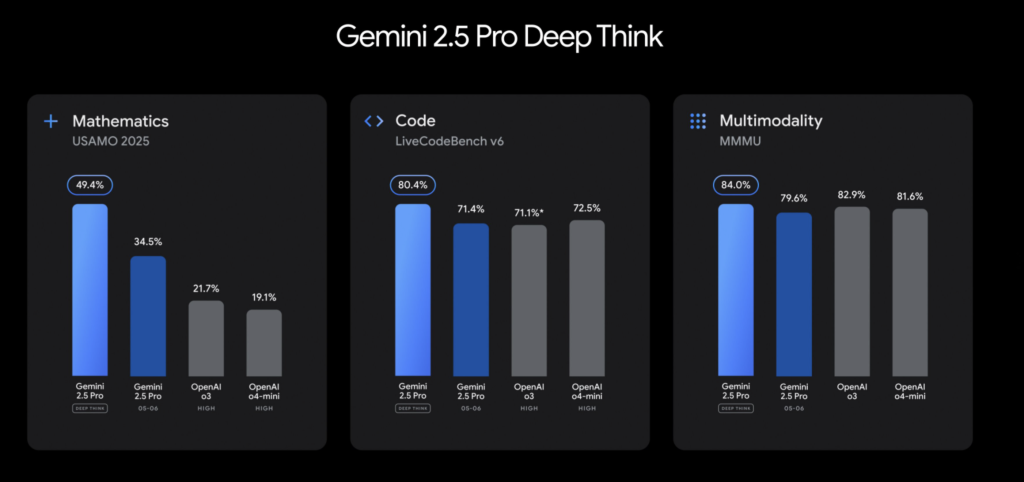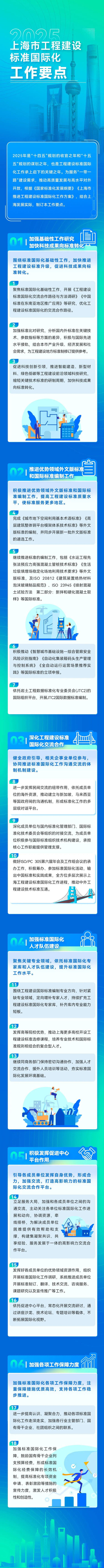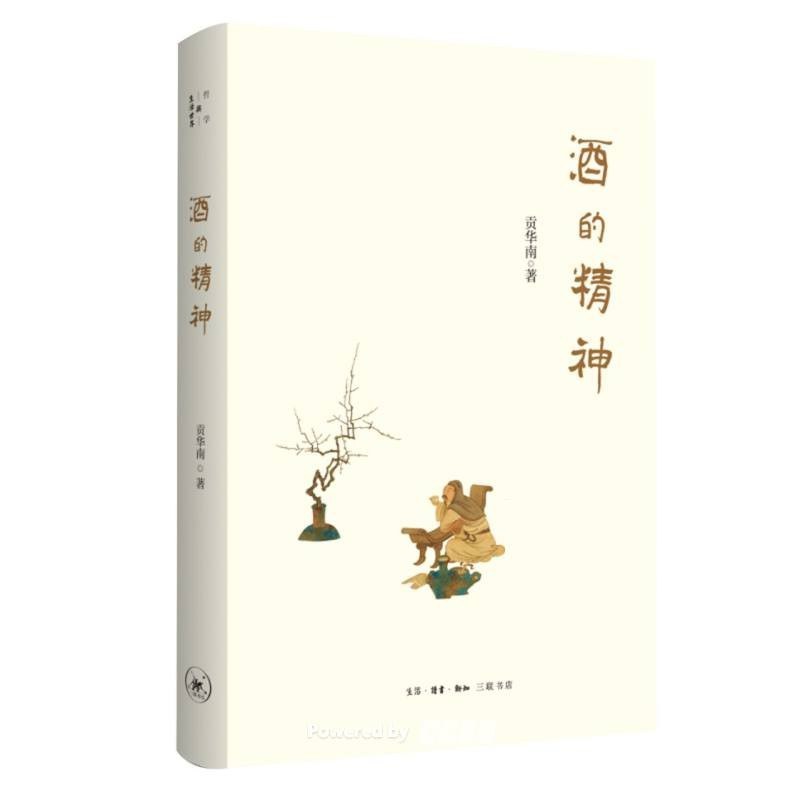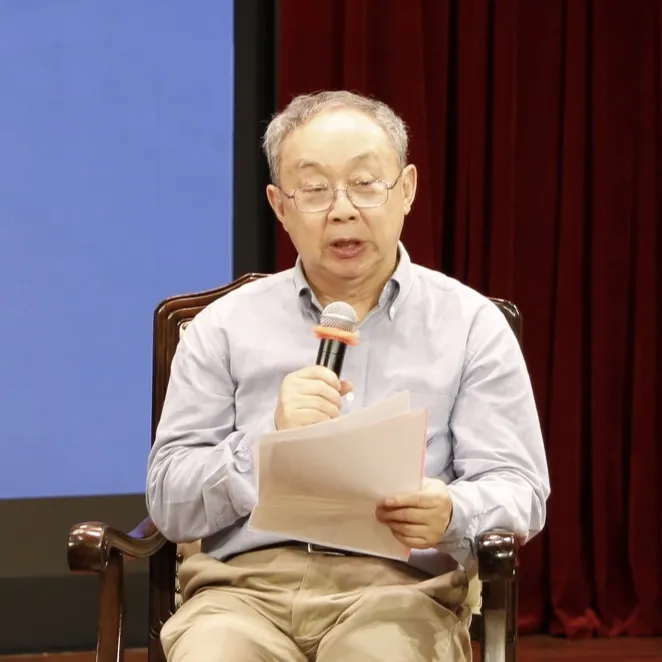王缉慈|迈向近零的产业集群需加强利益相关者合作行动
我的鄂尔多斯零碳产业园一文引起了行业内的关注,该文是偶读世界经济论坛(WEF)2025年白皮书有感而发的。最近我追溯到WEF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期间发布的产业集群转型倡议。该倡议旨在推动产业集群向净零转型。从WEF的集群地图可知,迄今世界上已有33个产业集群签署了该倡议,鄂尔多斯零碳产业园是其中之一。
解读世界经济论坛的系列报告
我大致看了WEF自2021年以来关于产业集群的系列报告,并选读了案例。读到比利时安特卫普-布鲁日港和英国东海岸这两个产业集群(后者包括亨伯ZeroCarbon Humber和蒂赛德净零集群Net Zero Teesside),我发现报告中的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范畴包括大规模重化工业集聚(industrial agglomeration)。钢铁、石化、水泥、化工等能源密集和资源依赖型产业是全球主要碳排放源,大部分净零排放项目的主要目标是使这些难以减碳的行业进行脱碳。我联想到了美国区域科学家艾萨德1959年所研究的波多黎各石化产业综合体(industrial complex),以及日本茨城县鹿岛1960年开始的综合开发规划。WEF系列报告的产业集群范畴比强调知识和创新的产业集群要宽泛得多,而后者是在1980年代中期与内生增长理论几乎同时兴起的理论。
WEF所倡议的产业集群概念的精髓,即位于同一地点的同行或跨行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的精诚合作,这与我们在《创新的空间》《园区和集群》等著述中所分析的创新集群相一致。为了加速脱碳,发展产业集群不仅可以使企业共享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共担风险,而且可以促使政府机构、碳捕获服务商和参加碳交易的工业承购商之间建立伙伴关系,而这些关系是支持大规模部署净零碳基础设施的要素。
WEF以及埃森哲(Accenture)等专业服务公司认为多家企业共栖(co-located)的“零碳集群”(或“净零碳集群”)使用可再生能源,通过专业知识的跨界合作,进行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简称CCUS)在技术和经济上是可行的。理想的状态,是在有地理边界的零碳园区里,通过碳排放监测、碳交易和碳汇管理等手段,确保碳排放量与碳吸收量达到平衡。由多个利益相关者所支持的互补性跨行业项目是最有效的,可能实现系统价值最大化。
“零碳集群方法”成功的关键
零碳园区涵盖了能源、产业、建筑、交通、物流等领域。广义地说,集群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各类企业、科研机构、金融机构、园区管委会(政府),以及社会公众等,使它们拥有共同愿景和使命是最重要的。“零碳集群方法”的成功关键在于供能、储能、用能的合作伙伴在技术和业务目标上的一致性,包括同步系统和开放数据等。
根据我对创新集群的研究,理解产业集群促进技术创新的要点,是将当代复杂技术的创新看作社会过程,把创新集群或创新型集群视作基于诚信的创新社区。同理,脱碳和减碳也是社会过程,而不是纯技术的过程。因此,用产业集群理念建设起来的零碳园区也需要“集群发展促进组织”这类非政府的、非营利性的第三方组织,除本地的正式交易活动之外,还需要非正式的面对面的知识交流。
天津泰达低碳经济促进中心的公众号“绿盟”推出了十篇“零碳园区建设指南系列”文章,包括一些案例。其中第二篇说得好:实现园区的净零碳排放是一项高度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克服技术、经济、制度、社会等多维度挑战。零碳转型的本质是技术-经济-社会系统的重构,需突破路径依赖、打破利益壁垒,通过多方协同实现从“高碳惯性”到“零碳韧性”的跨越。
大型零碳集群项目面临着挑战
然而,在国际上有些大型零碳集群项目在实际运作中明显存在问题,既包括利益相关者的不协作,也包括攻克CCUS技术的困难,这些问题需要引起中国零碳园区的实践者注意。例如英国的亨伯产业集群(HICP)项目,项目时间跨度长,前期资金投入大,失败的风险高。《能源研究与社会科学》2023年的一篇文章从社会技术系统的视角,调研了英国亨伯这个雄心勃勃的巨型净零项目实施情况,发现该项目的策略与多方面业务的现实不一致。另外,根据多家外媒报道,英国财政部将在2025年的支出审查(Spending Review)中对CCUS项目展开更严格的审视,部分项目或面临资金削减。
2024年1月WEF发布了新的《转型产业集群年度报告》,介绍了已签署2021年产业集群转型倡议的20个集群的经验,提出需要解决包括伙伴关系、政策、融资和技术的关键问题。
中国将产业园区作为脱碳的核心单元
将产业园区作为脱碳的核心单元已成为中国的共识。产业园区在中国不计其数,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全国产业园区超7.8万个,中研普华的数据是国家级和省级产业园区2543家。
2022年生态环境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2024年生态环境部公布了第一批城市和产业园区试点名单,包括43个产业园区,涉及钢铁、有色、石化、汽车、装备制造、新能源等多个行业。我注意到在方案和试点任务中,“协同”二字特别突出,例如探索协同减排技术路径、协同创新管理体系、基础设施协同模式、重点行业协同试点等。各个试点园区因地制宜采取了减污降碳的方法,例如合肥高新区实施工业企业碳积分制度;广西玉林龙潭产业园推动钢铁、锂电池原材料等重点污染源的提标改造;上海嘉定氢能港入围上海零碳园区,嘉昆太三地建立“双碳”联动工作机制等等。
2025年伊始,中国的净零碳或零碳园区迎来建设潮。零碳产业园千差万别,例如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与内蒙古的鄂尔多斯蒙苏经济开发区零碳产业园的脱碳途径就大不相同。前者是石化新材料产业集群,由碳排放企业海南石化与构建电网和储能设施的清洁能源企业合作,探索“绿电直供方案”;后者是清洁能源产业集群,以远景动力等10家新能源头部企业为核心,探索采煤沉陷区绿色转型。石化新材料产业集群的案例还有广东湛江巴斯夫、惠州大亚湾石化区等,清洁能源产业集群还有广东(阳江)绿能示范产业园、江苏盐城射阳港零碳产业园等。
关于园区和集群的再思考
在中国,关于产业园区的媒体报道和论文有很多是涉及产业集群的,不过,有的将集群作为园区的代名词,有的则用“集群化”或“集群式”表示园区招商的模式。关于园区和集群我曾经发表过很多论文。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还要对这两个概念再议一下。
产业园区指的是“地”,即经过战略规划而开发的有地理边界的一块土地,它通过提供交通设施和其他必要的公共设施来吸引企业,促进产业发展。产业集群涉及人,即一群利益相关组织,包括处于同行业或者虽然跨行业但是具有产业联系的企业,以及政府、研究机构、金融机构等,这些组织集聚在一地,可能位于园区内。所谓“集群化”或“集群式”的思维通常只是把产业上下游企业布局在园区内,而较少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合作行动。有鉴于此,我再次强调产业集群及其利益相关者合作行动的重要性。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肩负着实现碳达峰目标的艰巨任务,任重道远。聚焦于产业园区,以产业集群理念,加强利益相关者的精诚合作,不但能加速实现碳达峰,而且可以在推动全球脱碳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
王缉慈,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经济地理学教授,持续关注国内外产业园区和创新集群。本专栏以园区之思为主题,求索园区的初衷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