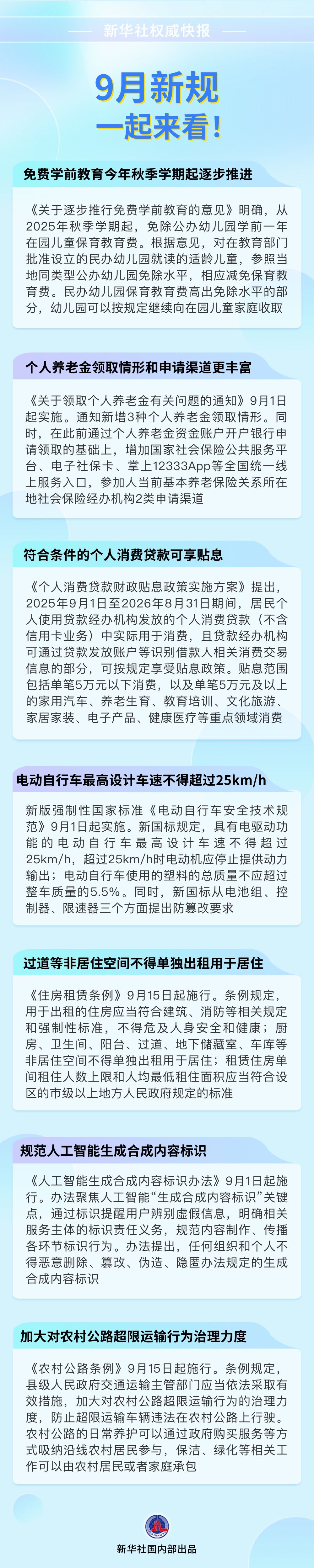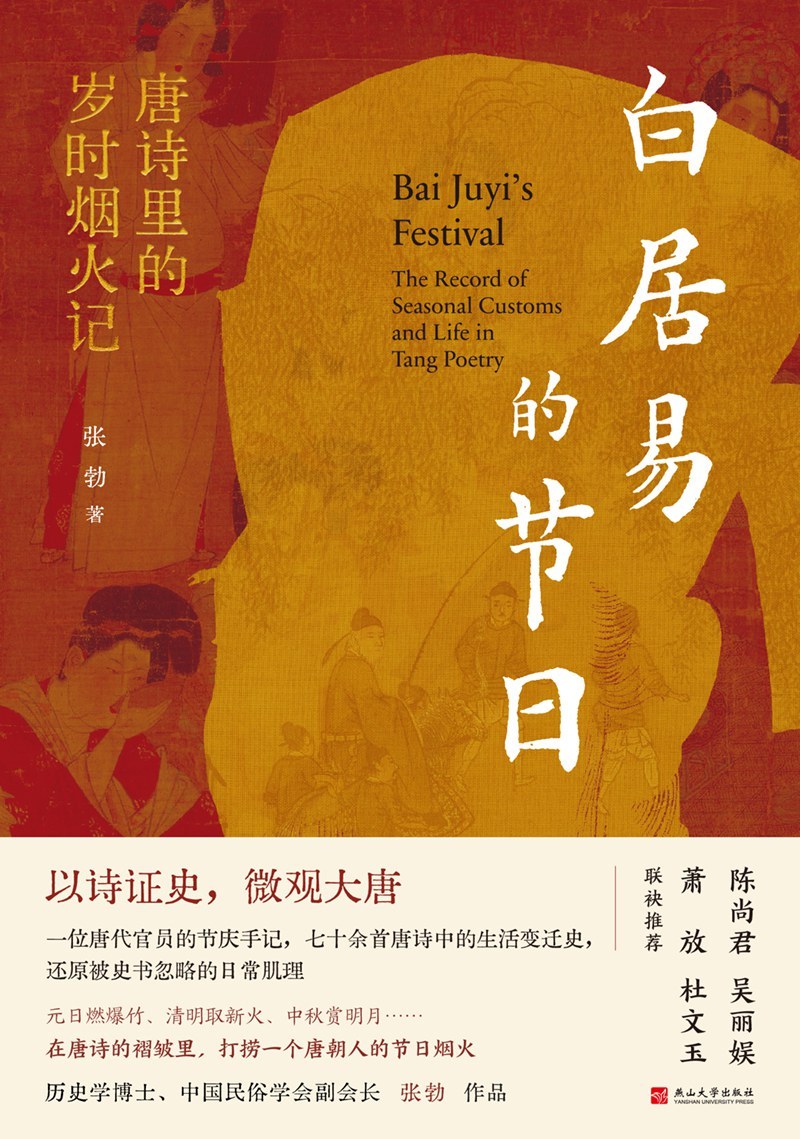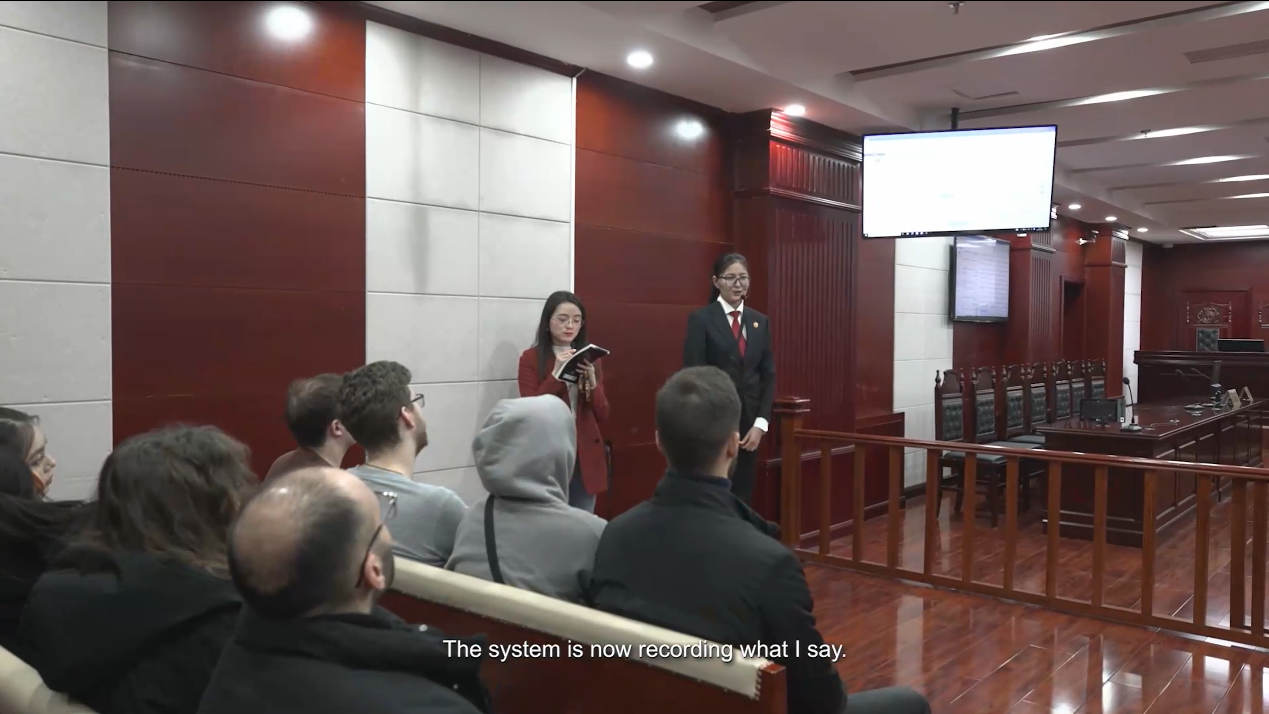《平遥话》:以方言保存文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平遥古城为:“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它保存了其所有特征,而且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
在相对静态的历史遗存中发掘活态的文化,也成为关于古城、关于历史遗迹的写作的重要课题。近日,作家出版社推出了刘伟波以平遥为主题写作的小说《平遥话》,并举办了新书发布会。

提起平遥,大家的目光总会被晋商辉煌的历史所吸引,而近几十年来,晋商也成为山西作家笔下的重要题材,《白银谷》《乔家大院》《立秋》等许多描写晋商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早已深入人心。但是在《平遥话》中,作者并未着眼于晋商鼎盛时期的票号财东、大掌柜,而是描绘了一个15岁时误打误撞来到平遥城闯荡的孤儿——刘。这个孤儿因缘际会赚了些小钱,充其量不过是略有成就的小商人,他在商海中的无奈与挣扎被充分展现,这种“怀揣梦想却只能拼力苟存”的遭遇在近些年的写作谱系中,似乎更能够引发读者共情。

8月13日,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视觉中国 图
在时代的选择上,《平遥话》也以民国初年到改革开放的近百年历史为时代背景,融合了古城的历史与民俗风物。
作者作为山西人,关于平遥的历史风物,有许多“独家揭秘”,比如写到驰名久远的平遥牛肉,刘伟波写:“平遥牛肉原本是骆驼肉。南来北往的商路上,奔走的是山西商人,运送物资的,是一长串一长串的驼队。……每年都得处理大量退役的老骆驼,更别说骆驼本身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的特产。不是中原的物产,骆驼肉也不好吃,纤维粗,咬不动,尤其是老骆驼。聪明的平遥人,就在做法上想办法,把杀好的骆驼肉先腌起来,腌好几天,再卤再煮,就好吃了。色泽红润,绵香可口。骆驼肉不好卖,谎称牛肉,久而久之,竟成特产。”
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认为,《平遥话》这样的小说,是文化小说、家族小说与方言体小说的融合体。作为文化小说,延续了文化寻根传统,但不同于外来者视角,作者生于斯长于斯,书写更具身份真实感。作为家族小说,它跨越百年,以轻喜剧笔调缓解悲剧命运的沉重。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也是文学作品的生命所在。《平遥话》中,作者刘伟波大量运用平遥古城的方言土话,还以方言词汇作为章节标题,这成为小说最大的特色。作者也从大量经史典籍中考证方言俚语的出处,并广泛与东北话、山东话、四川话、客家话、苏州话、西安话等各地方言词汇进行对比、关联。研讨会中,嘉宾们认为,这一突出的特点,对乡土文学、方言文学乃至农村题材、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鲜的探索。章节结构上,以俚语词汇作为作品的经纬架构,形式也很独特新颖。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吴义勤也关注到,小说以平遥方言为叙事经纬,将一个小商人的命运嵌入近百年的历史进程,在方言土语的韵律中,折射出个体生命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坚守。
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亚丽认为,《平遥话》对平遥方言的巧妙运用以及对普通人物命运的细腻刻画,是作者对故乡的深情与对历史的敬畏。小说用一个晋商小人物的命运轨迹,编织起中国现代史的微观图谱。评论家赵学文认为《平遥话》最大的特点是书写乡愁,方言是这部小说的灵魂所在。作品通过描述平遥的民俗、建筑和家族故事等细节,是作者对家乡的深厚情感。

作者刘伟波在现场分享了回应,小说中很多情节和人物都源于他对家乡的真实记忆和走访,这些鲜活的素材给予小说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情感,“我也想通过刘元这一人物形象,把平遥人的精神世界和历史变迁表现出来。同时也让方言这一传统语言形式在文学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刘伟波谈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