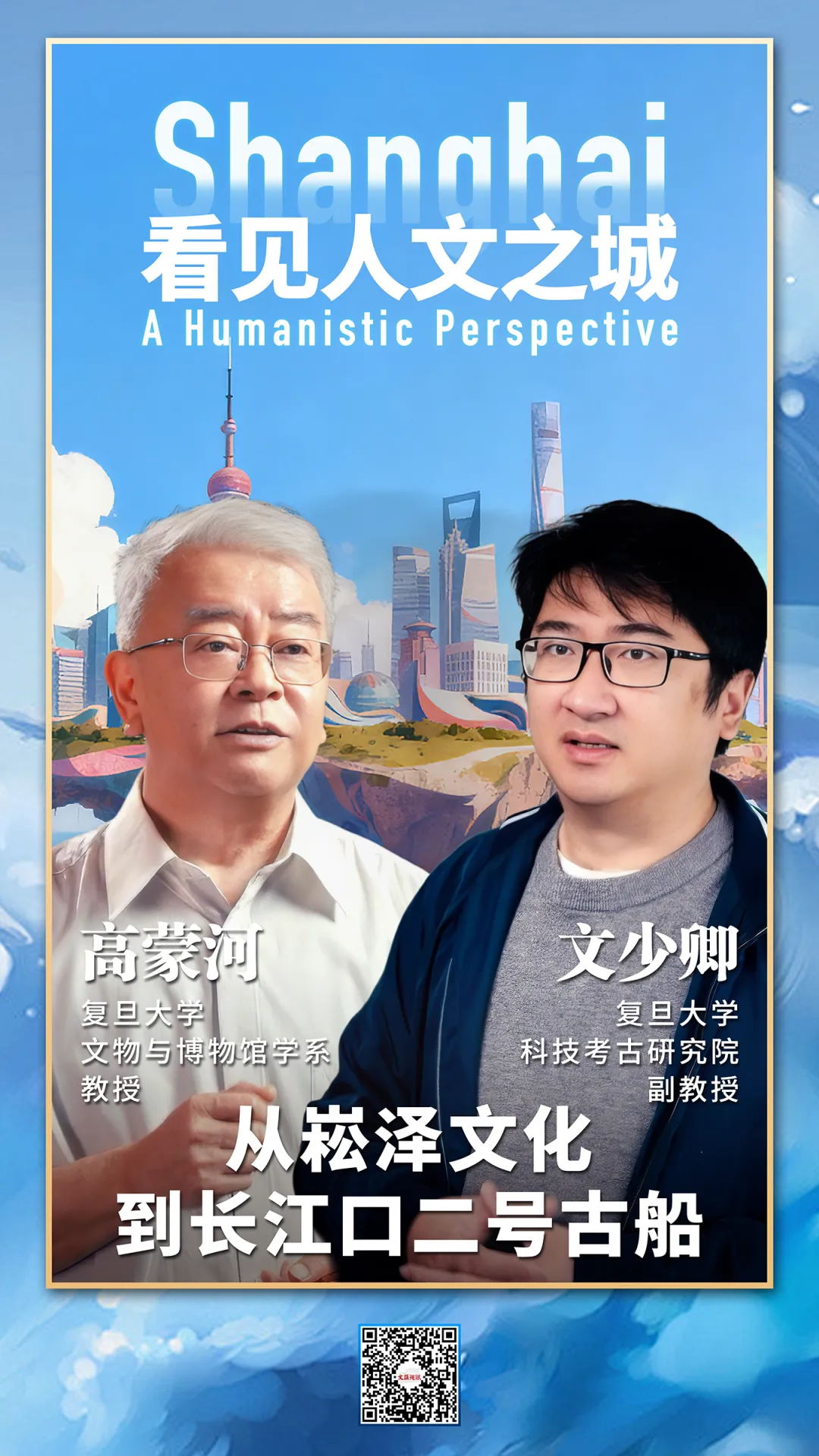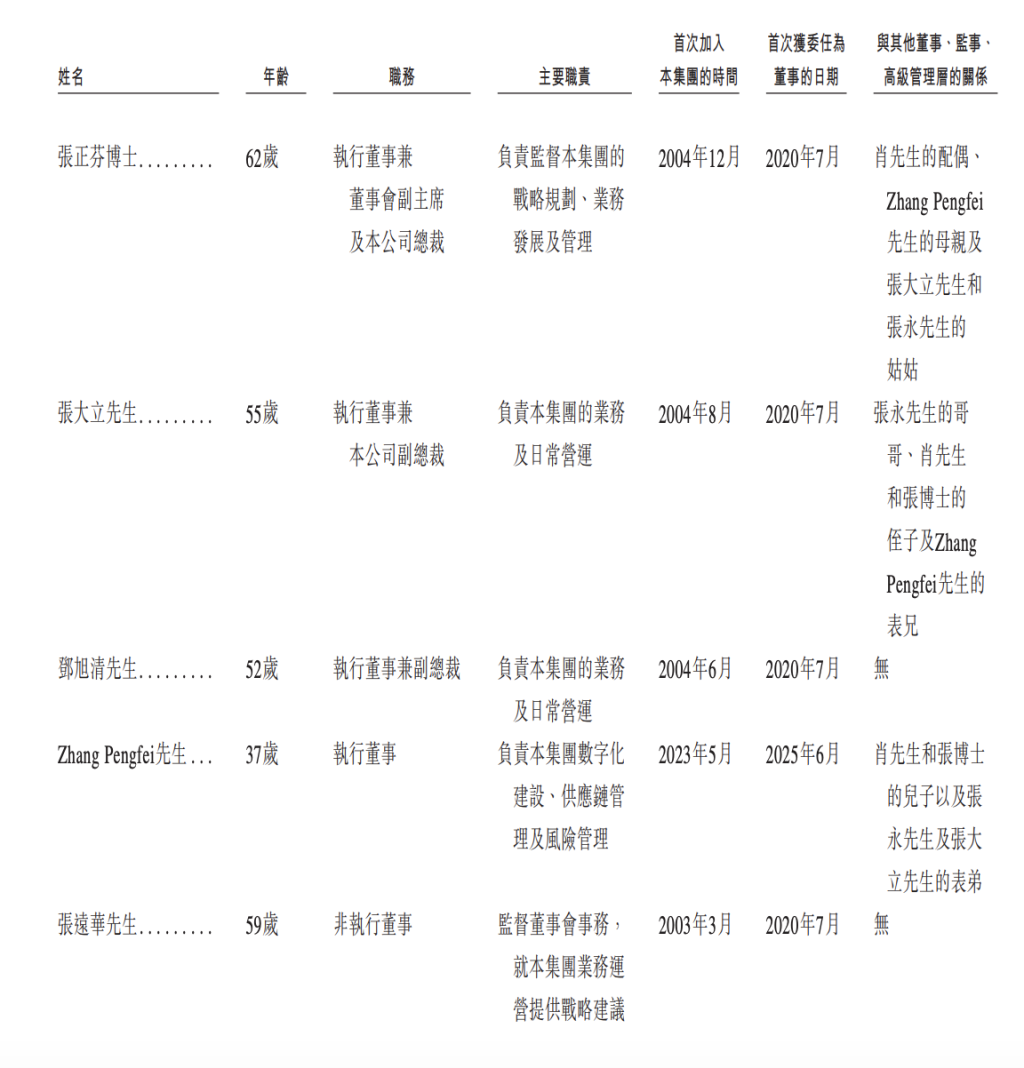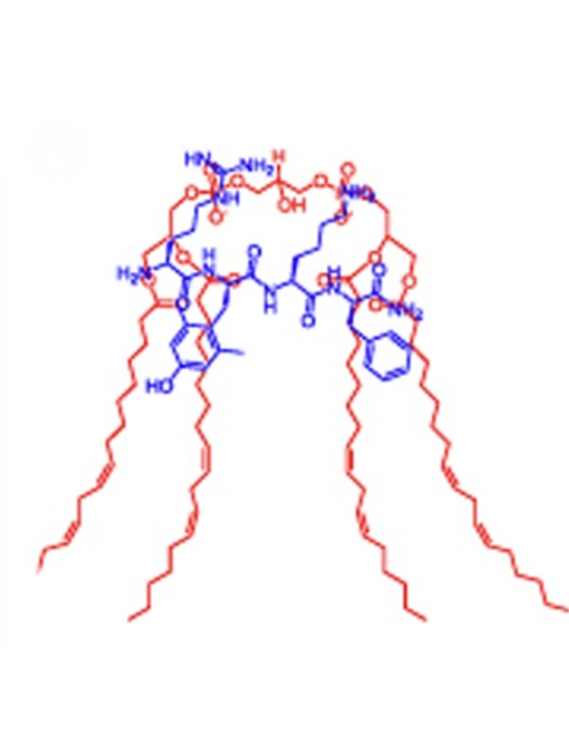钱雪松读《“更好”有多好》|人类增强计划:“更好”是个好目标?

《“更好”有多好?理解人类增强计划》,[德]迈克尔·豪斯凯勒著,钱雪松译,2025年5月出版,266页,80.00元
在技术议题上,“更好”是个好目标吗?
答案似乎不言而喻:就技术而言,“更好”当然是个好目标,而且要比“好”更值得追求。在我们通常的观念中,好和更好是依次递进的关系——更好要“优于”好(better than well)。因此,只要存在更好的方案或产品,甚至只是现实的技术可能性,选择“更好”就永远是理所当然的最优方案。
这正是晚近人类增强技术的众多倡导者心目中支持各类增强计划的核心理据所在。晚近增强技术的坚定拥护者在谈论“人类增强”(human enhancement)一词时,所表达的不仅是对技术能强化人的各种特定能力的乐观自信,他们真正为之欢呼雀跃的,是技术能让我们实现人类整体或“人之为人”本身的巨大提升这样一种可能性前景。
但在商务今年出版的《“更好”有多好?理解人类增强计划》(Better Humans? Understanding the Enhancement Project)一书中,哲学家迈克尔·豪斯凯勒(Michael Hauskeller)却对这样一个极其合乎我们直觉的回答提出了挑战。
在我看来,作者豪斯凯勒拥有一种对于哲学写作重要却在哲学家中颇为稀缺的能力,那就是他十分擅长运用综合性的视角,辅之以清晰、有趣又不失深度的语言风格,去谈论那些重要、复杂且能激发人们极大好奇心的哲学问题。因此,不论专业领域的学者还是非专业的普罗大众,往往都能从他的作品中获益匪浅,比如这本《“更好”有多好?理解人类增强计划》。在豪斯凯勒探讨人类增强的众多作品中,这本书出版时间最早,影响也最为深远。自2013年问世以来,它便引发了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全书聚焦于当前方兴未艾又充满争议的人类增强技术,对在认知、道德、医药、身心乃至容貌等领域发展迅猛的增强技术及其方案,以及心识上传、激进延寿、虚拟永生、人类赛博格化乃至人与技术之关系等前沿议题均一一探讨。人文关怀和哲学深度兼而有之,读来饶有趣味,又深受启发。
《“更好”有多好?理解人类增强计划》这部著作共十一章——头尾两章分别是“绪论”和“结语”,第二至九章分别对不同领域的人类增强方案做了分门别类的讨论,第十章“在此世安居”则从整体对人类增强方案加以批判性之反思。豪斯凯勒力求以哲学家的犀利思考和敏锐眼光深挖那些潜藏于各类增强计划底层且未经充分省思的思想观念,特别是晚近超人类主义者所推崇的以下主张——我们“应当”充分开发和运用一切人类增强技术以打造“更好的人”(Better Humans)!这一价值主张构成了隐含在各种增强计划中的深层动机和潜在意图。
“更好的人”这个说法看似简单,实际上包含了各类人类增强计划中最核心的两个关键词——“更好”(“增强”)和“人”。豪斯凯勒的核心关切正是此类增强计划对“人”和“增强”所做的可疑“联姻”。在他看来,这种联姻的背后隐含了一种他和桑德尔等学者所说的“普罗米修斯式的雄心壮志”,即寄希望于科技发展来“掌控一切”,从而实现人类整体的一种“更好”的存在方式。而豪斯凯勒在这本书里要告诉我们的正是,这种关于人类增强的思想方案和美好图景实际上是成问题的,其根本问题就隐藏在增强计划对“更好”和“人”的理解之中。由此看来,全书最核心的章节当属第十章和第五章,因为它们正好对应着“更好”和“人”这两大关键词。简言之,第十章从整体上批判性地反思了人类增强方案追求“更好”这一目标的优劣得失,第五章则对超人类主义者对“人”的根本预设提出质疑。
先看各类增强技术方案对“人”的理解。在这些方案中,有一类对人的理解表现得最为突出也最为激进,那就是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顾名思义,超人类主义的目标就是要打造“超人类”(transhuman)。按照博斯特洛姆(Nick Bostrom)的界定,所谓超人类,就是“至少有一种通用的核心能力极大地超出当前任何人类在不借助新技术手段的前提下所能达到的最大值的存在”(22-23页)。换言之,超人类就是比目前所有人都要“好”太多的人类。
超人类主义者对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福山(Francis Fukuyama)和凯斯(Leon Kass)等对增强技术持批判态度或保留意见的学者的一个常见批评,就是认为后者之所以不赞成增强技术,是因为他们相信人类内在有一些自然天性(nature)对“人之为人”而言是本质性的,因而人不仅应珍视这些天性,而且有责任保留跟这些天性相关的一切。这跟超人类主义者对于掌控的态度以及随自己心意重塑自然的“普罗米修斯式的雄心壮志”形成了鲜明对照。超人类主义者之所以认为我们可以随己心意去改造自然以打造更好的人,一个重要的理据正是他们并不认为人身上有何特性(自然天性)可视为“人之为人”的本质,因而也并不认为有何特性是人“应该”且“有责任”加以维护的。相反,在超人类主义者看来,“自然束缚着我们:为我们的渴求设定了边界。简言之,自然是敌非友。”(78页)
但是,豪斯凯勒敏锐地意识到,超人类主义者对“人”的理解实质上存在某种不一致。因为当超人类主义者为自己的激进方案提供辩护时,他们也同样诉诸了自然天性的概念,只不过他们的理解不同于他们的对手而已。假如我们问超人类主义者,为什么认为人应该努力追求“激进的自我变革”?他们的回答往往相当于在说“这是我们的天性,我们应忠于自己的天性”(79页)。如著名的超人类主义者马克斯·莫尔(Max More)认为,如果我们不能不断前进,就是“对内在于生命和意识中的那股原动力的背叛”(79页);另一位超人类主义者朱利安·萨乌列斯库(Julian Savulescu)则声称:“选择变得更好,实乃人之天性”(80页)。这些都并非纯粹描述性的表达,而是跟桑德尔、福山等人类似,表达了他们对人类天性的某种规范性论断,只不过指向相反的方向,即:如果我们要忠于自身,要成为“真正的人”,我们就必须“赞同、捍卫、促进”和“使用”“一切通用的、涉及生活方方面面的增强技术”(81页)。
换言之,超人类主义者并非不对人性作任何预设,他们只是预设了一套跟传统或其对手很不一样的人性概念,并将之体现在“超人类”的理想图景中。豪斯凯勒甚至认为:“一切激进的人类增强的拥护者都含蓄地诉诸人性概念”(85页)。因此,超人类主义者在对人的理解上多少有点言行不一。他们一方面否认人是一种拥有自然天性的存在,或认为就算这种天性存在,也没有任何规范性意义可言;但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却频繁倚赖某种对人性的含蓄理解以把握人类繁荣的观念,并主张我们有促成这一观念的道德责任”(87页)。
在豪斯凯勒看来,超人类主义者最根本的问题并不是他们设想的各种技术前景过于超前以至于无法实现,而是在于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主张的“超人类”概念中所预设的人性概念依然跟其对手一样,也是一种规范性的价值主张,从而以为自身立场“天然地”占据着某种优越地位。实际上,若真不预设任何人性概念,也不存在一套关于人“应是何存在”又“应如何存在”的规范性主张,超人类主义者就不可能有任何客观的理据可据以判定何种变化或提升才“更人性”,因而对人本身也“更好”。

桑德尔著《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
至于另一个关键词“更好”也不见得更好把握。豪斯凯勒在第十章对此做了精彩而深入的探讨。他同意桑德尔在《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The Case against Perfection: Ethics in the Age of Genetic Engineering)中的主张——我们并非自身命运和禀赋的真正“作者”,因而并不天然地对这一切享有完全的处置权。进而,他还对桑德尔的“礼物”(gift)概念和单纯的“被给予之物”的差异做出了辨析。豪斯凯勒认为,“任何实际上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好事,都会被体验为是一种礼物”(170页)。虽然礼物都是被给予的,但并非所有被给予之物皆可冠以“礼物”之名。豪斯凯勒对礼物概念的刻画涉及多个角度,其中最切要的是以下两点:首先,礼物不只是“被给予”之物,它还作为一种善给到我们(168页);其次,“礼物是无法要求而来的,也无法由习得或赚取而获得”,更重要的,它也并非“一个人原本就应得或配得的”。据此,一旦我们生命中获得了某种天赋之礼物,对此心怀感恩并予以回报就是自然而然的事(169页)。
但是,人类增强技术的强势介入,将破坏我们身上的这一“礼物”之维。如前所说,人类增强的拥护者不仅希望借助技术掌控一切,还坚信我们能利用这些技术让人自身不断变得更好。桑德尔将这类对技术追求的理解视为一种“能动性的僭越使用”(Hyperagency),即“一种对包括人性在内的自然天性加以重塑的普罗米修斯式的雄心壮志,以此让自然天性服务于我们的目的并满足我们的欲求”(164页)。豪斯凯勒指出,正是这样一种对“更好”的技术追求将消解人类自身禀赋的“礼物”维度,进而也让我们失去了对自身“天赋特质”(giftedness)的感受力和感恩之心。这样一种僭越之举使得增强计划的坚定支持者不再将人身上的禀赋以及由此而来的个人命运视作具有内在之善的“礼物”,反倒成了永远有待攻克的“课题”。这一转变所带来的影响是隐微而深远的:“失去了对天赋特质的感受力,我们并不会变坏;但我们会变得贫乏;我们会失去一些很重要、甚至对于过一种美好的人类生活来说本质性的东西。”(180页)
豪斯凯勒指出,让人类“变得贫乏”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对“更好”的无止境追求会导致人自身价值的“概念贬值”:
在此,被给予我们之物,其价值被视作是一种康德意义上的绝对价值,也就是说,一种不允许用于比较的价值。它并不只是因为更好缺席了,或跟更差的相比才成其为好。倒不如说,它本身就是好的,绝对的好。更好之所以是好的敌人,是因为当好跟“更好”相对峙,这个好就会改变其面貌,变成了“更差”才再度出场。当视线集中在我们有可能获得的更好时,我们往往就会忘记我们已经拥有之物的好。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概念上的贬值。(175-176页)
显然,这里的“被给予我们之物”主要特指作为“礼物”而“实际上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好事”。各类增强方案对“更好”的追求之所以会引发人的概念贬值,是因为这类方案通常隐含一种技术“幻觉”,即坚信对“更好”的技术追求最终必定能让人完全掌控一切“被给予”之物。然而,当我们的视线不断从当下事物转向可能出现的更好之物时,当下事物中一切的好都会不自觉地转变为仅仅是“相对的好”,即仅相对于此前“没那么好”而言的好;进而,相对于未来的更好,这样的好也会立刻变得“没那么好”(即比未来的好要更差)。换言之,一切的好和更好都是在相对性的比较中方能安立。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重要后果则是,我们会认为一切的好和更好都是人类能够获得也应当获得的。于是,人原本对给到自身的一切福祉(如自然禀赋和生命中的大小“确幸”)所怀有的感恩之心和回报之情也很可能随之消逝,取而代之的是那种力求掌控一切、改变一切的普罗米修斯式的野心——或说僭越。豪斯凯勒认为,这一转变甚至会摧毁我们每个人与所在的共同体和世界之间的“一体感”,从而让人在宇宙中变得愈发孤独(第十章)。因此,这一技术视线上的转向看似轻描淡写,但影响却极其深远甚至不可逆转。
由此反观“更好的人”这一观念,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豪斯凯勒在结语部分对人类增强方案所作的总体评价了:
这个方案的主要问题并非人类增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而是在于,我们对于人类增强实际上到底包含什么缺乏清晰的了解,同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的这种缺乏。如果我们将人类增强理解为对人之为人的增强,这样一种人类增强是不存在的。……从逻辑的意义看,人类增强并不存在。(185-186页)
行文至此,我不禁联想起影片《海上钢琴师》中的著名片段。在影片末尾,终其一生没有离开过那艘豪华巨轮的男主角,在船已废弃并即将被炸毁之际,向曾在船上一同演出过的小提琴手说出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你知道,钢琴只有八十八个键,随便什么琴都一样。它们不是无限的。你才是无限的!在琴键上制作出的音乐是无限的!……然而,如果琴键是无限的,那么那架琴上就再没有你能弹奏的音乐。你坐错了地方,那是上帝的钢琴。
这番点睛之笔向我们呈现了一个与人性(或许也与现代性)有关的深刻隐喻:人自身的确充满无限的可能,但这种内在于人的无限只有在弹奏“有限的”琴键时才有可能实现。

电影《海上钢琴师》剧照
在我看来,这个隐喻跟豪斯凯勒对增强计划的批评颇有共通之处。当技术向善论者极力主张,对“更好”的不断追求将开启人与技术之间更加丰富的可能性道路时,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开启是以对人与自然的单向度理解为代价的。本书给我的重要启发正是:仅从相对的好出发不断追求技术上可能出现的“更好”,我们永远不可能达成人本身的内在之善;相反,它很可能导致人对自身内在之善的“失落”。但在我看来,恰恰是这种内在之善,构成了人通往“无限”之所托。由此视角观之,我们可以说,以对“更好”的技术追求为目标,“止于至善”将不再可能。当超人类主义者力求将人置于仿佛“没有尽头”的技术迭代中时,人就像被抛掷到了一架琴键无限延伸的钢琴之上,但那是“上帝的钢琴”!很有可能,人在其上不仅再也找不到能弹奏的曲目,更会失落那原本让自身与宇宙之实在相贯通的无限性道路!就此而言,人类增强技术所带来的“更好”并不等同于人本身的好(善),它甚至会成为后一种好(善)的对立面——“更好”的确是好(善)的敌人!
不过,作者批判人类增强的核心观点与理论依据虽集中体现在第5、10两章,但并不意味着其他章节无足轻重。事实上,书中各章均不乏精彩洞见。以第6章为例,作者对“永生主义谬误”(Immortalist Fallacy)和死亡的层层剖析就极具启发,能促使读者重新审视“永生即善”“死亡即恶”等看似自明的固有认知。为保留阅读的思想乐趣,本文仅抛砖引玉,不再深入细节继续“剧透”。读者朋友只要把握了作者对上述两个关键词的理解,就相当于把握了理解全书的关窍和钥匙,当能自行探寻书中意趣,曲径通幽。
最后,让我们回到开篇的那个追问。或许单就技术而言,追求“更好”并没有错,但技术议题并非单纯的技术问题,亦不应仅从技术的对错来考量。隐喻地讲,即便技术真能让人拥有通往一切可能性的“方向盘”,却也有可能会让人失去“目的地”。或者借用赵汀阳的说法,“技术升级”并不必定导致人的“存在升级”(赵汀阳:《人工智能的神话或悲歌》,商务印书馆,2022年,70页),而后者正是哲学的领地。
因此,对增强计划的思想追问本质上是存在论和伦理学的,最终涉及我们对“人是什么”和“什么才是人‘应当’过的美好生活”的根本理解(这里的“伦理学”是宽泛意义上的。正如豪斯凯勒在官网的自述中所言:“大多数人可能会给我贴上伦理学家的标签,但这只在非常宽泛的意义上成立。我对于弄清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允许、什么不允许,并不十分感兴趣。在我看来,当人们争论这些问题时,他们实际上是在争论别的东西,即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我们想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中。”),故答案绝非不言而喻。该书的一个贡献正是让我们意识到其间问题的复杂与吊诡:任何增强技术,都隐含对人的规范性理解和对人类生活的价值主张,故我们无法独立于人的应然来评判增强技术的实然与或然。豪斯凯勒以娓娓道来的文风引导我们在技术“狂飙突进”的喧嚣中重新冷静地审视“人类增强”这一核心观念的诸多可疑之处,让我们看到了以追求“更好”为终极旨归的这一整套方案背后的隐忧和挑战。在我看来,本书至少有说服力地向读者表明,对技术的追问本身并不应拘囿于技术的领域,它本质上是一个要求我们不断回到“人”这个思考原点,并向技术和人存在的一切可能性前提开放的哲学“大哉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