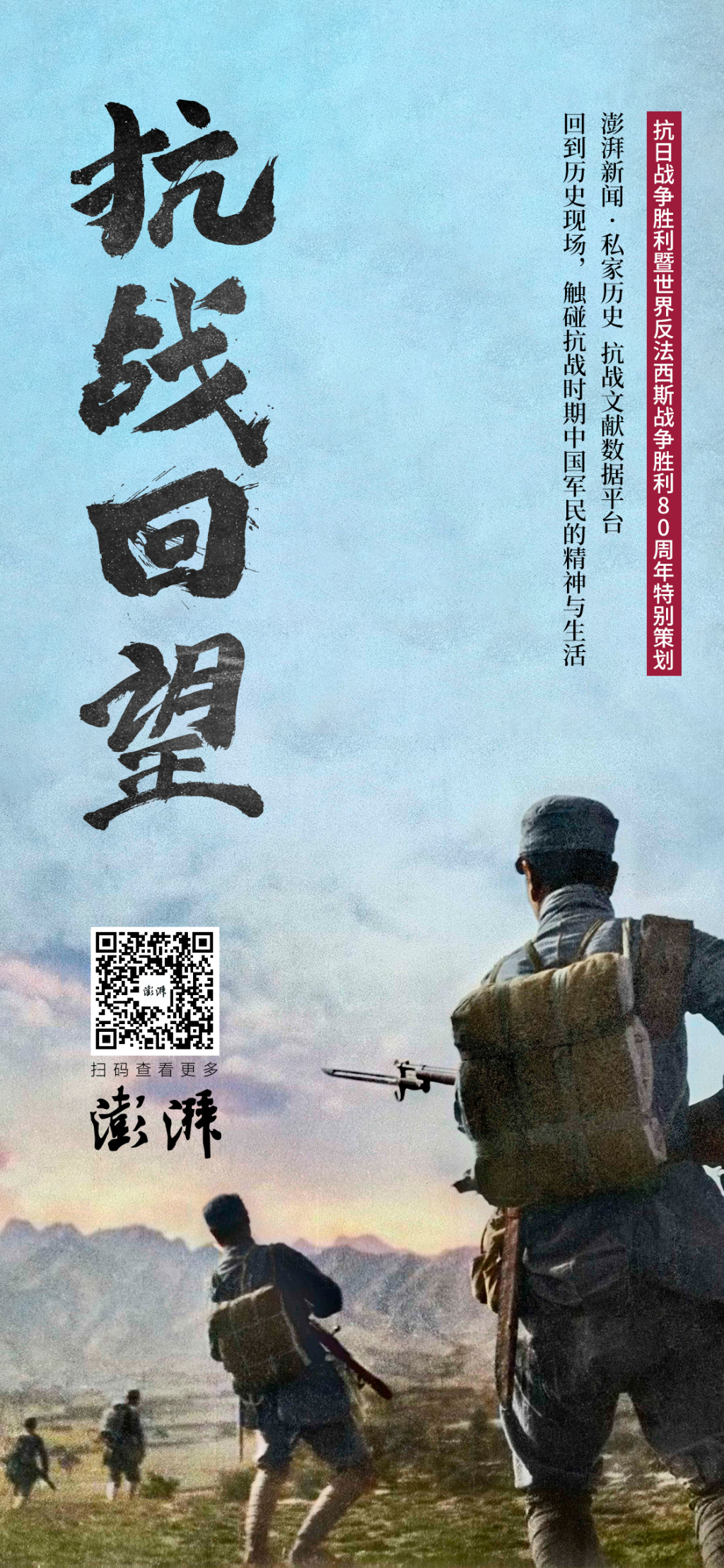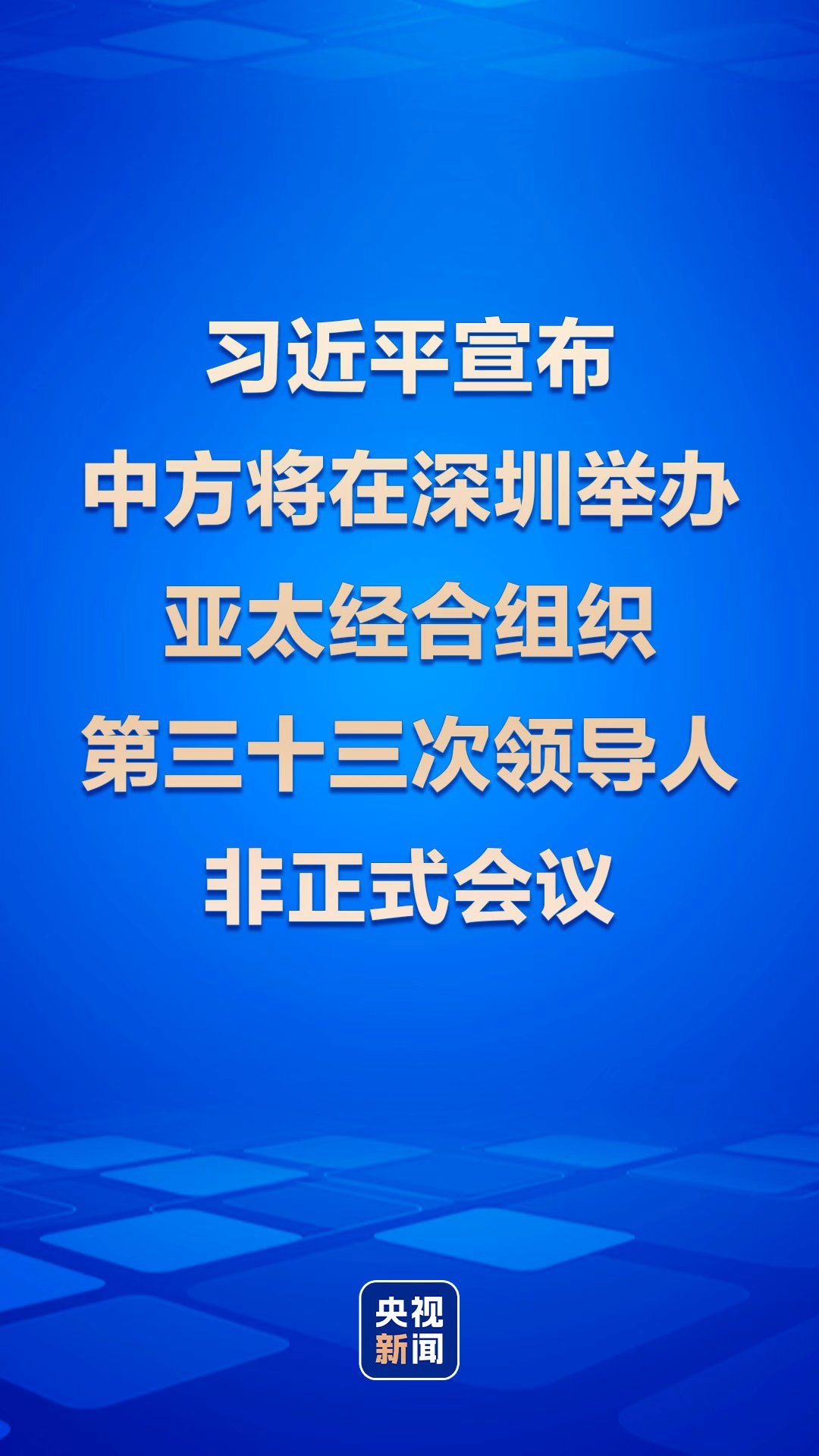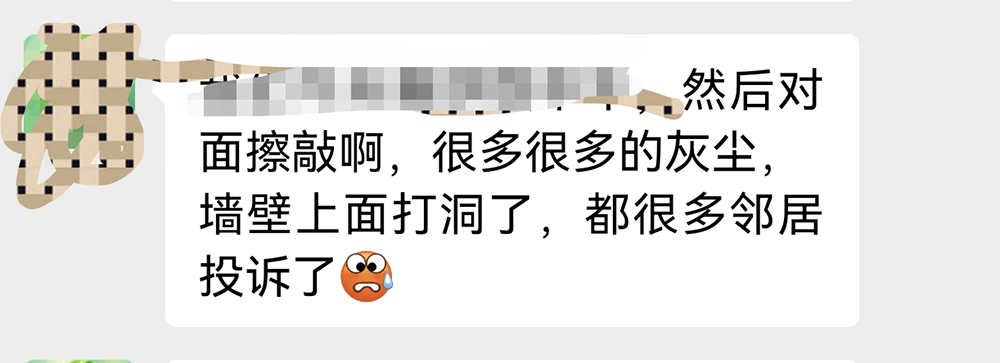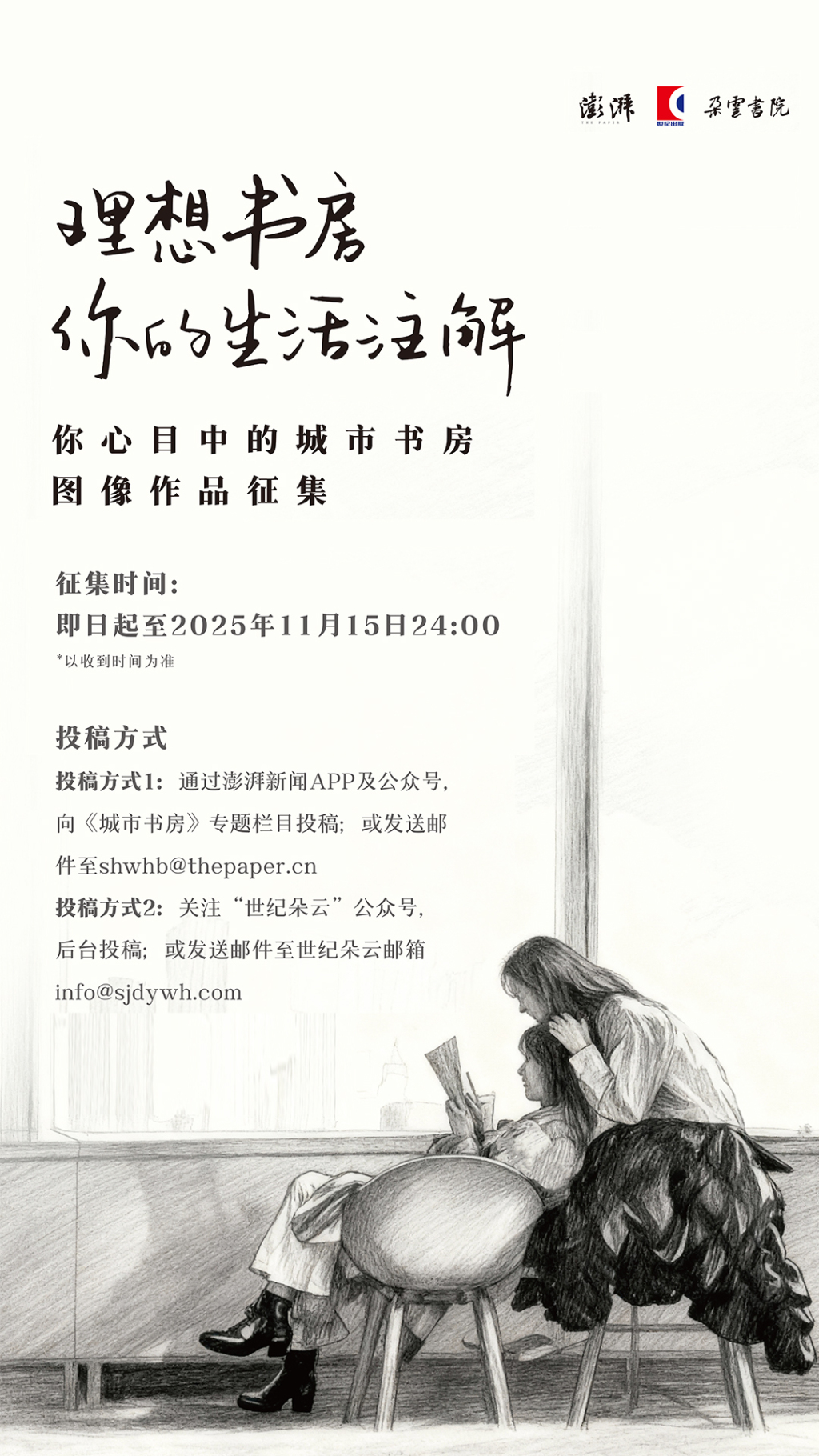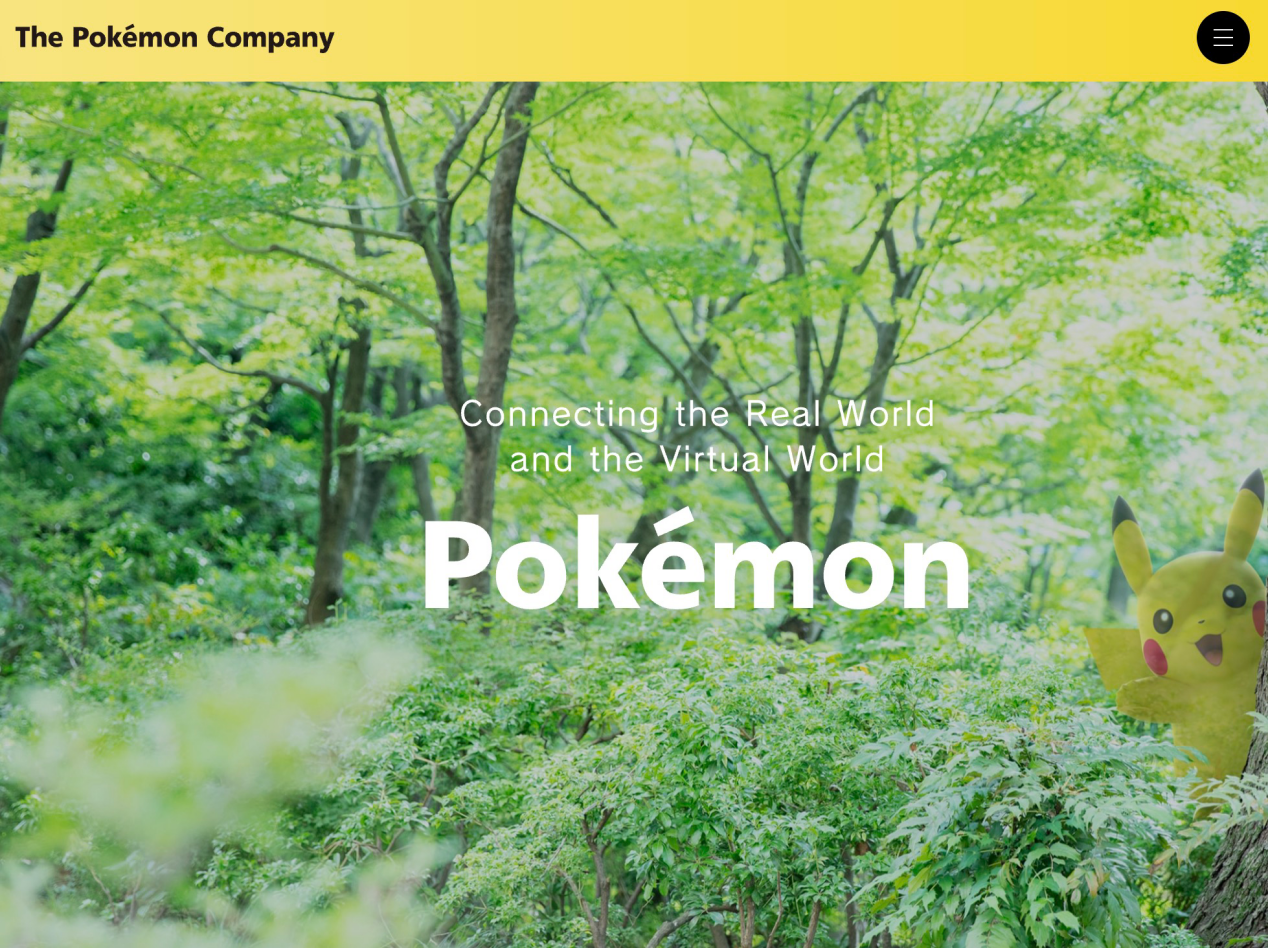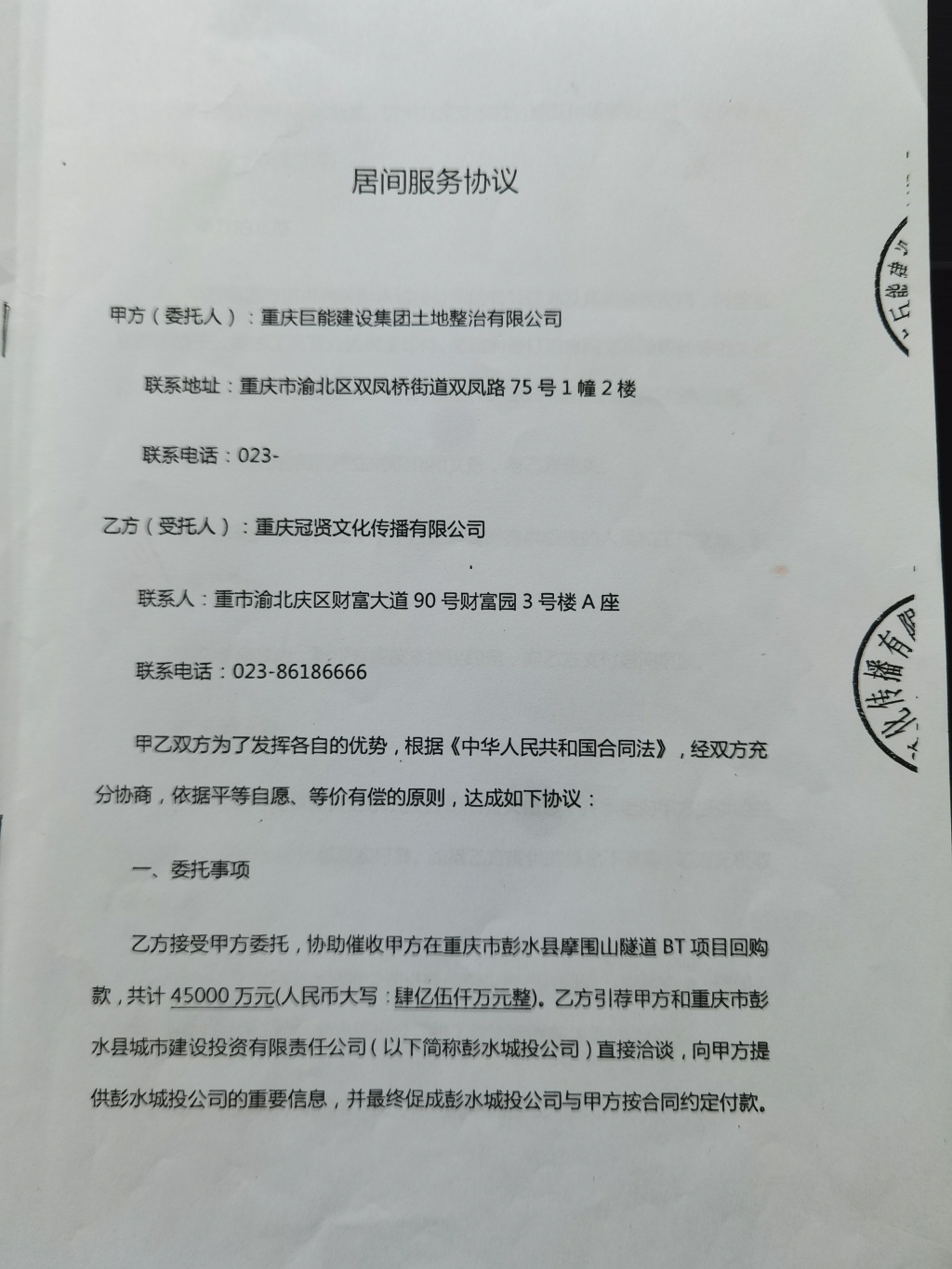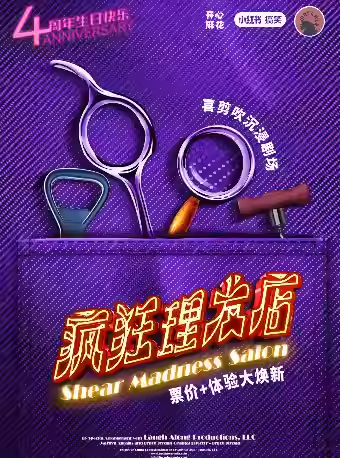浙粤寻鲜,风味的流转

杭州作为南宋首都临安,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大都市。从皇宫北面的和宁门通往北通向城市中心的御街,中段的街市最为热闹,《都城纪胜》说:“买卖关朴,酒楼歌馆,直至四鼓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林升在《题临安邸》写道:“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时序流转,至九十年代,杭州城里有了黄龙饭店。许多杭州人关于“外面世界”的念想,最早便是在这萌发的。店里头能做顶地道的粤菜,这并不稀奇——建立时本就带着粤港的渊源。那时岭南路远,却不承想,坐于西湖边,就能尝到正宗的豉油皇炒虾,喝上煲得浓香的老火汤。《繁花》里有这样一段,至真园遇困,爷叔指点宝总请来粤菜金厨,凭此一举逆风翻盘。可见当时,一家餐厅若能请来好的粤菜师傅,是有面子、也能稳局面的。三十七年历史的黄龙饭店,不声不响地已然与杭州融为一体,假设缺少了它,城市记忆似乎就难以完整。

如今,饭店的中餐厅“龙吟阁”,做的便是“浙粤菜”。它以浙江本土当季食材为基础,融入粤式烹饪技艺,形成独具一格的菜式与风格。浙江本地食材深谙一方水土的本味,而粤菜之妙,则在于“因材施艺”——无论是文火慢炖的老火汤,还是秒速灼烫的嫩菜心,皆体现出对食材特性的精准把握。正因如此,粤菜不强调主观调味,而更注重呈现食材的自然本味,追求对食物的真实表达。
为延续这份对品质的执着,我们深入乡野,探寻地道食材。一路上,遇见不少专注本味的农人,也见证了众多坚守传统的生产现场。在一趟趟旅程中,食物成为纽带,串联起一个个充满温度的人情交汇,我们也与这片土地建立了更深的联结。
寻:两浙山水的独到风物

譬如“小狗牛”。头一回听说这名,大家都愣了下。据说这种牛,只存在于“八山半水分半田”的天台。清康熙五十六年《天台县志》记载:“牛,体小俗称犬牛。”由于山地多、平地少,田块小,当地人世代选育后,便养出了这种体型小、擅走山路的牛。
从杭州去天台,开车不过两个半小时;可为了寻这牛,整整花了四十五天。在什么都求快的年头,这事儿透着点儿“憨”。初步寻访一无所获时,有人怀疑:怕不是没这东西?后多方打听,才了解到它确实存在,只是稀有难寻。一番周折,最后竟在天台的灵溪乡寻着了——山清水秀之间,满眼是朴拙的石头房子,那些正保种的小狗牛,就散养在那儿。
这牛只有寻常牛的一半大小,刷新了团队对牛的认知。它们常年奔走山间,筋骨结实,肌肉纤密。当地人习惯用土法料理,或卤或炒;龙吟阁主厨董强师傅顺着这思路,改用广式罐焖的法子,慢火煨上三四个钟头,口感近似红烧。上桌时,起了个颇具萌感的名字:牛牛菜。另一只“牛”,是白玉蜗牛。嘉兴南湖区大桥镇是我国的中华白玉蜗牛主产区,占全国市场的70%以上。小狗牛与蜗牛,在闷罐中吸收汤汁,形成了一种又Q又嫩的口感。
与寻小狗牛的艰辛相反,也有轻松的。比如在温州找槟榔芋,寻访小队赶到平阳,农户们却不着急挖,先拉我们吃饭,天黑了便说:“明天再挖罢。”这份松弛感,源于对自家产品的底气——好东西就在地里,不会跑。我们索性伴着灯火与他们闲话家常。次日清晨,芋头挖出后,董强师傅刮去泥土,一切为二,见表皮上还留有水分,这让他产生了即时灵感:就用蒸,然后蘸点白酱油。回来一试,比想象中更美味。这看似至简的做法,如果不是自己直接抵达食材的生长现场,和大地充分接触,我们未必能够与食物之间如此相互了解。
融:食材与技艺的交相辉映

当得知温州永嘉的农户还在制作“蒲瓜被”时,寻访小队开了两天车,又爬了两小时山,终于在半夜赶到了永嘉碧油坑村。海拔700多米的山岭上,星光点点。
天亮后,张燕经理才看清村民晾晒的蒲瓜被。蒲瓜是葫芦的一种,具有易成活、好打理的特点。村民们在农耕的同时顺便撒下种子,蒲瓜就会沿着田埂蔓延,开花结果。
将蒲瓜刨成极薄的片,一层层堆叠拼接起来,如同一床被子,再等晾晒成干,就成了蒲瓜被,这种传统而隐秘的美食。
这一见,倒让我们有了新念头。从前蒸海蟹,盘底那汪汁水最是可惜,虽说鲜美,却不知如何用,最后只好倒掉。现在有了蒲瓜被,将它垫在松叶蟹下面,让它浸饱鲜美汤汁,变得丰盈饱满,和松叶蟹的鲜美相互映衬。食客们吃一缕蟹肉,搭配上一口蒲瓜被,正好清甜去腻。
通过一种食物浸润另一种食材、使它们各自的鲜美形成交融,龙吟阁常有运用。例如除了蒲瓜被,还用到富阳鲜笋。
笋,是浙江出名的山珍;浙江人吃笋,是骨子里的传统爱好。当我们在富阳见到这种笋时,还是忍不住兴奋。
这笋是有来历的。九百多年前,大吃客苏轼行至新城(今富阳区新登镇),见到百姓用新出哺鸡鲜笋炖肉,大为感叹,留下“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芹烧笋饷春耕”的诗句。
它既非春笋,也不是冬笋,富阳鲜笋夏天最多。新安江畔昼夜温差大,这笋的甜味便比寻常的来得足。上山寻笋不是易事,我们为此爬坏了好几双鞋。
笋到厨房后,切成丝,也是和蟹做搭配。开渔后新捕的蟹,蒸烹时汁水把笋渗透,
一种食物的生命缓缓流入另一种食物的肌理,完成风味的转移与再造。
传:延续饮食多样性审美
前文说蘸槟榔芋头的白酱油,产自沈荡。
浙北杭嘉湖平原上河道密布,很多地名都带一个“荡”字。沈荡在嘉兴海盐,是作家余华的故乡。那里有一家发源于光绪年间的酿造厂。
我们本是去沈荡找黄酒。还没进酒窖,倒先闻见一阵清雅的豆香——循着味儿走去,正遇上酱油厂的第三代传人在补缸。那娴熟的手艺,让经理张燕心里一动:这儿的酱油,也是宝贝。

院子里,百来口酱缸戴着特制的“帽子”,静静晒着太阳。有酱油品牌标榜“晒足180天”,在沈荡这儿却算不得什么——他家的白酱油,得晒足五百多天。“白”,不是指颜色,是指酱油不掺入焦糖色,虽色淡,酱香反倒更馥郁、更醇厚。
“现在没有人学喽。”大叔在聊天时感慨。尽管白酱油入选嘉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手艺传承人依然有种“不知道哪天就失传了”的不安全感。
中国的手艺,多是口传心授,文字记不下那份火候与手感。“祖辈怎么酿,我们就怎么酿”,话虽朴实,却是酿造的真意。说是保护,不外乎是让它被更多人享用到,这让酿造者更有动力,也是我们选用沈荡白酱油的缘由。
除了蘸芋头,白酱油更经典的搭配是白切鸡。作为广东人,董强师傅对此引以为豪。不过这道菜的起源,在美食领域一直充满话题性。粤菜的白切鸡,沪菜的白斩鸡与川菜的白宰鸡,都自认是源头。到了龙吟阁,让我们暂且搁置争议,让皮脆肉嫩的白切鸡与白酱油一起,给舌尖感受一种不一样的鲜。

如果说选用沈荡白酱油是对传统的传承,那么选取绍兴笋干菜,则更多了一份深厚的乡土情谊。正是寻找笋干菜的过程,我们才开始理解杜宏新董事长坚持让我们走到乡村深处,遍寻食材的意义。
那是2021年,团队来到坡塘村。和许多空心化的村落一样,这里安静得只剩下闲坐路边的老人。似乎又将是一次一无所获的旅程。直到张燕注意到,家家户户都在晾晒的笋干菜,是一种几乎被忽略的、不可多得的纯天然好食材,
村民们起初只当她是说笑。他们从未想过,这些平日自家吃的东西,会被五星级酒店看中。以至于谈妥价格后,还是有点懵。后来由村书记牵头统筹,整个村子都动了起来,家家户户干劲十足。
第二年我们再去时,他们早已备好了苹果、笋干菜、花生米,脸上的兴奋藏也藏不住。那份喜悦,不仅来自实实在在的收入,更来自一种被看见的价值——深藏于家的好物产,终于走出乡土,端上了米其林的餐桌。
当然,选择笋干菜不单是出于帮扶,它本身也足够出色。董强师傅拿它煲汤——赤肉做底,笋干菜炖到嫩而不烂,最后加入鱼唇,如此,笋干菜那股独特的清香,便被最大程度地保留下来,原汁原味,入口生津。
“吃”的学问里,有滋味,也有人与天地万物的相处之道。知味,是口福;知位,是领悟。二者俱得,方才算得圆满。

品:从器物环境到情感记忆的始终如一
美食,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搭配的哲学。
在丽水景宁大漈乡,千余米的高山上常年云雾缭绕。这片仙气滋养下的冷水茭白,肉质格外脆嫩清甜。
以茭白入凉菜,古已有之。《武林旧事》中便有“茭白鲊”的记载,多为凉拌。董强师傅初次尝到这里的冷水茭白,心中便有了主张。他以柠檬、盐与醋调汁浸渍,取出后片成薄片,层层叠起,再缀以火腿、鱼子酱与香菜苗。整个过程如秤金量玉,分寸不差。
这样的搭配与摆盘,既打破了纯白的单调,形成色彩与质感的精妙碰撞,也进一步唤醒了食欲。冷水茭白入口,仿佛山涧溪水流过光滑的卵石,清冽中带着细腻;再配上一杯白葡萄酒,味道在舌尖柔和交融,轻盈起舞。
返:回到原点对美食的最高赞赏

一个地方的代表美食,往往会是对这个地方的乡愁。
晋人张翰因思念故乡的莼菜羹、鲈鱼脍,秋风起时便弃官归去,留下“莼鲈之思”的佳话,后人甚至为它配译“longing for home”,可谓贴切。白居易写“犹有鲈鱼莼菜兴,来春或拟住江东”,苏轼说“若问三吴胜事,不唯千里莼羹”,都把莼菜作为回忆江南的一种注脚。
不过,莼菜虽冠“西湖”之名,但它并不只产于西湖,而是泛指杭州周边地区。明代杭州人高濂在《四时幽赏录》里就指出:“旧闻莼生越之湘湖,初夏思莼,每每往彼采食;今西湖三塔基傍,莼生既多且美。”
如今上佳的莼菜,可在杭州西南的建德寻得。初夏采莼,团队必须凌晨两点出发,赶在清晨下水。眼前是浮于水面的无数椭圆形绿叶,水面浮满椭圆绿叶,如小荷铺展,莼菜就藏在叶下。还没来得及兴奋,却发现初夏清晨的水却是冰凉得难以落脚。可见任何有价值的寻觅,都不可能不费心力。
郁达夫曾说:“莼菜本身并无特殊味道,但其美味全在于精妙的汤品搭配。那嫩绿的色彩与丰富的诗意交融,无味之中竟能让人心驰神往。”我们董强师傅更直接:“胶质越多,越黏稠,莼菜品质越好。”
果然,一碗莼菜狮子头上桌,汤色至清,滋味至鲜、温润如玉。
重要的味道,不只存在于时间中,更扎根于情感里。单纯的味觉享受,永远比不上一种深植于记忆的情绪被唤醒。
谈到“莼鲈之思”,对中国人而言,最易生发乡愁的时刻,莫过于春节。作为龙吟阁经理,让张燕引以为豪的是,他们的年夜饭从不做宣传,却总是一座难求。来客多是熟客,年年相约,岁岁重逢。
他们中,不少人在年少时便在此初识美食滋味,长大后走南闯北,遍尝世间风味。可当风景看透,心底最眷恋的仍是这一口故乡的温度。于是他们带着自己的孩子回来,
再度成为座上宾。这种去而复返,难道不正是对食物之美的最高赞赏?
人间世事,就如同品尝美食的过程一样,往复循环,回到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