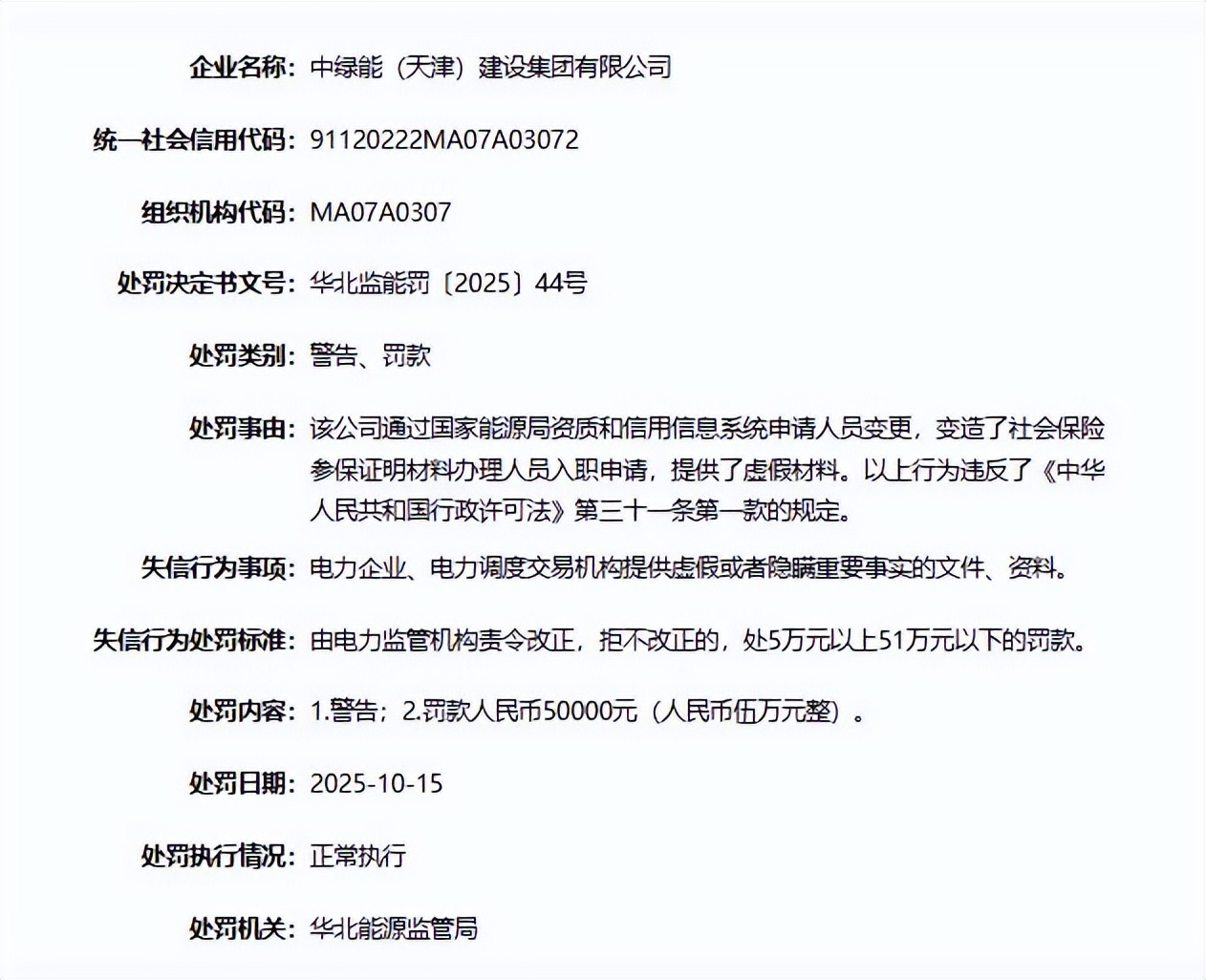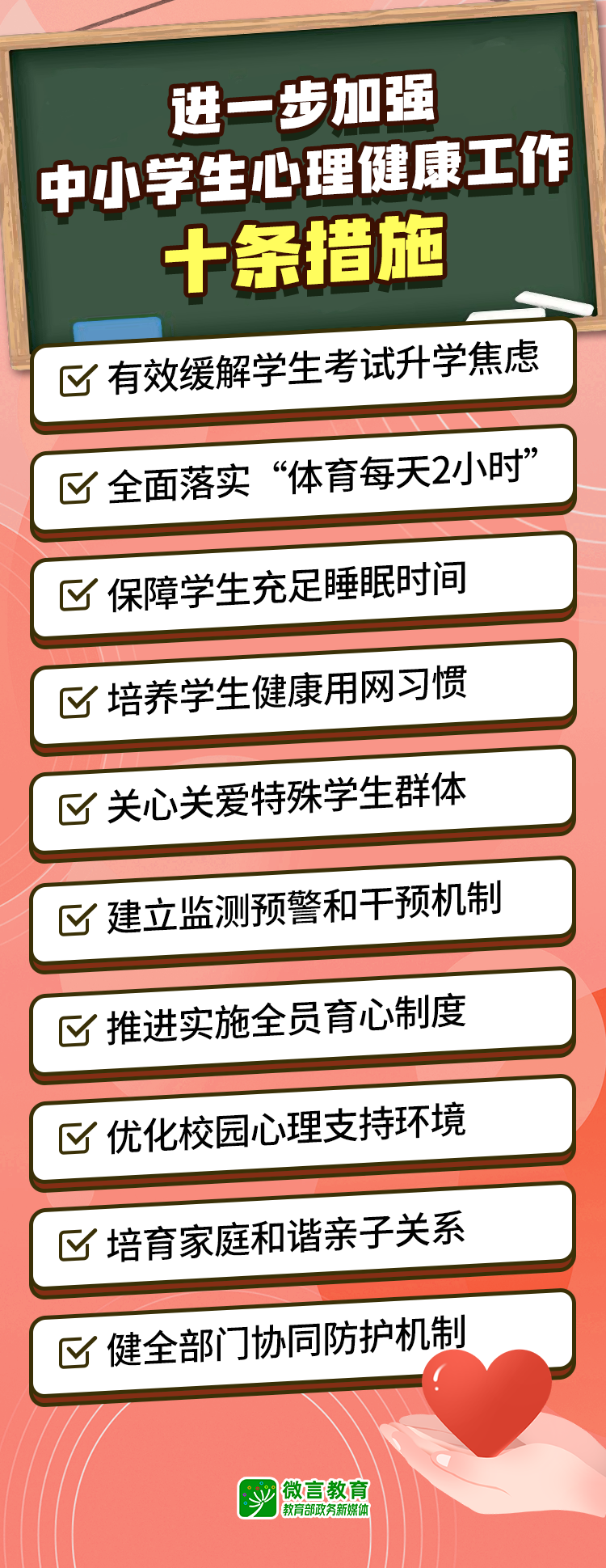包茂红|高山之巅:印加帝国的兴亡与环境
与世界历史上的绝大部分帝国不同,印加帝国主要建立在安第斯崇山峻岭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安第斯山系南北长8000多公里,东西宽300公里,平均海拔高达3660米,最高峰海拔达到6992米。就是在这样一个高山地区,印加人从15世纪初开始突然崛起,在没有文字、轮子的条件下,逐渐建立了一个庞大帝国,其疆域南北长达4000多公里,东西宽300公里,统治人口800万-1400万,是当时美洲最大的帝国,也是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帝国之一。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在一百年后处于鼎盛期突然灭亡,虽然这与西班牙殖民侵略直接相关,但皮萨罗百多人的殖民军之所以能征服这样一个帝国,一定还有更为关键的因素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印加帝国兴亡之谜值得深入探讨。

从空中俯瞰安第斯山脉
印加帝国的兴起
毫无疑问,印加帝国是印加人建立和主导的帝国,但是印加人只是起源于安第斯南部的喀喀湖附近地区的一个小部落,直到12世纪才迁徙到安第斯中部的库斯科,在与已经居住在库斯科的其它部落融合进程中逐步扩大自己的地盘。特别是印加•维拉科查晚期与钱卡人之战,不但巩固了印加人在库斯科的统治地位,还开启了向外大规模扩张的序幕。从1438年到1525年,三位皇帝南征北战、东征西讨,形成了组成帝国的四大区域(苏约),分别是北部的钦查苏约,南部的科利亚苏约,西部的孔蒂苏约和东部的安蒂苏约,这四大苏约共同构成塔万廷苏约,即印加帝国。(注:塔万廷苏约是印加帝国的正式名称,意为“四方之地”。印加是当地人对部落首领或国王的尊称,意为“太阳之子”。)与世界古代史上的帝国一样,印加帝国也形成了以印加皇室为中心的等级统治制度。皇室掌握着来自太阳神的所有权力,派到各苏约的总督代表皇帝行使权力,苏约之下以十为单位形成不同规模的地方组织。重要地方官员和被征服的部落首领的子嗣都要送到帝国首都接受教育,一方面使其熟悉帝国的制度规范,另一方面也有以人质统御全国的含义。显然,越是边远地区、越是晚征服地区,越是保有更大的自治权。不过,印加帝国也建设了与制度相匹配的基础设施,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遍布全国的驿路网络和烽火台。从北到南建成了分布在沿海和山区的两条道路,从这两条道路的重要节点上延伸出若干条从西到东的路线。每天有若干信使和健儿接力驰骋在驿路上传递信息或运送重要物资。据说把太平洋的新鲜鱼类从利马送到库斯科,即使路途遥远,但依然能够保鲜。把从帝国北部图米城的叶子上捉到的蜗牛,送到库斯科时依然活蹦乱跳。这不但说明驿路系统非常快捷高效,也证实了帝国信息流通的及时性。烽火台不但汇聚了大量战略物资,也能对地方出现的异常情况及时示警,以便中央政府做出及时有效的应对。

印加帝国驿路示意图
这样高效的统治系统之所以令人叹为观止,在于它主要建立在地形和生物文化景观极为多样的安第斯山区,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其实,“安第斯山脉极不利于文明孕育。由于干旱、过度降雨或是霜冻,作物每三年便会歉收一次。”[1]印加帝国从北到南跨越热带和亚热带,太平洋沿岸(海拔只有0-500米)受到洪堡暖流和秘鲁寒流的影响,在海上形成大鱼场,在陆上形成年降雨量不超过50毫米的沙漠,以及少量狭窄的河谷地带。安第斯山区不规则分布着谷地(海拔500-2300米)、高地(海拔2300-3500米)、丘陵和平原(海拔3500-4100米)和高山冻原(海拔4100米以上,常年积雪)等地形,气温也随着海拔的上升而降低。与此相关的是,在印加帝国之前,安第斯文化发展也呈现出奇异的多样性。早在初始期,在高原上形成了查文文化,修筑水渠进行灌溉,从事棉毛纺织业。在早中间期,随着查文文化的衰落,在沿海地区先后兴起了莫切文化、纳斯卡文化和卡哈马卡文化等,这些文化不但崇拜太阳神和月亮神,更因为生境狭小而崇拜武力征讨。在中同一期,在沿海兴起瓦里文化,在高原形成蒂亚瓦纳克文化,虽然这两种文化的象征(权杖上的图像)极其相似,但其基本内涵却大不相同,前者用国家驿道连接若干分散的行政中心,后者虽然神庙和行政中心集中,但通过商队贸易连接庞大地域。在公元1000年左右,瓦里文化中依赖低地河谷梯田的人和蒂亚瓦纳克文化中依赖整修田地的人都放弃了原来的居住地,迁徙到沿山脊修建的、具有更好防御功能的定居点,从事更加多元的农牧业。印加人就是在继承这些生态和文化传统基础上,吸收其复杂的经济体系以及直接或间接统治的灵感,形成了安第斯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
印加帝国的生计与环境
调节不同阶层和民族的关系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土地上能产出维持帝国所需要的各种物资。自从人类大约在14000年前出现在安第斯山区以来,逐渐适应当地环境,形成了垂直种植体系。在大约5000年前,人类在安第斯区域驯化了棉花、葫芦、玉米、藜麦、土豆和羽扇豆等作物和羊驼、骆马等骆驼科动物。这些动植物的生长需要不同的气温和阳光,在安第斯多样地形中逐渐形成不同生产分布区。在沿海地带,主要生业是捕鱼和种植棉花、葫芦、南瓜和水果;在海拔500-2300米的湿润谷底,种植古柯、玉米、辣椒;在海拔2300-3500米的高地,种植土豆;在海拔3500-4100米的丘陵地带,种植藜麦和羽扇豆;在4100米以上地带,放养羊驼和骆马。印加人在扩张过程中,保留和发展了这些适应当地环境的垂直种植体系。
古气候和孢粉研究证明,印加人是在中世纪气候异常期(约950-1250年)迁移到库斯科的。那时的安第斯山区明显温暖化,人口和作物都向更高海拔地区扩张,形成同一海拔不同部落混合和多元种植的新格局。在位于印加帝国核心区、欧雅台北部12公里处的马卡科查湖,古气候学家根据湖底沉积物中盘星藻属浓度上升判断,湖周围不但增加了玉米种植和骆驼科动物,而且种植了速生的赤杨等树种。这说明印加人加大了对库斯科周围地区的开发力度。在印加人开始大规模向外扩张、建立帝国之时,湖底沉积物中出现了无机物,这证明印加人建设了梯田;沉积物中桤木属植物孢粉浓度达到峰值和盘星藻属和豚草属灌木孢粉浓度降低,说明印加人在发展农林业,既提升了生产效率,又保护了水土。

马丘比丘的城市和梯田
农业是印加帝国建立、扩张和维持的命脉。印加人为了发展农林业,不但修筑了梯田和灌溉渠,还种植树木和饲养牲畜。在河谷地带,为了扩大种植面积,印加人通过修筑运河和水渠,把高山融水引到荒漠地带,形成新的农业开发区。在阳面山坡地带,印加人依据地势修建了宽幅和高度不等的梯田和灌渠。梯田建设追求坚固性、耐久性、实用性和美观性。坚固性就是在充分利用地形基础上,采用打制石料,通过精心设计和巧妙堆叠,建成能够抵御山洪的石墙。耐久性就是在坚固性基础上,通过蓄排结合,使梯田持续保持生产力。灌溉设施通过设置跌水,既防止过度冲刷,又能减缓流速,从而减小对梯田的压力,反向提升了梯田的使用年限。石墙内通常铺设四层物质,从下到上分别是石块、碎石、沙土和土壤。这样的组合既能保墒促进植物生长,又能滤水不损害植物根系,更能保障梯田不会因为洪水而被冲毁。实用性就是在方便耕作基础上提高作物产量,其中的核心是千方百计保持土壤肥力。主要办法是施肥,肥源来自烧荒的灰烬、牲畜的粪便和沿海鸟粪岛的鸟粪。印加人清理土地主要采用烧荒的形式,灰烬能够补充土壤所需要的碳和钾等营养物质,改善土壤结构。骆驼类动物粪便尽管数量不多,但在高地地区使用效果突出。来自沿海地区的鸟粪是不可缺少的天然有机肥,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帝国的农业生产,保证了帝国内不同民族丰衣足食,还能存有可供6-7年食用的余粮。然而,从沿海到马丘比丘,相隔600多公里,印加帝国主要靠羊驼商队运输鸟粪,而且沿海和内陆之间的往来主要不是依赖商品交换,而是通过某种程度上的调配和物物交换来完成。印加人的梯田不仅是农业生产场域,也是他们实践美学思想的杰作,实用性和美观性在梯田中完美融合。印加人仅在现在的秘鲁就修建了6000平方公里的梯田,在现在的玻利维亚修建了5000平方公里的梯田。这些梯田不仅“艺术性地补足了大自然所缺的东西”,还赋予安第斯山以“有梯田的山”的丰富内涵。[2]
在安第斯山区,林业和畜牧业不可或缺。桤木属植物的增加一方面说明随着气候变暖树木生长范围自然扩大,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人口持续增加的条件下树木生长范围的扩大似乎并不纯粹是自然扩大的结果,更可能是人为种植的产物。根据西班牙殖民者的记载,印加帝国不但严格限制森林砍伐,仅仅准许平民在政府许可的范围内伐木和采集林下产品,而且设立树木种植园,提高木材蓄积量,同时在神庙和城镇周围、道路和水渠两边种植树木,或提供林荫景观,或保持水土。因此,遍及印加帝国的森林既有原始林,也有次生林,既为帝国提供木材和薪材,也辅助农业生产和景观建设。印加人的纺织品主要是用棉花和羊驼毛制成,在高寒山区,毛织品对人的生存具有决定性作用。印加帝国视羊驼和骆马为“太阳神的美洲驼”,不但在某种意义上是圣物,而且不能随意捕猎,即使它们闯入人们的定居点及其花园。在捕猎节猎获的鹿中,雌鹿和强壮的雄鹿必须放生,其余的可以食其肉,用其皮;猎获的羊驼和骆马在剪毛后必须放回自然,使其自然生长和繁殖。捕猎在四个大区轮流进行,每次捕猎后都要用结绳记事的方法记录下捕杀和放生的动物数量,以便确定下一轮狩猎的目标数量。从这个意义上看,印加帝国的畜牧和狩猎是在一定程度上是计划行为,既能保证印加人的蛋白质和御寒需要,又能为农业提供肥料。
以梯田为标志的农林业无疑是印加帝国诸多辉煌成就中亮眼的一例,梯田充分利用了山地环境,也很美观,但其生产能力有限。现在无论是在萨克塞华曼(Sacsayhuaman)、圣谷还是马丘比丘,都能看到修缮完好、气势雄伟、排列整齐的梯田,确实彰显了印加人利用环境的高超技术和惊人创造,然而,正是这宏大的规模和当时并不先进的生产力之间的巨大反差使之成为难以解释的历史之谜。这一方面给印加历史平添更多的神秘色彩,另一方面也促使人们跳开梯田、从整体上重新认识印加历史。走出库斯科,进入齐秦罗丘陵地带和圣谷,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正是印加人在此开阔地带大面积种植不同品种的玉米和土豆,为首都库斯科的建设和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坐落在这一地域的育种基地(Moray)利用不同高度梯田上的气温微小差异培育了适应不同海拔山地的作物品种,这是印加人利用环境变化改造物种的一个成功范例。坐落在这一地域的盐田(Maras)把地下的咸水引入山谷,利用地形和气温晒出各种不同品质的盐,供帝国人畜享用。不远处的雪山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正是雪山融水滋润着这片丘陵地带,使之能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度上成为丰产之地。显然,是庞大的腹地支撑着帝国首都,是腹地的巨大生产力在某种程度上维持着帝国的扩张和运转。建在海拔2300多米悬崖峭壁上的马丘比丘是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它由设计神奇的城市和大面积的梯田两部分组成,周围环绕着乌鲁班巴河和高耸的群山。这个令人震撼的人造物已被列入“新世界七大奇迹”。且不管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在这个最不适合建设城市的地形上修建如此规模的城市已经让人难以置信,甚至思绪会自然顺着栓日石指示的方向以及冬至日神奇出现在太阳神庙窗口的那束光飞扬,飞向虚无缥缈。不过,“逸兴壮思”终究要收回,回到四通八达的印加古道走一遭,就会发现是脚下的古道把谷地、丘陵和高山平原与这座天空之城有机联系在一起,是垂直农业体系筑起了印加人的这座丰碑。

盐田

育种基地
印加帝国的信仰与环境保护
虽然印加人基本上采用的是适应环境的方式,但环境的承载力毕竟有限。为了维持和扩大环境容量和承载力,印加帝国采取了一系列保护环境的措施。在安第斯山区,森林不但是关键资源,更是具有保育水土功能的独特景观。印加帝国的原始森林原则上归皇室所有,由被称作“马尔奇卡马亚克”的官员来监管,严禁滥砍滥伐,对未获授权砍伐树木处以严厉惩罚。没有得到许可就砍伐树木、毁坏森林的行为最重可判处死刑。印加帝国的动物不但能够提供毛和皮,还能提供粪肥,但繁殖率低。为了保持足够数量,帝国法律严禁随意猎杀动物。鸟粪是支撑帝国农业、促进农作物生长的重要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帝国在海岸线的界限与秘鲁鸬鹚、秘鲁鹈鹕和秘鲁鲣鸟的活动范围一致。为了帝国的永续,印加人制定了严格的海鸟及其栖息地保护政策。首先划分了各省在鸟粪岛的开采范围,避免互相争抢和无序开发;其次对各省开采实行配额制,避免竭泽而渔式的过度开采。再次禁止在繁殖季节登岛盗取鸟蛋、干扰孵蛋,保证鸟类安全再生产。最后严惩杀害鸟类的行为,通过判处死刑形成强大震慑效应。这种对鸟粪来源物种及其栖息地的保护表面上看是为了帝国农业的可持续生产,但在客观上也形成了对鸟粪岛和太平洋沿岸生态系统的保护。这与工业化时代的国家公园式的环境保护具有异曲同工之效。
印加人利用和保护环境主要出于提高农业生产的需要,但也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印加人的信仰之核心是印加人自己的,但也整合了被帝国征服的其它部落和民族的信仰,形成了既具统一性又有多样性的复杂体系。印加人信仰中的世界分为三层,上界是天国,以秃鹫为代表。这是神灵居住的世界,象征宇宙和一切神圣之事。下界是冥界,以蛇为代表。虽是祖先亡灵之所,与黑暗相关,但也意味着重生。中界是尘世,以狮子为代表。这里体现了现世包括人在内的环境各因素之间的互动共存。这三界虽然主理事物不同,但相互关联,深度交织,形成三位一体的结构和格局。印加人信仰的底色是万物有灵论,认为万事万物都有生命,而人是所在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印加人在崇拜太阳神印蒂(皇帝是太阳之子)和月亮神玛玛基利亚(皇帝的姐妹和皇后)的同时,还敬拜帕查玛玛(大地女神)、玛玛科查(湖泊女神)、乌尔皮瓦查克(鸟粪女神)、森林女神、水神等。显然,与农作物或生产有关的大都是女神,表现出富有生命力而非暴力倾向。以太阳神崇拜为主的神庙的典型就是帕查卡马克,虽然它已被殖民者在劫掠之后捣毁,但从遗址的规模和发掘出的文物来看,这座神庙的影响波及整个帝国。皇室和太阳神神庙拥有全国大部分资源,这在客观上形成了对资源环境的保护。对其它神灵的崇拜虽然以多种不同形式表现出来,但都蕴含着敬畏并通过献祭使之繁育增殖的思想。莫切人和钦查人向鸟粪女神献祭不但展示了他们与鸟粪以及鸟之间的精神联系,也表现了希冀鸟粪能够用之不竭的愿望。塔博玛凯(Tambomachay)既是崇拜水神的圣殿,也是库斯科供水之源。那里至今依然涌流不息的喷泉似乎在诉说着水在印加人心目和生活中永不消逝的存在。印加人通过敬拜这些神灵,祈求维持把自然(宇宙)、神灵和印加人连为一体的整体的平衡。

崇拜水神的塔博玛凯
帝国的衰亡
虽然印加人很好地利用了环境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帝国,但是面对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仅仅180人、27匹马和2尊加农炮的侵略军几乎毫无还手之力,迅速崩溃。双方如此悬殊的实力对比和如此令人惊诧的结局同样也留下了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先前从欧洲角度出发的解释是:欧洲人的军事技术高明,印加人的冷兵器不是欧洲热兵器的对手;欧洲人的宗教是一神教,比印加人的万物有灵论高明,上帝站在欧洲人一边;欧洲人的文明高级,通过征服来教化印加人;等等。从进步论的角度来看,这些解释似乎能够说明印加帝国失败的原因,但仍然让人感觉匪夷所思,因为不到200人的军队在短时间内征服一个庞大的帝国实在难以想象。于是,视角转向了印加帝国,认为印加帝国的皇位继承制和为争夺皇位发生的严重内讧削弱了印加帝国的抵抗力,这一内讧被殖民者巧妙利用加速了帝国的灭亡。但是,不论是从欧洲人还是从印加人的角度来解释,都无法说明如此悬殊的实力怎么会导致相反的结果。其实,正如威廉·麦克尼尔所说,“削减潜在的纳税人和印第安劳动力,并不符合西班牙人和其他欧洲人的自身利益”。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出乎意料的后果呢?是随同殖民者一起来的病菌,旧世界的致命病菌在新土地上大展身手,杀伤力惊人。印第安人似乎只消见到、嗅到一名西班牙人,就足以令他们失魂丧命。

从萨克塞华曼看库斯科
之所以美洲土著面对欧洲疾病如此脆弱,关键在于美洲多年与世隔绝,人的免疫力和抵抗力都弱,另外,印加帝国在主要是高山环境中养活了如此多的人口导致生态紧张、土壤盐碱化和缺乏生态缓冲区,最终造成印加人对外来的病原体极度敏感。其实,在大约13900年前,来自亚洲的人在南美洲分化为四个种群:亚马逊人、安第斯人、查科美洲印第安人和巴塔哥尼亚人。他们从此不但与欧亚非大陆隔绝,相互之间也因居住环境差异而甚少交流。这种时空隔离降低了印加人的遗传和免疫多样性。进而言之,单一基因型宿主为病菌传播提供了适配的环境,加速毒力进化,与此同时由于遗传多样性弱,缺乏抗病基因,难以形成免疫抗病屏障。这一正一反都使印加人在面对欧洲人带来的传染病时毫无还手之力,最终导致帝国轰然垮塌。
这样的解释无疑是科学的,也似乎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但是,它重视的是作为个体的人,忽略了由个体组成的印加社会,也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揭示出殖民主义的邪恶和不义,更何况它不能解释是欧洲人而不是亚洲人把病菌带到了美洲,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是欧洲人征服了美洲而不是亚洲人或非洲人。因此,印加帝国在面对殖民入侵时的快速失败显然不能用单一因素来解释,需要从不同角度、综合多种相关因素来认识。反推回去,在解释印加帝国的兴起时,也要坚持这种视角和思路。
在认识印加帝国的兴亡时,环境无疑是不可缺少的关键因素,其基础作用不容忽视。但是,作为建立帝国的印加人不仅仅是具有社会性的人,还是安第斯环境的一部分。印加人是在环境整体中通过与环境的其它部分的相互作用创建了帝国,缺乏对环境在印加帝国兴起中的作用的认识是不全面的。同样,在分析印加帝国的灭亡时,仅仅关注西班牙殖民者和印加人的作用或者仅仅关注来自欧亚非大陆的病菌的作用也都是不全面的。凸显殖民者的高明实际上是欧洲中心论的表现,也是把殖民主义合法化的表现。过度强调病菌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历史宿命论的表现,客观上起到了弱化殖民主义罪恶的作用。对历史认识的创新不能用非此即彼的思维来完成,但全面的认识也不是面面俱到,环境因素与人类因素之间复杂的互动机制是应该深入解明的重点。
注释:
【1】肖恩威廉·米勒著,谷蕾,李小燕译,《被入侵的天堂:拉丁美洲环境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9页。
【2】肖恩威廉·米勒著,谷蕾,李小燕译,《被入侵的天堂:拉丁美洲环境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6-27页。
【3】威廉H·麦克尼尔著,余新忠,毕会成译,《瘟疫与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