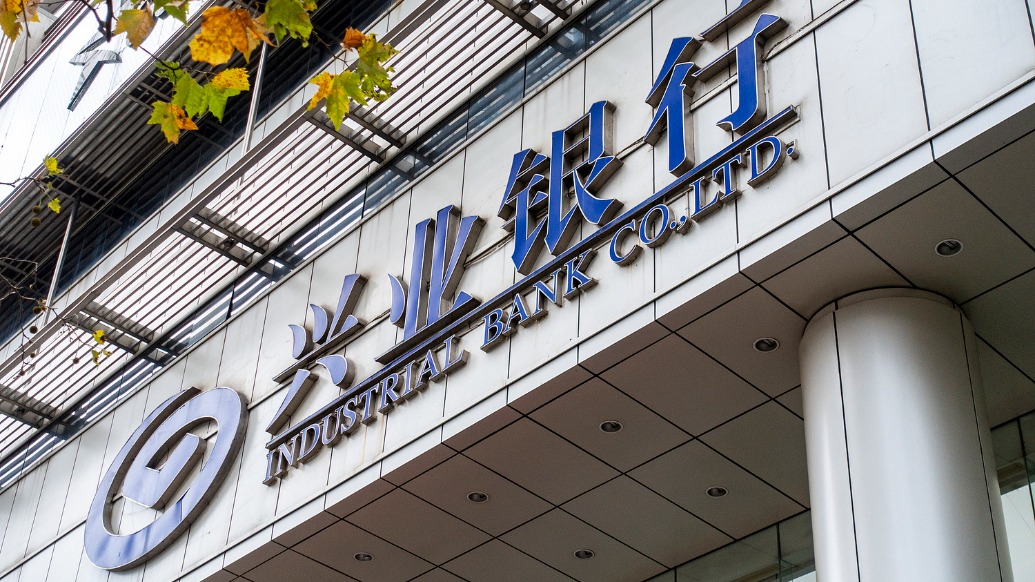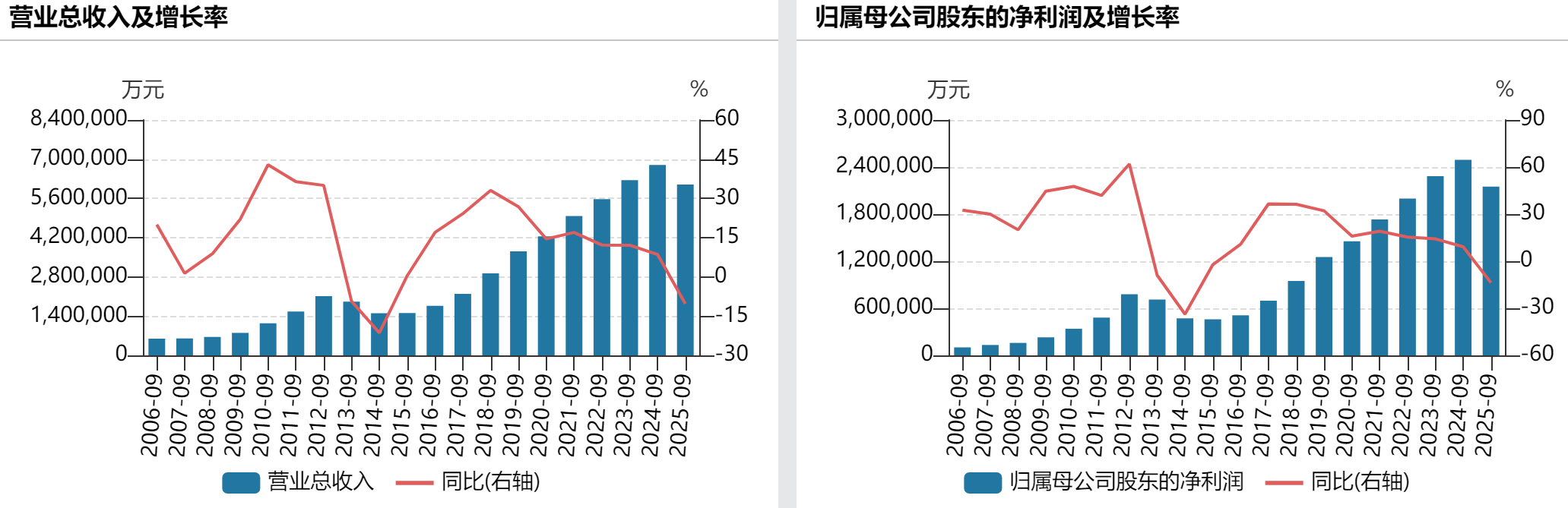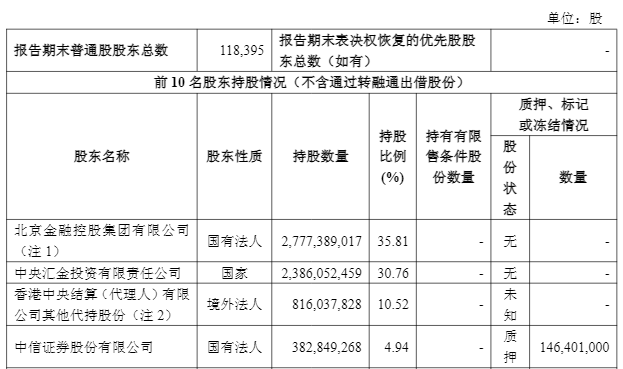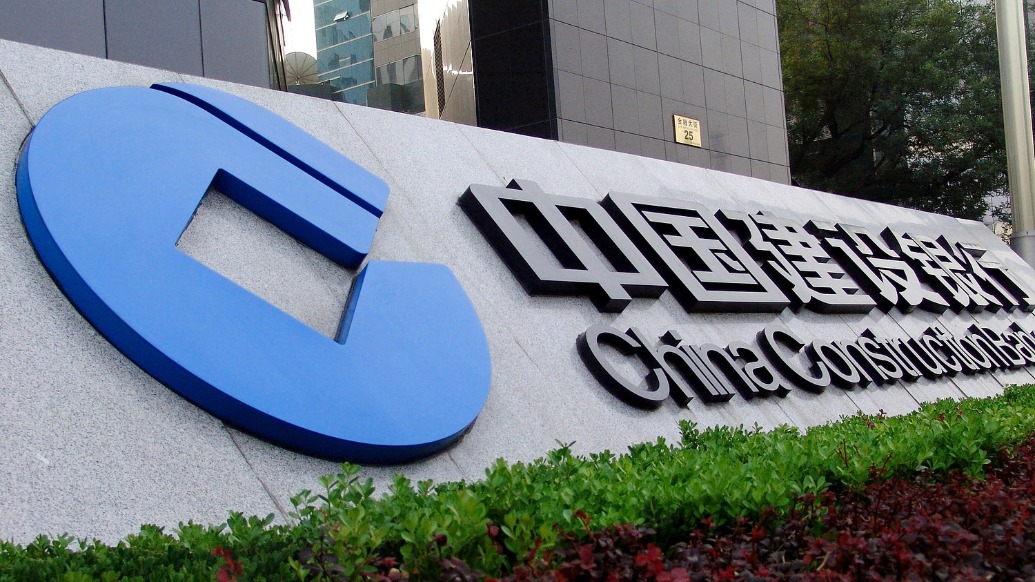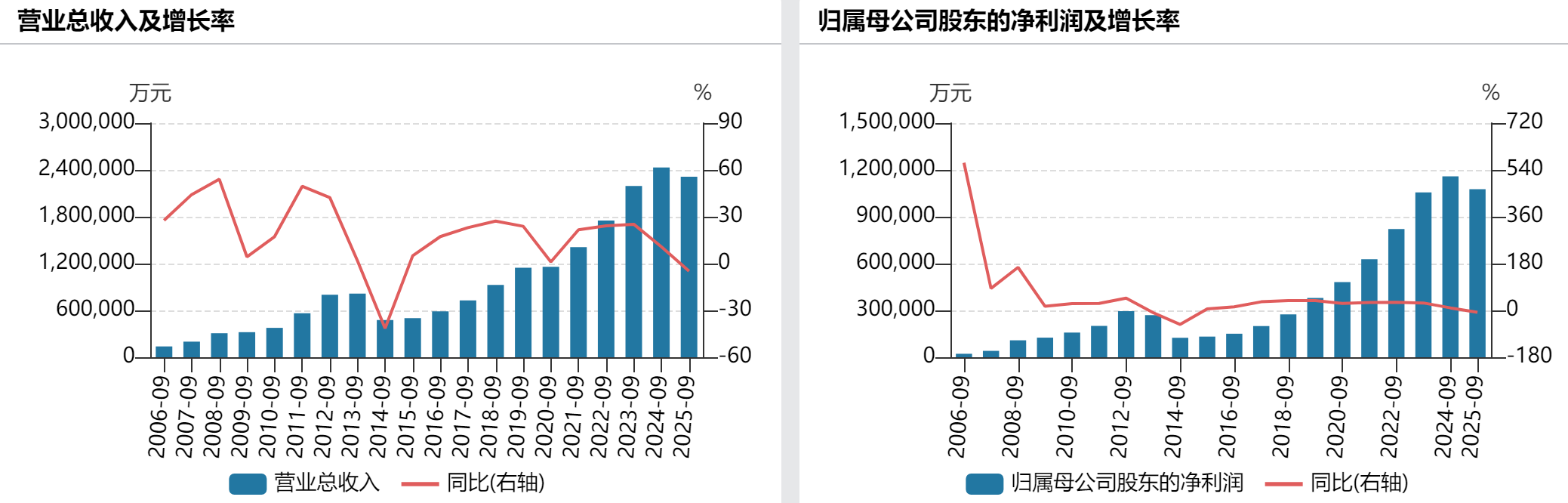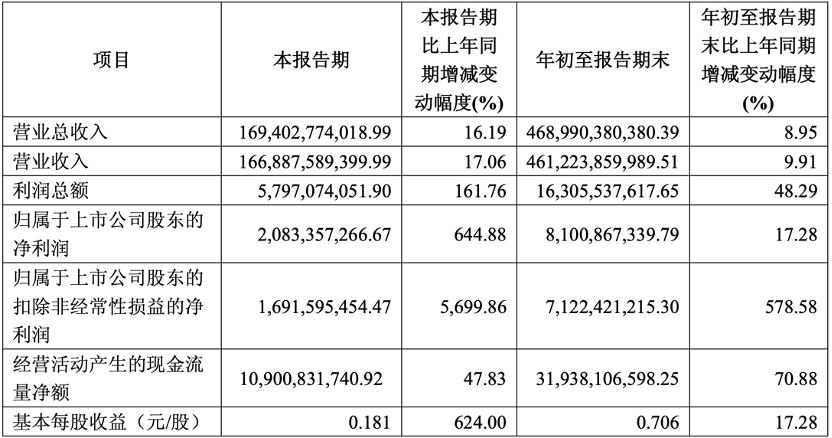夜读|我们和原生家庭的关系
每次假期进入倒计时,高铁车厢里大大小小的行李就会格外多。很多是离家的人,从他们的行李就看得出——大矿泉水瓶里装满鸡蛋,大桶颜色澄亮的土榨油,隔着多层塑料袋都能闻到香味的不知名食物。我自己的背包里,也背着出门时家人雷急火急买的几个现烤本地月饼,就因为中秋节那天夸过一句“好吃”。
在一年有限的几次见面里,不管是否发生过龃龉,很多家庭的惯常做法,都是尽可能向要离开家的那个人示好。而土特产里有彼此心照不宣的情感和记忆,是如此贴切的道具。
车厢里,有个已经坐定的女孩,正在用方言打电话。她的声音清脆又温柔,在一片喧哗中似乎自带结界。
我听出来了,她给家人买的几箱葱油饼刚送到,此刻正跟电话那头的人安排怎么分配,以及叮嘱他们要如何储存和加工。电话里逐个提到一众亲友,让人忍不住揣测,她应该有着融洽的原生家庭和亲戚关系。这个在旅途中拨打的温声软语的电话,证明她和家人们有着深厚的羁绊。
我的手机里,父母正在叮嘱我下车不要忘记行李,到达后吃点东西,早点休息。而我劝他们不要再把食物和药品囤到过期,别老玩手机到半夜。彼此都知道是些啰啰嗦嗦的话,而且大概率对对方来说都是废话。只是此刻,它自有分量。
很多人都说,放假回家和父母只能和平相处一两天,很快就会陷入“相看两厌”的境地。比如对彼此生活习惯的不适应,审美和思维的分歧,对对方兴趣爱好和人生经验的不理解。诸如此类,让年轻人窥见一代父母有一代父母的局限,以及生而为人的共同bug。
看电视剧《请回答1988》时,听到德善父亲说“德善呐,爸爸也是第一次当爸爸啊”,我突然意识到,一个人和原生家庭的那些互不对付、互相指控,也许并非“祸害”,而是课题。
我们和原生家庭的关系,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关系之一。无论如何都斩不断的血缘,对彼此的过高期待,不讲分寸乃至蛮横地关心,以及每个个体独自走向自己生活征途后所生的嫌隙和陌生,共同构成了我们和原生家庭的繁复关系与情感。
而工作、爱情甚至友情,成分都要纯粹得多。我甚至觉得,能够处理好和原生家庭关系的人,一定有能力处理好和其他关系。
此外,我也觉得原生家庭才算得上是我们实质拥有的关系。一方面源于最初我们都是被迫选择这个关系的,因此才有更多彼此塑造的余地。另一方面,也只有这个关系会真正与我们长久地缠斗。其他关系,大抵都没这种韧性。
小孩们总会在成长中的某个时刻,发现父母长辈的“无力”和“无能”,也会看到他们的不易和光辉。这是一种属于成年人之间的平等注视。而长辈则惊诧于晚辈已经完全不再是自己眼中的童稚小儿,他们心性大变,他们的世界广阔陌生到令人惊恐。于是彼此重新打量、周旋,并尝试调整新的关系格局。这个过程也许相当缓慢,甚至艰难。
但我总觉得,比起动辄就叫人“断亲”,对原生家庭多一点注视和耐心,哪怕多个电话、多条信息,也许才算是真正的成年人的勇敢。
有次跟一个朋友聊天,他问我:如果你得了急症,能找到马上抛下一切送你去医院的人吗?我反问他,他仔细想了一下,说可能只有父母吧。只是很多人跟原生家庭相隔太远,远水救不了近火。于是他感叹,我们应该试着建立起一些可以救命的关系,这也是最基础的生存储备。
我们很多成年人,遇到艰难时刻,真正的避难所,可能还是原生家庭。原生家庭可能导致我们天然受限,但这也是一切的基础。无论疾驰的列车带我们奔向何方,我们都知道有个家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