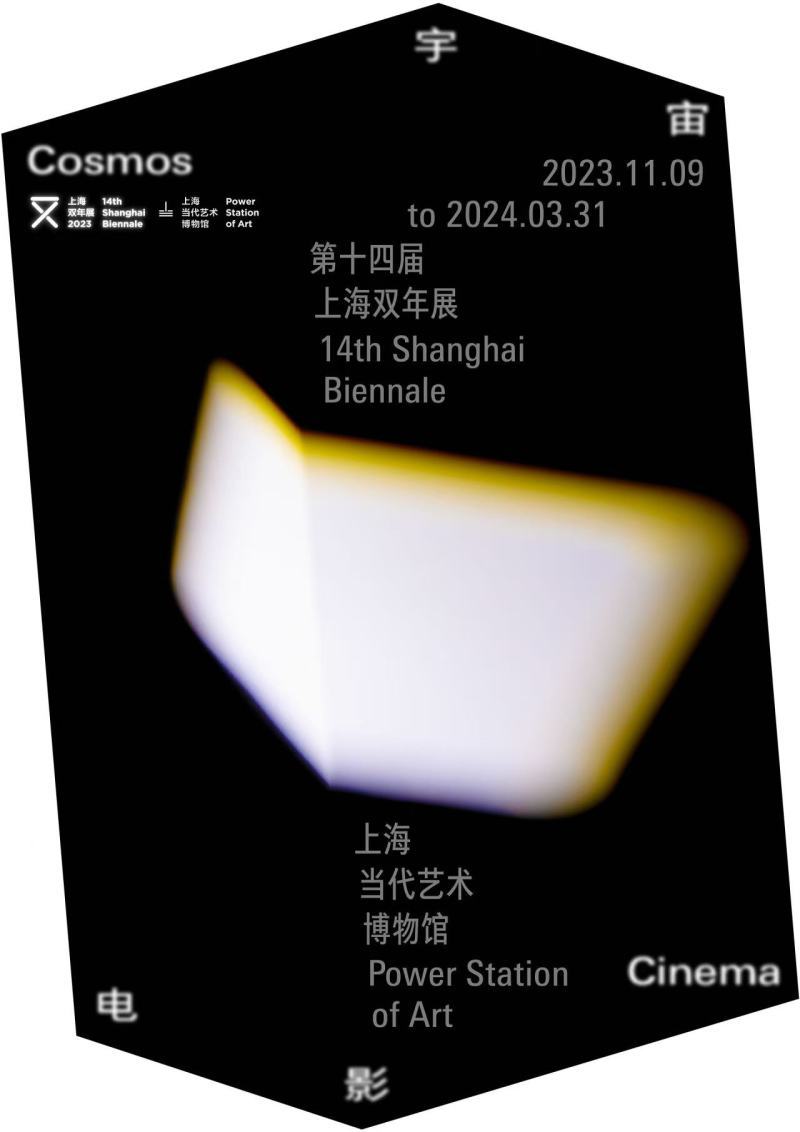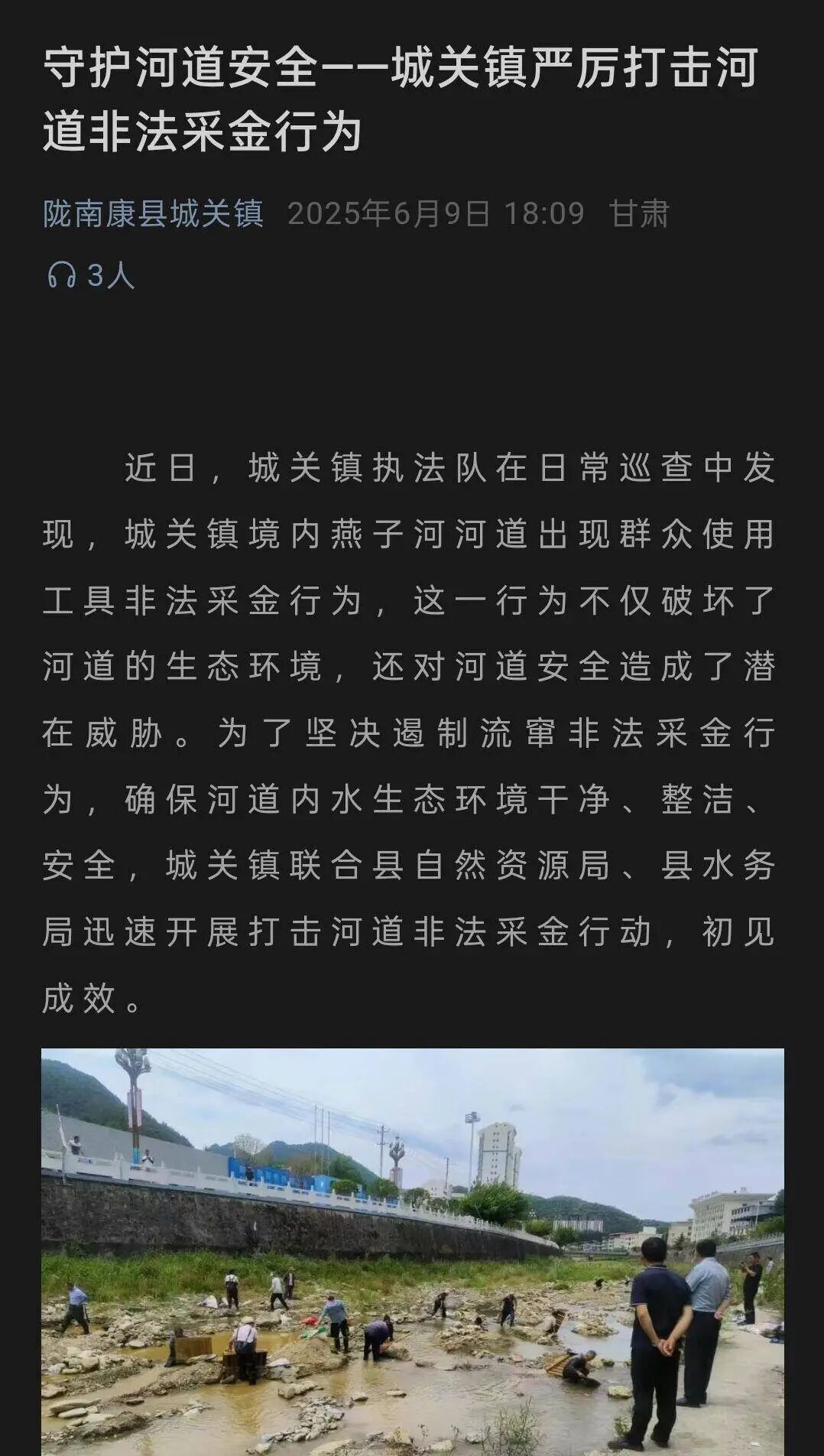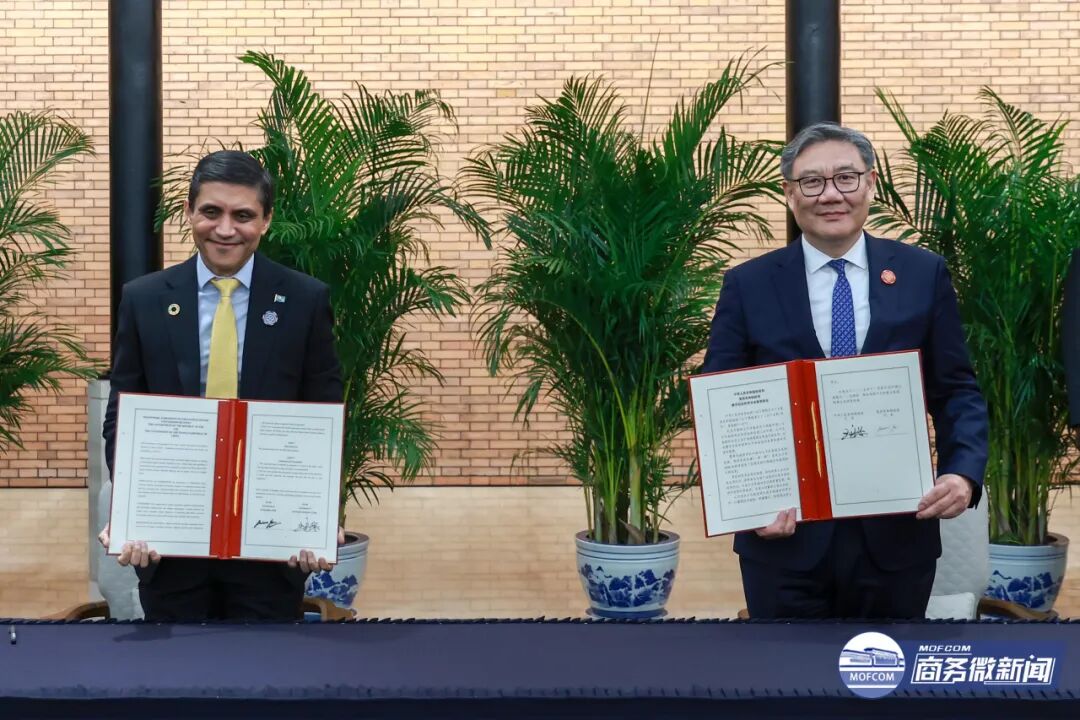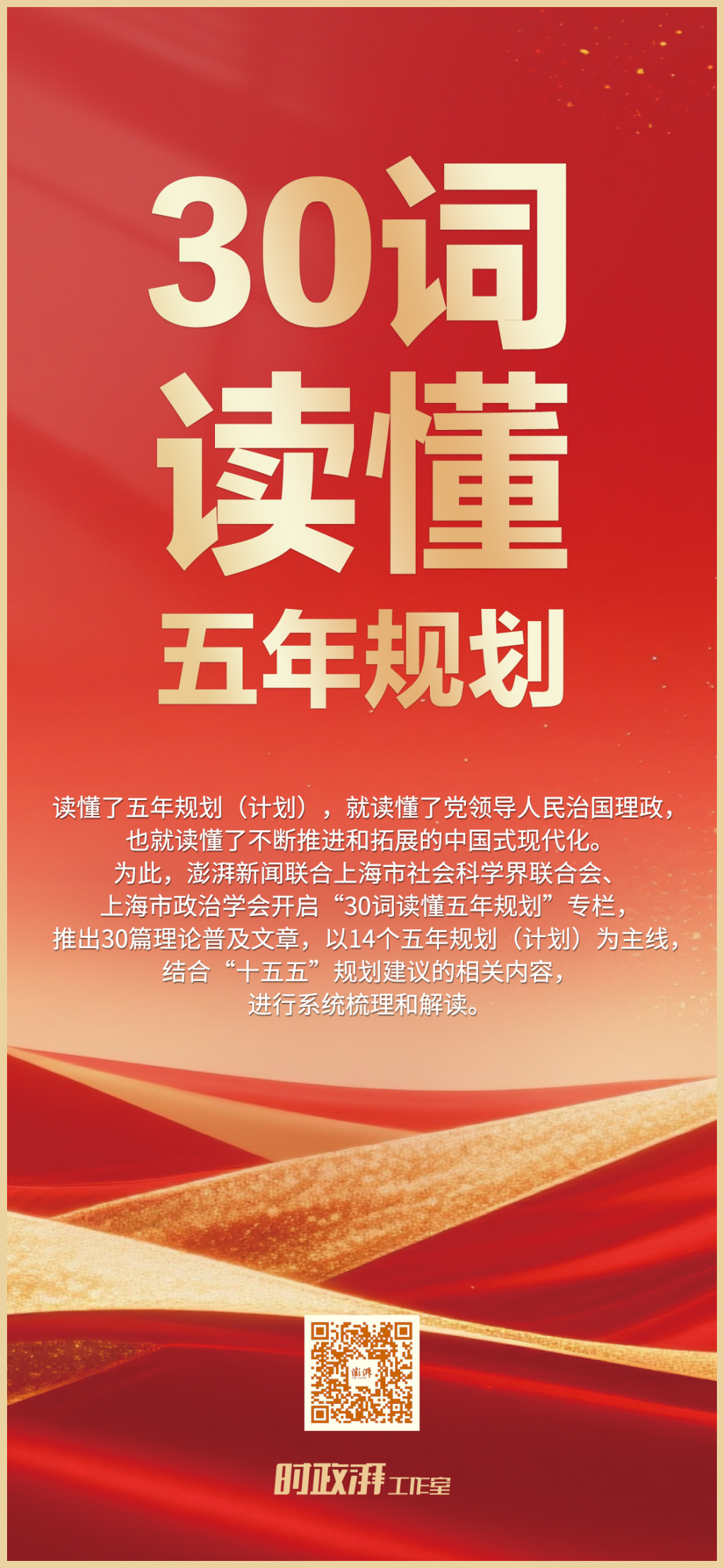辽京:在《白露春分》中捕捉分岔的时间
11月1日,青年作家辽京凭借长篇小说《白露春分》摘得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辽京的作品以家族史为脉络,通过女性视角的细腻刻画,将线性时间打碎重组,在记忆的褶皱中挖掘人性的复杂与真实。作家辽京在获得文学奖后,接受了专访,她表示:“我是一个女人,习惯使用我最熟悉的视角,用自己的经验去面对小说里的全新世界,每个角色身上都有作者的一小片影子。”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位不愿意披露真实名姓的80后女作家介绍说,在准备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书《新婚之夜》(小说合集)的时候,都还没有合适的笔名,只有一个很淘气的网名,“编辑建议我取一个笔名,我就拣了两个常见简单的字‘辽、京’,当时怎么想到这两个字的情形,我已经不太确定了。”

北京80后女作家辽京摘得第八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
衰老与记忆:秀梅的“声音”如何穿透时间
《白露春分》的创作源于辽京对祖母的回忆。她在自述中写道:“我奶奶是一个有声音的形象,她很健谈,爱说,爱唱,也爱笑。后来她不爱笑了,因为同她聊天的人变少了……从热闹,到静默,是一个人衰老的过程。”小说中的核心人物秀梅,正是这种衰老过程的文学投射。辽京将家族闲谈中的时间感融入叙事:“闲谈中时间是充满弹性的,就像小说。说完人的一生,也不过刚刚到了该准备晚饭的时候。”

《白露春分》 辽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这种非线性时间观与本届文学奖主题形成呼应。辽京在接受采访时解释说:“在这本小说里,我尝试重新整理记忆和时间,小说中发生了许多次时间的跳跃,故事不断回到过去或者跳到将来,一切人事都不是在线性的时间上依次发生,而是细碎地分布在小说的各个地方,像人的真实记忆一样随机。当我们回想自己家的往事的时候,也常会如此,因为遥远,时间的先后顺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一些对人和事的印象,组合起来,留在心里。”
她认为,中国大家庭的消解是时代共性,而写作正是通过重组记忆,让私人经验与集体共鸣交织:“每个人都有一个家,中国人的大家庭在近些年渐渐消失了,它是如何消失的,如何现实中后退到记忆中,这是我想用这本书讲述的主题,也是许多人都有共鸣的故事,因为大家都是从那里走出来的。”
熟悉就是穿透力:女性角色在写作中逐渐摆脱作者控制
辽京在创作中敢于直面家庭“最难堪的根底”。她笔下的陈立远是一个中年失意的长子,失业后欺骗母亲秀梅的装修费,却始终被内心的羞耻感折磨。“这样的人其实很痛苦……他心底里存着一把戒尺,一直在悄悄抽打自己。”辽京指出,传统家庭中“孝道”的虚伪与真实情感的缺失,导致成员活在“面子”的枷锁下:“至亲的人,也不讲真话。”
这种对家庭关系的冷峻观察,与评委、作家孙甘露对时代共性的洞察不谋而合。孙甘露在评奖讨论时提到:“此次入围的作者经历、受教育背景乃至工作都非常相近……这也许是时代的文化氛围对创作者带来的影响。”他引用贡布里希的比喻:“旗帜在飘扬,其实是风在吹。那么,这个支配写作者的时代力量是什么?非常值得玩味。”
辽京则通过女性视角的“穿透力”回应这一问题,她告诉记者:“我是一个女人,习惯使用我最熟悉的视角,熟悉就是穿透力,不一定是完全的自我代入,而是用自己的经验去面对小说里的全新世界,每个角色身上都有作者的一小片影子。”
她认为,女性角色在写作中逐渐摆脱作者控制的过程,正是叙事生命力的体现:“佳月、佳圆和秀梅的视角,是女性的视角,我的视角,也是女性的视角。作为作者,我似乎拥有着控制她们的特权,但是写到后来,我发现她们的声音越来越大,摆脱了我的控制,要想得到救赎,就非如此不可。”
现实主义并非枯竭的路径,而是无限的探索
施战军以时间比喻五部决选作品:《野蜂飞舞》是“时间的声音”,《天鹅旅馆》是“时间的结构”,《不上锁的人》是“时间的工具”,而《白露春分》则是“时间的秘密”。他认为,文学的价值在于捕捉线性历史之外的“分岔点”:“在直线当中寻找分岔的冲动,展现了一种在冗长历史情境之下的野心的存留。”
辽京对此深有共鸣。她表示:“写作这件事,既消耗时间,也在对抗时间。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那些记忆才会活过来,纷纷涌到我的眼前,写作即是回忆本身,不写是不会去想的,而一开始写作,新的世界就形成了,像题目里讲的,时间就此分岔。”
在疫情期间完成的《白露春分》,通过回溯家族记忆,构建了一个与现实并行的时空。辽京强调,现实主义并非枯竭的路径,而是无限的探索:“家庭的内幕,是一个幽深的所在,常被遮蔽和忽略,我想要揭开这个盖子,晒出那些人人心里有,却没人讲过的故事。而现实主义是永远讲不完的,故事越真,反而材料越多,可能性也就越多。我不觉得人的经验会被写作写到枯竭,因为小说允许作者进行各式各样的尝试,旧故事,新视角;或者新故事,旧手法,永远可以找到那一点点新。”
死亡与救赎:文学中的必然与偶然
对于小说中衰老与死亡的主题,辽京认为:“对每个人来说,死亡是最古老的问题,也是最新的答案,它对每个人是一视同仁的,它就是它,无所谓开端和结束,既是必然,也是偶然。小说里写了衰老和死亡必然性的那一部分,也只是呈现,追问留给读者。”
她通过秀梅的死亡和家庭的离散,呈现了一种超越伦理枷锁的救赎可能:“写到最后所有人的选择都只剩下唯一的一个,成长的离开了,衰老的死亡了,剩下一个空屋子,和一些曾经熟悉却变得陌生的邻人。”
施战军在评委对谈中进一步阐释了文学与时间的关系:“我们已经习惯于线性的思维……提出‘时间的分岔’很有意思,它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了文学和艺术的本体。”他以茨威格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为例,说明个体在特定时刻的行动如何改变历史轨迹,而作家的任务正是捕捉这种“分岔的冲动”。
青年写作的挑战:活生生的人没有“典型”一说
本届评委对青年作家的创作生态多有探讨。施战军指出,当下写作资源驳杂,但部分作品缺乏“野趣”与“本质性的东西”:“不要盲目排斥‘宏大’与‘深刻’,要重新唤起对于野趣的兴趣。”孙甘露则提醒,青年作家需警惕同质化:“此次入围的作品差异性不强、特异性不明显……这也许是时代的文化氛围对创作者带来的影响。”
辽京的写作实践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她拒绝将人物典型化:“只有‘人物’才有‘典型’一说,活生生的人是没有的,人总是有来处,有归途。我希望他们不止活在纸上。”在《白露春分》中,她以“不断做减法”的方式,从庞杂的家族素材中提炼出个体的挣扎与尊严。
颁奖典礼上,辽京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表示:“这本小说其实不是我第一次写长篇小说,但是对我来说,我愿意把它看作是自己第一部真正的长篇小说,来自我自己的生活,跟我自己的童年、家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本书能出版对我来说就已经是非常快乐的事情。今天能够得这个奖非常开心、非常荣幸。”
图:主办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