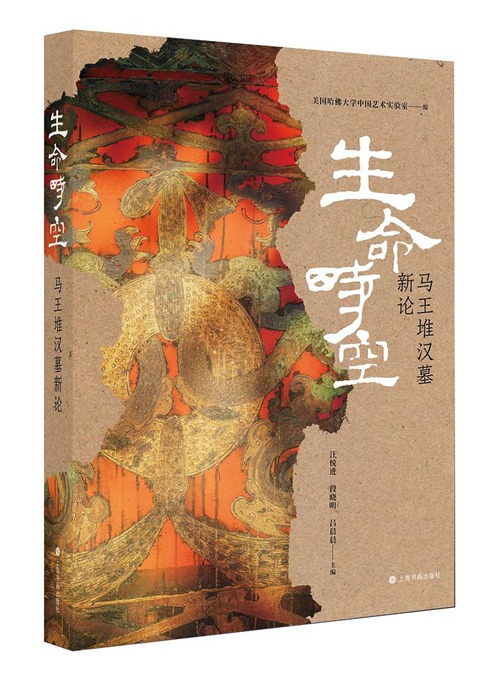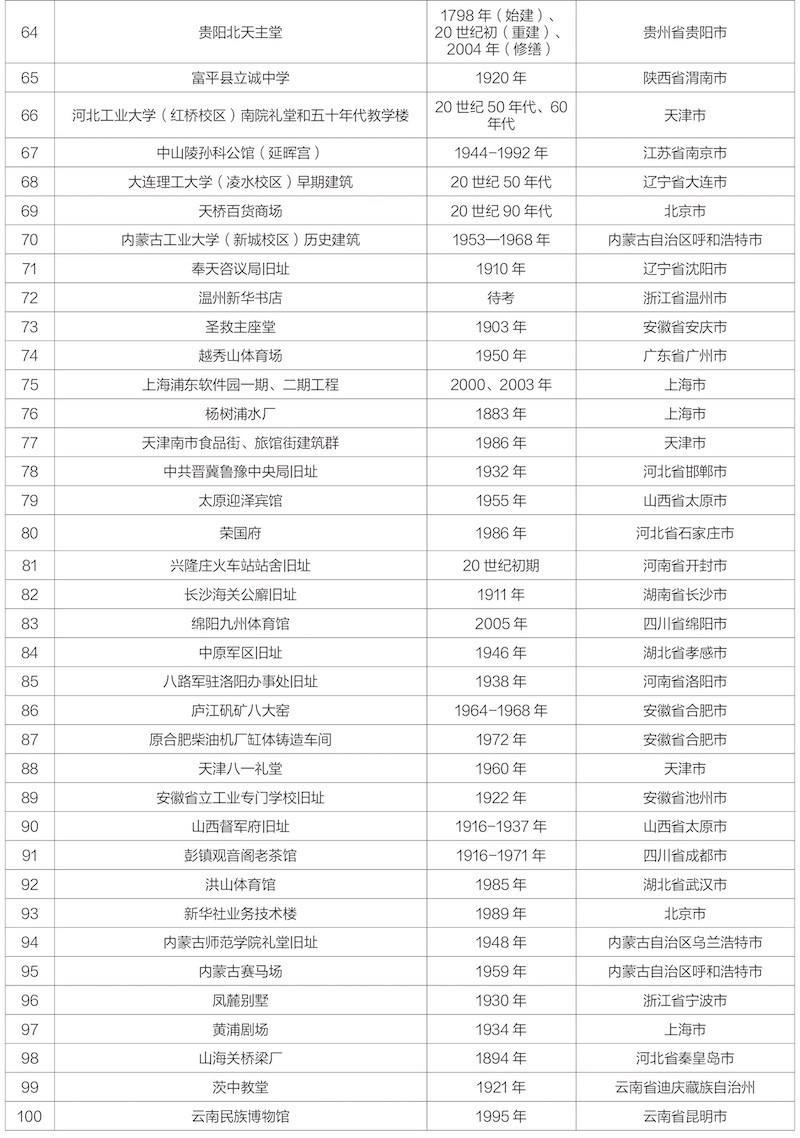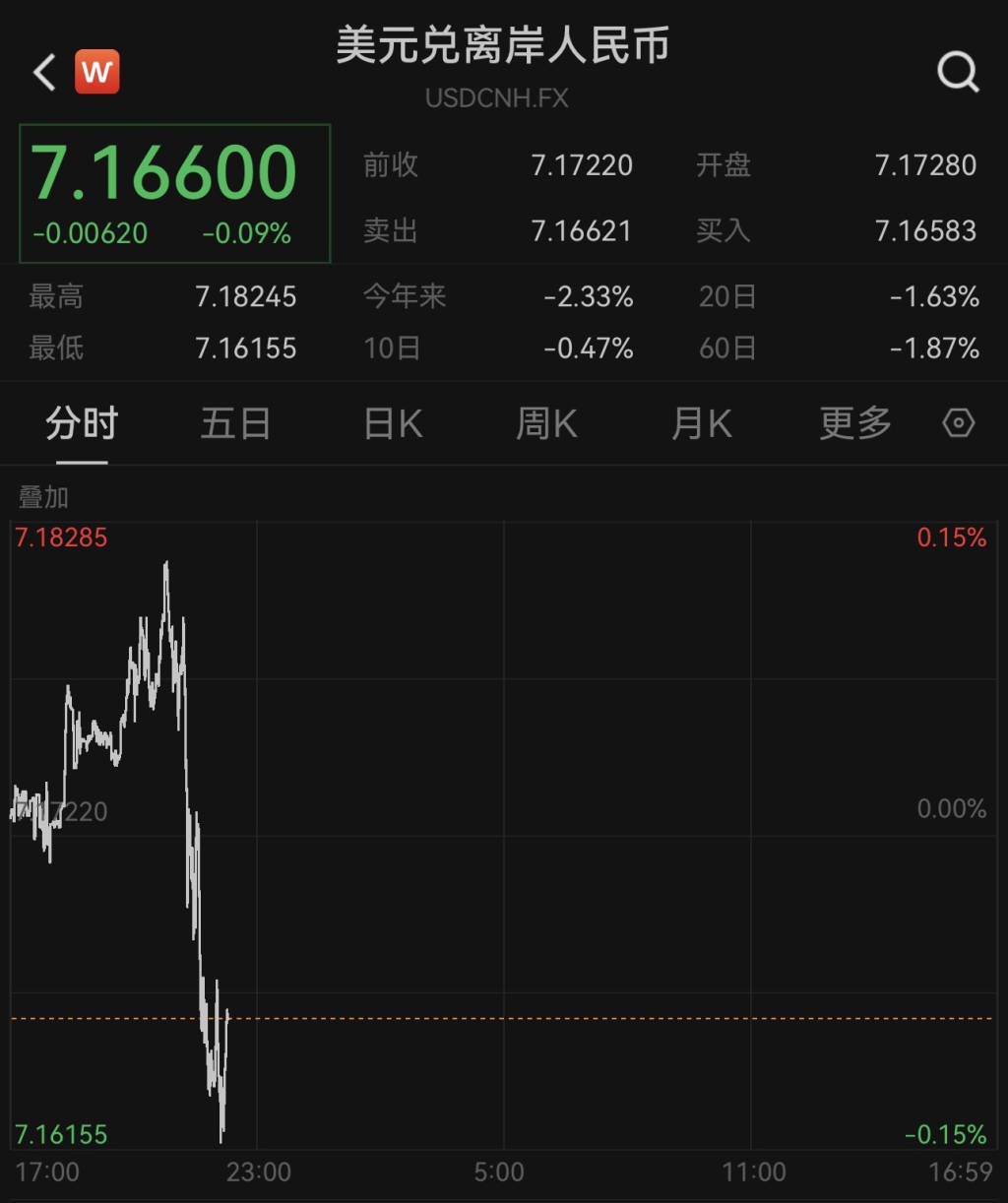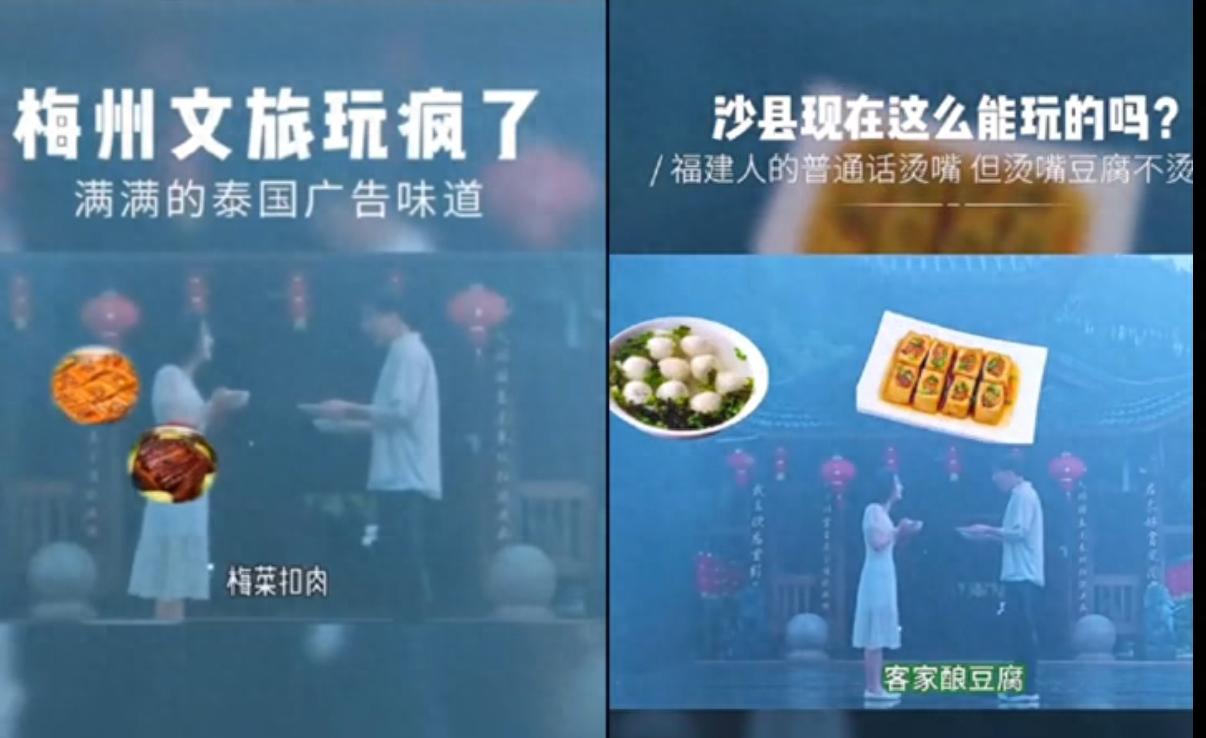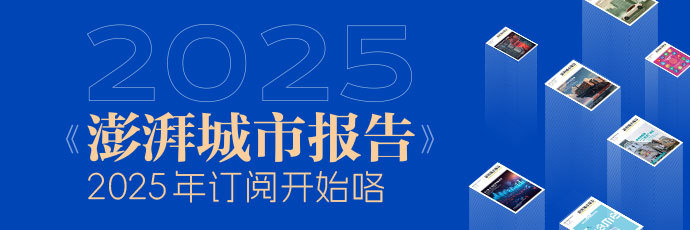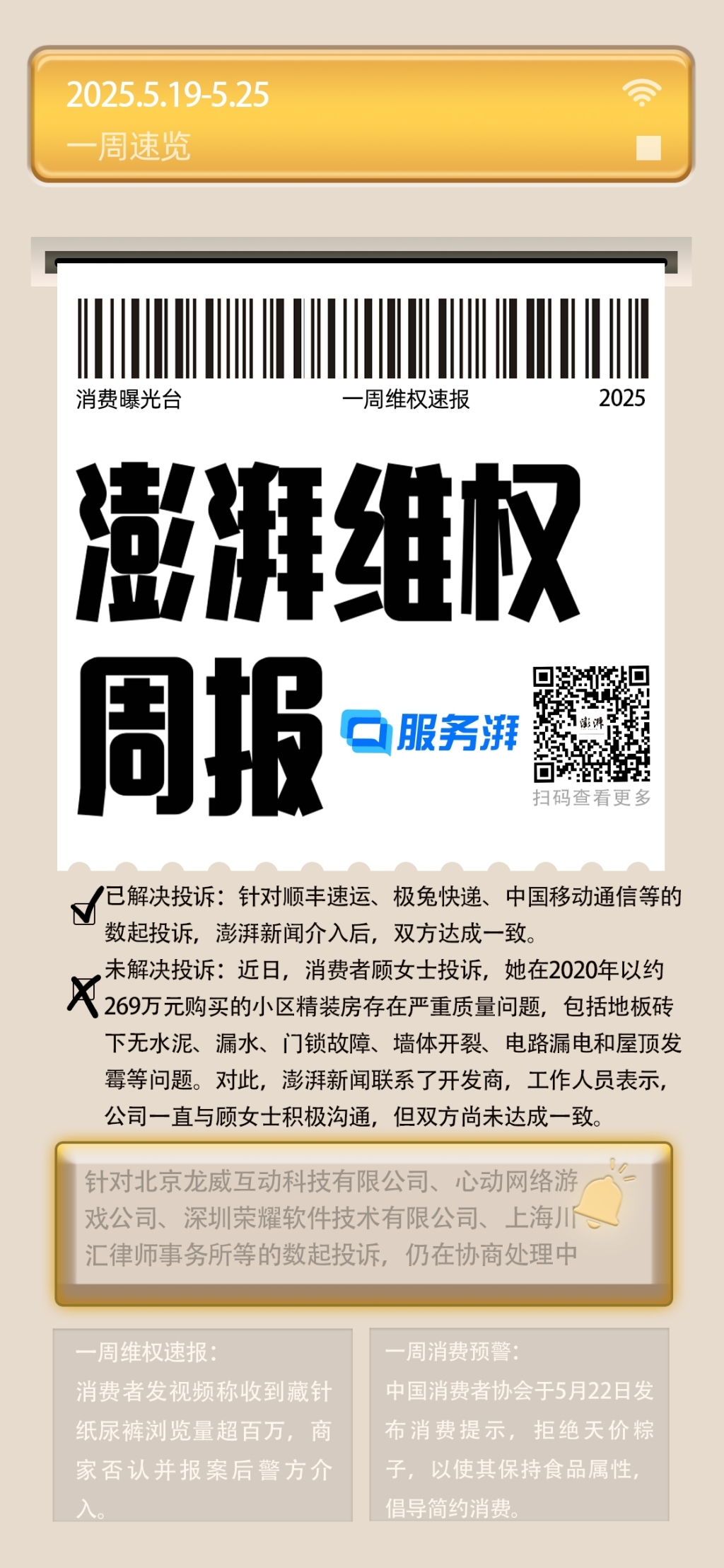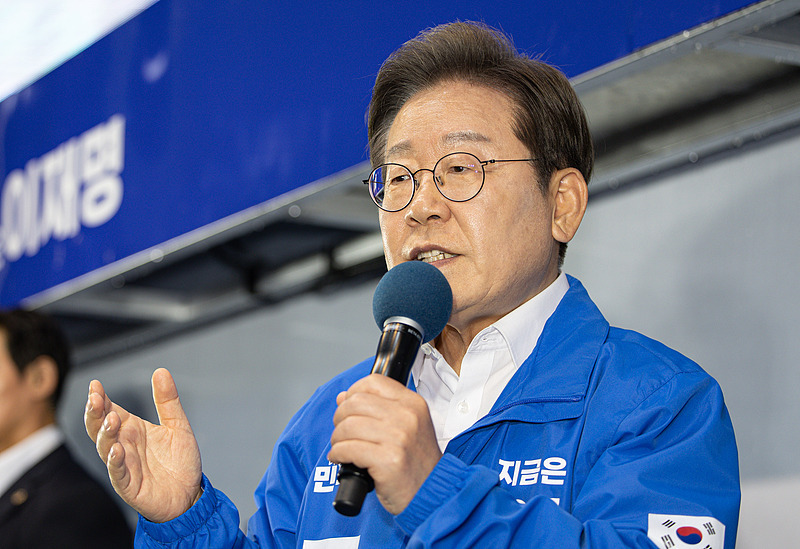关于《哲学家的小王子》的“席明纳”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刘梁剑教授近日出版的《哲学家的小王子》(中西书局,2025年),尝试对《小王子》这部家喻户晓的“童书”进行哲学解读。该书由萧阳、朱承、程亮、樊沁永四位学者作序,无形中开展了一次精彩的书前“席明纳”(seminar)。“席明纳”者何?席,一席。明,讲明道理,澄明心智,启明精神。纳,集思广益,容纳不同的声音。四位学者的背景不尽相同:萧阳,美国肯庸学院哲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朱承,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程亮,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樊沁永,扬州大学徐梵澄研究中心主任。最后是华东师范大学-法国里昂高师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相凤的读后感。

《哲学家的小王子》,刘梁剑著,中西书局,2025年5月版
萧阳:小王子蒙太奇
梁剑的这本书《哲学家的小王子》在结构上有一个新颖的设计:在正文前面读者首先看到的是他的几个朋友写的几篇小文章,叫做“书前席明纳”。我也有幸忝列其中。如果把这些小作文看作是几道饭前下胃小菜,我很荣幸梁剑邀请我来做一道,让读者在吃他做的正餐之前尝一尝,用它来吊一吊读者的胃口。我是一个吃货,通常会立即联想到的比喻往往与吃有关。我曾经为此感到羞愧。但是,后来,有一天却感到释然了,那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这其实是中国哲学的一个古老传统,最早的那个著名的关于舍生取义的比喻就是将生命与正义分别比喻为两道最为宝贵的美食:“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不过,我想,在这里可能还是应当尝试为这本奇特的书找到一个更为恰当的比喻。有一个我喜欢的英国哲学家达米特曾经说过,一本没有导言的书就像一个在大门与客厅之间没有走廊的房子:客人一进门,就是客厅。达米特是一个讲究礼节的老派的英国人(尽管他在涉及移民与反对种族歧视等公共政策方面属于进步的新左翼),在他看来,这是一个相当粗鲁的设计。作为这本书的“建筑师”的梁剑所设计的这个“房子”,没有这个毛病。他在大门与客厅之间建了一个“走廊”:读者一定要先读相当于导言的第一章“遇见”与书末的“跋语”以及书的“目录”。从那里读者可以惊鸿一瞥,看见客厅的一角,看见房子内部大致的格局(比如,有几个房间,有些什么家具,书房的书架上有些什么书 ——尤其他们会注意到《庄子》这本书),甚至还可以穿过房间透过窗户看见房子的另一边远方的景色。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建筑,达米特应当会相当满意。
甚至感到惊喜。达米特大概不知道一本书的导言前面还可以有“书前席明纳”——这里的“席明纳”是“seminar”(研讨班)这个英文词的一个巧妙的音译。我在美国去过一种派对,叫做“house warming party”(庆祝乔迁之喜的派对)。或许也可以将这本书的“席明纳”写成“喜鸣啦”——想象这是建筑大师的一些朋友,他们从庆祝新房建成的乔迁之“喜”的派对,从客厅经过走廊,走出了大门,端着酒,他们漫步走到了房子前面花园的草坪上,大声地称赞(“鸣”)这个房子有多好。他们是这个建筑师的“啦啦队”。作为这个啦啦队的一员,假如我有更多的时间,我大概会给那些碰巧路过的读者讲一讲,这个房子所坐落的这个社区在这座叫做“哲学”的城市里位于何处,有什么特点,它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建筑,为什么应当建,它有什么奇特之处, 为什么值得登门拜访,里面大致有些什么值得仔细玩赏的宝藏。
这本书的出版的确是一件可庆可贺的喜事。它是属于中国“儿童哲学”(或“儿童与哲学”)这个运动的一件大事。这个运动是中国哲学界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最有意义,最有创新的一个草根运动。它的起点或许可以从三联书店1989年出版的美国哲学家马修斯(Gareth Mathews)的《哲学与幼童》算起。这是马修斯1980年出版的英文专著Philosophy and the Young Child的中译(译者陈国容在“译后记”中提到这是钱锺书先生给三联书店推荐的)。近几十年来,不仅有不少人写关于儿童哲学的博士论文,而且在很多译著之外,也有不少中国哲学家写的关于儿童哲学的专著(四川大学的刘莘,杭州师范大学的高振宇,台湾辅仁大学的潘小慧——仅仅提几个我所知道的学者)。在这里,一个最有意义的最激动人心的新动向是有人开始了建设“中国儿童哲学”的尝试(比如暨南大学的陈永宝刚刚出版了一本专论朱熹与儿童哲学的专著)。梁剑的这本书对于《小王子》所给出的一个庄子式的解读是他在“中国儿童哲学”这个城市的一个新的开发区建的一座新房子。我想象在不久的将来应当会有人写专论庄子与儿童哲学的博士论文或专著。或许这是当下已经在发生的事(华东师大的尹紫涵同学刚刚告诉我,厦门大学的黄睿2022年在台湾出版了一本庄子教育哲学研究的书,其中也论及庄子与儿童哲学)。
中国的儿童哲学不是一个局限于大学哲学系的纯粹的学术事件,而是一个与社会互动的草根运动。许多年轻的哲学工作者已经开始在幼儿园,小学与中学开展形形色色的儿童哲学活动。就其运动的规模宏大这一点而言,中国的儿童哲学,尽管起步晚,应当非常接近世界前沿。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与中国智慧研究院哲学教育研修中心是这个运动中的一支生力军。梁剑的这本书是一套丛书《开端:面向青少年的哲学》(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中国智慧研究院组编,杨国荣主编)的第一本特辑。在这之前已经有两本论文集在这套丛书中出版。由于《小王子》是一本在中国儿童哲学运动中广泛使用的教材,对于那些在中国儿童哲学运动的前线作战的践行者而言,我相信梁剑的书将会成为一本人人手边必备的实用手册。
中国哲学界近年来的另外一个激动人心的新动向是大学校园里的“哲学戏剧”运动。首都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内蒙古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分别由程广云、夏莹与肖薇、吴童立、库慧君、王惠灵、武娟与何雨洋等引领)是先行者。我觉得,可以把哲学戏剧看着是一个更为广大的“文学与哲学”运动的一部分。可以期待,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有人把《小王子》变幻为一个舞台剧。在这个意义上,梁剑的书也是中国的方兴未艾的文学与哲学运动中的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件:他以《小王子》这本儿童文学名著为例,具体地演示给我们,如何像一个哲学家一样来读一个文学作品,文学如何是伦理学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我们如果不再做“伦理学理论”了,“作为伦理学的文学”或许会成为一种更好的做伦理学思考的风格?
如果有更多的时间,对于梁剑的这个奇妙的“房子”,我还有太多的话想说。比如,它有很多朝阳的窗户,采光好,这使得你能够看清楚很多你以前看不太清楚的风景, 甚至看明白你原来身处一个洞穴这件事。在美国农村,人们喜欢在一个房子外加建一个他们称之为“阳光房”(sunroom)的小屋子。想象住在没有阳光的建筑里的人是玫瑰花,阳光房就是他们的花房。这也是夏天做阳光浴和晚上乘凉的好地方。梁剑的这个房子有两个令人惊艳的阳光房:第6章“《小王子》新编”,附录“《齐物论》新编及释”。这两个部分是一个充满了光的地方,如果要给梁剑的这个房子命名,我会称之为“以明楼”或“莫若室”。
这本书的书名可以有好多个含义,取决于书名中的“哲学家”一词如何理解。“哲学家”至少有三个可能的含义(由此形成“三种书”)。首先,它可以指的是《小王子》一书的作者,圣埃克苏佩里,这样理解的时候,这是一本阐发这个法国作家的哲学思想的书:正如梁剑所说,“作为童话的《小王子》……其文简,而其义丰,具有丰厚的哲学意蕴,很耐读。圣埃克苏佩里是飞行员,是作家,也是哲人”。其次,“哲学家”也可以是单数,指的是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梁剑,此时,这本书是梁剑作为哲学家对《小王子》这本家喻户晓的儿童文学经典所作的哲学诠释。当然,还可以有第三种解读:“哲学家”是复数,指的是许多的哲学家,尤其是那些梁剑“驯养”多年的老朋友:从老子、庄子、王船山到熊十力、金岳霖、冯契、杨国荣、崔宜明、贡华南,从歌德、尼采、罗姆巴赫,到阿罗频多、徐梵澄。梁剑的天才式的想法是这样的:把《小王子》与这些哲学家的书放在一起来读,让它们开始对话,由此会“兴”发出什么样的思想呢?
梁剑的读书法可以追溯到中国古老的“《诗经》并置读书法”或者“《诗经》蒙太奇读书法”(蒙太奇是来自电影的一个术语,它指的就是把两个画面先后并置)。孔子应当是第一个注意到《诗经》的如下这个特点的人:《诗经》中常见的一个叙述条理是先说A,然后紧接着说B,两者先后并置。比如说,《诗经》的第一首诗的第一段是由A与B所组成的,其中A是关于自然界的一个画面的描写(“关关雎鸠,在河之洲”),B是关于人世间的一个画面的描写(“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两个画面先后“放映”出来,兴发出(intimate)许多的思想。我们只要看一眼《论语》中孔子教弟子如何读《诗经》的那些具体例子,就可以知道,孔子想要他的弟子用这种“兴”的方法来读诗(“诗可以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本《哲学家的小王子》所兴发的 “哲学”和周保松的《小王子的领悟》(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所兴发的“哲学领悟”会非常不同,这是因为他们把《小王子》和一些非常不一样的书并置在一起读的缘故。很容易想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关于《小王子》的书,通过又一种不同的并置,还可能兴发出又一种不同的解读。 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并置蒙太奇,以及由此引发的“兴”(intimation)。
在我看来,梁剑的书是上面提到的“三种书”融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一本书。很难说清这三种书中的哪一种在哪里结束,哪一种又在哪里开始。不过,在大多数时候,我们读到的是第三种书:梁剑把他的阳光房变成了一个跨越古今中外的文艺沙龙,作为这个沙龙的主人,他邀请上面提到的这些哲学大师和化身为小王子的圣埃克苏佩里在一起喝酒聊天。
亲爱的读者,我现在就邀请你和我一起进入大门,穿过长廊,来到客厅,加入梁剑和小王子与这些哲学家的对话。让属于你自己的“兴”开始吧。
朱承:突破哲学工作者的自限
梁剑乐言《小王子》,这是我20多年前就知道的事情,但我没想到他居然以此为题写出了一本书。当年,我是受梁剑的影响才知道并去阅读《小王子》的,不过青年时代陷入生计,当时只道是寻常。女儿小学三年级时,为了完成学校老师布置的家校协作任务,要到她的课堂上分享一本书,于是我又想起梁剑常说的这部老少咸宜的《小王子》,重新阅读并与一群懵懂的儿童叽叽喳喳地讨论了一番,当时说了什么,我早已忘却,但经此一遭,《小王子》于我又多了一份“最难风雨故人来”之感。这次,“小王子”又翩然而至,二十年来仿佛轮回,我还得再次面对《小王子》,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是《哲学家的小王子》。
诗人写诗,一切事物皆可入诗,天地风霜、草木山川、鸢飞鱼跃、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世事人情、往古来今,几乎没有什么不入诗人之眼;可是眼下学院里的哲学工作者写文章,似乎有其特定的对象,除了以哲学术语进行理论书写之外,最常见的工作就是对既定的哲学文本进行诠释和分析,这也是我们目前哲学训练和哲学书写的主要路径,哲学工作者们都自觉地恪守学术规程,用专业的术语、概念、命题反复揣摩着流传下来的思想文本。作为一个从业近30年的学院派哲学工作者,梁剑当然非常熟悉哲学规程的界限所在,好在他没有以此“自限”。“自限”是梁剑自己的话,大约十年前,他曾经提出“以儒家自居还是以儒家自限”的问题,虽然他这个话是针对“儒学复兴”的文化现象而说的,但我一直觉得“自居还是自限”的提问方式可以用在很多场域。比如,对于哲学工作者的学术工作来说,“以阐释哲学史上的文本自居还是自限?”显然,能够精深地阐释哲学史上流传下来的文本是哲学工作者的立业之本,在当前的学术生态下,没有这个能力大概是难以在高校或研究机构找到一份研究哲学的工作的。然而哲学工作者是否要以解读“纯化”的哲学史文本自限?答案显然是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无必要”是因为哲学思想本身的开放性,蕴含在一切可以解读的文本、事物之中,没有必要仅仅把目光局限在传统的哲学史意义上的文本中;“无可能”是因为随着人们阅读和理解对象的扩大化,既存的哲学文本已经不能够满足哲学工作者的兴趣和关切,必然要不断地扩展研究对象。由此而言,哲学工作者所深耕的“文本”不断“泛化”是势之所趋。
梁剑没有以解读哲学史文本的哲学工作者自限,而更像是一位不断进行开疆拓土的思想骑士,他这次开拓的一个新疆域是《小王子》。《小王子》显然不是“纯化”的哲学文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小王子》是一部童书,故事在小王子“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的飞行中展开,是儿童眼中奇幻的“星际旅行记”。但这部“星际旅行记”,同时也是一部哲学意义上的“童心”之作,描绘了“应然世界”对“实然世界”的童幻抵抗:世界本该如此,虽然还不如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剑将《小王子》引申为“哲学家的小王子”,对书中的“驯养”“责任”“友谊”等话题乃至伦理精神作了哲学阐发,进而将阐发《小王子》变成了哲学工作者的“正事”。梁剑没有以解读“纯化”的哲学史文本“自限”,我们才有了这部有趣的《哲学家的小王子》。
“对你驯养过的东西,你永远负有责任。”梁剑“驯养”《小王子》已经20多年了,他也有“责任”对这部书作一次哲学的阐发。虽然梁剑在书中每一章的标题下都引用了老庄话语,出尘脱俗,然而人间世上毕竟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责任,最近几年梁剑太忙,似乎对于熟和不熟的事务都负有责任,如果他能够稍微闲一点的话,《哲学家的小王子》会写得更加“神采奕奕”。
程亮:哲学家的用“心”
举凡名作,其意义都不限于一时一地,更不囿于一人一事,而是持续开放、不断生成的,也是常读常新的。对于《小王子》这样的经典,每个人自是可以有不同的视角,带着不同的生活经验,解读其所触及的主题,共情其所呈现的角色,体味其所蕴含的意义。梁剑兄这本《哲学家的小王子》,殊是用“心”,囊括中外古今,以哲学的方式进行深入的阐释和演绎,即便不是“独辟蹊径”,也是“别有洞天”。
一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小王子》无疑是一部具有哲学意蕴的文学作品,或可称得上是“文学化的哲学”或“哲学化的文学”。但是,这种哲学意蕴,不同于有待“发现”、需要“说明”的自然之物,而是有赖于作为主体的我们,特别是“哲学家”,去创发和解释的。书名“哲学家的小王子”,恰恰暗含着哲学探究的这种“个人化”面向”和“解释学”维度,意味着不同的“哲学家”往往(或总是)会以不同的方式进入《小王子》的意义世界。
但在“这里”,谁是“哲学家”呢?在“跋语”中,梁剑兄特别指出,他所说的“哲学家”是《小王子》的作者,而谦称自己只是“哲学工作者”。不过,若是把“哲学家”看作是从事哲学研究的“专门家”,圣埃克苏佩里未必比梁剑兄更是一个“哲学家”;如果“哲学家”是指那些真正以自己的思想,“邀请”和“引导”我们参与哲学对话的人,圣埃克苏佩里与梁剑兄自然都在其列。就后者而言,圣埃克苏佩里以文学的方式创作了“小王子”,传递了他有关宇宙人生问题的洞见,梁剑兄则以哲学的方式重构了“小王子”,阐释了《小王子》所涉及的“大问题”,绘制了《小王子》的“哲学地图”,为我们把握《小王子》的哲学深意提供了指引。
正是在“这里”,梁剑兄在与圣埃克苏佩里展开了一场哲学的对话。作为读者,我们也正在“观看”这场对话。此时此刻,我们是不是也已加入其中,带着我们的“小王子”,与两位“哲学家”的“小王子”对话呢?如果是,我们也可能是“哲学家”吗?就此而言,“哲学家的小王子”这个书名很是耐人寻味,尤其内含着解释学的张力和可能性。或许,我们还可以颠倒一下书名,变成“小王子的哲学家”。那么,谁又是小王子的“哲学家”呢?
二
对于《小王子》的阅读和写作,梁剑兄是“切己的”,是用“心”的。这种“切己”用“心”,首先与他作为一个专业的“哲学家”身份有关。梁剑兄尤长中国哲学,推重汉语言哲学,但又不是拘泥于中国哲学,而是围绕共通的哲学问题,推动中国哲学与外国(尤其是西方)哲学的对话,定位中国哲学的世界意义和独特贡献。他将自己的这种哲学之“心”(mind)引入《小王子》这个“西方”作品,离析出其中与哲学有关的重要主题(如“懂”“责任”“正事”“驯养”等),更是富有洞见地观察到这些主题与中国哲学(特别是庄子哲学)的呼应、关联和共鸣。文中各篇不仅以庄子为引子,从“小王子”中看见“庄子”,用“庄子”回应“小王子”,而且更是颇有创意地对《齐物论》和《小王子》进行了互鉴和新编。
不得不说,梁剑兄对于《小王子》的这种处理,多少体现了古今中外哲学之间的一种会通和融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从事一项工作,并不单单是因为它重要,而可能是因为它“有意思”,或者它“打动了”我们。初遇《小王子》的时候,梁剑兄已是“大人”,却“依然被《小王子》简约而深刻的美丽深深打动”。情之所至,当时就写下了以“月色皎洁,星光灿烂”为题的文字。他称之为是一种奇妙的“到时”体验,这种体验固然与《小王子》本身内含的情感叙事有关,但也离不开梁剑兄个人的生命体验和生活敏感。倘若没有这种“心”(heart)之所动,他就很难沉浸在《小王子》的故事和圣埃克苏佩里的传奇里,穿梭在各派哲学家的思想丛林中,更不能在不经意间融入自己生活中的奇妙“相遇”(如从童世骏的“哲学家”之辨、崔宜明“意义敞口”等)。
三
惟其用“心”,梁剑兄对《小王子》的书写,总能在文学叙事、哲学分析与现实观照之间形成自然的“链接”,让人倍感亲切,又深受启迪。其中,很多哲学意蕴的阐发,都是在不离“小孩-大人”的框架,因而就必然关联到“成长”(或“教育”)的话题。实际上,“成长”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
作为一个童话故事,《小王子》对孩子来说,自然有教化、教育或成长的意义,但圣埃克苏佩里说,它也是“写给大人们看的”。它有助于每个孩子的自我理解,更有助于促动每个大人重新看待孩子的世界,重新看待我们对待孩子的方式,乃至于重新理解我们自己生活本身。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大人们常常认为孩子什么都不懂,童年不过是成年的预备,其本身没什么独特或内在的价值。但在小王子看来,大人们才是什么也不懂,往往只看表面,自私自利,不懂温情,生活没有目的。这种看法意味着,我们对孩子应采取一种内在的、积极的立场,而不是一种外部的、比较的立场。杜威(Dewey,J.)就说,大人确实在某些理智或道德的方面应该向孩子学习,应该成为孩子。
不过,这种内在的立场并没有让“成长”问题变得简单。如果孩子本来就是好的,就像圣埃克苏佩里所认为的,“每个人的童年都是莫扎特,心中都有一颗种子”,那么,大人们所要做的,就是给予他们适当的培养,等待他们发芽、长大。但问题在于,这个世界不仅先于孩子而存在,而且是不完美甚至是糟糕的;身处其中的很多大人都成了小王子所说的“什么也不懂”的样子,也忘记了童年、失去了童心。那么,一个孩子究竟怎样才能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长大成人呢?这确实是个教育上的难题,圣埃克苏佩里也没有直接的答案。不过,在《小王子》中,他或多或少让我们见证了小王子的“成长”:从不懂得爱到懂得了爱,从决然离开到毅然归去。这个历程或许意味着,“成长”(或“教育”)就是一场“际遇”,是一种“驯养”,是一次出离的“旅行”,最终也是一种自我的澄明或领悟。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它都是一份特别的“礼物”。
四
与梁剑兄“相遇”有年,虽学科有别,但殊为“知契”。《哲学家的小王子》甫一竣事,梁剑兄就让先睹为快,并嘱咐在“书前席明纳”中写些体会的文字。认真读后,最直接的感受就是,与《小王子》是圣埃克苏佩里用“心”之作一样,这本书也可谓是梁剑兄作为“哲学家”的用“心”之作。正如《小王子》中所说,“用心去看才看得清楚。本质的东西用眼是看不见的。”在这种意义上,梁剑兄确实是“切己体察”,在用“心”去体悟小王子的哲学时刻,体味圣埃克苏佩里的人生境况,对话古今中外的伟大心灵。最后,对于梁剑兄的这份用“心”,也祈望我们每个读者都能用“心”感受到!
樊沁永:启明·驯养·责任
5月31日,梁剑兄微信发来了《哲学家的小王子》的书稿,这本书是我六一儿童节收到的唯一礼物。略回顾三年前,梁剑兄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组织的“现代中国哲学的谱系反思”活动刚好也是在儿童节,当时收到了张文江老师签赠的《太史公自序讲记》。这是我成年后印象最深的两次儿童节了,多了一些“好好学习”的鼓励,由之,可以砥砺“天天向上”的志气。
人的精神可以不断发育和成长,不受限于身体,总要超出自身一头地,有了这个念头,生活就回到了“正事”。当然,也会遇到更加朴实和优秀的同行者,哲学家就是如此遇到了《小王子》。
一
《小王子》是内返自身从而打开世界的童话。以成人和儿童对举,撑开了“蒙”的张力。书中讨论“大人需要回蒙”,大抵是社会的“启蒙”还有“蒙蔽”“理实”的状况。让人难安的是,生命的“理实”究竟是什么?读写给大人的童话,是要复归童心看世界,破除掉一些外在习得的知见,甚而还有被语言掌控的存在方式。可见,这世间最大的“道”一旦“分殊”破裂之后,“理”就变得不是那么实在。梵澄先生用“启明”替代“启蒙”,把性灵成长的变数消解在了“明”中,内在的理解,是“为道日损”的工夫,这个工夫不阻碍文化熏习和师生传授的“为学日益”,性灵连缀本然道体,贯注了自“一”而来的“明”,可以自作主宰。心火自明,“文”才有了显“质”的可能,求知欲引导下开出的光明和知见的增益是两回事。“为道日损”的工夫仍需乾健的努力方能得之,只是德性上用力向来不像体力劳动,但也不会因为无形就无从着力,念念善护本心发动,自然在日常行事中有不同的气象散发,并影响周遭之境。
《论语》首章言“学”不言“教”,是“明师”潜藏在所有需要成长的学生内中,成长的悦乐是不断地超出自身,“学”是人的天性。《周易·蒙卦》“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把师生关系外化为二,“童”为儿童,“求蒙”的儿童则是学生,求之于师,“蒙”卦比“学”多了一层“教”的意涵。“大人需要回蒙”则从精神性上看到了“学”与“人”内在本性,超越了生理性的理解,看到了童心和青春与天地大化的联动。“教”“学”是以同源而有方向之别,一旦“二”则有了两种可能性,师所传授是“发蒙”理实,还是以错误知见“蒙蔽”心灵,“蒙”有了变数。这个道理同样在柏拉图的“洞穴”喻中有深刻的表达,走出“洞穴”,何以知道外面不是更大的“洞穴”?不但破局的本体“明”仍然在学生内中,破局的动力“启”也在学生内中。
二
学术写作,灵动的统合难能可贵。这本书源于口述、对话,我更愿意看成是梁剑兄精神成长的阶段性自传,虽然是自传,却一直在消解“自我”,一部分重叠了圣埃克絮佩里和庄子的心思,更多的还以千手千眼的手法收摄了古今中外学术大家的妙语,为读者接引了思考“正事”的通道,其“用眼”“用心”开阔,是“懂”读者的,这个“懂”对话的是诚实的灵魂,一旦同意“正事”是培育理想人格,可以依循传统,也可以超越具体的文明和宗派,进而超越语言和逻辑,为精神挺立后的价值、秩序重新确立了方向,任重而道远。
大多数人饱尝内卷的困苦并非不“懂”其弊端,而是苦于不“懂”何为“正事”。“懂”古文右边又作“蕫”,正是童心蒙发处,要活生生的内在建立与周遭世界的联动。庄子惠子濠上之辩正是外求造成的无解,倘若反观内心,找到“懂”的通道,悬心率性,必能无言默会,迦叶拈花亦合此理。
倘若“懂”不是西方的认识论意涵,自然就会衔接到“驯养”的工夫。这对于中国人并不陌生,通俗言,就是在生活中用心打交道,也是儒家的“仁”,佛教“善巧方便”的佛德,印度教的“瑜伽”,“驯养”是在主体的意义上熟悉的联动了有差异性的他者,在这个意义上,千差万别的个体可以在“驯养”的工夫中连结成更大的主体,“亲亲、仁民、爱物”“民胞物与”与小王子驯养世界的方式是多么的相似!这不是在普遍意义上抽象出某种属性的哲学,而是与世界打交道的生存智慧!
三
书中引《小王子》:“对你驯养过的东西,你永远负有责任。”《道德经》云:“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可以作为最佳的注脚,这才是“责任”的正解。由此,书中展开了“战争与和平”的议题。大到国家与文明,小到家庭与教养,责任并不意味着占有,追寻普遍性不可避免的会以某种文明和观念为基底,粗暴的格式化他者。几乎失败的教育和糟糕的国际政治、文明冲突都源于此。梵澄先生曾在《玄理参同》序中说:“现代人士盛言世界大同,理想实为高远。然求世界大同,必先有学术之会通;学术之会通,在于义理之互证。在义理上既得契合,在思想上乃可和谐。不妨其为异,不碍其为同,万类攸归,‘多’通于‘一’。然后此等现实界的理想,如种种国际性的联合组织或统一组织,方可冀其渐次实现。那非可一蹴而至,但无论道路多么悠远,希望多么渺茫,舍从此基地前进,亦别无其他途径可循。”这本小书的用心与之同。“多”通于“一”,用《哲学家的小王子》的概念,靠的就是以“驯养”来通达。“驯养”(apprivoiser)这个词在翻译家有忠实原文和儿童理解多方面的考虑,以我粗浅的理解,汉语当前用法的好处是通俗,上通学理,下通民心,没有用哲学的帽子吓跑很多人。
梵澄先生说:“精神哲学属于内学,内学首重证悟。”(《玄理参同》序)人类文明璀璨绚烂,但需要特定的打开方式,要从“正事”去印证。需要“艮其背”的勇气和定力,读者选择书,书也选读者。《哲学家的小王子》是一本真诚面对自己就能够读懂的书,读者需要一定的钝感和慧力,不惧怕专业性的“黑话”。梁剑兄这本书呈现的恰恰是把不太好懂的“黑话”转化为“易则易知,简则易从”的行动之道。但这也不意味着这是一本现成就容易读的书,因为作者以中西印三大文明作为游戏的空间,以精神进化为主旨,图写了一幅生动的学术山水。不过,没有专业的训练也无妨,读书的兴趣不如从触动处进入、卧游,因为在“正事”里,心火向来自明,读书从来没有哪本应该作为开端。
书中妙处随处可见,诸如伦理学、数学、语言等等,发旧学,引新思,方便入门,又可证道,展能动情明理,掩可深思体悟,想必读者会有和我一样的共鸣!
由衷赞叹又多了一本养护心志、雅俗共赏的好书!
相凤:哲学家的小王子来啦!——我愿写信告诉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小王子》的结尾说:如果小王子回来了,一定要快点写信告诉他,不要让他太过悲伤......
读书解惑:相遇不易 相知更难
我好久没有读书了。打工人下班的日常是“不如躺着、刷刷手机、刷刷视频”。《哲学家的小王子》却是我迫不及待地想读的。缘由之一是解惑。我看过小王子,隐隐约约觉得这个小男孩说了很多道理,但他讲话没头没尾的。我不懂,我需要二手文献的帮助。果然,刘梁剑老师在39-42页这节里清楚地勾画了全书章节逻辑,用全书“第一个小高潮”即小王子的“思想危机”(第9章)、“全书的高潮”“义理最为密集”(第21章)等词语提炼和概括了小王子的思想历程,我觉得这样写我能懂。
刘梁剑老师在“听书系列”讲过小王子。那是在疫情期间,我们都窝在家里,“听书”是很有创意又有趣的想法,我记得胡晓明馆长的这个活动,是那个季度简报里关于学术交流板块的一项工作亮点。那时候我也在家陪读,床头边就有一本图画版的《小王子》,我和小朋友一起看,我俩都很没有耐心,他一会就走开了,我很快翻完了但还是有点懵。回蒙有点难:相遇不易,相知更难。
我真的读懂小王子可能还需要更多时间。为什么刘梁剑老师遇见这小男孩时就有了“到时”体验:月色皎洁,星光灿烂?慧根当然不同,还因为他自己也是像小王子一样的有趣灵魂。萧阳老师“大伦理”课上讲到的书叫“哲学家的狗”,是刘梁剑老师这本书的名字缘起。书前的席名纳像个朋友聚会,一本书竟然还有一个暖房派对(house warming party)! 这些有趣的事都是有趣的人才会做得出来。
刘梁剑老师是我的老师。我们大二的时候他刚留校任教,给我们上中国哲学的课程,讲过中国佛教,印象深的是读过《波若菠罗蜜多心经》,还请加大拿学者Barry Allen进课堂。现在回想,那时刘老师就给我们描绘中国哲学的世界面貌了呢!后来,刘梁剑老师也是我求学和工作中的重要引路人。他说话声音有点轻,大学时候的督导商老师为此经常来听课。但不妨碍他是一个内心即为纯净的人,就像小王子一样。我甚至觉得小王子说话应该也是这样轻轻地。
我很庆幸,我还在这里,离这些有趣的人和事这么近。我愿不做小王子拜访的第四颗星球上那个只知道数数、统计数据的忙人。
事上磨炼:如何过上神采奕奕的生活?
人与各种各样的事打交道,杨国荣老师说“人因事而在”(杨国荣:《人与世界:以事观之》,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哲学家“做哲学”之事,以哲学做事,在遣词造句、辨名析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过程之中成就一番经天纬地的事业(刘梁剑:《感受与中国哲学如何做事——对“事”哲学的方法论考察》,《哲学动态》2020年第3期)。我也在做事,坐在工位上忙着“正事”。但这些正事,有时就像是工厂流水线上的一环,似乎是不是我都没有关系,机器人可以取代我的工作。就像AI时代的数据标注工,他们一边训练机器,一边等待着将被机器取代的命运悖论一样。如此一来,事还因人而有吗?从人与万物的关联来看,事因“人”而有,但从微小的“我”来看,事似乎不因“我”而有。
我们生活在技术繁盛、物质丰裕、信息膨胀的时代,却也正在面临着个体孤独、精神空虚、茧房困境等各种新的问题。如何才能“过上神采奕奕的生活”?前段时间读赵修义老师《故旧往事 欲说还休》了解到他曾经历的时代困惑: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的背景下如何回答和解决“哲学贫困”的问题,他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辩护问题”做出了理论解答(赵修义:《故旧往事 欲说还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5年)。当下,AI数智技术迭代发展,哲学等人文学科再次面临被质疑的境地,这场景倒有些似曾相识了。时代固然有其大,个体更应体会“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的精神愉悦,在具体而微的事上磨练,“即凡而圣”(《哲学家的小王子》第114页),这也是杨国荣老师说的日常生活与终极关切的须臾不可离之理吧(参见杨国荣:《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八章)。
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刘梁剑老师在第四章“正事”里给出了提示:忙着干正事的大人是蘑菇。不得不说,这个反讽还挺可爱的。如何从正在忙碌着的纷繁事务中抬起头来,仰望星空辽阔、月色皎洁?书中引了很多Saint-Exupéry另一的作品《风沙星辰》的论述来呼应,如何从物质生活中提炼出过精神生活的方式,而这方面中国哲学有很多可以对照的智慧之思。虽然在这章节处刘梁剑老师都借引了《老子》《庄子》的金句来呼应主题,但他仍未限于道家,更是“听到了儒家民胞物与、悲天悯人的精神及大乘菩萨道慈悲精神在现代西方的奇妙回响”(《哲学家的小王子》第122页),世界哲学的图景又显现在眼面前了。但也仍然有惑,哲学其大其广,总觉得少了些人间烟火气息。
小王子与法国哲学
从时代背景来看,小王子诞生于二战期间,作者在题词中把这本书献给莱翁·维尔特,“这个大人生活在法国,正在挨饿受冻。他很需要得到安慰。”封底上的“以童心叩问存在本质”,也点出了小王子的哲学气质。除了书中以中国哲学资源做了理论对照外,这里简要回顾下法国哲学的印象,做个延伸思考。
狐狸告诉小王子,要用“心眼”观看:本质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On ne voit bien qu’avec le cœur . L’essentiel est invisible pour les yeux.(Antoine de Saint-Exupéry,Le Petit Prince, Gallimard,2007.p.92)
19世纪的法国,视觉已经从“最高尚的感觉”(笛卡尔语)跌落神坛,进入“视觉中心主义衰落年代”,马丁·杰伊在《低垂之眼:20世纪法国思想对视觉的贬损》中梳理了从柏格森、萨特、梅洛-庞蒂、福柯、拉康、巴特、德里达等法国20世纪的思想家,对视觉感官特权及其带来的思想影响的质疑。(马丁·杰伊,孔锐才译,《低垂之眼:20世纪法国思想对视觉的贬损》,重庆大学出版社,2021年)这与贡华南老师《味与味道》以“感思”对“心眼观看”的反思也有相似旨趣(贡华南,《味与味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这些或许可以看做小王子哲学意义的中外思想共鸣。放在这个历史脉络中,小王子的哲学气质呼之欲出。
封底的另外一句话是“以哲学解读文学经典”,这也是小王子的法国哲学气质其二,即文学和哲学的融合。朱承老师说,这本书突破了哲学工作者的自限,是文学与哲学的思想交汇。法国的哲学家正是具有这样的特质,正如柏格森、加缪、萨特都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换言之,我倾向于认为,小王子是哲学家。萧阳老师解读书题“哲学家的小王子”“三种书”没有讲这种,小王子自己就是哲学家。也许还不够充分的理由是,一是语言层面的“的”字不好解释;二是小王子的开悟靠的是狐狸,狐狸似乎更像智者形象。对第一点,可读成“作为哲学家的小王子”;对第二点也可以这样回应,哲学家也是有悟道过程的,荀子劝学,朱子格物致知,阳明龙场悟道,有先例。
朱承老师说,《小王子》是一部具有哲学意义的“童心”之作,描绘了“应然世界”对“实然世界”的童幻抵抗。朱老师是现实的。小王子虽抵抗,但仍是童幻式的。谁还不是个孩子呢!Toutes les grandes personnes ont d’abord été des enfants.(Mais peu d’entre elles s’en souviennent.)祝我们儿童节快乐!